|

|
|
秦可卿在《红楼梦》中的形象(2)
|
秦可卿托梦的两人,一个是贾府的接班人贾宝玉,一个是贾府的当家人王熙凤,都是《红楼梦》的轴心人物。“宁荣二公”在天之灵把贾府未来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了,并把挽救其家族颓危的办法托付给了警幻仙姑。她和其妹秦可卿充当媒介传给贾宝玉和王熙凤。然而,在“宁荣二公”看来聪明灵慧、略可望成的贾宝玉并没有从警幻仙姑的规引中入正,反而走向背离封建正统的道路。贾府精明的当家人王熙凤听了秦可卿一番“心愿”嘱托,梦醒后除了“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之外,并没有放在心上。她仍然不放过机会,挖空心思,聚敛钱财。什么祖宗大业、子孙退路,都弃之脑后,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悲剧,落了个“家亡人散各奔腾”。
秦可卿在《红楼梦》叙事结构中是一个隐喻式的人物,她穿插在梦幻仙境和现实人间,连接太虚幻境和大观园这两个世界,幻中显真,以幻拟真,以真托幻,把她点染得飘渺幽微,如烟如云。
秦可卿在《红楼梦》现实生活中只是一个过场人物,来去匆匆。直接描写她的笔墨不多,大多是借别人之口的间接描写。在第五回她刚露脸时,就放弃了对她直接的详细描写,而是选取了贾府最高权威——贾母的视角,对其作了侧面的勾勒:“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妇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及至她重病卧床时,通过她婆婆尤氏发一番感慨说:“这么个模样,这么个性情的人,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他这为人行事,那个亲戚、那个一家的长辈不喜欢他?”直到她去世,此类侧笔描写曾多次反复出现。而与这些复沓的侧面描写相联系的,只有两次正面简短的对话。在第七回中秦氏还是生气勃勃、招呼亲朋、照应周到的东府少奶奶,没有一点得病的征兆。当凤姐携宝玉来到宁府门口,“早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媳妇秦氏婆媳两个带着多少侍妾丫环等接出仪门”。接着就是一阵尤氏、凤姐、众媳妇婆子的嘲笑、嬉闹。秦氏则忙向宝玉推荐弟弟秦钟:“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宝二叔要见我兄弟,今儿他在这里书房里坐着呢,为什么不瞧瞧去?’”接下来就是凤姐见秦钟,赏东西。一时吃过了饭,尤氏、凤姐、秦氏等抹骨牌。尤氏、秦氏在玩牌时输了,还承诺下了隔一天再请凤姐的宴席,可见秦氏的精神很好。当秦氏再一次出场时,第十回,她已一病不起了。焦虑、忧伤、懊悔、恐惧、羞辱诸多情绪的纠缠,把一个在第七回里还是那样生气勃勃的人儿折磨得眼看越不了冬,过不了年,死期将临,“不过是挨日子”。一共两次短暂的亮相,我们无法在小说的现实生活里切近秦可卿这一艺术形象。只能从间接的描写、补叙和一些似隐似现的文字中去勾画她的基本形象特征。
从学术界研究的观点归纳,大致如下:
(一)秦可卿出自寒门
秦可卿是“赫赫扬扬,已近百载”的宁国公府长重孙媳,是国公夫人和公府家政无可争辩的合法继承人。身处如此显赫的豪门贵族,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社会,秦氏按理说该有个高贵的出身吧。然而,秦氏却单单出自“寒儒薄官”的家庭。她是个连自己亲生父母是谁,自己真实姓名都不知道的弃婴。她因养父“年至五旬时尚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来的,并取“小名叫做可儿,又起个官名叫做兼美。”按传统观念,一个“宦囊羞涩”郎中的养女,是不配与侯门公子结婚的。秦可卿没有薛宝钗那样的豪富家的势力,也不是孙绍祖那样的官场新贵,并不具备与宁府结成财产与权势联盟的联姻条件。然而,生活是复杂的,犹如东去的黄河,九曲十八湾,但毕竟 “奔流到海不复回”,对于把亲生女儿以五千两银子作为抵押的贾赦,孙绍祖手中的银子是光闪闪的;而对于荒淫无耻的贾珍父子,秦可卿的妩媚风流则是具有异常魅力的。这就是为什么宁国府两代家妇尤、秦二氏,都是出自寒门的原因。
(二)秦可卿性格特征
秦可卿的外貌特征:“生得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唤作“兼美”,“兼”具林黛玉、薛宝钗之“美”。性情温和,她自己对王熙凤说:“婶娘的侄儿(指她的丈夫贾蓉)虽说年轻,却也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正因为夫妻相亲相敬,所以贾蓉对秦氏的病“好不焦心”。贾珍和尤氏对这位儿媳非常满意。她说公婆把自己“当自己的女孩儿似的待”,她处人和,待下慈。“温柔和平”,得到贾府上上下下的喜爱。秦氏死讯传出,“那长一辈的想她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她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她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她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
只是太心细,正如婆婆尤氏所说的:“他可心细,心又重,不拘听见个什么话,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 从张太医之口可知用心太过伤神:“据我看这脉息: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的聪明不过的人;聪明忒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
(三)秦可卿生病
第十回从尤氏口中得知秦可卿已病得不轻:“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有来”,又“并不是喜”,“到了下半天就懒待动,话也懒说,眼神也发眩”,三四个大夫轮流着一天几次看脉。后来冯紫英推荐了个姓张的先生,贾珍请来看过,这位先生说是病已耽搁,“显出一个水亏木旺的症候来”,只有“三分治得”了。并且暗示难以挨过来年春天。到了九月中旬贾敬生日,秦可卿已是“十分支持不住”,卧床不起,自己已预感到“未必熬得过年去”。此后则“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样”。到了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前后,“也没见添病,也不见甚好”。这正应了那位张先生的话:“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又到了“腊尽春回”。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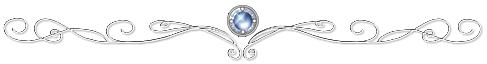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