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附录:俞平伯:穿行苍凉 文·南焱
|
在解放前就已享誉海内外的俞平伯,同样没有躲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然在1986年得到彻底平反,但32年的政治阴影笼罩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与俞平伯生活了42个春秋的外孙韦柰教授在回忆外公晚年凄凉的生活境况时,年过半百的他哽噎着,让伤痛的眼泪又回到了内心……
情缘
1917年,俞平伯18岁娶了舅父许引之的女儿许宝驯为妻,这对姑表亲相伴60多个春秋,他俩的感情已被文坛传为佳话。
据韦柰说,俞家和许家在浙江都是大户,到俞平伯这一代已是三代姻缘。也许是家世和自身太过亲近,他们的爱情真正演绎了世纪绝唱。自结婚后他们就不曾有过长时间的分离,抗战时期,北平沦陷,日本人曾多次希望俞平伯能与他们合作,都遭到拒绝,若不是他的老师周作人从中周旋,他可能要进班房。那时家里非常清苦,上有老下有小,若为日本人做事,收入会相当可观,日子一定好过些,但他没有。妻子许宝驯深深理解丈夫的爱国之情,她挑起了家里所有的活。
结婚三年后,俞平伯自费赴英国留学,谁知去了没多久就回国,有人说,他穿不惯洋衣服,吃不惯洋饭;还有人说是丢不下夫人。大多数人都坚信后者,因而此事曾一时传为美谈。
60年代末,俞平伯被下放河南,原本夫人是可以不去的。但当许宝驯得知这突来的消息后,二话没说,收拾起行囊就随夫君而去,没有丝毫犹豫。1974年,许宝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因此病发展态势较慢,大家都没重视,直到1976年3月,许宝驯才遵医嘱住院治疗。俞平伯因行动不便,不能常去医院探望,便书信往来,从3月中旬到4月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俞平伯竟写了22封信,他的信多是询问、关心,更多的是悄悄话:"本不拟作长书,日半夜里梦醒之间得诗二句,另纸写奉。我生平送你的诗不少,却说不出我二人的感情之实况,因之我总不惬意,诗稿或有或否也毫不在乎。这两句用你的口吻来描写我,把我写像了(我想是非常像,你道如何?)。就把双感情也表现出来了。近虽常和圣陶通信,却不敢写给他看,怕他笑。只可写给您看看,原笺请为保存。上面的款识,似青年时所写,然已八旬矣……"
1982年2月7日就在妻子去世的前一天,俞平伯展开日记,详细记录了许氏生病的全过程。妻子死时,他就睡在她的身边,深切地感受了在生死之间的痛苦与幸福。
妻子的死对俞平伯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韦柰回忆说:"自外祖母离开外公后,他变得寡言少语多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把自己关在卧房里,因为那里放着我外祖母的骨灰。我相信,在那里自有他的,一个旁人无法涉足的天地,那是他的世界,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爱的永恒的世界……"
在他病重期间,他无论如何不肯离开放着许氏骨灰的卧室,并且已亲笔拟好与许氏合葬的碑文:"德清俞平伯,杭州许宝驯合葬之墓。"这些是出于家人预料之外的,正当全家为碑文发愁时,韦柰无意中寻到俞先生这份爱情的"墓志铭",他们的故事,真可谓是爱情中的经典了。
人缘
俞平伯天性率直、善良,他不仅用笔关注生活的底层、珍爱友人的情谊,而且用生命亲历了广泛友爱中的每一个生动的细节。
据韦柰回忆,1966年"抄家"后不久,他在单位里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首批被揪了出来,他每天都必须到单位听报告。那时"大串连"轰轰烈烈,公交不堪重负,年近七旬的他每天要挤公共汽车无疑是件痛苦的事。一次,俞平伯无意中结识了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三轮车夫老钱头。当时老钱头带着红卫兵的袖套,在蹬三轮的行列中没人敢惹。他见到俞先生总感到这"臭老九"与众不同,于是每天早晨,就在俞家楼下的公路边等,晚上,他又准时在单位门口远远地守候。这两个钟点,有客时也被他推了,每次收俞先生的车费,他总要打折。春夏秋冬、寒暑往来,俞平伯都是坐着他的三轮车,直到离京赴"五七"干校,老钱头还专程到车站去送行。俞平伯从干校回京后,特地让韦柰去找老钱头,但没有找到,后来从别的车夫那里得知老钱头已经死了。为此,俞平伯还难过了好一阵子。
俞平伯对生活的洒脱和待人的诚意,对外孙韦柰影响至深。他回忆说,自河南回京后,他们家每年都会收到俞平伯干校房东顾家千里迢迢寄来的一刀咸肉,尽管收到的时候已不新鲜,但那份心意给俞家不知增添了多少欢乐。当俞平伯得知顾家要装电灯,却买不到电线时,马上要韦奈买了寄去。韦奈说:"评论家评论他的诗词、散文有股涩味,但他的为人却一点也不涩。"
1990年,90岁高龄的俞平伯因脑血栓再度中风,只能在床上度日,谈话和思维已断断续续让人不可捉摸。但一天下午,他突然把韦柰叫到床头,让他取出存放零用钱的壁柜,用含糊不清的碎语对韦柰说:"拿……拿200元出来。"韦柰迅速将钱拿出来,送到他眼前。他又接着断断续续说:"送……送给……写文章的人。""写文章的人太多,送给谁?"韦柰把外公所知道写文章的人说了一遍,当提到潘耀明这个名字时,他点了点头。这个人是俞平伯的香港朋友,他为俞先生1986年访问香港讲学做了大量的工作。
韦柰说:"我当时紧捏着手中的200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200元,这个数目太小了,然而,那份在半昏迷中仍流露出的友情,价值该有多重。接到潘耀明致谢的回信,外公已听不懂我对他讲了些什么,他也不能记住这件事了,但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红"缘
俞平伯的晚年境况是凄凉的,自夫人许宝驯病逝后,这种情景更为突出,他几乎到了足不出户的程度,客人来了也不愿接见,常独自闷在屋里,并且时常半夜三更大喊大叫,甚至有时喊出:"我要死……"当家人惊奇地赶到他的房里,却发现他好好的。80年代张贤亮到北京拜访俞平伯时,曾亲历过此景,并就此写过文章,认为俞平伯的这种表现是鸣心中之不平。
1954年在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俞平伯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但他仍然坚持对红学研究。1958年出版了他和王惜时校注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这之后还写了甲戍本《红楼梦序》,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他还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留存的有关《红楼梦》的全部资料、笔记毁于一旦,他才终止了一切研究工作。
1969年俞平伯被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后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得以返京,1975年应周总理的邀请参加了国庆招待会,这个会无疑让他多年坎坷的生活有了些亮色。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庆祝会,胡绳院长在大会致词中,为俞平伯在1954年因《红楼梦》的学术问题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彻底平反。然而32年的阴影,如何能一朝祛除。
韦柰说:"从1966年到1986年这20年中,外公从来不公开谈《红楼梦》,我的外祖母时刻在'严密监督',我们在家也很少提红楼梦。1986年11月,外公去香港演讲《红楼梦》研究,若是外祖母在世,恐怕不会成行。"
俞平伯后来曾悲愤地说:"老实讲,我还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红楼梦〉一百问》,还有过去所谈的也有许多不妥之处,应予纠正。但手头没有资料了,还搞什么。"《红楼梦》的研究让俞先生蒙受了半辈子的不白之冤,但《红楼梦》的情结一直埋在他内心的深处。
据韦柰回忆,1990年6月病重后,处在半昏迷状态中的俞先生每次见到他,总重复说一句话:"你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好后拿给我看。"那时,这话让韦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久,韦柰才知道外公的话与《红楼梦》的后40回有关,但他还是搞不清楚外公的真正意图。那时,俞平伯已病入膏肓,思维只能出,不能入。经过反复断断续续的对话,韦柰终于弄清了他的想法,他要重新评价后40回。并且用颤抖的手写下:"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他还亲口对韦柰的母亲俞成说:"我不能写了,由你们完成,不写完它,我不能死!"
韦柰激动地说:"外公在晚年,很少谈《红楼梦》,不想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地牵挂它。这是压抑了多年的一次总发泄、一次反弹。如果没有1954年那场不公正的批判,如果没有动乱的10年,如果为他平反的纪念会能早些举行,也许就不会是这样。我相信他定是带着对《红楼梦》的惦念和不甘心离开人世的。"
亲缘
在俞平伯的孙辈中,惟有韦柰与外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从2岁就相伴,直至外公生命的最后一刻。
韦柰10岁时,外公就让他熟背唐宋诗词,诵读四书五经。而他与外公真正的交流是在他下放到农村后。那时,他才20来岁,就在外公被贬到河南的那年夏天,他抽农闲放假,大包小包买上外公喜欢吃的罐头等食品,赶往河南。就在见到外公的一刹那,他简直无法相信两位老人住的地方是一间简陋的茅草房,有门无窗,后开一尺见方的小口于后墙,四壁透风,门是秸杆扎的。韦柰无法想像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当外公与他握手拥抱后,第一句话就是:"这里逢双日有集市,明天一早我们去看看,可以买些吃的回来。"短短几句话,让韦柰吃了"定心丸",他感到外公、外祖母在这里生活的相当坦然。这种豁达的品性,无疑给韦柰当时茫然的心绪点亮了一盏希望的明灯,他自河南回到京郊农场,开始发愤自学。
在家里外公是棵大树,但这棵大树只是信念和知识的大树,俞平伯丝毫没有让后辈有乘凉的感觉。韦柰说:"我们家里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努力,外公从未帮我们办过一件事,他这棵大树不好乘凉。"他说,他之所以有今天,全是自己的奋斗。
就在北京舞蹈学院招考教师那年,韦柰的专业课全部通过,但在政审时被学校卡住了,外公的好友叶圣陶先生得知后很气愤,就立即打电话给廖承志,廖承志办公室便打电话到学校说:"如果韦柰的专业课通过,你们不应该在政审上卡他。"尽管这件事受到叶老的帮助,但俞平伯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在孙辈中,韦柰是外公最宠的一个。在外公面前,他的话也最具权威,外公的脾气倔是出了名的,有病不看医生、不吃药,这时在大家都做不通工作的情况下,韦柰出面做,如果韦柰说服不了,那么家里再也没有人能做通了。1990年,俞平伯病重前,就提前将他的日记手稿和部分未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稿交给韦柰,嘱待他死后再去发表。直到外公离世,韦柰一直守在身边。
位于香山脚下的外公墓地与韦柰现在工作的学校相隔很近,他说,他每年都要到墓地看望两次,而每次去他的灵魂就得到一次净化。这也许就是他退休后为什么又选择民办艺校的注脚,这也许就是他始终一介布衣,淡泊明志的出处吧。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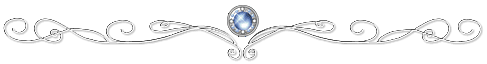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