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2)
|
由此我们还可以重新认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或者说究竟曹雪芹认为什么)才是林黛玉的主要缺点?通常都认为是她的小性。现在看来似乎不尽如此,那至多只是表象而非本质。小性是后天的弱点,而对贾宝玉的极度依赖却是先天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曹雪芹的“悼红”主旨中还包含着对女性自我意识、自强意识的欠缺,将心爱的男人看成自己的一切的批评,这应当也是“当自嗟”的成份之一。这种具有超时空意义的内涵,其思想深度和能够提供给读者的思考都大大超过续书的以调包计为核心的封建家族破坏婚姻自主的故事。因为时至21世纪今日的中国,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也还不是很多,女性对男性的过分依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再过100年也未必能彻底解决。弄清这一点,那么曹雪芹原设计结尾林黛玉泪尽而逝的思想性强弱就显而易见了。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其实,曹雪芹对林黛玉“当自嗟”的委婉批评并非仅此一处。早在第三回林黛玉初入荣国府时,曹雪芹对她就有一句评语:“心较比干多一窍。”比干不惜以死相谏,触怒纣王。纣王道:“吾闻圣人心有七窍。”结果“剖比干,观其心”(《史记· 殷本记》)。说林黛玉的心较比干的心窍还多,很明显不是将她喻指圣人,而是说她多心,是贬义。类似批评还有一些:四十九回宝黛二人有一段对话颇可玩味。当时“黛玉因又说起宝琴来,想起自己没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宝玉忙劝道:‘你又自寻烦恼了。你瞧瞧,今年比旧年越发瘦了,你还不保养。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寻烦恼,哭一会子,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黛玉拭泪道:‘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象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宝玉道:‘这是你哭惯了心里疑的,岂有眼泪会少的!’”宝玉这些话显然不是平常的安慰解脱之语,他深深了解黛玉的性格为人,两个“自寻烦恼”和“又、必、惯、疑”,道出了黛玉精神上的某种严重病态。正是这种性格上的根本弱点,导致她病情日益加重,有好几次她生气后呕吐和发病便是证明。六十七回黛玉见到宝钗送来的故乡之物又勾起心病,紫鹃劝道:“……再者这里老太太们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计请好大夫配药诊治,也为是姑娘的病好。这如今才好些,又这样哭哭啼啼,岂不是自己糟蹋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烦了么?况且姑娘这病,原是素日忧虑过度,伤了血气……”可见大家都认为黛玉固然从小体弱多病,但她的病之所以越来越重,乃性格所致。显然这也是曹雪芹认为她“当自嗟”之处。
总之,我们从林黛玉形象的塑造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曹雪芹艺术创作的“玉、石”两重性的原则与手法:只不过她不是由“石”变“玉”,身上既具有“石性”,又带有“玉性”;而是由草变神(人),在她身上的人性同样既有高尚的接近神性的一面,又保留着“草性”——“草”的生命力非常脆弱与过分依赖他人的弱点。
周思源看红楼是是非非宝丫头从林黛玉形象塑造及其研究的分歧中,我们可以悟出曹雪芹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些宝贵经验。其中包括: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画龙点睛式的提示;人物自身感觉与实际情况的出入等等。这些手法在塑造薛宝钗时运用得更加出神入化,从而使这个人物变得十分复杂和更为扑朔迷离,甚至连人物个性的基调都难以确定。和对林黛玉的思想评价过高正好相反,长期以来对薛宝钗的评价却似乎过低了一些。当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薛宝钗形象的评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对她全盘否定的意见难得听见了,但对她的某些“误会”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换句话说,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广泛使用玉石两重性创作方法来看,薛宝钗的某些“玉”成份依旧被认为是“石”,或者虽然确实是“石”,却是特别差的“石”。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多种,或者说是曹雪芹以多种非常规手法塑造了薛宝钗的艺术形象,这是我们在解读这个人物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有些读者认为薛姨妈在贾府故意赖着不走,在破坏宝玉和黛玉的婚姻上设置“陷阱”。但薛姨妈的打算不等于薛宝钗的想法,要把二者区别开来。
是是非非宝丫头曹雪芹笔下的薛姨妈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艺术形象。她属于那种笔墨不多,地位微妙,一时很难说清楚而且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这个形象之所以经得起品味与咀嚼,关键在于曹雪芹牢牢把握住了刻画人物的“度”。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觊觎宝二奶奶宝座”是薛姨妈的一大罪状。从薛姨妈久居贾府不走来看,想实现“金玉良缘”的想法很可能有。但是,曹雪芹写得分寸适度,而且让薛姨妈一开始就处于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境地。其实薛姨妈一家住在贾府最初恰恰是贾家的人提出来的。先是贾政派人来对王夫人说:“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轻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们东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间房,白空闲着,打扫了,请姨太太和姐儿哥儿住了甚好。”由于薛蟠是在金陵惹了人命官司来至都中的,贾政出于怕他再“生事”而劝他们同住于此,合情合理。当时贾母也派人来说:“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亲密些。”因此并非仅仅是薛姨妈“正要同居一处,方可拘紧些儿子;若另居在外,又恐他纵性惹祸”。作为人母,为儿女的婚事操心本系分内大事,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更成为寡母的首要心事。所以薛姨妈为女儿的婚事操心无可非议。作为借居于此的亲戚,她从不介入贾府的任何纷争,遇到问题要么息事宁人,要么索性回避,如后来迁出大观园。她看出黛玉深爱宝玉,五十七回她关于宝黛结合“四角俱全”的说法并非虚伪之论。五十八回贾母因给老太妃送灵,特别拜托薛姨妈照管黛玉,“薛姨妈素习也最怜爱他的,今既巧遇这事,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这些地方正是她为人忠厚之处。她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为女儿争夺这桩婚事,更没有做任何伤害黛玉的事,看来她更多地是寄希望于事情的自然发展。应当说这样并无不义、不妥之处。因为宝玉与黛玉并未结婚,甚至连起码的名分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些猜测(如兴儿)。因此从当代观念来看,固然没有任何过错;即使在当时,也无可厚非。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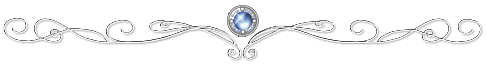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