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五详红楼梦--旧时真本(之二)
|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中游“旧时真本”的资料(第九二七至九四○页)。我把它整理归纳了一下,分列出来,代加着重点:
①平布青着“霞外(提手旁鹿下加困)屑”卷九:“石头记”原本内湘云嫁宝玉,故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回目;宝钗早寡,故有“恩爱夫妻不到冬”谜语。此本与程本先后出刻本,此本遂湮。平氏在北京琉璃厂的书店买到一部,被同年朱味莲携去。
②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引“续阅微草堂笔记”:戴诚夫曾见一旧时真本,“后数十回文字皆与今本绝异。”荣宁籍没后皆极萧条,宝钗亦早卒,宝玉无以作家至沦为击柝之流,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仍成夫妇。
臞蝯“红楼梦佚话”:同。
赵之谦“章安杂记”(咸丰十一年稿本)引“涤甫师”言:红楼梦〔按:显指八十回本“石头记”〕尚有四十回,至宝玉作看街兵,史湘云再醮与宝玉,方完卷。想为人删去。
③董康“书舶庸谭”卷四:“先慈尝语之云:幼时见是书原本,林薛夭亡,荣宁衰替宝玉糟糠之配实惟湘云,此回目中所以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也。”
王伯沆王希廉本红楼梦,引濮文[走之旁加显](字青士)言:“都中‘痴人说梦’云:宝玉系娶湘云,后贫苦。……──有似拾煤渣时光景。”(批“贫穷难耐凄凉”)“宝玉实娶湘云,晚年贫极,夫妇在都中拾煤球为活云。”(批第二十一回)“……曾在京师见‘痴人说梦’一书,颇多本书异事,如宝玉所娶系湘云,其后流落饥寒,至栖于街卒木棚中云云。”(批第四十九回)周汝昌按:甲戌本后有濮文[走之旁加显]跋语。苕溪渔隐着“痴人说梦”、二知道人着“红楼梦说梦”、梦痴学人着“梦痴说梦”中无所引之八十回后事。此或濮氏误称,或王氏误记,必系另一书。
④扈功“记传闻之红楼梦异本事”引画家关松房述陈[左弓上山下支]庵言:光绪初曾见南京刻版旧本,宝钗产后病死,湘云寡,在醮宝玉。宝玉曾沦为看街人,住堆子中──昔日街口例有小屋,为看街人居住守望之处,俗称堆子。──北靖(〔静〕误)王路过,未出侍候,为仆役捉出,将责打,王闻宝玉呼辩,认出声音,延入王府。作者自云当时也在府中,同住宾馆,遂得相识,闻述身世,乃作此书。周汝昌按:王梦阮着“红楼梦索隐提要”云:乾隆索阅,将为禁书,曹雪芹乃一再修改;内廷进本取吉祥,因此使鳏寡的宝玉湘云结合。此说如属实,亦必已写宝湘贫极为丐,方可撮合二人,适足证明此本非他人所补撰。纵非真原本,亦当是真本迷失之后有知七情节而循拟以为续补者。
⑤“红楼梦补”犀脊山樵序:曾见京中原本,仅八十回,叙至金玉联姻,黛玉谢世而止。金玉联姻,盖奉元妃之命,宝玉无可如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郁而亡。
⑥境遍佛声着“读红楼梦札记”(载一九一七年三月“说丛”第一期):相传旧本末卷作袭人嫁琪官后家道兴隆,既享温饱,不复忆故主。一日大雪,扶小婢出庭中赏雪,忽闻门外诵经化斋声甚熟悉,而一时不能记忆为谁,遂偕小婢自户审视,化斋者恰至门前,则门内为袭人,门外为宝玉,彼此相视,皆不能出一语,默对许时,二人因仆地而殁。
⑦“石头记集评”卷下,引傅钟麟言:闻有抄本,与坊本不同,宝玉走失后甄宝玉始进京,至贾府,人皆错认为宝玉。莺儿窃窥之,深替宝钗后悔,不若嫁与此人,亦是一样。甄宝玉梦宝玉已为僧,告以出家原因,并云神游太虚,闻黛玉乃神女,已归位。……〔按:甄宝玉进京至贾府,宝玉走失,以及神游太虚闻黛玉云云,皆程本情节,显系程本出版后据以改写的一个抄本。〕⑧万松山房丛书本“饮水诗词集”唯我跋:曾见“石头记”旧版,不止一百二十回,结局有湘云流为女佣,宝钗黛玉沦落教坊。某笔记云乾隆幸满人某家,适某外出,检书籍,得“石头记”,挟其一册而去。某归大惧,急就原本删改进呈。乃付武英殿刊印,书仅四百部,故世不多也。今本即当时武英殿删削本也。见原本始知钗黛沦落等事确犯忌。
⑨一九四二年冬,日籍哲学教授儿玉达童告北大文学系学生张琦翔云:日本有三六桥百十回红楼梦,内容有宝玉入狱,小红探监;小红与贾芸结[衣补旁加离];宝钗难产而卒,宝玉娶湘云;探春远嫁──“杏元和番”;妙玉为娼;凤姐被休弃。三六桥即蒙人三多,清末官至库伦办事大臣,未尝至日本。或云此本仍在上海。张琦翔“读红楼梦札记”(载一九四三年六月北大文学)中提及三六桥本,后三十回误作后四十回。
⑩褚德彝跋幽篁图(曹雪芹画像题记,传抄本):宣统年间在京见端方藏红楼梦抄本,宝玉湘云有染,及碧痕同浴处,多媟亵语。八十回后黛死娶钗同今本;但“婚后家计日落,流荡益甚,逾年宝钗以娩亡,宝玉更放纵,至贫不能自存。欲谋为拜堂阿(无品级之管事人,钱粮略高于步兵,提升可补笔帖式),以年长格于例”,甚至充任拨什库(佐领下掌管登记档册发饷之兵丁,须识满汉字,亦服杂役如糊饰宫殿、扫雪除草等。周汝昌疑与“拜堂阿”颠倒)。湘云新寡,“穷无所归”,遂为宝玉续弦。蒋玉菡脱乐籍后拥巨资,在外城设质库,宝玉屡往告贷,终欲令铺兵撵逐,袭人斥之方罢。一日大雪,市苦酒羊胛,与湘云纵饮赋诗赏雪,强为欢乐。九门提督路过,以失仪为从者所执,视之乃北靖王也。王念旧,赒赠有加,送入銮仪卫充云麾使,迄潦倒以终。
上列十项,①是根据“恩爱夫妻不到冬”谜语写宝钗早寡──当然是嫁了别人,不是宝玉,宝玉在此本内与湘云白头偕老。宝钗制竹夫人谜是甲辰本代补的,谜下批:“此宝钗金玉成空。”此本是看了批语全删的甲辰本续书的,再不然就是为了迁就“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回目,不管这句批语。这刻本与程本先后出版,即使在程本后,似乎不会是看了程本,改写后四十回。
⑦是根据程本改写的。⑧的记载中引乾隆携去一册的轶事,书主急删改进呈,删削本即程本。但是我们知道程本的来历并不是这样。当然这是附会的传说。不过既然说程本是此本删削而成,可见这部“旧版石头记”的内容大部份与程本相同,显然是添改程本的又一刻本。第三十二回湘云在家里已经操劳,替叔婶做针线,不难联想她帮佣,但是当时的仆人都是卖身为奴,当然是抄家的另一面,惊心动魄,钗黛入教坊,更杀谗过瘾,是清末林黛玉艳帜的先驱。周汝昌似也欣赏此本的构想,不过入教坊色情气氛太浓厚,不合“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要求,因此只推测八十回后史家抄没时──根据“自传说”,周汝昌认为史家影射曹雪芹的舅公李煦家,与曹家先后籍没──湘云与其他妇女同被发卖“为奴为‘佣’”,并举出雍正二年李煦事败后,总管内务府的一道奏摺为例:
准〔‘淮’误〕总督查弼纳来文称李煦家属及其家仆钱仲[王睿]等男女并男童幼女共二百余名口,在苏州变卖迄今将及一年,南省人民均知为旗人,无人敢买。现将应留审讯之人暂时候审外,其余记档送往总管内务府衙门,应如何办理之处,并经具奏,奉旨:依议,钦此。经派江南理事同知和升额解送前来等因,当经臣衙门查明:在途中病故男子一、妇人一及幼女一不记外,现送到人数共二百二十七名,其中有李煦之妇孺十口,除交给李煦外,计仆人二百十七名,均交崇文门监督五十一等变价。其留候审讯钱仲[王睿]等八人,俟审明后,亦交崇文门变价等因,为此缮摺请旨。……
──“红楼梦新证”第九二○页
明朝对大臣最酷虐,动不动庭杖,抄家不知道是否也有时候妻女如教坊,家属发卖为奴。清朝没有。但看李煦这件案例,“李煦家属及其家仆”送到北京,共二百二十七人。减去“李煦之妇孺十口”──交给李煦了──还剩“仆人二百十七名,均交崇文门监督五十一等变价”。仆人按男女年貌体力技能,分五十一个等级定价变卖。周汝昌认为“五十一”为音译人名,崇文门监督的名字,满清政府绝对不会译得这样滑稽,嘲弄自己满人。
①、⑦、⑧都是续书,十种“旧本”剔去三项后,⑤、⑥两种与史湘云无关,也先搁过一边再说。剩下②、③、④、⑨、⑩这五项,内中⑨看似可信性高──“三六桥百十回红楼梦真本”。周汝昌也非常重视,因为“所述情节,与近今研究者推考所得的结果,颇有吻合之点”。当是之下列数点:⑴蒙古王府本第三回有条批:“后百十回黛玉之泪,总不能出此二语。”周汝昌认为证实全书一百十回──八十回本加“后卅回”。〔我在“三详红楼梦”里解释过,此处的“百十”与“千百”、“万千”同是约计,并不能推翻第二十五回畸笏批的“全部百回”与第二回戚本、蒙本总批“以百回之大文……”〕⑵“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回目似指宝玉湘云偕老,而回前总批说:“金玉姻缘已定,又写一金麒麟,是间色法也,何颦儿为其所惑?”周汝昌曲解总批为中间还隔着金玉姻缘,将来湘云的事黛玉不必管。〔前面说过,“白首双星”是从早本保留下来的回目,结局已改,因此冲突,批者代为遮盖辩护。〕⑶俞平伯把十二钗册子上关于凤姐的“拆字格”预言拆成“冷来休”,主休弃。此外太虚幻境关于妙玉的曲文分明预言堕落风尘。畸笏有一再提起“抄没、狱神庙诸事”、“狱神庙回有茜雪红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红玉后有宝玉大得力处”似都符合此本情节。
贾芸红玉的恋爱是一七六○本新添的,伏下抄没时与抄没后他们俩是两员大将,一个“仗义探庵”,一个在狱神庙援助宝玉。三六桥本兼有一七六○以来与第一个早本的情节,当是根据早本续书,兼采脂批内的线索。续书人看过庚本,从第二十一回回前总批上知道有“后卅回”,因此在八十回后凑足三十回。他看到庚本畸笏关于“抄没、狱神庙诸事”的批语,迳将狱神庙当作监狱。此人应是曹雪芹亲友圈的外围人物,但是显然与畸笏没有接触。
儿玉达童教授述及此本时,因为语言不通,用笔谈,讲到探春,写了“远嫁,杏元和番”六字。末四字似是回目的一部份。“杏元”该是封号。番王例必要求尚主,才有面子,因此探春出国前封了杏元公主或郡主。第六十三回占花名酒令,探春抽到杏花,主得贵婿。众人说:“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不成?”原来这句顽话也是预言,而且探春作王妃也应当是番王妃,才合远嫁的预言。
第六十三回来自极早的早本,当时元妃还是王妃,当然也就不会有元妃的封号。──元春封元妃非常特别,因为从前女子闺名不让外人知道,妃嫔封号用自己名字的史无前例。金废帝海陵王有个元妃,大概作者喜爱这名字。而且元春称元妃也更容易记忆,正如多浑虫之妻灯姑娘改称多姑娘。书中几百个人物,而人名使人过目不忘,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元春改为贵妃后,起初只称贾妃,因此第十八回省亲一节清一色都是贾妃,只有宝玉晋见的一小段接连三个“元妃”,前几句刚提起宝玉的时候又有个“元妃”。
书中宝玉的年龄减低好几次,最初只比元春小一岁,所以第二回叙述元春诞生后,各脂本都是“次年有生一位公子”。全抄本第二十五回是一七五四本初稿,宝玉还是十五岁,甲戌本此回是一七五四本定稿,已改十三岁(见“二详红楼梦”)。第十八回也是写这一年的事。庚本第十七、十八合回回末有“正是”二字,下缺诗联,是准备用诗联作结──一七五五年左右改写的标志;回前附叶没有书名,与第七十五回一样,两回都是一七五六年定稿(见“三详”)。宝玉晋见一段,先事贾政报告园中匾对都是宝玉拟的。
元妃听了宝玉能题,便含笑说:“进益了。”贾政退出。贾妃见宝林二人益发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软玉一般;因问宝玉为何不进见,贾母乃启无职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进来。小太监出去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元妃命他近前,携手揽于怀内,又扶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尤氏凤姐等上来启道:“筵宴齐备,请贵妃游幸。”元妃等起身,命宝玉道引。
此回只有这四次用“元妃”都与宝玉有关。一提起钗黛,就又还原,仍用“贾妃”,而此处称宝钗黛玉为“宝林二人”,显然这一场没有宝玉,二宝不致混淆不清。看来早本此回宝玉已经十七八岁,与贾珍贾琏同等身分,男性外戚除了生父都不能晋见。“携手揽于怀内”等语,是对小孩的动作与口吻,当是一七五四本最后一次改小年龄后,一七五五年加的润色,感人至深。所有的“元妃”都是这次添写宝玉晋见时用的。因此迟至一七五五年才有“元妃”这名称,“杏元和番”则是第一个早本就有的,隔的年数太多,以至于“元”字封号犯重。
庚本第六十三回芳官改名一节末尾分段,看得出此节是后加的,原稿本中间插入两页,末了忘了指示,令抄手“续下页”。但是回内怡红夜宴并没改写过,因此还留着两个漏网之鱼的“王妃”。席上行占花名酒令,袭人拈到“桃红又是一年春”,麝月拈到“开到荼蘼花事了”,预言袭人别嫁,最后只剩下一个麝月。第一个早本内元春是王妃,看来当时已有第六十三回,结局已有麝月独留,袭人别嫁──湘云达到了与她同嫁一人的愿望,而仍旧不能相聚。
三六桥本的续书人如果仅知道早本情节,遵循着补撰,就不会用杏元封号,犯了元妃的讳。换一个字还不容易?显然“杏元和番”这一回是直接从第一个早本上抄来的。续书人手中有这本子。
三六桥本虽然是续书,有部份早本保留在内,仍旧是极珍贵的。既然四○初叶还在日本,只要在战火中无恙,日本也有研究红楼梦的,一经唤起广大的注意,也许不久就会有消息了。但是周汝昌提了一声“或云在上海”。倘在上海,那就不大有希望了,恐怕又像南京的靖本一样,昙花一现,又遗失了,似是隐匿起来,避免“收归国有”。
“旧本”之四──南京刻本──写宝玉作看街兵,住“堆子”中。看街兵制度始于乾隆元年,上谕废除京师的巡检官:“……外城街巷孔多,虑藏奸匪,各树栅栏,以司启闭,……其栅栏仍照旧交与督察院五城及步兵统领,酌派兵役看守。”(“东华录”)。我在报上看见台湾鹿港古迹的照片,也有拦街的木栅,设门,不过没有附有小屋,大概因为气候暖,不象北方,看守人至少要个木栅遮蔽风雪。中土已经湮灭了的,有时候在边远地区还可以找到。
乾隆六十年杨米人“都门竹枝词”有:“赶车终日不知愁,堆子吆喝往下浏”;“堆子日斜争泼水,红尘也有暂停时。”看街兵夜间打更,白天洒水净尘,指挥交通。京中大街中高旁底,居中行走限官员轿马,所以吆喝着叫骡车靠边走,一靠边就直往下溜。
“旧本”之二写宝玉“沦为击柝之流”。之三写宝玉湘云暮年,“夫妇在都中拾煤球(‘渣’误?)为活”,“流落饥寒,至栖于街卒木棚中”。周汝昌按:“栖于街卒木棚中,为‘沦为击柝之流’一语之正解,可见非谓宝玉本人充当看街兵,实即穷得无处住耳。”这推测得十分合理。
嘉庆九年,御史书君兴奏:煤铺煤缺,和土作块。似是煤球之始,那么乾隆年间著书时还没有煤球。宝玉湘云只是在垃圾堆里拣出烧剩的煤核,有人收买,跟现在一样。但是“街卒木棚”是个时代的标志,使③成为可靠的原本。
关于此本内容的记载,只说“荣宁衰替”,没提抄家。老了才赤贫,显然不是为了抄家──八十回内看得出,绝对不会等宝玉老了才抄家。
一七五四本前,贾家本来没抄家。但是百回“红楼梦”中两府获罪,荣府在原址苦撑了一个时期之后,也还是“子孙流散”,宝玉不到三十岁已经出了家──一七五四本第二十五回初稿(全抄本),宝玉十五岁“尘缘已满了大半了”,见“二详”──③写宝玉老了才一贫如洗,显然贾家并未获罪,所以落到这田地尚需时日。没抄家,也没获罪,宝玉湘云白头偕老──这分明就是第一个早本。
“荣宁衰替”──第一个早本其实还没有宁府。董康传述他亡母幼年看的书的内容,自然记不清楚了。不幸关于③的两条记载都非常模糊,王伯沆引濮文[走之旁加显]的话,所举的出处,也把书名记错了。
端方本──⑩──前八十回同程本,不过加了两段秽亵的文字。写宝玉湘云先奸后(续)娶,大概是被“醉眠芍药裀”引起了遐想。“八十回以后,黛玉逝世,宝钗完婚情节亦同,此后甚不相类矣。”想必娶宝钗也有掉包等情节。此本改写程本,但是有一特色:
宝玉完婚后,家计日落,流荡益甚;逾年宝钗以娩而亡,宝玉更放纵,至贫不能自存。欲谋为拜堂阿,以年长格于例,至充拨什库以糊口。适湘云新寡,穷无所归,遂为宝玉胶续。
“家计日落”仍旧是第七十二回林之孝向贾琏说的“家道艰难”,需要紧缩,不过这是几年后,又更不如前了。照理续书没有不写抄没的,因为书中抄家的暗示太明显,而此本删去程本的抄家,代以什么事都没发生,又并不改成好下场,这样写实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只能是这一部份来自第一个早本。宝玉穷到无法度日,已经“年长”,等到老了捡煤渣,“流落饥寒”,也正吻合。端方本采用这败落的方式,当是因为归罪于宝玉。这是个年代较晚的抄本,迟至一九一○年左右还存在,作风接近晚清的夸张的讽刺小说,把宝玉湘云写成最不堪的一种名士派。但是此处写败家子宝玉只用“放纵”二字,轻飘而含糊得奇怪,与第三十六回王夫人口中的“放纵”遥相呼应──王夫人解释袭人不收房的原因:“……三则那宝玉见袭人是个丫头,总(纵)有放纵的事,到(倒)能听他的劝。”──后回宝玉的罪名不过是“放纵”,看来也是第一个早本的原文。当然原本不会有“拜堂阿”、“拨什库”。端方本九十七八回后从程本过渡到第一个早本,但是受程本后四十回作者的影响,也处处点明书中人是满人,卖弄续书人自己也是满人,熟悉满洲语文风俗。
前面说过,关于第一个早本的记载模糊异常。“林薛夭亡,荣宁衰替,宝玉糟糠之配实维湘云”,没提宝钗嫁宝玉后才死。王伯沆引濮文[走之旁加显]的话,更是口口声声“宝玉系娶湘云”,“宝玉所娶系湘云”,仿佛双方都是第一次结婚。难道宝钗也是未婚而死?
端方本自娶宝钗后败落的经过用第一个早本,因此娶宝钗是原有的。董康等没提,大概因为是尽人皆知的情节。至于湘云是否再醮,宝玉搞到生活无着的时候已经年纪不轻了,然后续娶湘云;湘云早先定的亲如果变卦,也不会这些年来一直待字闺中,当然原著也是写她结过婚,而且也不是小寡妇。宝玉鳏居多年,显然本来无意续弦。他们的结合比较像中年孤苦的两兄妹。连端方本也都没插入色情场面写他们旧梦重温。
“旧本”之二,八十回后与程本不同,但是也有抄家,因此是家境骤衰。抄没后宝玉湘云流落重逢而结合,应当年纪还轻,与第一个早本的老夫妻流落正相反。此本也是根据这早本续书,不过将流落提前,结婚宕后,增加戏剧性。“后数十会文字,皆与今本绝异”,是没参用程本,似是较早的续书。大概不会有第一个早本的原文在内──用不上。
南京刻本──④──写宝玉作看街人,因而重逢北静王,不是重逢湘云。此点南京刻本与②是互相排除的,并不是记载不全,顾此失彼,因为不可能先遇见湘云,然后又遇见北静王──②写到宝玉湘云重逢后结合,全书已完;如果是先遇见北静王,那就已经转运,不做看街人了,也不会再在凄惨的情形下遇见湘云。这两个本子似是各自分别续书,而同是自然而然的将街卒木棚中过宿渲染成自任看街兵。
再来细看南京刻本的内容:
画家关松房先生云:“尝闻陈[左弓上山下又,音tao]庵先生言其三十余岁时(光绪初年)曾观旧本红楼梦,与今本情节殊不同。薛宝钗嫁后,以产后病死。史湘云出嫁而寡,后与宝玉结[衣补旁加离]。宝玉曾落魄为看街人,住堆子中。一日,北靖王舆从自街头经过,看街人未出侍候,为仆役捉出,将加[竹字头加垂]楚,宝玉呼辩,为北靖王所闻,识其声为故人子,因延入府中。书中作者自称当时亦在府中,与宝玉同居宾馆,遂得相识,闻宝玉叙述平生,乃写成此书云云。
──扈功着“记传闻之红楼梦异本事”
宝钗死于产难,湘云再醮宝玉,与端方本相同,遇北静王也大同小异,且都误作“北靖王”。扈功文内转述关松房听到的陈[左弓上山下又,音tao]庵的话,两次都是口述。“静”误作“靖”显然是扈功的笔误。但是民初褚德彝记端方本事,也与近人扈功同误“静”为“靖”,未免巧合得有点不可思议。难道周汝昌引扈、褚二文,两次都抄错了?
“红楼梦新证”书中错字相当多。如果不是误植,还有个可能的解释:听某某人说,也可能是书信上说的。如果扈功所引的是关松房陈[左弓上山下又,音tao]庵信上的话,那就是南京刻本于端方本间的一个连锁。
其实这两个本子的关系用不着“北靖王”作证。南京刻本把第一个早本的宿街卒木棚中渲染成自任看街兵,看街这样的贱役,清初应是只有汉人充当。端方本注重书中是满人这一点,改写“充拨什库以糊口”,表示一个满人至不济也还可以当拨什库。
遇北静王一节,端方本作宝玉“市苦酒羊胛,与湘云纵饮赋诗”赏雪,“适九门提督经其地,以失仪为从者所执,视之盖北靖王也。”苦中作乐赏雪,与芦雪亭对照,借此刻画二人个性。但是不及南京刻本看街巧遇北静王,与职务有关,较浑成自然。
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京师城外巡捕三营、督捕、督察院、五城所管事宜交步军统领管理,换给“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印信(见“红楼梦新证”第三五○页)。步军统领本来只管城内治安,自此兼管城外,“九门提督”是他的新衔。端方本内北静王现任九门提督,也是此本的润色,当代的本地风光。是端方本改南京刻本,应无疑义。
延入王府,端方本显然认为太优遇了,改为代找了个小差使:“越日送入銮仪卫充云麾使,迄潦倒以终云。”云麾使如果执云帚──也就是拂尘;省亲时仪仗中“有有值(执)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漱盂扫尘等类,一队队过完”──毕抗旗伞轻便。后妃用太监,銮仪卫想必另在满人中挑选。
南京刻本末尾著书人根据宝玉口述,写成此书,这著书的经过于楔子冲突,也与卷首作者自述冲突,显出另手。但是重逢北静王是否第一个早本原有的?
今本第十四、十五、十六回、第二十四、第七十一回都有北静王。秦可卿出殡途中,北静王初次出场。“风月宝鉴”收入此书后,书中才有秦氏。第一个早本还没有写秦氏丧事的第十四、十五回。
第二次提起北静王,是第十六回林如海死后黛玉从扬州回来,宝玉将北静王所赠的[脊鸟][令鸟]香串转赠黛玉,被拒绝了。早本黛玉初来时已经父母双亡,后改丧母后寄居外家多年,方才丧父(见“二详”)。因此初名“石头记”时没有林如海病重,黛玉回扬州的事,当然也没有自扬州回京,与宝玉那一小场戏。
第二十四回主要是介绍贾芸,一七六○本新添的人物。贾芸初见红玉一场,又介绍红玉,早本旧有的人物。通回都是新材料,只把早本宝玉初见红玉一场用了进去,加上两句提起贾芸的对白。宝玉红玉一节这样开始:
这日晚上从北静王府里回来,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回至园内,换了衣服,正要洗澡。袭人因被宝钗烦了去打结子,秋纹、碧痕两个去催(炊)水,檀云(全抄本作“晴雯”)又因他母的生日,接了回去,麝月现在家中养病。虽还有几个做粗活听唤的丫头,估量着叫不着他们,都出去寻伙觅伴的顽去了。
写此节时,晴雯的故事还与金钏儿的故事相仿佛。书名“红楼梦”期之前有个时期,添写金钏儿这人物,晴雯改为孤儿,因将此处的晴雯改檀云(见“三详”)。所以加金钏儿时改写过此节,一七六○本将此节收入全新的第二十四回,又改写过一次。两次中有一次顺便一提北静王,免得冷落了这后添的人物。原先宝玉也许是从亲戚家回来。
前面说过,加了贾赦邢夫人迎春后,才写第七十一回。回内贾母做寿,贺客有北静王与北静王妃。
有北静王的五回都是后添的。第一个早本没有北静王,因此结尾也不会有宝玉重逢北静王。那是南京刻本代加的好下场。
南京刻本前文应有北静王,否则无法写重逢北静王。因此南京刻本前部是今本。它也是根据第一个早本续书,而不是通部补撰传闻中的早本。
关于此本的记录,叙事层次不清,说到续娶湘云,下接“宝玉曾落魄为看街人”。如果看街巧遇北静王,因祸得福后才续弦,那在湘云这方面就毫无情义可言了。但是宝玉在王府认识了著书人,想必就是同住宾馆时自述身世──包括续娶湘云的事。所以先续弦后落魄。这也就是第一个早本的结局:宝钗产后病故,续娶湘云,后贫苦。后人复述,偏重续书杜撰的遇贵人一节,因为故事性较强,便于记忆,而原本后部是毫无变故的下坡路,没有获罪,更没有抄家──并不是略去不提。
端方本这一部份用第一个早本,只到“年长”时穷得过活不了,续娶湘云为止,而南京刻本一直到末了晚年流落,不过把街卒木棚过宿加油加酱说成看街。端方本续书人手中未见得有第一个早本,大概就是参用南京刻本改写程本。
端方本改看街兵为拨什库,而看街又来自宿街口木棚中,可见原本内没做任何工作,也没找过事。但是原本宝玉搞到过不了日子的时候,已经年纪不轻了,所以端方本此处插入找事一节,就用超龄作为不合格的理由。
湘云不识当票(第五十七回),可见社会上的事一无所知。她与宝玉一样任性,而比宝玉天真,所以是跟她在一起才终于落到绝境中。湘云精于女红,但是即使领些针线来做,也需要世故些,上门走动,会趋奉逢迎。
第一回“好了歌”有:“金满箱,银满箱,展(转)眼乞丐人皆谤。”甲戌本夹批:“甄玉贾玉一干人。”并没有说湘云做乞丐。讲宝玉也着重在“谤”字上,可能仅只是说一成了穷光蛋,人人都骂不上进。当然,这一系列批语已经不是批第一个早本了。稍前有这两句歌词:“说什么粉正浓,脂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甲戌本夹批:“宝钗湘云一干人。”作批的时候宝钗早卒,已经改去。
但是第一个早本内宝玉湘云再婚这样迟,然后白头偕老,纵使流落,显然并未失散了再重逢。“旧本”之二写湘云为丐,无非是为了使她能在风雪之夜与敲更的宝玉重逢。
因此湘云为丐与宝玉打更一样,都不是原有的。他们俩生活在社会体系外,略似现代西方的嘻痞──进来大都译为“嘻皮”,不免使人联想到“嘻皮笑脸”,其实他们并不──但是嘻痞是寄生在富裕宽容的社会上──对年轻人尤其宽容,老了也还混不下去。宝玉湘云晚景之惨,可想而知。
庚、戚本第二十二回有两则极长的批注,批宝玉续庄子的事。第二段如下:
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阿凤是机心所误。宝钗是博知所误。湘云是自爱所误。袭人是好胜所误。皆不能跳出庄叟言外,悲亦甚矣。
黛玉太聪明了,过于敏感,自己伤身体。宝钗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娶了个Mrs.Know-all,不免影响夫妻感情。“湘云是自爱所误”,只能是指第一个早本内,再醮宝玉前,其实她并不是没有出路,可以不必去跟宝玉受苦,不过她是有所不为。
“阿凤是机心所误”,可见第一个早本已有凤姐,此回要角之一,更可以确定第二十二回来自最初的早本。
第三十一回袭人吐血,“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觉滴下泪来。”“袭人是好胜所误”,是说贾家败落后,她恨宝玉不争气,以至于琵琶别抱。这条批是批第一个早本,当时已有袭人别嫁的情节,这也是一个旁证。第三十二回隐约提起的湘云袭人十年前西边暖阁夜话,同嫁一个丈夫的愿望,预言不幸言中而又不中。袭人另外嫁人,总是年轻的时候,于湘云一去一来,相隔多年,根本没有共处过。
书中用古代地名,讳言京城是北京,早本尤其严格。北京分里城外城。端方本内蒋玉菡的当铺开在外城,又是端方本特有的笔触,与此书的态度相悖。
第一个早本内袭人并没有与蒋玉菡一同奉养宝玉夫妇,因为与宝玉湘云的下场不合。袭人嫁的是否蒋玉菡,嫁后是否故事还发展下去,不得而知。蒋玉菡嫌宝玉屡次来借钱,要叫铺兵驱逐,“为袭人所斥而罢”,大概是端方本编出来骂宝玉的。南京刻本就没有──复述者该不会遗漏这样触目的情节。
端方本续书人鄙视宝玉,想必是因为第一个早本对宝玉的强烈的自贬。
此本还没有卷首作者自述一节,但是那段自述写得极早。在这阶段,此书自承是自传──当然是与脂砚揉合的自画像。第一个早本的“老来贫”结局却完全出于想像。作者这时候还年轻,但是也许感到来日茫茫的恐怖。有些自传性的资料此本毫不掩饰,用了进去,如曹寅之女平郡王福晋,在书中也是王妃。但是避讳的要点完全隐去,非但不写抄家,甚至避免写获罪。第一个早本离抄家最远,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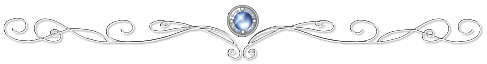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