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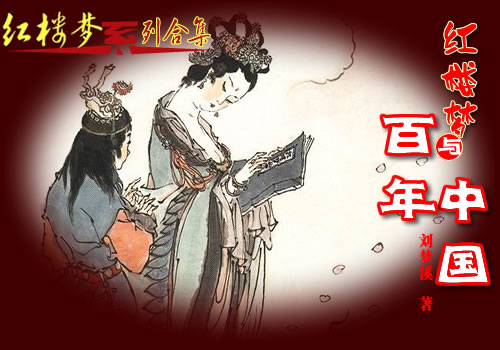
|
|
遭到考证派打击之后(2)
|
寿鹏飞自己的正面主张,是认为《红楼梦》影射雍正夺嫡。他说:“然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与其谓为历史小说,不如径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当然此说并非他的首创,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中即提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第26页。“林、薛二人之争宝玉,当是康熙末允禩诸人夺嫡事。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著者故明言为一块顽石矣。”参见《红楼梦卷》第2册,第421页。蔡元培也说过宝玉象征传国玺,指太子允礽。寿氏发挥说,宝玉是指传国玉玺,因系国宝,所以叫宝玉;通灵玉上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字样,传国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寿氏据此认为前者影射后者甚为明显。又玉玺为诸皇子及群雄所争,所以“见宝玉者,人人皆生恋爱关系”。还说贾母因是康熙的影子,贾母爱宝玉是比喻其宝爱帝座,“不肯即以黛玉配之者,喻帝之不肯轻立储二,以宝位畀允礽也”。金陵十二钗分正册、副册、又副册,恰好三十六人,分别影射康熙的三十六个儿子。宝钗、袭人都影射雍正,“袭人二字,有乘虚掩袭之意”,比喻雍正“袭取帝位”。蒋玉函是指“藏玺之函椟”,所以“名曰玉函,且住紫檀堡,明言玺函以紫檀为之”。袭人的猩红裤带,以及宝玉换赠给蒋玉函的松花带子,都指的是“玺绶”。宝玉与蒋玉函发生暖昧关系,是说“与传国玺有特别恋爱者,惟此函椟耳”。而袭人后来嫁给蒋玉函,是“极言清室玉步已移,此龙衣人所争得者,亦止空函而已”。参见《红楼梦本事辨证》第37至第44页这样一些说法是否可信,可以权当别论,我们不能不佩服索隐者的想像力,而且与其他索隐派相比,隐约感到也许上述说法真的捕捉到了一点什么东西。“玉玺”为什么住在“紫檀堡”?考虑到曹雪芹给书中人物命名的惯例,恐怕不是毫无意义的巧合。甄宝玉在《红楼梦》中出现,使很多研究者感到费解,对此,寿鹏飞提出新说,认为甄宝玉是南明弘光帝的影子,作者用甄、贾二宝玉象征南北两朝对峙局面。作为探讨《红楼梦》命意的一说,或至少作为一种猜测,应该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
问题是不能把索隐扩大化,以为人人、事事都有影射。寿氏对林黛玉是废太子理亲王胤扔的影子的索隐,使他完全陷入他所批评的以往各种索隐的故辙。他说:“林者二木,二木云者,木为十八之合,两个十八为三十六,康熙三十六子,恰合二木之数。而理王为三十六子中之一人也。黛玉者,乃代理二字之分合也:分黛字之黑字与玉字合,而去其四点,则为代理二字,明云以此代理亲王也。”又说,“胤礽于康熙十四年立为皇太子,故黛玉到贾府时,假定为年十四也。”如此曲为弥缝,与王、沈以及邓狂言的附会实无二致。况且黛玉进贾府时明明是七岁参阅拙著《红楼梦新论》第3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寿氏为了能够与康熙十四年立储位在数字上相吻合,便擅自将黛玉的年龄增加一倍,这种做法虽勉强可以“将胤礽一生遭际及心事曲曲传出”,却丧失了自己立论的全部说服力。
寿鹏飞对《红楼梦》作者的看法最为离奇。他相信一位叫马水臣的人的妄说,认为作者是无锡人曹一士,生于康熙十五年,卒于雍正十二年,《红楼梦》是在康熙五十五年“诸皇子夺嫡剧烈时”写就的。旁证是陈镛的《樗散轩丛谈》里有“《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参见《红楼梦卷》第349页。的记载。寿氏推论道;“考得一士于康熙季年未通籍时,入京假馆某府者十余年,所居与海宁陈相国比邻,然则与《樗散轩丛谈》所云,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者适合,意即其人乎?”把《红楼梦》区分为原作和改作两种,雪芹只不过是后来的“增删”者,原作另有其人,从王梦阮、沈瓶庵到邓狂言,都是这样看的,可以说是索隐派的共同主张,寿氏亦持此说,并不足为怪。但他将原作者坐实为曹一士,则是于史无征的主观臆断,特别是当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被胡适公之于世之后,更见出其说的虚拟性。但蔡元培认为此说不无继续研讨之价值,可见蔡先生对胡适的自传说成见亦深矣。
第二部著作是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1934年西京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卷,约十四万字,比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篇幅大得多。上卷开首是一篇纲要,然后分叙论,先论命名,次论薛林取姓,次论满汉明清,再专论宝玉,论书中诗词,论著者思想几部分,并有附录、别录、杂评、杂录多则。下卷则是对王梦阮、沈瓶庵及邓狂言的索隐的系统批评。景梅九的基本观点,略同于王、蔡、邓诸家,虽有异见,却没有另立门户,而是对王、蔡、邓各家索隐的补充、发挥、折衷。王、沈力主的顺治帝与董小宛的恋爱故事说,蔡元培关于十二钗影射康熙时诸名士说,邓狂言的许多扩大化的索隐,寿鹏飞的康熙诸皇子夺嫡的观点,景氏均予以兼收并蓄。他在谈到自己著书缘起时,特地援引一位友人的话,作为《红楼梦真谛》的立论基础。这段话的全文如下: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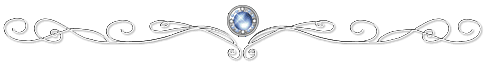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