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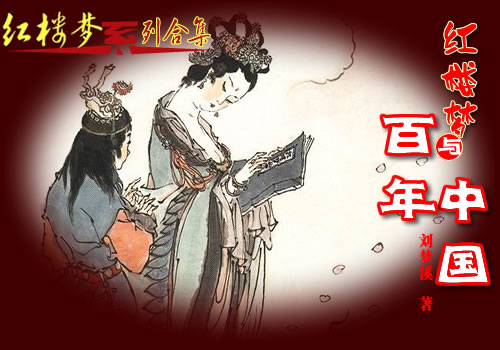
|
|
索隐派的复活(1)
|
索隐派红学在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的打击之下,自二十年代以来便进入了衰歇期。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正》、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在二三十年代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影响并不大。四十年代中期方豪发表《红楼梦新考》,表示确信顺治与董妃恋爱故事说“有一部分真实性”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00页。,只是一笔带过,未做任何论证。五十年代以后,索隐派在大陆上基本上消失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索隐派在大陆上虽基本消失,却在海外得到复活。1959年,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了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潘重规:《红楼梦新解》第1页,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年印行,下面引录该书不一一注出。,把多少年来争论不休的作品的本事问题又提了出来。潘先生表示同意蔡元培的观察,而不同意胡适的“作者自述生平”的观点。具体论证方面,《红楼梦新解》则显得鲜于创见,许多提法,如说宝玉影射传国玉玺,林黛玉代表明朝,薛宝钗代表清朝,林、薛争取宝玉象征明、清争夺政权,《风月宝鉴》就是明清宝鉴,以及列举的理由,包括宝钗的“钗”字拆开为“又金”,亦即后金,薛蟠的“蟠”字从虫,“犹狄从犬”,是指其为异族番人,通灵玉的形状和传国玺差不多,上面的刻字略同于玉玺上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还有袭人是龙衣人,蒋玉函住在紫檀堡,暗含有装玉玺的匣子的意思,等等,都可以从王、蔡、邓、寿、景诸家著作中找到出处。潘重规先生的发挥之处,一是认为“宝玉爱吃胭脂,是从玉玺要印朱泥上想出来的”,而且说第四十四回提到的胭脂盒就是印泥盒;二是把有关的理由编缀起来,变成:“一块玉石,镌上传国玺的文字,印上朱泥,盛在紫檀盒子里,用龙衣包袱缠裹,试问,这是甚么捞什子呢?这不分明点醒读者,宝玉就是传国玺吗?在这里,我们既知宝玉即是传国玺,所以衔玉而生的这个人自然是天子的身份。”旁证是,第三十四回薛蟠有“难道宝玉是天王”的话;第四十六回鸳鸯也说过“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第十六回又写宝玉的威力可以吓倒鬼判。在引述这些例证之后,潘重规先生写道:“由于全书中这一类的明呼暗唤、旁敲侧击的启示触目皆是,所以我说宝玉是影射传国玺,而不敢相信《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的说法。”
关于《红楼梦》的创作目的,潘先生认为第一是反清,第二是复明,与蔡元培的观点完全相同。他说第七回焦大的醉骂,是影射清初皇太后下嫁睿亲王多尔衮之事,用以揭露清室的秽德;第十九回宝玉的除“明明德”外无书的议论,是暗示明朝才是正统。应该说,这都算不得什么新鲜见解,只不过在考证派红学占优势的情况下,索隐派几乎销声匿迹,又重提旧案,在不甚了解《红楼梦》研究历史的读者群中,仍不失某种新鲜感。就潘重规本人来说,也应看做是在学术上有勇气的表现,因为他是在向胡适挑战,至少要冒被指为“猜笨谜”的危险。《红楼梦新解》不同于以往的索隐的地方,是没有把索隐扩大化,主要围绕作者的立意即创作思想加以探究,避免了将书中的情节与人物一一指实的做法,更没有征引大量野史轶闻进行比附,在思路的出发点上和蔡元培较为接近,因此不失为聪明的、保持学术向度的索隐。
索隐派一般都否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潘重规先生亦如是。但他没有指实具体人物,只揣想是出自明末清初某一隐名的遗民志士的手笔,后来又说原作者就是书中屡屡出现的“石头”潘重规:《红楼梦的发端》,参见《红楼梦新辨》第72至第94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从书中的具体描写看,“石头”拥有作者的身份,似不成问题,只不过何以知道“石头”就一定不是曹雪芹的化身?所以对著作权问题提出疑问可以,论定则缺乏证据。总的看,潘先生的《红楼梦新解》,并不比以前的诸家索隐有多少前进,而且是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出现的,不能算作索隐方法的系统撰述。但他持论甚坚,在论证宝玉的帝王身份方面颇具说服力。潘先生研究《红楼梦》,不是只采用索隐一种方法,在考证和小说批评方面也多有发挥,这里来不及评估他治红学的全部成果。
1972年在台中市印行的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是继潘重规先生的《红楼梦新解》之后的又一部索隐派著作,全书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总论”七篇,三十三章;“各论”十四篇,五十章,共二十一篇,八十三章,三十多万字,是自索隐派问世以来篇幅最大、最具系统的一部红学论著杜氏在《红楼梦原理》“例言”中称,该书系在其所著《红楼梦悲金悼玉考实》一书的基础上删改而成,《考实》笔者未见。。
杜世杰在《红楼梦原理》中阐述的基本观点略同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蔡氏关于“《石头记》者,清康熙朝之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见解“非常正确”,但不满意只着重于康熙朝的几个名士,认为蔡氏“没有发现红学真实结构,而愈走愈偏,给胡适以攻击之弱点”。对王梦阮、沈瓶庵的索隐,杜世杰同样感到不尽满意,他说:“对红学真事隐发现最多的,要算王梦阮之《石头记索隐》,但王氏之方法一无可取。王氏熟悉明清史实及清宫掌故,完全以历史故事附会《红楼梦》上各情节,因而有许多情节被他射中,而他自己所留下的矛盾,也足以否定他自己,所以经不起胡适的攻击。”那么,杜世杰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所发现的红学的“真实结构”在哪里?《红楼梦原理》的总论部分第一、第二两篇对此做了回答。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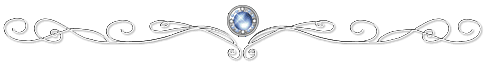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