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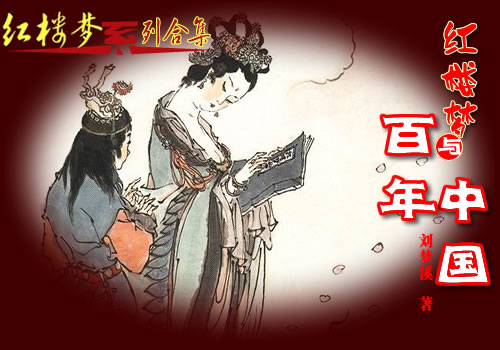
|
|
俞平伯所代表的考证派红学(2)
|
我们读着俞平伯先生的娓娓论述,只觉得他艺术鉴赏的眼光敏锐,体味深细,笔致隽永,恰如分际。如果说王国维的小说批评,主要是侧重从美学的角度说明《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俞平伯的批评则是鉴赏式的,有理论阐述,却不离开本文,重视从整体艺术风格上把握作品,在艺术领悟方面,比王国维又进了一步。
《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续书应如何评价?这直接涉及文学考证。《红楼梦辨》中的不少篇文章,都是细心考证这一问题的,如《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高鹗续书的依据》、《后四十回的批评》、《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等,基本上都是考证文字。但如前所说,俞先生所做的是文学考证,是与小说批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在比较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文字异同的同时,更从艺术创作的特征出发,得出“凡书都不能续”《红楼梦辨》第210页、第3页。的结论。他说:
凡好的文章,都有个性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泼地。因为如此,所以文章本难续,好的文章更难续。为什么难续呢?作者有他的个性,续书人也有他的个性,万万不能融洽的。不能融洽的思想、情感和文学的手段,却要勉强去合作一部出,当然是个“四不像”。故就作者论,不但反对任何人来续他的著作,即是他自己,如环境心境改变了,也不能勉强写完未了的文章。这是从事文艺的应具的诚实。
至就续者论,他最好的方法,是抛弃这个妄想;若是不能如此,便将陷于不可解决的困难。文章贵有个性,续他人的文章,却最忌的是有个性。因为如果表现了你的个性,便不能算是续作;如一定要续作,当然须要尊重作者的个性,时时去代他立言。但果然如此,阻抑自己的才性所长,而俯仰随人,不特行文时如囚犯一样未免太苦,且即使勉强成文,也只是“尸居余气”罢了。
我认为没有什么人能够反驳俞先生的观点,因为他是依据艺术规律进行论证的,而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观点。虽然想续写《红楼梦》者代不乏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成功的,连程、高补作的水平也达不到。此无他,就是俞先生讲的:“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见《红楼梦辨》第3页。也就是艺术规律不能违背。由此可以看到,使用小说批评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有考证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具有说服人的力量,可以弥补单证的不足。
俞平伯治红学的初衷,似乎也是在追求一种文学考证和小说批评的结合。顾序讲的他们主要在“本文上用力”,固是一证,俞先生在《红楼梦辨》的附录札记中,更反复致意。一则说:“考证虽是近于科学的、历史的,但并无妨于文艺底领略,且岂但无妨,更可以引读者做深一层的领略。”见《红楼梦辨》第212页、213页。二则说:“我们可以一方做《红楼梦》的分析工夫,但一方仍可以综合地去赏鉴、陶醉;不能说因为有了考证,便妨害人们的鉴赏。”②③见《红楼梦辨》第212页、213页。三则说:“考证和赏鉴是两方面的观察,无冲突的可能。”②四则说:“考证正是游山的向导,地理风土志,是游人所必备的东西”,因此“要荡瑕涤秽,要使读者得恢复赏鉴的能力,认识那一种作品的庐山真面”。③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从前我们不理解俞平伯先生的苦诣孤心,或者对他的书读得不细,误认为他的考证和胡适一样,没有看到他对红学的独特追求,失之交臂而不自知,确是一件殊可遗憾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俞先生在1925年所写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这篇文章的具体背景,我们已经无法查考了,审其行文语意,当是有所为而发。请看下面的措词:
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做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做一篇科学的论文。对于文艺,除掉赏鉴以外,不妨做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成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我不说那些方法不可参用到趣味的研究上去;我亦不是说趣味的研究另有一种妙法,可以传人。我说欣赏文艺时附带一点研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若拿了一把解剖刀来切割,恐怕割来割去了无所得。这不怪你的手术欠佳,或你的宝刀欠快,只是“割鸡焉用牛刀”耳。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至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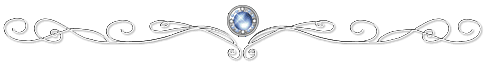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