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四章 诗词曲赋的隐喻意味和叙事功能(7)
|
这种异同早在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中便暗示出来了。当宝玉细想戏文中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句意味时,不禁大哭,然后立占一偈: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结果让林黛玉见了,续上一句:
无立足境,方是干净。
且不说二人在佛教境界上的悟性高低如何,可以显见是林黛玉在人生姿态上比贾宝玉的那种彻底性。正是这种彻底性,使这位少女在前一回中看了贾宝玉在庄子
《胠箧》所作的续文后,又气又笑,嘲讽道:
无端弄笔是何人?剿袭《南华》庄子文,不悔自家无见识,却将丑语诋他人。
虽然宝黛二者童心相合,但毕竟境遇迥异。林黛玉孤苦伶仃,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故一开始就被迫义无返顾地忠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而贾宝玉却为一片世俗的宠爱娇惯所包围,且面对诸多诱惑,不免有些瞻前顾后。这种差异在客观上导致了宝黛之间持续不断的磨擦试探,也造成了彼此在诗作上的不同色调。同样是对大观园世界那种欣欣向荣光景的感受,贾宝玉写出的是快乐的四时即事,而林黛玉写出的却是哀怨的葬花辞。
四时即事也许是整个小说中最为明媚的诗篇,尽管笔墨所至均为夜景,但让人的感觉却阳光灿烂。这里有公子的欢笑,小姐的娇嗔,但没有主仆的尊卑,丫环也同样因娇惯而意态慵懒。当然,这里的气息与其说是大观园的,不如说是桃花源的。事实上,这个人工的仙境,在骨子里正好是桃花源的一个幻象。自然的情趣在此体现为人际的平等,而天人齐物和平等相处,又正好是同一种人类理想的两种不同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贾宝玉所感受的快乐与其说是世俗的满足,不如说是天国的幸福。只是人们往往自己出于某种世俗念头,每每不无妒意地把这组即事诗仅仅读成公子之乐。因为这组诗歌虽然具有种种富贵气,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蕴含其中的自然心。或许正因如此,小说才会在这组诗之前特意加上一句:“虽不算好,却是真情真景”。其情之真,真在童心使然;其景之真,真在与太虚幻境那样的桃花源世界遥相映照。但即使如此,小说又认为不算佳作。我想,小说认为可算佳作的,也许当推林黛玉的葬花辞。
正如在历次诗会中的林诗以比拟的方式从外观上对自身形象作了娇羞倦倚的描绘一样,林黛玉葬花辞一类即兴抒发式的自我咏叹,以酣畅淋漓的抒情坦露出她作为大观园诗魂所具有的内心世界。葬花辞是她整个咏叹系列中的第一篇,贾宝玉的四时即事写于小说第二十三回,她的葬花辞写于第二十七回。面对着同样的大观园世界的春天景象,贾宝玉投入其中的是一颗天真的童心,收获起来的是一派稚气的快乐;而林黛玉赖以置身的却是一种孤苦无依的极易受伤的孤寂和敏感,因此她即便面对春天所能唱出的也只是一片呜咽悲泣。尽管心中充满爱情,举目所至,“花谢花飞飞满天”,情满天下。但又有谁关心那“红消香断”的薄命红颜。与贾宝玉“拥衾不耐笑言频”那副快乐的傻相截然相反,林黛玉所感受到的是“游丝软系”和“落絮轻沾”的紧张和小心,连同“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严寒和冷酷。即便“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和“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那样的感慨,也不是乐极生悲式的自怜自叹,而是对无常命运的悉心领略。这首葬花辞在小说的叙事上可与贾宝玉的四时即事诗对照着读出宝黛之间摩擦纷争的根本缘由,而在诗作本身的隐喻意味上,又可读着是小说对中国历史上所有杰出女子的深情悲悼。这种深意就小说本身而言可由后面林黛玉的“五美吟”和薛宝琴的“怀古诗”作证,就其诗歌本身的诸种意象及其象征意味而言,葬花辞所葬者乃历代红颜之情也。那些幽灵们如同沉沉黑夜中划过的一颗颗慧星,“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一掊净土掩风流”。所谓男人如泥,女儿似水,于此获得诗意十足的全面诠释。而作为这种悲叹的呼应,七十八回中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将这具有总纲意味的葬花辞作了具体的唱和性的阐发。总之,如果说林黛玉是整个大观园世界中之诗魂的话,那么她的葬花辞则是这个诗歌王国的国徽。这样的标记在其纵深度上,以悼亡的方式颠覆了由男人主宰和男人断言的历史;在其横向性上,则总结了小说中大观园人物韵文的基本指向和整体风貌。一部《红楼梦》在整个叙事结构上,就灵的层面而言,须读懂第一回中的顽石故事;就梦的层面而言,第五回的太虚幻境是阅读关键;而就情的层面而言,林黛玉的葬花辞连同后面贾宝的呼应即芙蓉女儿诔则是小说的点晴之处。而且,葬花辞向读者点亮的是林黛玉的眼睛,而后面的芙蓉女儿诔点亮的则是贾宝玉的眼睛;相形之下,写四时即事诗的贾宝玉不过是一个混沌未开的孩子,直到大观园世界被摧毁之际,他才突然长大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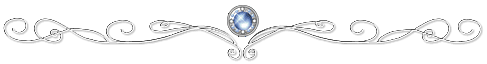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