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四章 诗词曲赋的隐喻意味和叙事功能(10)
|
这篇与林黛玉《葬花辞》相得益彰的诔文,作者明言:“远师楚人之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而且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起首之句“维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日,无可奈何之日”乃出自阮籍《达庄论》中的“伊单阏之辰,执徐之岁,万物权与之时,季秋遥夜之月”数句变化而成。可谓熔屈原、庄子、阮籍等精神风骨于一炉。太平不易、蓉桂竞芳、无可奈何,仅此三句,便含多少寓意,更何况以下滔滔长文。昔日林黛玉葬花的种种悲哀,此刻变成贾宝玉祭花的一场痛哭,敬献于那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薄命少女,纯洁刚烈的芙蓉仙子。
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
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鸷翻遭;妨其臭,兰竟被芟!
岂招尤则替,实攘垢而终。既怀幽沉于不尽,复含轨罔屈于无穷。高标见嫉,闺闱恨比长沙;贞烈遭危,巾帼惨于雁塞。
岂道是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汝南斑斑泪血,洒向西风;梓泽默默余衷,诉凭冷月。呜呼!固鬼域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毁 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念犹未释!
整个诗词将骈文与骚体并举,将晴雯并贾谊、鲧等一干刚直之士共提;情意缠绵,词句悲切,格调高昂,气势磅礴;就小说叙述而言,总收愤激之情;而就诔文本身而言,堪为千古绝唱。不仅历史经由这样的悲悼被全然重新构写,而且文学本身也因此获得观念上的巨大颠覆。过去为二十四史所忽略不计的冤屈悲剧,于此得以昭雪申张;同样,当年屈原在《离骚》中那样的满腹牢骚,在此不过是悼念一个不见经传的屈死的丫环。文学的内涵连同定义随着历史的颠覆和重新命名从忠君报国之类的圭臬断然转向怜香惜玉式的人文主题。在此,不仅人比国家更为重要,而且花柳般最易被摧折的无辜少女比一听到文死谏武死战就混闹起来的须眉浊物更具人格力量和审美价值。屈原为楚国怀王的覆灭奔走呼号,乃至投水自沉;而宝玉则为被谗言谋杀的丫环愤愤不平,从而长歌当哭。前者经由岳飞演化至今日,便是所谓“血染的风采”之标榜;后者经由王国维的殉身推至当代,人们可读到的乃是著名学者陈寅属在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柳如是别传》。正如历史的谎言总被一遍遍地重复一样,文化的气脉却在这种对丫环(如晴雯)小妇(如柳如是)的歌赞记传中悄然延伸。联系到小说着意推出的《五美吟》和《怀古诗》,被谎言覆盖的历史和被人性照亮的文化之分野,岂不是一目了然了么?承《离骚》这一脉文学而成的《芙蓉女儿诔》所颠覆的恰好正是《离骚》传统,如此气度,又正是小说开卷所述作者自云的深意所在:“今风尘碌碌,一事无居,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或许是得了小说的这种启示,后来的鲁迅在指斥吃人历史的《狂人日记》中以同样的笔法更为激越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满本写着的是二个字:吃人!”
指明了《芙蓉女儿诔》之于历史——文学的这种颠覆性之后,这篇诔文在叙事上的承上启下也就得以顺理成章地阐述了。虽然就小说人物韵文而言,这篇诔文乃是《葬花辞》的具体深化和全面发挥;但就故事的叙述而言,此处对晴雯的祭悼一方面归结了大观园中丫环层少女们的悲惨遭际,一方面又开启了大观园中小姐层少女们的风开云散,尤其是铺垫出了小说整个女儿世界中的核心形象林黛玉的摧折趋向。如果说大观园女儿世界以群芳题咏为序幕,那么其最后一幕则由《芙蓉女儿诔》的愤激赫然挑开。作为这种唇亡齿寒式的转折过渡的又一标记,则是贾宝玉在下一回中所吟唱的《紫菱洲歌》。
《紫菱洲歌》当然不及《芙蓉女儿诔》那么回肠荡气,但其声调之凄切,亦已迥异于贾宝玉当日的《四时即事诗》。“抱衾婢至舒金风,倚槛人归落翠花”似的闲情逸志,此刻全然为“蓼花菱叶不胜悲,重露繁霜压纤梗”的苍凉感叹所替代。而且,这种“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菱荷红玉影”的残红飘零刚刚开始,首当其冲的受难者迎春,也不是平日与贾宝玉比较亲密的姐妹如探春者,更何况日后大祸降临到他那日夜牵挂的林妹妹身上,真不知会有怎样一番情景。《紫菱洲歌》在人物韵文系列上的叙事作用颇类于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在小说叙事结构上的方位,只是那回使用的是一叶知秋式的笔法,此诗显示的是一首秋歌揭开一串悲的渐趋递进之手法;只不过从五十八回的起于青萍之末,读者可以看到七十七回的风吹花落:“俏丫环抱屈夭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月”;而从《紫菱洲歌》以后,读者却再也读不到原作者设计的人物韵文了。人们只能就此止步,即便流连绯徊,也只好望洋兴叹。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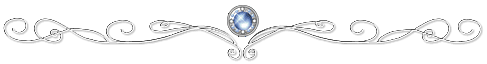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