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小说与荒唐言(1)
|
一个是人生的荒唐感。我说人生感,没说人生观。因为很难说《红楼梦》里头宣传了人生的一种观点,一种理论,一种信仰。但是他有很多的感慨,而且把这个人生感慨写到了极限,写到了极致。这里有人生本身的荒唐,这里我暂时不谈。更重要的是由于小说,他选择了小说这样一个形式,而小说本身就有几分荒唐。
我们不妨讨论一下中国和西洋对“小说”的解释。《辞源》上讲,“小说”最早见于《庄子》。庄子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就是说,小说是些浅薄琐屑的言论。所以庄子说,你用这个小说来说些比较大的事情,那距离太远了。还有一个材料也很好玩,《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为九流十家之末。我们讲三教九流嘛,起码是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那时候也称小说家。小说家是九流之末,不但是臭老九,而且是臭老九里头最低的一种。《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之流,盖出于稗官。”稗官就是小官儿,像稗子一样的,不是稻子,不是谷子,是稗子,稗子苗,它不成材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所谓稗官野史,到后来把它发展成引车卖浆之流。从中国古人的眼光来说,这个小说家是最低的。官儿大了是不能写小说的,写了小说也是不能作大官儿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性,而且是一种城市性,“街谈巷议”,它不是田头,不是村头,也不是河边。
但到了汉朝呢,那个桓谭又说:“小说,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就是说小说虽然是一些稗官野史,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不经之言,但是里边也能牵扯到一个人的修身和齐家,家庭关系呀,孝悌忠信呀,也有“可观之辞”,也有两下子。小说在末流之中,靠自己的贡献吧,引起了社会的一点点重视。清朝罗浮居士写过一本书,叫作《蜃楼志序》,所谓海市蜃楼,他说:“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就是说,它不是“大言”,“一言乎小”。第一是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心诚意,概勿讲焉”,这里不讲经传,不讲正心诚意,不讲治国化民,所以它是小。第二、“一言乎说”,它不是文,它是说,更加口语化的,“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辩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就是那种比较非常文雅的、非常经典的东西,它没有。就是说,它没有特别重大的内容,也没有那种经典性,“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之正宗也……《大雅》犹多隙漏,复何讥于自《郐》以下乎!”意思就是说,它是比较通俗的。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说法。
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另一面的说法。比如梁启超,他就认为小说特别重要,“兴一国之政治者,先兴一国之小说;兴一国之经济者,先兴一国之小说;兴一国之风俗者,先兴一国之小说”。就是不管什么事,先从小说开始,要改革社会,你小说写出理想的社会来;要改革家庭,你写出理想的家庭来;要改革市场,你写出理想的市场来。我们还知道鲁迅的说法,鲁迅说他辍医转文,是为了拯救、疗救所谓国民的灵魂。这些说法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它起码有这一面,就是“小”和“说”。它有一定的边缘性。大概在十几年以前吧,我们有几个评论家,当时就抨击,说现在小说都喜欢写些小东西,写的都是小猫小狗,小男小女,小花小草,小屋小河,小这个小那个。我当时对他们的抨击不太赞成,我就提醒他们说,还有一小,小说,我们要改革这几个“小”呀,首先要把小说改成“大说”,以后不许写小说,写大说,那么一上来就不是小猫小狗,一上来就是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前途,人类的未来。几个评论家的抨击,反映了中国对小说的另一种观念。
那么曹雪芹呢,他选择了写小说。这本身就是荒唐。他不阐述四书五经,不写策论,不写《出师表》,不写《过秦论》,而写什么贾宝玉呀,林黛玉呀,这就是荒唐嘛。因为正经一个大男人读书识字,不好好干大事,你写小说干什么,这就是荒唐。这种荒唐本身就是它所描写的女娲补天无材入选,把这块石头变成一块顽石,被淘汰下来。属于被社会的主流所淘汰的,所搁置的,所闲置的,属于一个废物,无用的,多余的。中国式的所谓多余的人。这是中国人对小说的观念。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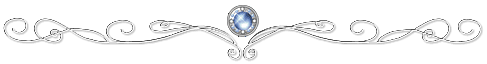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