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多情、同情 、至情(2)
|
目前,同性恋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人权问题,而越出了道德的范畴。在《红楼梦》中,同性恋的表现也因人而异。贾宝玉仍然是一种钟情与尊重的姿态,与他在异性恋中的诚挚相同。甚至“以同性恋行为来表达他对社会的平等博爱思想”,如因与戏子蒋玉涵交往而受到鞭笞。这与别人将同性恋对象视为人格贬低者,完全不同。
可见曹雪芹对同性恋现象已颇具现代观,即是:重在对于双方人格人权的尊重平行愿,在生理上没有什么贵贱之分。同性恋享有与异性恋同等的标准,就是说,不能是强迫的侮辱的单方面的。所以,薛蟠要吃柳湘莲一顿痛打;而宝玉却为了蒋玉函忍受父亲贾政的狠毒鞭笞。
贾宝玉讲“伦理”,是人性化了的伦理,而对非人性化的伦理则一律排斥。对贾政等以父权身份强加于他的封建科举,宝玉一贯阳奉阴违,或攻击否定。贾雨村之流所谓“经济仕途”中的雅客,为他所不耐烦相见。
而戏子琪官儿,他却可以结为知音。连乡村一个灵巧的二丫头,亦令他回首留恋。从媒人口里闻知的,未见过面的“傅家妹子”亦令他爱惜有加。刘老老瞎编的“抽柴禾”的女孩,亦令他记挂,盘问。
书中宝玉与诸女性的关系,各有隐情,而作者所推崇与赞赏的,是他与黛玉那种互视为知己的,默契如神、相共生死的爱情。
而恰恰是黛玉与晴雯这两个最富灵慧美质的女性,宝玉独没有与她们有任何的床弟关系和产生性逗挑的迷惑。宝玉与黛玉、晴雯间演绎的这种异性爱,正是作者所追求的情天情海的最高境界,也是以通灵玉为灵魂的这个人物的最本性的追求。
如果说其他各种尘缘不过是顽石之壳,或石上之灰土,那么这种至性的追求,正是顽石内中的美玉。
贾宝玉在人世上所受到的臧否,常常会令人想到中国春秋《左传》故事里的“和氏璧”。
一个叫和氏的人,怀揣价值连城的璞玉,却不被人识,而反被诬为有欺君之罪,祸及截肢酷刑。然他持其璞,终不悔。经历改朝换代,终于遇上识货的人,终于从这璞中分剖出一块价值连城的晶莹美玉。从此“和氏璧”成为镇国之宝。
贾宝玉所具有的诸多为众人否定的异质行为,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情愫,就象是这块和氏所怀的美玉,外面有顽石尘土所作的包裹;而作者蕴藏于他身上的那种高超于世的思想与理想,就象包在顽石之内不为人所识的和氏璧。
联想到《红楼梦》这本书在社会上曾经几禁几开,既使“洛阳纸贵”,又屡遭铲除。联想到在那个时代里,李贽一类启蒙思想家所受到的异端诘难,排斥诬蔑,就会完全理解了书中对贾宝玉的批诗:“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那完全是一种自嘲啊。
然而,书中又借林黛玉谈禅机说出:“至坚者宝,至贵者玉。尔有何坚?尔有何贵?”
面对如此强大系统的封建压力,宝玉是坚者,坚若顽石,绝不倒退和妥协,亦无怨无悔。他“空对着,山路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而面对众多被压迫被摆布的女性,宝玉是可贵的知音与救星,具有精神上的通灵之妙。
将宝玉比为顽石,比为美玉,皆是对他这种品格与不屈服的人性思想之赞美。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珠与玉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是被人格化与人间化的。
石头化为了扇坠大小的一块美玉。玉又重新还原成一方大顽石。这里面蕴含着中国的“玉文化”。
看书中,通灵玉昏蒙,则宝玉亦昏蒙病倒,玉晶莹,则宝玉清醒病愈。看似奇诡杜撰,其实,这也源自中国的玉文化。中国自来有“玉能养身辟邪”之说。也有“玉饰能随所佩者气色变化”一说。
黛玉其实也归在了玉之列。在宝玉初会林妹妹时就引过西方有石名黛可画眉之典。中国人说黄金有价玉无价。故黛玉在“葬花诗”中有“质本洁来还洁去”这一说。她也是一块自然干净的石头。
中国文化中,对“石”是独有情结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出生于石,原生时就叫石猴,这是本真的名字。“悟空”是唐僧救他收徒之后,为之取的法名。
这倒有点像《红楼梦》中的宝玉,原来是混混茫茫中的一个天然生命,进入红尘世界,接受红尘制约,后来又悟而出家为“情僧”。故《红楼梦》又名《情僧录》。
《水浒》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也是起源于“石”。一块石碣被人揭起,因而放出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是天上星宿,出来演绎故事。
今宝玉由石转世,变成一位衔玉而生的公子,最后则复归青梗峰下,还原为一块镌了字的顽石。
《红楼梦》一书中扑朔迷离的笔法,以贾宝玉这个形象为最典型。这是一个在艺术上最纯粹,在个性上最真实,而在来龙去脉上又最富于幻想力的,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
贾宝玉既是大观园中的贵公子,又是大荒山上的顽石;既是多情有染的血肉之躯,又有一颗虔诚坚贞的至爱之心;既是一个来完成尘缘的混世魔王,又是一位清醒伤感,记叙往事的石兄;既是被作者调笑嘲弄的书中痴人,又是作者自己在俗世上的代言人。
如果我们再细一点推敲,《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空灵”,写大荒山下那块石头、石头被渺渺真人化为的美玉,这二者与宝玉其人是交叉的关系,而并非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因真人大士们要送一批冤家下凡历劫,那绛珠草与神瑛侍者都在案中,这石头是夹带进去的。
也就是说,宝玉的前身是赤霞宫神瑛侍者,石头也好宝玉也好,都是被命运安排夹带下凡的。石头的使命主要是纪录。而生活情感阅历则由神瑛侍者所创造。
这种写法,这种通过神话仙境不断转换的角度,在文学史上也是举世无双的。而又能够达到读者的理解和勾起更加浓郁的兴趣。
它不会因为转换的无稽,引起混乱,而抛下读这本书的念头,反而因为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线索,产生“剪不断理还乱”的二百年《红楼梦》情结。这是中国文学中情、理、哲、诗合一的美学风格的一个旷世创造。
《红楼梦》所创造的成功之丰碑,不是一块人为的花岗石,而是一条滚滚不尽的东逝春水,流淌在世世代代、年年月月的中国人心坎,滋润中国人古往今来的感情花园,灌溉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爱恨情仇之花蕊。
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虽在当代经历“浩劫”,但《红楼梦》还在;石头城不在了,石兄尤在,纪录的故事在,文化与人性就在。这是曹雪芹与宝玉的珠联璧合。
《红楼梦》所留下的,决不仅止是那一片“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与“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的个人世界,这是一个博大的感知的世界。
贾宝玉也决不是一般花花公子的代名词,而是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在数千年封建压抑之下,人性情感之大海不仅没有为之干枯,反而更加深沉和丰富,细腻与生动。
贾宝玉展示了我们这个严肃的民族多情的一面,那一块通灵玉,那一个与天地同在的补天遗石,乃是人性不灭的象征。
石兄在,则人性在,则大观园在。
因而,我们仍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懂得感情价值,女性风采与命运,人生无常,人如草木,终当复归自然等至高知性与知识的民族;因为有《红楼梦》,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懂得享受文明之美,珍视缘份,善待人生的文明之族;是世界上民族之林中的智者与善者。
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出现在具有数千年“男尊女卑”传统的东方中国,是一个奇迹,故书中亦称其为“异端”。西方十九世纪骑士精神曾经风靡一时。但那其实仍是以女性为筹码,为装点男性胜利的花瓶。而贾宝玉对女性的充分肯定和理解,维护,则站在一个更为平等博爱的人性的高度。
呜呼!世有解语之人,遂有浮生之叹。人生如梦,此梦强如他梦。愿为此梦,勿复为别梦。
中国传统小说所创造出的艺术,决不只是那种“依着葫芦画瓢”照相式的做法。我们何苦临渊空羡,生硬模仿外国《尤利西斯》之流的新颖别致,何不退而结网,将这《红楼梦》重读深思?
在中国,有多少文人一生梦想着自己也写出一部《红楼梦》式的书来。
吾父亦早嘱咐于我:可从《红楼梦》中学习艺术。但我一直在犯古人“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则惘”之训戒。读时贪图美受,不复深思,偶有所思,又无暇复读。终为竖子也。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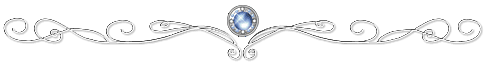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