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性文化
|
有人把《红楼梦》当作才子佳人的小说来欣赏。
但如果稍微涉猎一下古代小说,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涉及“性”的艺术都或多或少是“反儒”的。当然,现在大家可以自由批评儒家的观点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清楚的,正是这或明或暗的关于“性”的描写击中了儒家的“要害”。
首先,早期儒学,对此还不是特别敏感。例如孟子说“食色性也”。我们知道,孟子他老人家是主张要适“性”的。这就是说,孟子在高谈阔论之后,往往情不自禁地会淫荡地一瞥。
孔子循规蹈矩,从来也没有滔滔不绝。孔子承认,他的学说不如这个问题有吸引力:可悲啊!道德!大脑失败于没有廉耻的器官。这就是人类!
当然我们不必进一步引申了。否则我们就会悲哀地发现,按照儒学,人类全部的理智力量居然如此可悲:“人”被置于“动物”的水平。
佛教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怀疑论的态度。佛教认为万物都是“空”。所以你没有必要思考,同样也没有必要勃起。“如梦亦如露,应作如是观”。看看就得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释迦牟尼如是说。
道家历来比较洒脱。你喜欢吗?好吧,尽力去做。道士甚至练了很多“灵丹妙药”帮助人们获得这个方面的“感受”。至于服药的人是不是因此送命,这就和道士没有关系了。反正人是要死的,不同的死法不会使问题有所不同。
相反倒是皇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显得简洁得多。皇帝统共就是那么一刀。这样一来困扰孔子几千年的“德”“色”之争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
由于皇帝属于文盲一类,我们不准备就之多做评论。这里只是注意到,我们聪明的古人是如何在这个问题上给儒家造成了大量的“可爱”的麻烦。当然,准确地说,不是孔子、孟子那个时代的儒家,而是宋明的“理学”。
应该看到,“理学”在对待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前辈要好。“理学”既不如孟子那样顺其自然,也不如孔子那样豁达大度。在这个方面,“理学”似乎和皇帝的作法有些相似。皇帝就是那么一刀;理学也是那么一刀。皇帝的刀斩在器官实体之上;而理学的刀斩在意识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气”上。理学高喊“存天理、灭人欲”。然后就出现了大量的这样或者那样的小说来和它唱反调。
所以我们这些后人还是要谢谢理学。如果不是他们这些理学家这么折腾,这些描写古代风俗文化,文笔隽永的文章就不会和我们见面了。如果理学把它的反对面扩大一千倍,它干脆就反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我们的享受可能就会更加丰富了。
例如《肉蒲团》这本小说的确是一部典型的作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的用意何在。如同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一样,在作品中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的世界,肉欲的世界;另一个则是精神的世界,理的世界。贯穿着两个世界的核心人物即所谓“未央生”。
在前一个世界中,未央生处于主动的地位,书中作者甚至把他比做儒学中的老师。而在后一个世界中,未央生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是老和尚的徒弟。
我们看到,未央生在这两个世界中的遭遇形成如此鲜明的反差:
1.在前者是未央生给淫妇磕头;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给老和尚磕头。偏偏老和尚在这个时候又“入定”去了,以至于未央生磕的头未必比给淫妇磕的少。
2.在前者,未央生入的是肉口袋;而在后者则是布口袋。老和尚偏偏就叫做什么“布袋和尚”,还要把世人尽皆装入口袋。而未央生也的确是头顶着布袋去见和尚。特别是考虑到未央生后来也出家落发,这种情况就更加显得是岂有此理了。最后还必须注意到,和尚的布口袋挂在树上,历经数年,不见腐朽,反而“硬挣”,这就更加令人怀疑这是有“生命力”的东西了。
3.如果把荡妇和和尚加以对比,这当然不能说是出于对和尚的尊敬。然而佛教对此似乎无所谓。佛教认为,只要能够使人超脱苦海,佛教徒理应遭受一切苦难。据说就有黄金锁子甲观音化为娼妓普渡众生的故事。无论如何,佛教徒的慈悲胸怀,放弃“小我”,献身“大我”的精神是可贵的。
4.这样一来,问题的矛头就指向儒家,特别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了。这些先生们不是很道学的吗?可是我们看到了,未央生和他的娼妇之间的关系,正是最标准的儒家老师与门生的关系。如果大家比较仔细地体会一下理学的要义,就会承认作者在《肉蒲团》中所做的描写一点也不过分。既然理学鼓吹“灭人欲”,又不是像和尚们一样,光明正大地出家,脱离尘世,其结果的确和纵欲的道家没有什么分别。而且我们也知道,道家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房中术”也的确是在理学昌盛的明代大行其道。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们,究竟与娼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5.不妨看一看未央生在两个世界的遭遇。在前一个世界中,未央生有妻子、有朋友、有地位也有情人。用法国人的观点来衡量,这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人生。但是未央生的美梦被一个“老实”人完全破坏了。未央生寻欢作乐完全出于享受的目的;而老实人不求享受,他只追求报复。按照贾宝玉“爱物”的观点,未央生是个才子,而权老实则是个虐待狂。
理学不仅训练出权老实这样的人物来破坏未央生的幸福生活,理学思想同样毒害着未央生本人。未央生正是因为遭到了权老实的损害,骤然之间痛心疾首,心灰意冷,完全听凭理学的摆布,不仅出了家,而且按照皇帝的要求自行了断。这就是说,至少在前一种情况下,未央生还是一个完人,而后来则成了残废。
当然,这里不是在讨伐“理学”。理学的产生还是多少有一些进步意义。例如“存天理、灭人欲”,这也可以是限制皇权的一条依据。本来是要约束皇权,但很容易被皇帝拿来作为针对士大夫集团的精神武器。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聪明的古人打破理学的藩篱,谋求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可以说,中国古典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反对儒家思想的,尽管所站的立场并不相同。但是这些反对儒家文化的小说,在与官方哲学做斗争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性文化”这个阵地进行攻击。的确,这个问题始终是儒学的绝症。不论儒家学者如何鼓吹他们学说的优越性,但是这些家伙就是摆不平那件事物。甚至孔子的学生也认为孔子在见了南子的时候,那面“大旗”竖立起来。急得老先生赌咒发誓,我如果举了那面旗帜,则“天厌之”。
于是后来有的学者对老先生的誓言嗤之以鼻:你老先生就是举了旗子,又能怎么样呢?什么叫做“天厌之”呢?你哪怕说“天雷击之”或者都更加可靠一些。
我们当然不能说甚至《水浒》也是性文化小说,但没有人否认《水浒》在这个方面所获得的经典式的成功。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当时的官方哲学,理学,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反对意见:
*按照“存天理”的提法,我们看到,结果“天理”被破坏得荡然无存。可以说,所有的规矩都被《水浒》好汉破坏了。而且我们还不得不说,破坏得好。我们接受毛主席的教导,反对反动的思想制度是个大进步。
*而“灭人欲”呢?“人欲”被压抑之后,代替“人欲”就是不折不扣的“兽欲”。
这样,我们就从两个方面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理学所提倡的就是人类文明的毁灭,就是把人的标准降低到动物的标准。
从这个角度说,那个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的水平实在是在文学家之下。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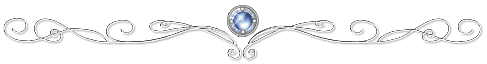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