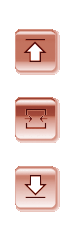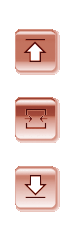|
|
|
|
第三章 陇东高原(一)
|
一清早,旅司令部举行干部会议。会上,旅首长讲了:要进行新战役。王成德、周大勇开罢会,回到连队的时候,太阳挂在西边山线上。
他俩把在旅部开会时光记的笔记,翻来翻去捉摸了好一阵,便让文书用四张大麻纸,把陕北敌人兵力分布的情况画了张简单的图,准备本连队开战斗动员会议时候使用。
参加会议的支部委员、党小组组长和班排干部都来了。他们都变得更英俊了:服装整齐,脸膛儿光彩;腰里的皮带和腿上的绑带都扎得很正规。
王成德说:“同志们,要打仗了!”他声音很低,说得很平常。
可是,这句话像吸铁石一样,一下子把战士们的情绪、眼光和注意力都紧紧地吸住了。战士们的脸膛更加豁亮生动了,一双双黑嘟辘辘的眼睛,闪着严肃、热情的光。眨眼间,每一个人心里也闪动着各种情绪和想法。王老虎脊背靠墙站着。他瞅着自己嘴边的小烟锅,像是“要打仗了!”这句话他根本没听到。其实,他不光是听到了,而且心里的想法比别人并不少。蟠龙镇战斗,他第一个登上积玉峁,成了陕甘宁边区出名的英雄。真武洞五万多人的祝捷大会上,他跟周恩来同志、彭副总司令肩靠肩坐在主席台上;还被选入主席团。当一名大英雄那是闹着玩的吗?要功上加功呀。可是在这回部队行动中立什么功呢?他想到巩固部队,想到要求最艰苦的任务,还想到自己班里有人打仗胆儿小、行军时脚上常常起泡……嗨嗨,该有多少事情啊!马全有呢,一听“要打仗了”就*#踥/oo地冲起一站,心里轰地冒起一股火。他觉着,要打仗马上就走,走到就打。打的时候最好拚刺刀;再迟一分钟心都会炸!再说,下次战役中他要捉十个俘虏--这计划是自己向党支部提出并保证要完成的,说话要算数。李江国呢,他是急着想表决心;想挑战,还偏偏要和马长胜这老牛筋挑战。马长胜扭着脖子噘起嘴,脸色黑煞煞的;谁也不看,眼珠子固执地盯着自己的脸膛。他窝了满肚子的气,想跟人吵架。他生谁的气?生自己的气。瞧瞧,要打仗了,可是自己班里有个闹病的,而那个战士闹病是因为自己关心不够。只有老炊事班长孙全厚的样子出奇,打指导员一开口说话的时光,他就咧开嘴,喜眉笑眼的像有满心眼的高兴。因为蟠龙镇战斗中,他搞到敌人的两口行军锅,又轻又大。从今向后,到哪里再不必向人央告着借锅啦!管它什么战役,就是走到天边上,炊事班先不发愁--有口锅,不论是稠的稀的,总能让同志们吃上口热的。
王成德说:“同志们,看,敌人整个架势就是这样:胡宗南的主力队伍从绥德城窜回来以后,就在这延安附近摆着!”他的手指移到地图上延安老西边的地方,说:“这是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分区。青海马步芳的一百旅……还有宁夏马家匪徒的八十一师……占着我们陇东分区。”他念了很多地名和番号。接着他又指着陕西西北角靠长城边的地方说:“这是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分区。宁夏马鸿逵匪徒有五六个团的兵力占着我们这块地方。”他的手指在陇东分区和三边分区画了个大圈子,又说:“三月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宁夏和青海的马家匪徒,趁我们跟胡宗南打得抽不出手来,就出兵占了我们这两个分区。这多时,他们在这一带'清剿'哩,杀人放火,老百姓苦得撑不住!同志们,敌人阵势就是这样。咱们大家先合计一番,看下次战役怎么打。”马全有说:“先不管他什么马家匪徒,那是篮子里的菜,迟早会收拾他的。我们先集中力量打胡宗南匪徒。”
六班班长说:“就是嘛,擒贼先擒王,搞掉胡宗南再说。”李江国把人豁开朝前走了一步,说:“算啦,同志们!打仗是凭自己的意愿?仗怎么打是要根据敌情来决定。我们对敌人的活动跟打算两眼墨黑,这样讨论到牛年马年也是白搭!”
王成德说:“还是旧话,蒋介石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他要胡宗南赶快结束陕北战争,然后把兵力抽出来,送到别的战场上去。”
马长胜闷声闷气,像坐在瓮里说话:“他来得容易,想走,可不能那么简单!让胡宗南试试看!”
周大勇插上说:“是呀,敌人知道不消灭我们的军队,我们就要砸碎他的锅。这么,敌人就有个消灭我们的阴谋。”李江国说:“什么阴谋不阴谋,他们那一套,我们见过。
胡宗南肚子里没货,是个草包!”
王成德把那幅四张麻纸的大地图,往墙上一挂,说:“延安以南是咱们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胡宗南要他关中分区的队伍向北进攻,要陇东分区的马家匪徒向东攻,配合延安地区胡匪主力把我们围在这安塞地区消灭。瞧,敌人这盘算打得多带劲呀!”
一排排长说:“胡宗南的部队死挤成一团,我们目下还啃不动。现在先收拾马家这些狗杂种,教敌人'合围'不成。”
周大勇说:“对呀。敌人想让他们的几股子部队分头猛进,在这里围歼我们。可是我们不等他动,就先打他个头昏眼花。
这样:第一,打碎了敌人的'合围'计划;第二;不等敌人拧到一块,我们就把他零敲碎打了。”一个班长说:“打这儿向西到陇东地区,要走三四百里,还要穿过大森林;要是再去三边分区,还得过沙漠呀!这也得估划估划。”
马全有说:“不要说翻大山钻梢林过沙漠,党中央让我们到天边上去帮助劳动人民翻身,我们也不怕;要怕,还叫什么共产党员!”
李江国说:“钻梢林过沙漠那唬不住人,可我也不同意到什么陇东分区和三边分区去。咱们先把胡宗南收拾光让党中央和毛主席回到延安再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回不到延安,我们心里难受!”
周大勇说:“我们在延安周围打运动战就行,运动到远处就不行!同志们,这算什么军事思想?”
王成德说:“如果上级决定去陇东分区作战呢?”
马长胜说:“那就坚决执行呗!”
窑洞里挺闷气,没人说话没人吱声。王成德用拳头撑住下巴,忽眨着眼。
周大勇双手撑在腰里,望望这个瞅瞅那个。他躁气了,说:
“同志们,你们怎么连一点道理都闹不通!我们不能光看到陕北和延安,我们还要朝全国看,要有战略头脑呀!”
周大勇讲罢,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嘟嘟哝哝地在议论。这工夫,王老虎悄悄地蹲在墙角,思量什么。像是,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人家不注意他。
李江国喊:“老虎,说话呀!三个人里头有诸葛亮,大伙一讨论,就把这理弄明白了。说话呀,老虎!”
王老虎磨磨蹭蹭站起来,低着头,用脚轻轻踢地下的石头子,说:“要是上级决定进行陇东战役,我们就舍命地去执行;要是上级还没决定,让大伙出主意、讨论,那……延安多会才能收复?……同志们,我也拿不定主意啊!”他不自在地微微一笑,又眯缝着眼睛,想算着什么。
王成德说:“同志们!上级决定要进行陇东战役。我们向陇东分区进军去打马家匪徒。眼下看,我们是把西北战场最主要的敌人胡宗南放下了,实在呢,我们是把他箝制得更紧了。因为,敌人怕我们从陇东地区插出去,戳到他们后方去。所以,我们一动,胡宗南一定跟上我们转……再说,我们用零敲碎打的办法,把胡宗南的帮凶一个一个地敲掉,那胡宗南就孤立了,就好打了。说到敌人还占着我们延安,这不要紧,反正敌人要的是地方,我们要的是胜利。……”散了会,王成德坐在门坎上,双手捧住头,心里火热毛辣的。周大勇朝墙站着,用拳头咚咚地捶打墙壁。突然,他转过身,说:“今天的战斗动员会,就没开出个名堂!真他妈的窝囊,什么工作都不能干得称心如意,老是疙里疙瘩的!老王!咱们再召集支委会,从头重来!我就不信世界上还有作不好的事情!”
第一连开罢第一次战斗动员会的第三天--五月二十一日夜里,风不吹草不动,一轮明月挂在天空,照得山沟如同白昼。
安塞县真武洞前后左右的山沟、河槽里,挤满了马上要出动的西北野战军的部队。战士们集合在川道里,除了轻微的咳嗽声以外,什么声响也听不见。河槽里驮山炮的骡子,一排一排站着,都不叫唤。它们也像是懂得,现在需要特别肃静。
部队临出发的时光,王成德接到上级的命令:跟团政治处的几位干部一块到黄河边去带训练好的新兵,补充部队。周大勇说:“老王,我说指导员跟连长的工作没有好大分别,你还强辩。瞧!现在不是连长跟指导员的工作都搁在我肩上了吗?”
王成德说:“喊什么冤!我不用几天工夫就回来了。”
部队出发了,像往常一样,开头走动的时候好拥挤哟!战士、担架队的老乡们,战马,驮炮骡子……南来的北往的,插过来穿过去,像是乱踏踏的没有次序。直到部队走出十来里路,那就利索了:这一路在这一条沟,那一路在那一条沟,一道道的人流,从不同的道路上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地流去。天亮了,部队行列里红火了,荒山冷沟也变得热闹而有生气了。沿部队行列,每隔五六百公尺就有一个师政治部或团政治处的宣传员,拉开嗓子给战士们讲新战役的意义跟行军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山坡上,路旁边,每隔三五十步就贴着一张鼓动战士们行军的标语或图画。战士们上大山的时候,就能听到宣传员在山顶敲锣打鼓,用喊话筒呼喊:“上一山又一山,我们是铁腿英雄汉……”各连队的行列里更热闹:有的战士说书、讲笑话,有的说快板,有的唱民歌小调。
晌午,部队进入到一条大川道里。
周大勇走在第一连行列前头。他朝前看,前边是伸到远方的部队行列。朝后看,后边是望不见尾的队伍。路随山转,部队行列也弯弯曲曲地向前流去。他觉着,他是这人流中的一滴水,是这伟大组织的一个细胞。他要离开这个整体,他的生命就完结了。这许许多多的人,大半他都认不得,可是他们的欢乐、难过,就是他的欢乐、难过;他们是他的同志、亲人。他又觉得,部队行列像个大链子,自己的连队,只不过是这链子当中的一个小环子,可也是不能少的一个环子。这许多环子中的一个环子是不是结实,那就看自己的工作了。他觉得责任的担子沉重,而工作又做得不够强,心里着急、惭愧。可是他返转寻思,往上数有营长教导员,团、旅首长……往下数有排长、班长和战士,只要自己在这严密的组织中,努力向前,那么,自己就有学不完的东西,说不尽的快乐。他猛地抬头一看,前边部队已经伸入黑山森林里去了。二
战士们经过了一夜又两天的行军。一天,太阳快压山的时候,部队在没有人烟的森林里宿营了。
战士们依着一棵棵的大树,用树枝搭起了准备睡觉的小棚子。炊事班烧火做饭了,一股一股的烟,冒出森林伸展到天空。西边天上的红彩霞,把树梢抹成了红的。树上有各种鸟雀叫唤,像是比赛唱歌。黄刺玫花,散放着香味。遍地都是叫不起名字的小花,有的红艳艳,有的黄登登,有的蓝灿灿,有的红彤彤,实在是美。
沟渠里,炮兵们在饮牲口。有的炮兵战士脱光衣服,在沟里的小水流里洗澡、唱歌;有些个战士绕树干追赶着闹着玩。一个骑兵通讯员背着手顺山坡朝上走,马跟在他后边。他蹲下,马就站住,他跑,马就跟上跑。他吹起口哨,那马的头就一摆一摆,有节奏地踏着蹄子,像是对它的主人表演什么。他猛地往地下一扑,说:“卧倒!”那马也就卧倒;他的头靠着马头,手还比画着,像是对那匹精灵的马,说什么蛮有味道的事情。
森林中,到处是战士们欢乐的笑声;到处是雄壮的歌声: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警卫员们,给团首长用树枝在一棵大树下搭起一个棚子。这棚子比战士们的棚子阔气多啦:三面还用被单遮着。团参谋长卫毅,盘着腿坐在团首长住的棚子里,跟他弟弟卫刚谈话。
卫毅摸摸自己的左腿,那左腿膝盖下边的伤口还没痊愈。他说:“羊马河战斗中我负伤以后,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一个月。现在总算赶上了部队!往后,我负了伤,愿意坐上担架在前方转,可千万再不去医院压床铺了。躺在床上老是惦记部队,心像油煎!这一回来,碰巧赶上打仗,我可真有这份福气!卫刚,怎么着,你连队工作搞得很起劲吗?你还是冒冒腾腾地凭一股子热情办事?”
卫刚把手里的一根小树枝折来折去,赌气地说:“我只有一股蛮劲,再没别的能耐。工作也只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
卫毅亲热地望着他的弟弟,他打心眼里喜欢他。他觉得他太年青,得到的表扬已经太多;经不起表扬的人,并不是没有的。他说:“只有一股蛮劲还行?听说,你不想作政治工作而想作什么'单纯的军事工作'。奇怪啊!”
卫刚觉得他哥误会了他的意思,蛮抱屈地说:“我是说,不想作指导员,想作个指挥员,比方,当个排长也行。”
卫毅说:“这想法并不坏呀,可是为什么不想当指导员?
太麻烦,是不是?”
卫刚用树枝在腿上轻轻地敲打着,不吱声,像是有满肚子牢骚似的。
卫毅从马褡子里抽出几本书,说:“这几本书,是我在山西给你买的。你再忙,学习总是不能放松。”
卫刚把书往胳肢窝下一夹,站起来就准备走。
卫毅问:“就走吗?”
“我还有工作。”
“你还需要什?”
卫刚一脚踏出了棚子,说:“什么也不需要!”
卫毅走出棚子,赶上了卫刚,跟他并肩走着。他问:“你怎么啦?”
卫刚憋了两三分钟才说:“你对我的看法不全面!”
卫毅笑了,望着数不清的参天大树,说:“卫刚,让我怎么说哪?战斗中,我看见你把战士们带上去了,平素看到你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我就比别人更高兴。可是你为什么做出芝麻大点的事情,就要让人看见呢?这不好啊!看看我们的战士,他们都是些朴实稳厚的人,完成惊天动地的业绩,也不作声。卫刚,你我不论作出多大的功绩,也不需要向人显示,因为那是我们本分以内的。”他双臂帮在胸前,凝视着树上归窠的鸟雀,思量了一阵,又说:“我常想,就算我单枪匹马消灭了上万的敌人,立了大功。但是这比起党教养我的苦辛来,比起共产主义事业来,又算得什么?卫刚,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这说法还有错?”卫刚的声音平和了。
卫刚迈大步走开以后,卫毅还双手撑在腰里,在原地站立了好一阵。他回想着他的弟弟,微微耸动肩膀,自言自语地说:“还太年青啊!”
团政治委员李诚,从下面山坡上走上来。他一走近棚子,就看见卫毅找来几个刚从连队上回来的参谋,汇报今天行军中的各种情况。他想:“卫毅的腿真快!半点钟以前我还看见他在二营,转眼他又回到团部来了。”
李诚看见棚子很小,里边挤得人太多,就蹲在一棵大树下。
卫毅看见政治委员,他轻轻耸了一下肩膀,微微一笑。李政委也随便地扬起手向他打招呼。
团政治委员李诚,高个儿,脸有点瘦。不论谁一见他,就觉得他那肌肉并不丰满的身体里,像是储藏着使用不尽的精力。
李诚翻开放在膝盖上的小日记本,边看边思量。
部队今年三月临过黄河的时光,他就跟旅政治委员到晋绥军区分“建军会议”去了。他离开部队三个来月,觉得自己对部队情况有点生疏。因此,他回来的这五天工夫,成天在各营、连跟干部、战士谈话。他要具体掌握部队情况,特别是思想情况。
他反复分析了他了解到的各种情况,看到,随着战争的发展,政治工作者面前摆下了繁重的任务。不错,那种勇往直前、信心百倍的战斗精神,非常旺盛。但是,现在斗争特别艰苦: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大兵团作战,没有房子住;粮食少,战士们常是饥一顿饱一顿;长途行军,整天翻山过岭;特别是,战斗残酷、复杂而又频繁。因此,那些软弱的东西也就暴露出来了!李诚想起团党委会讨论过的几个人。这些人的错误思想,虽然表现为各种式样,但是归结起来就是:向困难低头,畏缩不前。他站起来望着身旁什么地方,望了好一阵,然后,把右拳提到胸前向下击着,独自说:“要朝这些坏思想开火!哪怕这坏思想是一星星一点点,也要肃清它,彻底肃清它!”
李诚的举动显出:紧张的战斗生活,不光把人平时举止态度上的细节磨掉了,就连人那些迟缓柔弱、犹豫不定的脾性也磨掉了。它让人作风雷厉风行,性情果敢爽直。
李诚穿过灌木林,走到团政治处的宿营地旁边。
政治处的电话机就安在一棵大树下。组织股的一个干事,正在电话上和二营教导员谈工作。另一个干事,在文件箱里翻寻什么材料。一个戴近视眼镜的保卫干事,坐在草地上,把手枪放在两腿中间,正审问一个混入部队的特务。有一个年青人,趴在地下,画着明天鼓动战士们行军的图画。一棵大树旁边的文件箱子上,趴着一个刻小报的油印员。他刻的文章多半是快板、诗歌和“顺口溜”。油印员刻着刻着就把头搁在手背上睡着了。李诚轻手轻脚地走到油印员对面,蹲下去,把钢板、蜡纸和铁笔挪过来,帮油印员刻了一小段,又摇着头独自说:“我当宣传员的时候也刻过钢板,可是我刻写的技术比这小鬼差远啦!”他亲切地望着油印员那孩子式的脸颊,那脸颊被太阳晒得起了一些白色而透明的簿皮。
李诚朝一棵大树跟前走去。那里团政治处杨主任,召集了十来个干部正在开会。
团政治处的那些干部,都是每天行军时候,杨主任派到各个连队上去的。他们和战士们一道行军,帮助连队工作,了解战士们的思想情绪等。每天,部队宿营后,他们就回到团政治处,给团政治委员和政治主任汇报了解到的各种情况。李诚对这种“汇报会议”很关心,每队都去参加。
宣教股长汇报。他讲,第六连创造了一种行军中鼓励战士情绪的新方法。
杨主任把本本上记的话看了看,说:“高股长,像你这样深入连队了解问题,可就丰富了咱们政治处的工作。同志们,加油干哪!有了你们这些人深入连队,就有了很多看不见的线把团党委和战士们连接起来了!”他抬起头,看见李诚站在自己身边。又说:“政委!你来迟了一步,没听上高股长的汇报!”
“妙哇!把团党委和战士们连接起来了!”李诚边想边对高股长说:“你再讲一遍!”
李诚垂着两手,头微微低着,望着旁边什么地方。听了好一阵,他说:“杨主任!让高股长和二营教导员一道到六连,把这种新方法再从头到尾了解一番。经过仔细研究以后,真正证明它是有效的方法,那就请二营教导员到一、三营去作一次报告,让大家都学习这种方法。”
杨主任说:“着啊,这样做稳当些。”接着又有一个宣传干事汇报。他的脸膛看来又俊秀又聪明。他拿出个小本子看着,说:“杨主任,我了解第五连的情形是这样的:战士们非常疲劳,他们情绪都不太高,有一两个班排干部也愁眉苦脸……”李诚瞅了那个宣传干事一眼,问:“什么原因?”
“不知道。……他们的指导员看起来办法也不多!”
杨主任问:“你这个代表政治机关去的人,又给他们出了些什么主意呢?”
“我,我也累得喘不过气。我……”“不说你,还谈五连的情况吧!”
“恐怕再没有什么了!”
李诚一字一板地说:“不要说什么'恐怕,恐怕',确实一点说!”
宣传干事慌了,瞧瞧左右坐的几个干事、工作员,像是求援。他说:“我想,大概再没有什么了。……”李诚脸色凝然不动,那千百斤重似的眼光,压在宣传干事身上。他说:“算啦!谁知道你说了一大篇什么!不要你汇报五连情况,先请你弄清,你为什么这样愁眉苦脸呢?”他直盯着那个宣传干事,盯了好一阵,说:“奇怪,热腾腾的连队生活反映在你脑子里,就是这样!照你的说法,战士们日夜行军,艰苦奋战的英雄气概怎么解释呢?你看不见那些病了硬说没病,自己脚磨得出了血,还一样鼓舞别人帮助别人的人吗?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坚强的,有个把子让困难吓倒了的人。对这些人应该做的工作,营团党委已经具体布置了。你最好到五连再住几天,呼吸呼吸战士们的正气。这对你现在有好处,对你将来也有好处。”他向前走了几步,停住脚步,回头望着那个宣传干事,说:“有一次咱们旅政治委员给我谈:'严格地说,如果你在一天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新的感觉,那么你这一天便算过得很糊涂;如果你根本感觉不到那不断涌现的推动自己向上的思想,或者说失掉了对新鲜事物敏锐的感觉,那你的脑筋就快要干枯啦!'我看,这几句话,对你也很有用处。”
断黑,树枝梢上挂满晶亮的星星。森林的空地上,炊事员们烧起一堆堆的火。黑暗中,不时发出哨兵威严的喊声。李诚时而在树林边向站哨的战士询问什么,时而在火堆跟前和炊事员聊天,时而又向教导员或指导员指示什么。
李诚靠一棵树干站着。树上的鸟儿扑噜扑噜扇着翅膀,像是对这森林里突然出现的热闹生活很不习惯。李诚的警卫员站在一棵树下,他很想拣起块石头朝鸟窝扔去,可又怕打扰了李诚的思索。咦!政治委员在想什么哩?兴许他正在谛听这森林晚间是怎样呼吸?其实政治委员正在听着战士们讲话。“事事立功嘛!大伙没意见就给宁金山记一功。”这是班长王老虎的声音。
“梁世德也应该记功。他行军中帮助别人扛枪,宿了营又帮炊事班挑水。……”“不行,梁世德今天行军的工夫,踏了老乡的庄稼苗。这呀,是个了不起的错误。说说,咱们为什么打仗?为了人民利益哪。可踏了老乡庄稼,不就破坏了人民利益?一个革命战士嘛,自个儿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他心里就像锥子扎。可梁世德就没有在大伙面前坦白这件事,这就是阶级觉悟不高呀!”
“不要胡拉被子乱扯毡。有功记功,有过记过,这是两回事呀!”
“说得出奇!怎么是两回事?……”李诚一动也不动地听着、思量着。像他在战斗生活中千百次体验过的一样:战士们说的话中,有很多宝贵的思想。这些思想是闪闪发光的,具体的,仿佛伸手就可以摸到似的。他调查研究,到处看到处听,并思量分析这一切,已经成了习惯。他跟战士们一块生活、呼吸,好像也一分钟不能间断。
他调查研究,便能从日常的生活现象中,领悟到一些重大问题。他到处看到处听,便能从战士们的面容、眼色、笑声、不关紧要的说话当中,锐敏地感觉思想的动静。常有这样的事情:他从一个连部驻的院子门口走过,看见一个战士站在那里发愣。他就到连部对指导员说:第几班某某人,大概有什么样的心思。指导员一研究,果真不错。有时候,他突然在电话上对某营教导员说,哪一连哪一班有个叫什么名字的战士,家里来了封信。信里头说,他母亲病亡,你们要很好地安慰那个战士。接电话的干部听到这些话很奇怪:今天就没见政治委员到营里来呀,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只要有机会,李诚总愿意把铺盖搬到连队上去住。因为他跟战士生活在一块,就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智慧、想法、要求、愿望,向他脑子里流来。这各种向他脑子涌流来的东西是复杂紊乱的,可是这一切很快就在他脑子里起了变化,有了条理。有时候,李诚装了满脑子问题一时抓不住要领,可是干部或战士的某一句话给他提起了头,一切立刻都明确了;事物的内涵或单纯的本质,也都立刻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当儿,他得到别人意想不到的愉快。这种心情,让他工作精力更加充沛。
周大勇从一棵大树边闪过来。李诚问他干什么去?周大勇说,他刚开完支部会,现在去找个战士谈点问题。
李诚问了第一连战斗动员的情形以后,说:“周大勇同志!你光给战士们讲,我们是为自己打仗,一定要完成任务,这还不够。我们的战士,不是普通的士兵,他们都是革命家、军事家。因此,不仅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而且要让他们知道用什么方法取得胜利。这样,他们才有不能摧毁的必胜信心。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只零零碎碎进行了点教育工作,非常不够。周大勇,行军当中,你要利用每一分钟,拿我们实战的例子,简单生动地给战士们讲解我们的作战原则。当然,这件事要做好,还必须全团很好地组织一番学习,但是我们不能等待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才做工作。不能等待,说干就干,不能大干就小干,能干多少先干多少。”
周大勇想起部队出发前,在本连队的战斗动员会上,自己就因为没有想到这些问题使工作走了弯路。李政委刚回到部队,可是他劈头就提出这个问题!
这时光,山坡上爬上来两个战士。他俩,走累了,坐在一棵倒下的树干上,抽着烟,笑哈哈地闲聊。
“我把你父亲来信的事,向连长一报告,连长再向政治委员一报告,那你小子就有好受的了!”
“你成心跟我作对!我又没有捏死你的儿子。政治委员的眼睛多尖!你不多嘴,保不定他啥时候也会知道。真个的,咱们俩感情挺好,包庇点!”他咕咕咕地笑了。
“别怕!我不给你公开宣传就对了。不过,说公道话,你这愣小子,可也就太叫人恼火!”
“如今这翻身农民,说话可就气粗!我父亲那封信末尾还写着:'儿呀,白日盼,夜里盼,半年盼不来你一个字。你不给家里写信,我就要写信批评你们的政治委员。他是干什么的?他怎样指引我的儿子……'我心里直扑腾,他老人家要真的……”黑暗中有人插话:“牛子才,你父亲说得很对。他应当批评我,他有权利批评我。”
嗬!政治委员的声音。天晓得,悄悄话让他给听见了!两个战士像让火烧了脚后跟一样,一蹦跳起来,立正站着,又吃惊又好笑。
李诚问:“你好久没有给家里写信了?”
牛子才嘴里像憋满东西,乞乞吭吭地说:“从过黄河……
过黄河……到如今,一个字也……”李诚说:“来,来,坐下!”
两个战士坐在政治委员旁边。周大勇,站在他们对面。
李诚说:“周大勇,你也坐下听听。凑巧,这不近情理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连队。”他侧过脸问牛子才:“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理由大致是战斗频繁,行军紧张,忙!你说说?”
牛子才摸摸枪,肩膀动动,像是蚊子钻到衬衣里,浑身痒痒又不好去搔。
李诚说:“你家里是翻身户,想来过去你父亲不是长工便是贫农。”
牛子才说:“我父亲揽过多半辈子长工,土地改革当中,我家分到十九亩三分地。”
李诚望着树梢的星星,手轻轻地拍着膝盖,说:“劳动人民屎一把尿一把,从贫困生活里把自己的子女拉扯成人。战争来了,他们又把子女送到自己军队里。为了他们养育了那些英雄的子女,中国人民世世代代都会感激他们的。这样的人--用自己的肩胛扛着人民解放事业的人,谁会有一时一刻忘记他们?更不要说他们的亲生骨肉啦!你父亲在信里对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表示不满。我听了,心里不是股滋味……嗬嗬,我还是一个政治委员,鬼才晓得!”他望树边站的周大勇,问:“你说哩?”
周大勇含含糊糊地说:“我们也要负责!”他心里直嘀咕,提防着。他觉得政治委员总在转弯抹角把批评重点向他身上移。
李诚说:“我们把事情办糟了,就拍胸膛喊:我负责。负什么责?碰鬼,一句空话!”他转过身又问牛子才:“你不写信,你家里人埋怨谁?埋怨共产党。注意,同志!就连这些私人的小事情,也关联到我们党的威望和事业!这些重大问题你都没有好好想过。是这样吗?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讲哇。”
停了好一阵,他站起来又说:“作事不近情理的人,就不是很好的革命战士。牛子才,明天一宿营,你就给你家里写封信。
记住!”
两个战士走开以后,李诚跟周大勇在树林里散步似地转游。李诚抽的烟卷,一闪一闪发亮。风刮树叶嘶啦啦价响。空气中,飘着山间野花的香味。一群一群的雁鸣叫着飞过天空。李诚说:“这里实在好啊!将来仗打完了,说不定我们还会来这里搞建设。那时候,也许还能看到我们现在搭的这些小棚子。”
周大勇有口无心地说:“是嘛!”其实鸟叫也好花香也好,将来到这里搞建设也好,他都无心去注意。牛子才那封信的事,又把他单纯的心境搅乱了。什么鬼把心窍迷啦?自己成天跟战士们一块滚,有些问题硬是看不见。李政委一来,那些自己看不见的问题又偏偏跳出来露丑!周大勇那颗年青而要强的心,让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攫住在审问。
李诚感觉到周大勇的心情了。他说:“你还在想牛子才的家信?很恼火吗?嗬,同志!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要像父母亲一样爱护、关心战士。这样,万千劳动人民的父母,把子女交给我们带领,才会放心。看来,牛子才家里来信的事,你根本不知道。”
周大勇秉着他爽直的性情承认:“不知道!”
李诚说:“好干部连他的每个战士睡下说什么梦话,怎样磨牙统知道。好的干部是战士思想情绪的体温表。你注意到了没有?咱们在老乡家里驻扎,老乡的女人抱着个吃奶的孩子。那孩子咿咿呀呀说话,咱们什么名堂也听不出,可是那位母亲全听清了,而且很有味道地和她的孩子谈话。有时候,老乡的女人在院子里筛麦子,突然,她跑回去给她刚出月子的孩子加件衣服。我问过老乡的女人:为什么突然要给孩子加件衣服?她说,她觉着她的孩子需要加件衣服。瞧!原来母亲和孩子的感觉是相通的。一个干部应该是最好的母亲!多想一想,周大勇。生活中到处可以学习,去,该睡觉啦!”
李诚和周大勇谈罢话以后,穿过树林,踏着地下厚厚的落叶,朝团首长睡的棚子里走去。远处的森林里有一种什么鸟儿,用柔和而清晰的声音,在不停地歌唱。近处,有流水声,有唧唧的虫叫声;有萤火虫在飞窜。猫一样大的小兽,从身边窜过去,嗖地爬上大树。树上的鸟儿扑噜噜地飞起,冲撞着树的枝叶。李诚停住脚步很有趣地望着树梢,静听着。三
西北野战军,不分日夜地钻森林、上山翻沟向西挺进。
团政治委员李诚,在行军中不是按照一般习惯:首长骑着马走在部队前头,有时候往后传两句什么命令。他总是这样:部队开始走开了,他和团长赵劲骑着马在部队前边走,走上五六里路,他跳下马闪出队列站着。过来一个教导员,他叮咛几句话。再过来一个指导员,他又喊:“为什么你行军中一定要跟在连队尾巴上走呢?反正是走路嘛,一面走,一面就找个战士谈话。这样,一天你不就可以和五六个人谈过话吗?要你们做工作,你们总说没时间,行军的时间就是指导员做工作的全部时间。”有时候,他也加入到某一个连队行列中和战士们谈话,听他们的心思,看他们对上级作战意图了解的程度。走上一阵,他又闪出部队行列,站到那里,一个一个告诉那些做政治工作的干部:今天行军中应该做些什么工作。一直到他这个团走完,他又骑上马赶到本团队伍的最前头。然后跳下马,又站在那里,又给一个个干部吩咐事情,布置、检查工作。
有时候,李诚的警卫员和饲养员,跟着他上来下去地奔跑。他们好不满意啊!
饲养员对警卫员说:“四二号来回跑个啥子哟!”
“跑啥子,他的事多嘛!”
警卫员趁空对李诚说:“四二号,你这样来回跑,会把身体跑垮的。再说,我们来回跟上你跑……”李诚说:“谁叫你们跟上我跑呢:你们只会叫苦!叫苦!”
警卫员再没敢往下说,可是心里嘀咕:“我哪里是为我叫苦啊!”
饲养员看说话的机会不可错过,他赶紧插了一句,说:
“四二号,我拉上马跟直属队走,你骑啥子哟?”
李诚把手一摆,边走边说:“好呀!骑马,骑马!上级为什么给我一匹马骑?因为我是政治委员应该骑马吗?不是,同志!上级给我发一匹马,那是叫我骑上它少消耗一些体力,多用一些脑筋;上级要我这个骑马的干部顶两个三个干部工作。因此,行起军来,我不能老是压马。同志,懂了吗?”
一天,部队行军五十里以后,停下来作半小时的休息。李诚,像往常一样:抓紧时间,立刻召集来七八位干部。他简单明了地问:“你们的单位半月前补充的新解放战士,今天行军中有什么思想反映?”
有的干部很具体地说出了一些重要问题。有的干部说:
“情绪很高,没有问题。”
李诚对那些能具体地了解战士思想情绪的干部,巧妙地称赞几句。对那些说“情绪很高,没有问题”的干部,就非常严厉地批评:“简直不能容忍!你整天跟战士们一起生活,而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情况,这算什么政治工作者呢?'没问题'?那你可以睡大觉啊!同志,只要有工作就有问题。好啦,这里有一位老师。”他扭头对一个指导员说:“请你把刚才给我谈的话,再对大家讲讲。”
那位指导员说:“以前我的工作情形是这样:喜欢使用那老一套的简单办法:部队临出发的时候,我站在队前问:'完成今天的行军任务有信心没有?'战士们喊:'有信心!'我便满意了,认为自己要做的工作做完了。可是工作中常出毛病。我们教导员帮我总结领导方法的时候说:'你要让战士们对上级的作战意图或行军任务真正心里有底,那就不是队前简单地讲几句话便能解决问题,而要仔细切实地做工作。'这几天我改变了工作方法。比方,刚才我和我连一排长谈话。他说:
他们排里的战士们情绪都很高,没有问题。但是我深入一步研究,就发现第一排有不少战士在说:'马家的队伍落后得很,连迫击炮也没有。我们在延安周围作战,缴了胡宗南很多大炮,这次我们打仗不用费劲,炮把敌人一轰垮,便冲上去了!'这就是说,还有些战士有轻视敌人和过分依赖炮火的思想。”
一个瘦高个子的指导员说:“这种思想有是有,不过只是个别的人……”“个别的?”李诚接过来话头问。“多奇怪的想法啊!同志,要是百万大军中有一个人的想法和我们的奋斗目标有抵触,那么,我们就要耐心艰苦地做工作,使大家齐心。不做艰苦的工作,光说'不可战胜',那是一句骗人的空话。”他深沉锐敏的眼光,慢慢地从这个干部脸上移到那个干部的脸上,察看他们的思想活动。“同志们,团党委指示:一个政治工作者他应当了解全连每个战士,像了解他的五个手指头一样!……
这指示中列举了很多具体办法。这些办法是集中了全团人的智慧订出来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愿意把它挂在口头上,而不愿意真正地掌握它。”
“前进!前进!”战士们转述着指挥员的命令,部队又继续向前移动了。
李诚站在部队旁边,战士们从他身边流过去。他扭头看后面那长长的人流。他在那么多的指战员中,远远地就认出了周大勇。
李诚在天气黑洞洞的夜行军中,本团部队从他身旁过去,他从那行军速度的急缓上,能识别出每一个连队。部队宿营的时候,他住在房子里,窗外走过一个人,他从脚步声就能听出那是谁。
李诚第一次看到一个新战士,他就问清他的名字、成分,并且观察他身材、脸膛上的特点,还在心里默写着这问到和看到的一切。他要牢牢地记住他。因此,全团有一个月军龄的战士,李诚就可以叫起他的名字;有两个月军龄的战士,他就能说出他的出身、年龄、籍贯、一般的思想表现;说到老战士,那他连他们的脾气、长处、习惯、立过什么功,都能一清二楚地说上来。有时候,在夜战中,一个战士负了重伤,筋疲力竭,突然,李诚在黑暗中喊那个战士的名字,鼓励他几句。那个战士便获得了生命和气力,从血和绝望中勇敢地站起来了。
现在,李诚远远地就认出了周大勇,并不是他看清了周大勇的模样。他是从那结实高大的形样和走起路跨大步的姿态上,感觉到那是周大勇。
周大勇气昂昂地上来了,李诚跟他肩靠肩朝前走去。
李诚对周大勇这浑身每个汗毛孔里都渗透着忠诚和勇敢的干部,是打心眼里喜欢的。他觉得,在整一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周大勇变得老练了。
周大勇的米袋搭在肩上。现在他是连长又是指导员,所以除驳壳枪以外,他还背了一个挂包,为的是装党内文件和各种材料用。他看来总是精干、利索的。
李诚问:“后天我们就可能进入战斗。战士们情绪怎么样?”
“很高!”
“好高?谈谈,你做了些什么具体工作?”
周大勇讲:党支部怎样研究上级打好第一仗的意图,战士们怎样讨论,他又和谁作了个别谈话。
李诚想:“嗯,他的确做了不少工作。”又问:“你觉得你们连队,在进行战斗动员的工作上还存在什么问题?”
“没有。”
李政委看了他一眼,停了好一阵,声音低沉地说:“'没有'这两个字,你是经过仔细思考的吗?你对自己的任何话,一说出口就准备负责到底吗?”
这一问,倒把周大勇问愣了。
“嗬!我们要求万众一心,可是一个连队就该有多么复杂!
你们连队,共有九十七个人。这九十七人来自天南海北。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有新战士、老战士;新战士里头有解放战士有翻身农民……思想水平不同,出身不同,性情不同,战斗经历不同……而你要把他们的思想统统集中到战斗上来。战斗,对一个战士提出了最高的要求。想想,你对每一个人该要作多少工作呀!”
李诚的话,给周大勇的心里放了一把火。在先,周大勇觉得本连队战斗动员工作做得还凑合,目下,又觉得工作中问题又挺多,心里有点着慌。
战士们哗哗地前进,前边不断地传来命令:“跟上!”“迈大步跟上!”
李诚和周大勇肩并肩向前走。他走得很快很稳,低着头。
他脑子像重机关枪连发那样紧张地思考事情。一个骑兵通讯员,顺着部队行列上来,递给他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信,李诚拆开看了一下,装在衣袋里。他问:“有些战士对背米袋子的事很恼火!是吗?”
周大勇想了一下,说:“嗯,新战士特别恼火!”
李诚说:“我刚才听见李江国用山西小调唱:
我的米袋四尺长,
这就是我的大后方,
不要说是背上累,
有粮就能打胜仗。”
周大勇笑了,说:“我早就听见了。编编唱唱这一套是李江国的拿手好戏!”
李诚说:“你听见了?那你为什么不让全连战士跟他学着唱这个歌呢?拿战士们的话教育战士们,这不是很妙的教育方法嘛?”他指着周大勇肩上搭的米袋,问:“它搭在你肩上和搭在战士们肩上有什么不同?”“政委,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沉!”
“不。周大勇同志!我们常常是希望上级给我一套工作办法,却不在自己身边的生活中去找寻工作办法!”
这一说,让周大勇脑子里又兜起了很多问题。他望了望政治委员那锐敏而深思的眼睛,思量政治委员的话。
“你让你肩膀上的这个水袋子,发挥更大的作用吧。”李诚从口袋里掏出刚才接到的信,说:“李干事给团政治处写来的这封信,应该立刻传给全团的干部看。信里头说,各连队的新战士对背米袋的事都有意见,可是九连的新战士不但没有意见而且乐意背。因为九连指导员给战士们讲话的时候,指着自己肩上的米袋说:'同志们背米袋累,我也很累。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背呢?'他就向新战士解释:自古以来打仗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我们呢,新兵补上了,想给新兵发的武器还在敌人的仓库里;部队行动了,要吃的面粉还在西安胡宗南的面粉公司。我们必须背三天粮食,不背就要饿肚子。他还把他在战争中体验到的事实--米袋、干粮袋如何救了我们命的事实,讲了那么几段,然后发动老战士们也来向大伙儿讲。周大勇!我想,这些办法可能比我们干巴巴地讲一通道理强得多。”
周大勇心里豁然亮了,脸上喜盈盈的。他真恨不得一把握住政治委员的手,说几句亲热的感激的话。
李诚说:“这些办法,你可以试试看。不过实地做起来,就不像说话这样不费力气。”他边走边筹思什么。猛然,他偏过头,瞅着周大勇说;“费力气?费力气又有什么?党把你选拔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你有超过平常人的精力。一般人身上发出的力量只能带动一部机器,你身上发出的力量就要带动十部机器。同志,想想,你要没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怎样能发动战士们高度的战斗意志,使他产生压倒一切的威力呢?”
李诚跨上马,把马的缰绳一扯,回头说:“周大勇,脑筋是个伟大的东西,但是不去思想,它就会像那路边的石头一样--没有多大用处。”
李诚催马顺着队伍行列向前面跑去了。马蹄扬起的灰尘,遮住了他的背影。
周大勇不眨眼地望着那马蹄扬起的灰尘。他想:啊,自己和这样的人并肩踏着征战的道路前进,不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嘛?有一种感情在他胸中回荡。它不像人们打了胜仗以后的那种欢乐,也不像当了英雄出席庆功会那样高兴,这是一种把人推向思想高处的更严肃更深刻的感情。
部队从遮盖天日的森林中,日夜行进。弯弯曲曲的山路又窄又陡。黑压压的山头,一个刚移过去,一个又横挡在战士们前面。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