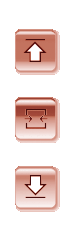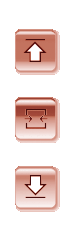|
|
|
|
第三回 索专权漫天飞电报 隔激流两帅投奇石
|
两河口会议,张国焘不同意毛泽东等人所提出的北进计划,并且提出了与之正好相反的“南下川康边”方案,终被大家否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
会议在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和日军进攻北平的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手下。我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并在部队中宣传抗日,反对放弃华北,以发动群众。”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周恩来、朱德在毛泽东说完后,立即表示赞成这一提案。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通电和文章,并向国民党军队中派工作人员。会议接着研究了红军的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常委会散会时已是中午。张国焘在餐桌上正在吃饭,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神秘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报纸,递给了张国焘。这是一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报》,是在懋功地区出版并发行的第一张报纸。
“这里。”李特打开报纸,指着第一版显著位置说。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登载的是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署名文章:《列宁论联邦》。
“论联邦!主要讲了什么?”张国焘边吃饭边用眼睛粗略地浏览着报纸。
“大意是说列宁反对欧洲联邦,进而推论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是违反了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否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特简要地回答。
张国焘的脸色沉下来,他把饭碗一推:“不吃了,走!”
李特等人也跟着退了出去。
“我知道他们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张国焘愤愤不平地说:“我推测他们曾经开会慎重讨论过,决定由凯丰写这篇文章。你从哪里得到这份报纸的?”
“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给我的。据说他们在两三天前就发了这张报纸,并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央怎么能这样干呢!好像一、四方面军不是一个娘养的一样。”李特的话对张国焘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油。
张国焘心中的怨气越积越深,把他那张报纸展开仔细地看了一遍,问李特:“你对苏联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说说对这篇文章怎么看?”
李特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不稳,列宁虽然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从根本上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一员,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真感叹中央的那些留俄人物,怎么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们!”
在这时,张国焘比较信任的年轻人除黄超外,就是这个时年33岁的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他比张国焘小5岁,是个天资很高的才子。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乳名豹子,皖西霍邱刘庙村人,其父是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李特随父入湘在长沙读书,深受其父影响。1921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3年后由交大赴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后调到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时蒋经国等人也在这里学习。在苏联期间,20多岁的李特,身体长得不高,胖墩墩的脸蛋在西欧人群中显得很特别,因此,大家通常不喊他的原名,而戏称他“little”,这是英文,矮小的意思,谐中文音“李特”,常而久之,李特也习惯和喜欢上了这个谐音名字。1930年他回国后,也就正式用“李特”这个名字。
李特可谓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是“豹子”脾气难改,常常为一点小事发火。他回国后相继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军彭杨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职,基本上可说回国后的这5年时间是与张国焘共事在一起的。因此,他和张国焘两人也彼此比较了解,一说到苏联的问题,张国焘往往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张国焘对李特关于“列宁论联邦”的辩解和回答比较满意,气也消了一些,得意地说道:“就是嘛,他们懂个啥?要说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圈子内见过列宁的人也就唯我一个,他们在那里枉自谈论什么‘列宁论联邦’,学了几句俄语就感到学到了马列主义的真谛,早着呢!李特,以后有什么动静就赶快转告我。”
“是。”李特回答,他为提供了这张对张主席有用的报纸而感到得意。
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有些军长也来向张国焘报告:“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说我们四方面军没有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是比现在四方面军强得多,尚且不是敌手,何况区区四方面军。因此我们担心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中央领导着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哪里去?”
有人向张国焘汇报:“中央最近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四方面军中调查,他们往往夸大了四方面军的缺点,找到几个军官打士兵的例子,就说整个四方面军中有着浓厚的军阀习气。这些调查者还说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而不知道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就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
“我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与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在一起对付我。”张国焘语气深沉地说:“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经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当在党内团结和一、四方面军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在此严重关头,不宜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我也觉得中央和一方面军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
张国焘的心思在向中央的权力上聚焦,他对中央刚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并不满意。在红四军总部,他拿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名单,着急地说:“我们现在急需督促他们解决的是政治、组织问题。我们的人在政治局中的太少了,一开会表决就吃大亏。你们看看,政治局都是他们的人,怎能体现我们8万人的意志?”
“对,张主席的意见很重要,政治局和总部中应该再加上几个我们的人,开会总要举手表决嘛!”有些官迷心窍的人应声附和。
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谈话中,大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来到部队中作游说,站在主席台上,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自问自答:“有的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又是什么呢?我们有些高级领导人自以为文化高,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了些什么?”
作为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说出的话很容易迷惑人。因此,由于他的着意引导和煽动,红四方面军中有些人也跟着起哄,军中一时风言四起:
“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
“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
“军事指挥不统一,应该统一军权。”
两个方面军部队之间也出现了不信任情绪,由互相的指责和批评发展为感情用事。四方面军中有人说:“这些小脑壳一来,我们红四方面军反而什么也不是了。”因为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戴的军帽小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所以有人说出了这么一个代名词——“小脑壳”、“尖脑壳”,有的还称“老机”(机会主义)。
由于受感情冲动的驱使,两个方面军中有人开始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
红一方面军中有人指责红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加之凯丰的《列宁论联邦》文章,公开批评张国焘等人所建立的西北联邦政府,这也给张国焘闹分裂以借口。
红四方面军有的人看到红一方面军的人,大有瞧不起的神气:“哼!尖脑壳里装的全是机会主义思想,兵不像兵,马不像马的,稀稀拉拉。他们也不想想中央苏区是怎么丢的,那还不是吃了机会主义的亏。”
两河口会议看来并没有统一两个方面军的思想,反而因种种原因更加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会议后,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当时松潘附近有胡宗南部队共16个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红军“迅速、机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之国民党军,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3路军:左路军由第1、第3、第5、第9军团组成,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浩率右路军,分别从懋功、理县、茂县北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准备趁国民党胡宗南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之机,迅速迂回过去,坚决攻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要道,以利红军向北开进,进入甘南。
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即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古山、施罗岗等数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中旬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然而,张国焘却迟迟没有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他致电中央,提出另外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叩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
“这个张国焘怎么如此出尔反尔呢?”毛泽东接电后感到很气愤。
“还有更让人捉摸不定的呢!”张闻天把一封电报递到毛泽东的手中。
原来在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
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有人要急于黄袍加身。看来问题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复杂得多呢!”王稼祥看完电报担忧地说。
果然,毛泽东、张闻天在近几天中接连收到许多内容相同的电报。
张国焘在电报中的措辞已很严厉,要求中央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川陕省委一些人在张国焘授意下,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
“军委主席,独断专行?好大的口气哟!”毛泽东手捏一摞电报气愤异常。
所有这些,实质上就是张国焘要取代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地位。
到了这时,毛泽东明白了,大家虽然都诚心诚意祝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也都希望把两个拳头捏在一起。然而,这两个拳头却很难捏在一起,其中原因已很明显,这就是左、右手都想自己捏成一个拳头,张国焘最终要亮出自己的拳头。
张国焘在当时中共中央的地位是较高的,他已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充当第一号人物。因此在他听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实际取代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后,就非常不满,并不加隐瞒地表露出来,接二连三地提出要立即解决政治、组织问题。
张闻天把那些电报又翻了一遍,说道:“这些来自四方面军部队的如此同样内容的电报,放在一起一比较,就可看出张国焘在唆使他的追随者要挟中央,他们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一句话,张国焘要将红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我要找他谈谈。”
张闻天从电话里找到了张国焘,解释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两军会合后,一切也都很顺利。红军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张国焘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再三强调党内的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为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失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个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我看政治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决的,等军事情况有了好转后再作讨论吧。”张闻天不无忧虑地说:“我对党内发生的纠纷,深表忧虑。国焘同志,你还是站在大局的角度,多忍耐些,不要再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
张闻天与张国焘两人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
此时的张国焘,与其说是一个在耍弄政治手腕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大商人,他的资本就是红四方面军这8万人枪。他在与张闻天的电话谈话中断后,立即抓起话筒,向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发出“各部队无权擅自接近中央慰问团”的决定,嘱咐参谋人员要把中央慰问团的住处安排在离部队和司令部都较远的地方。
刚刚在遵义会议后舒心半年的毛泽东又陷入党内斗争中,他异常着急,深知此时的红军万万不能自乱内讧,一切都必须从大局考虑。他责备凯丰不应该发表那篇文章,并对红一方面军的人讲:“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有些分歧暂时不要说,还是要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十分珍惜两军的团结,一定要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于两军团结的言论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
到了这时,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面临着3种斗争:与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的斗争;与大自然的斗争;同时,还要与张国焘的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这后一种斗争看似没有流血牺牲,但比起前两种斗争,毛泽东等人感到要艰难得多。
“先向前走吧,能抱多远就算多远。天塌不下来的!”毛泽东说。他在遇到困难又一时需要忍耐和形势紧张时,总爱说这句“天塌不下来的”话。
“张国焘人多势众,我们应有所考虑。”
“让我们向他妥协?办不到。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吗?天塌下来有山顶着!”毛泽东横眉以对,把电报纸“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他倒背着手,来回踱着步,昂首挺胸畅吟道: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张国焘的倔强脾气在两河口会议后毕竟没有“倔”过毛泽东,主要还在担心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徐向前的现实意向还不明,他暂时只好勉勉强强地随队北上。7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奉命介别率军出发。
徐向前率中路军的10余个团,沿黑水河岸蜿蜒前进。一路上又要防备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又要对付藏族地方武装的偷袭,又要拔除敌人盘踞的堡寨,每天行进不到30公里。
在快接近黑水的途中,徐向前接到彭德怀的一份电报,说红3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已带部队上来。
徐向前异常高兴,对司令部中的参谋人员说:“这个‘彭’就是江西中央苏区‘朱、毛、彭、黄’中的‘彭’,过去对这几位只是闻其大名,可从来没有机会见面。现在,彭德怀同志来到近前,我一定要亲自去迎接。”
参谋人员把地图铺在徐向前的面前。
“立即发电报表示热烈欢迎,约请彭德怀同志在黑水河的渡口会面。”徐向前对参谋说。
第二天早晨,徐向前和随行的通信排,骑上战马向黑水河畔飞驰而去。
黑水河仅从地图上看,很不起眼。这条小河是岷江支流之一,宽虽然只有20多米,但水深流急,波涛汹涌,冰冷刺骨,难以徒步涉过。这里的人来往过河,只有依靠铁索桥和溜索。
当徐向前一行抵达黑水河边后,不见桥梁也不见船只。陈参谋腰间拴上绳子下河试了试水,赶紧退回来,向着岸上叫喊:“冰冷得很!不能过,水流太猛,岸边简直就站不住脚!”“要是能找到一只小船就好了。”警卫员康先海叹息道,他弯腰拣起一块石头,投向河中,石头在浪尖上跳了几跳,转眼间就被急流卷走了。
“讨厌,讨厌!”徐向前在岸边一边踱步,一边自言自语。
这是他在遇到紧急情况又一时没有寻思出办法下的习惯用语,有时子弹在他身边飞,他也总是不慌不忙地一手持望远镜观察敌情,一手在耳边挥挥手,好像是在吆喝苍蝇,习惯性地说着:“讨厌,讨厌!”
“对岸有人!”康先海眼尖,首先报告说。
“是自己人,可能就是彭军团长。”徐向前从望远镜中看到对岸是支红军队伍,都骑着马,判断道。
两岸的红军将士都互相招手,但喊话声是谁也听不见,被喧嚣的河水奔腾声淹没。
河对岸的红军正是彭德怀一行。昨天,彭德怀率部进到黑水寺时,军委命令他立即带红11团沿黑水河右岸东进,至石雕楼迎接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黑水河。红3军团主力和军团部暂留芦花。
无法过河,徐向前等人只好顺流而上寻找渡河点。
“这个画地图的人简直是太马虎了,这么大一条河流画在地图上竟然如一条小溪流,懂不懂比例?”参谋人员埋怨。
徐向前微笑道:“不要怨这怨那个的,让你现在就此画一张现地地图,说不定还不如缴获来的这个图画得准确呢!川西北河流密集,如果都上地图,那你准会画成江南的水网地,甚至画成一片汪洋大海,那才叫比例失调哩。”
两岸红军将士都向地图上标有铁索桥的方位走去,准备过河到对岸。
“哎呀!不好,总指挥,你看,铁索桥被破坏了!”康先海尖声叫道。
大家的目光顿时凝集在不远处风水河流上的铁索桥,只见激流上空剩下几根光溜溜的铁索在山风中悠荡。
轰鸣的河水在咆哮着。徐向前陷入沉思。
这时,对面河岸上的一队人马也接近了岸边。这里的河面较窄,看得清楚,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等身材、体魄健壮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灰布军装,戴着一顶草帽,在见到河对岸有队伍后,便摘下草帽呼喊。
徐向前也挥动军帽答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会见的人。
“讨厌,真讨厌!”徐向前咒骂着河水。
“总指挥,你看!他们在干什么?”康先海指着对岸说。
徐向前举起望远镜,他清楚地看到一个战士在扯着一根绳子,几个人都围着他;好像是在做过河的准备。
“那么点绳子,能过河?”徐向前把望远镜递给了陈参谋。
不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河这边打了个手势,接着那个战士在用力甩那段只有一米多长的绳子,旋转中那绳子突然向对岸飞来。原来他们借助绳子的惯性力,扔过来一小块石头,石头上用细绳捆着一张纸条。
“这绳子上有纸条!”康先海把纸条递给徐向前。
徐向前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我带3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
“古有鸿雁传书,红军今有奇石传信,妙!妙!”徐向前高兴极了,忙从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写着:“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把这张纸条也用绳子拴在小石头上甩过河去。
“飞燕”到了对岸,河两岸一片欢呼声。
彭德怀接到纸条后,高兴地挥动着大草帽,向着河对岸致意。
“通信员,把电话架过河去!”彭德怀命令。
“这河……”
“人不能过河,电线还不能过河?”彭德怀反问:“哈哈,笨蛋!我刚才怎么把信送过河去的。”
“哎呀!我明白了。”马上,通信兵隔河又投开了石头,用绳子在河面上拉起一条电话线。彭德怀和徐向前第一次通话,互相问候。
“我们一定要见面!”彭德怀对着奔腾喧嚣的河水大声喊叫。
“明天吧,黑水河上游还有一个渡口,是个地名叫亦念的小村庄,那里有座铁索桥,我们在那里见面,怎么样?”
“就这样,一言为定,明天亦念握手相见。”
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是中午,彭德怀也刚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被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
“徐总,前边河面上有一条溜索,我们先过去把电话架起来。”通信兵建议。
向上流望去,果然见一条绳索悬挂在河两岸,上面悬挂着一个竹编筐子。这是附近山民渡河用的常用工具。
“不必架设电话了,我一个人过去。”徐向前说着向前走去。
“不行,徐总。那太危险!”随行人员都加以阻止。
“这玩艺儿我还真没有坐过,也试试新。当地老百姓都敢坐,我们为什么不敢坐?”徐向前想与彭德怀见面心切,执意跨上了竹筐。然后,用脚向岩石上一蹬,反作用力推动着竹筐带人向对岸溜去。
轰隆隆的河水在徐向前的脚底滚滚而下,溜索时而慢,时而快,时而又停在半空中,让人紧张地喘不过气来。两岸的人都悬着心,望着河流上空的溜索。
“谁过来了?这很危险!”彭德怀问。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我是徐向前,你好啊,彭军团长!”徐向前没待溜索竹筐靠上岸就开始亲切地招呼。
彭德怀大步迎上前来:“徐总指挥,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本事!”
“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
“真让人担心!”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两军会师,两员主将奇特的相会,这给彭德怀和徐向前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两人一见面还经常提起这黑水河上“奇石传信”和“空中飞人”的场景。1956年,红军长征胜利20周年,徐向前还专门写了一篇《黑水河畔》的文章,以纪念他与彭德怀的如此“飞石”初相识。
彭德怀率红11团到达亦念后,又先后接引了王宏坤、余天云等军的顺利北上。
第三天,张国焘的特使黄超来到亦念,和彭德怀住在一起。黄超的嘴巴很能说,见面就说:“张主席说此地给养艰难,让我特来慰劳彭军团长。带来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元银洋。请军团长笑纳。”
若是仅送一点吃的,彭德怀不会感到稀奇,会像往常一样收下,可这200多元银洋却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他心中在犯嘀咕:“这不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嘛!”
“我无功受禄,实在不敢当。你实话实说,这次来是想干什么?”彭德怀的话直截了当。
黄超住下后问起了会理会议的情况。彭德怀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你怎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与你谈了?”
“我是听张主席谈的,可能中央在什么会上提起过吧。”
“如果中央谈了,又问我彭德怀干什么?”
黄超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又说道:“张主席很了解你。”
“怪了,我们过去没见过面。他能了解我什么。”
黄超又说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前的战略方针,我认为欲北伐必先南征。”
彭德怀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办法。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不能把全国的形势看成漆黑一团。也不能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成果。”
“西北马家骑兵可是厉害得很呀!应该避开他们才好。”
彭德怀到此把上面的谈话综合起来一想,知来者非善意,黄超此行是来当说客的。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又从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入手,企图破坏党内的团结。
第二天,口直心快的彭德怀对徐向前说:“这个张副主席看来想拉我到四方面军工作。”
“你千万不要来,我都想法离开。”
“为什么?”
“一言难尽,这边的人并不好相处。”徐向前面露愁容,没有再说别的。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两军会合之初,徐向前即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因为他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虽然共事多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舒畅。具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头衔的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喜欢自作主张。徐向前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屈求全,完全是凭党性在坚持工作。
在理番时的一天晚上,徐向前与陈昌浩交谈中即提出:“我这个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代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感到突然,问道:“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回答:“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当时就表示不同意:“你还是先别考虑这件事。”因此,两军会师后,徐向前的主要想法还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是,还没等徐向前提出这个要求,他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个漩涡中去了。
7月初,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时,经下东门见到徐向前,简要讲了中央红军的情况和攻取松潘的计划,并即兴渲染讲道:“南面来的这些洋鬼子,戴眼镜,修洋头,穿西装,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他们不要我们!”
“什么?”徐向前感到很惊讶。
“他们说我们政治落后是土匪主义,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张国焘的概括能力很强,一口气说出这两个主义。
“这两顶大帽子我们可戴不起!我们是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的,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难道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徐向前在最近也风言风语听到一些传闻,现在听张国焘这么一说,也感到特别的反感和委屈。
“大概你也听到一些。其实,你对我们四方面军最了解,怎么他们一来,我们一夜之间就突然变成土匪了呢?”张国焘的话似乎很伤心。
“我们四方面军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还不至于一团漆黑吧。这支部队从鄂豫皖的一支300多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铁的红军队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应看到这个主流。我们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到来的……”徐向前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个“是”,情绪也有些激动。但他突然意识到张国焘的话中有话,声调也就变得低了些:“反正这对两军的团结没有任何好处。我相信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同志会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
张国焘匆匆回茂县了,但他的话在徐向前的心中却翻起了千层浪。其实,徐向前此时脑子里的这些驱之不去的问号,也正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的共同疑问。是呀,正打着红旗闹革命的热血青年,无论是谁听到别人说自己是“土匪”时,恐怕心中都感到是一种耻辱、委屈和不平。只不过对身兼重任的徐向前来说,他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自我约束能力,不仅自己不谈论这些事,而且严格要求部属不要瞎议论,要顾大局,讲团结。
不久,张国焘与党中央的严重分歧日益表面化,徐向前作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无疑也被挤入这场争论的夹缝中。政治斗争的这种复杂局面,对于一直忙于以“十二万分热忱欢迎中央红军”的徐向前来说是感到很突然的,对此,他很是苦恼。徐向前这时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程训宣已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了。徐向前是到延安后才知此事的。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