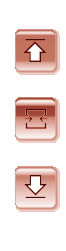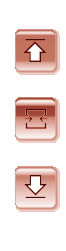|
|
|
|
(六十)
|
彭德怀也象全军的指战员一样,对当前不战不进的局面闷闷不乐。这天,他正坐在一家藏民的木楼上闷着头考虑什么,忽听一个参谋在电话上报告,说四方面军张国焘的秘书前来探望,便坐在楼上等候着。
不一时,警卫员就将一个人领上楼来。这人向彭德怀恭恭敬敬而又很潇洒地打了一个敬礼,接着说:
“我是张主席的秘书黄超,是奉张主席之命来慰问彭军团长的。”
彭德怀一打量来人,是个相当年轻漂亮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副曼长脸,面孔白皙,两只闪闪的大眼睛,透露着聪明灵活,善知人意。彭德怀同他握了手,就请他在火塘边坐下。
黄超一坐下,便滔滔不绝,称赞彭德怀是海内名将,无人不晓,自己作为后生小辈已倾慕多年,今日是相见恨晚了。
彭德怀见他说个没完,就说:
“都是自己人嘛,不要太客气了。”
“这怎么是客气呢!”黄超讲得更加来劲,“一方面军西征行程一万八九千里,彭军团长斩关夺隘,声震遐迩,不要说自己人,就是敌人也闻风丧胆。张主席平日常谈起彭军团长,他觉得这地方生活很苦,所以叫我送点东西来,表示慰劳。”
“那我就谢谢他了。”彭德怀说。
黄超转过头看了看警卫员已经出去,就试探着问:
“彭军团长,你是不是参加过一个会理会议?”“参加过。”彭德怀答道;一面心中暗想:“他为什么要问这个?”
“你那次处境不大好吧?”黄超闪着一双机灵的眼睛。
“处境?什么处境?”
彭德怀对这位年轻人提出的问题感到意外。
黄超笑了笑,说:
“一个人遭到不白之冤,总是叫人不愉快的。”
彭德怀带有几分粗野地望了黄超一眼:
“无非是受了一点批评,这在我们党内也很平常。”“批评自然是常事,”黄超笑着说,“如果太不公平,也会叫人沮丧。”
“没什么!”彭德怀紧接上去,“仗没有打好,有点右倾情绪,受点批评,这是很自然的。”
说到这里,彭德怀盯住黄超:
“怎么,你要了解会理会议?中央给你谈了?”
黄超涨红着脸说:
“不不,我只是随便问问。……张主席是很知道你的,也很关心……”
彭德怀木着脸,没有表情,冷倔倔地捅出一句:
“我们过去没见过面。”
黄超的勇敢进攻受了挫折,伤了几分锐气,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继续鼓劲。他眼珠转了几转,便改了话题。
“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确实力量大了。但是战略方针还要正确。如果这方面发生偏差,兵力再大也不行。”
彭德怀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
“黄秘书,你看怎么才算正确?”
黄超不免有点尴尬,带着几分忸怩地说:
“不是我看,是张主席考虑:还是南下才是上策。他曾跟我说,'欲北伐必先南征'。”
“那是什么情况?”彭德怀轻蔑地一笑,“那是诸葛亮巩固蜀国后方的办法。我们现在连根据地都没有,哪里有这样的后方?”
黄超挨了一棒,心里已有几分恼怒,但在这个威严人物的面前,毕竟不敢放肆,就客气地反驳道:
“彭军团长,北进也不那么容易吧,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武器装备是最精良的,战斗力很不一般。还有马家军的骑兵,不仅装备好,而且训练有素,每人一把大马刀,在草原上跑起来简直象……”
彭德怀脸有愠色,立刻打断他:
“你是叫他们吓昏了吧!”
黄超满脸通红。沉了一下,继续争辩说:
“对形势的看法是需要冷静、客观才能得出正确答案的。张主席多次说,当前苏维埃运动已经处于低潮。这是不能不承认的。张主席还告诫说,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仍然不能从'左'的躯壳里解放出来,这将是我们这一代最大的悲剧。”
彭德怀有些惊讶,面前这个黄口乳子竟敢放肆地冒出这种宏论!他厌烦地把头歪在一边,下嘴唇撅着,两个嘴角弯成了一个彭德怀式的弧线,不作声了。
黄超觉得自己有点操之过急,就站起来,对着楼梯口叫:
“警卫员!把东西拿上来!”
原来他带的两个警卫员等在楼下,这时闻声走了上来。一个背着一大一小两个口袭,另一个背着一个沉甸甸的皮包。黄超满脸堆笑,指着那个小口袋说:“这是几斤牛肉干,味道蛮不错的。”又指指那个大口袋说:“这是几升大米,是我们张主席从川陕带来的,这地方想找这个就太不容易了。”
说过,他又从另一个警卫员手里接过沉甸甸的皮包,从里面取出几个包包,笑得很迷人的:
“这是三百块白洋,只不过是张主席的一点微意。”
彭德怀看见大米和牛肉干,还微微点了点头,一见递过来的白洋,脸色立刻变了。
“这是干什么!”他的语调有些严厉。
“也不过怕军团长手头不便……”
彭德怀终于克制住自己,没有发作,但是他站在那里一声不响,简直象石头雕像一样冷峻。
黄超异常狼狈,只好慌慌张张把钱放在一个用木板搭成的桌案上。他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幸亏他脑子聪敏灵活,就乓地打了个潇洒的敬礼,笑着说:
“彭军团长,您恐怕很疲劳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彭德怀站起来,勉强点了点头。黄超带着警卫员慌乱地下楼去了。
直到黄超走出很远,他还觉得满心不舒服,望着这个张国焘的使者,狠狠骂道:
“呸!什么东西!纯粹是旧军阀的一套!”
说过,他就坐在火塘边陷入深深的沉思里。他一遍又一遍地想着这个黄口乳子的来意。
这时,三军团的政治委员杨尚昆走了进来,他一见彭德怀满脸怒容,就问:
“德怀同志,黄超在这里谈什么了?”
彭德怀的火立刻又升腾起来,他指了指桌上的白洋,骂道:
“张国焘他把我彭德怀看成什么人了?他把我当成军阀!
我要当军阀,还来红军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家伙值得警惕!”杨尚昆也沉到思索中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