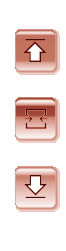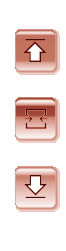|
|
|
|
(六十一)
|
在毛儿盖度过的时日,象钝力子割肉一样痛苦而又漫长。夜间在村边、地头露营的战士们,不知道一夜冻醒几次;白天又为辘辘饥肠骚扰得片刻不宁;尤其是居民远离所造成的寂寞,更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些都使人难以忍受。
刘英也象大家一样焦躁不安。一有工夫,她就跑到张闻天那里闲谈一回。他们的关系早已瓜熟蒂落,只是由于刘英顽强地据守着最后一道防线——不到长征胜利不结婚,两人才没有完成那人生重要的一幕。
这天早晨,两人正围着火塘闲坐,警卫员递过一封信来,说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政治委员陈昌浩派人送过来的。张闻天打开信一看,上面笔迹颇为潇洒:
闻天同志如晤:
你我天各一方,多年相违,每思同窗之谊,悬念殊深。前日匆匆一面,未及深谈。如能来我处一叙,则不胜欣幸之至。
耑此
即致
布礼!
陈昌浩即日
张闻天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对警卫员说:
“你告诉来人,我呆会儿就去。”
警卫员下楼去了。张闻天仍然拿着那封信在吟味着,脸上渐渐出现了微笑。
刘英凑过来看了看,不解地问道:
“你笑什么?”
张闻天收起信,把近视镜往上推了推,说:
“这是要给我做工作哩!”
“你们这些人就是心多,”刘英撇撇嘴说,“都是老同学了,好几年不见,也是想在一起谈谈。”
“这倒是。”张闻天说,“可是,你不知道,前几天张国焘就派人到彭德怀那里送东西,弄得彭德怀啼笑皆非。”“那你也给他做点工作嘛!”刘英说,“现在连一个松潘也打不成,气得毛主席没有办法,眼看着我们非在这里困死不可!我们和陈昌浩都是老同学,他在张国焘那里很红,张国焘很信任他,你去劝说劝说,恐怕还是会起作用的。”
张闻天连连点头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前几天泽东同志就跟我说,人家已经来说客了,闻天同志,你是不是也学学苏秦、张仪,争取早点打松潘哪?”
刘英满有信心地说:
“那你就去吧!我们在莫斯科,同陈昌浩还是很不错的。
张国焘那个人老奸巨滑,陈昌浩比他还是单纯得多。”
“你是不是同我一起去?”张闻天笑着问。
“你们是谈军机大事,我去干什么!”
张闻天略作准备就下楼去了。陈昌浩住在另一个小寨子,相距并不甚远,张闻天就带着两个警卫员沿着田间小路不慌不忙地走去。
四方面军总部现在已经作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张闻天刚走到门口,高高个子的陈昌浩已经笑嘻嘻地迎了出来。他头戴大八角红星军帽,身材魁伟英挺,举止敏捷,全身充满一种蓬勃的青春之气。张闻天记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陈昌浩还是一位年轻的小弟弟,现在已经是威风凛凛的高级将领了。
两人沿着小木梯上了藏族人的小楼。室内布置得相当整洁,一面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铺着一条军毯,颇有一点司令部的严整气氛。两人在椅子上坐下来,警卫员端上茶,就下楼去了。
自然,寒暄话旧占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们的确为革命的友情,为共同经历的同窗生活陶醉了。张闻天从眼镜里亲昵地望着他这位英俊的伙伴:
“昌浩,那时候你还不过十八九岁吧?”
“哪里,还刚刚十七岁。”
“是嘛,那时候大家都把你当成小弟弟看,想不到几年工夫,你已经纵横疆场,指挥十万大军了。”
陈昌浩的脸上立刻呈现出一种红润耀目的光彩和踌躇满志的笑容。这是那种青云直上一帆风顺的人所常有的。他略微谦逊几句,就滔滔不绝地说道:
“是的,我到鄂豫皖任少共省委书记还不到二十四岁。后来肃反,国焘同志撤了曾中生的职,就要我去当红四军的政委。我开始认为自己军事上外行,没有多大把握,后来三打两打,觉得打仗也不过如此。”接着,他就得意洋洋地讲,他和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时间不长,由于贯彻了四中全会的路线,局面很快就起了变化。到三一年底就发展到三万多人,成立了红四方面军。接着就进行了四大战役,消灭了敌人六万多人,还活捉了敌人的总指挥和几个师旅长。其中成建制的敌军就有四十个团。鄂豫皖苏区的总人口已经发展到三百五十万以上了。
陈昌浩神采飞扬,颇露出得意之色。张闻天笑着问:
“听人们传说,打黄安时你还亲自坐了飞机去扔炸弹,这事可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陈昌浩微笑着,显得更兴奋了。他说,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架德国容克式双翼飞机,飞机师经过教育转过来了。他们就把这架飞机油漆一新,取名“列宁”号,机身上写了“列宁”两个大字,机翼上还有两颗闪闪的红星。打黄安时,敌人的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被围了几十天都不肯投降。他们就决定让“列宁”号直接参战,在总攻之前给敌人点厉害瞧瞧。大家都说:过去敌人的飞机老是跟着我们瞎嗡嗡,这次也让敌人尝尝我们红军的“鸡蛋”到底是咸的还是淡的。说到这里,陈昌浩嘎嘎地笑起来,说:“飞机临起飞前,我就上了飞机,同志们一看急了,就说,不行呵,政治委员,你怎么能坐上飞机去扔炸弹呢!我说,有什么不可以,这才是最生动最能提高士气的政治工作!说着,我就乘着飞机飞上去了。那天正是雪后初晴,阳光灿烂,下面看得非常清楚。成千上万的战士看见自己的飞机真是激动极了,纷纷跳跃着,把帽子扔上天空。我们飞到黄安上空,敌人还傻乎乎地以为是自己的飞机,我们把翅膀一歪,一串迫击炮弹就丢下去了,下面升起了一团团浓烟。飞了一圈,又把翅膀往另一边一歪,又一串迫击炮弹象饺子下锅似地丢下去了。敌人迷迷糊糊,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弄错了目标,纷纷摆出标志,这时我把大批的传单一批一批丢了下去,整个黄安上空红绿传单满天飞扬,他们才知道是红军的飞机在他们头上。敌人绝望了,时间不长就进行突围,被我们全部消灭……”
张闻天听得津津有味。他的这位年轻同学如此勇敢和富有朝气,给了他强烈的印象。
“不过,这种行动,毕竟太冒险了!”他微笑着说。“不然!”陈昌浩笑着反驳道。“战争本身就有一点冒险的味道。完全不冒险的事是没有的。”
“不,我说的是你本身,作为一个方面军的政治委员……”
“哎,洛甫同志,你还体会不深咧!”陈昌浩腔调里带些老味说,“一个指挥员在火线上的表现非常重要。也有人批评我,不应当在第一线去打机枪,好象是有背于自己的职责。实际不然!在危险时刻就是要这样做。你看我们的部队一打起冲锋就象小老虎似的,战斗作风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张闻天笑了笑,不再争辩。他刚想转换话题,陈昌浩又兴致勃勃地讲下去。
他说,自从离开鄂豫皖,经过三千里转战,部队确实吃了一些苦头,最后剩下一万四五千人。可是迅速开辟了川陕新苏区,兵力呼啦一下子发展到八万多人。全苏区人口拥有五百多万,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最大的根据地了。在这期间,他们先后进行了反三路围攻,三次外线进攻和反六路围攻,歼灭敌人十三万人。其中特别是反六路围攻,面对四川军阀的二十余万兵力,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奋战,歼灭了敌军八万人,终于把敌人的围攻粉碎了!
陈昌浩目光四射,神采奕奕,流露出一种战胜之军的那种不可抑制的自豪感。张闻天也连连点头称赞道:
“确实成绩很大!四方面军的同志确实打出威风来了!”
陈昌浩得到总书记的称赞,满面是笑。稍停了停又接着说:
“这些成绩的得来,是同国焘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公正地说,国焘同志确实很有能力,很有魄力,是足以肩负大任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断听到一点闲言碎语,说什么张国焘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
“他到底把问题提出来了!”张闻天从眼镜后面望着陈昌浩,心里暗暗地想。然而,作为总书记又不能不坚持党的原则,就笑着说,“这样说,自然不好,可是国焘同志也是有缺点的。大家都清楚,在严重的历史关头,他往往是掌握得不大稳的。”
“什么地方不稳?”陈昌浩觉得很不顺耳。
张闻天觉得今天显然不宜辩论这种问题。可是为了使当年的这位“小弟弟”清醒一点,略略说几句也有必要,就以和缓的语调说:
“我说的不大稳,指的是在根本路线上,有时'左'了,有时又偏右了。”他举出大革命时期,张国焘开始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后来统一战线实现了,他又跑到陈独秀右的一边去了。
陈昌浩年少气盛,立刻打断张闻天的话说:
“这都是过去的事。我觉得,首先应当看到一个人的成绩,应当看到主流。国焘同志是拥护国际的,是忠实执行四中全会路线的。从实践结果看也是这样,他领导的部队发展到八万多人,这一点比别人并不差嘛!我可以大胆地说,即使让他担任军委主席,也并不过分!”
张闻天沉默了。脸上的微笑尚未退去,又出现了几丝冷峻的表情。他扶了扶滑下来的眼镜暗暗想道:“今天的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如果说得过分反而影响大局,还不如谈点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还是留待以后再讨论吧!”张闻天带着几分勉强地笑着,“国焘同志现在已经在指挥全军的岗位上了。我看英雄已经有了用武之地,还是研究一下早点打松潘吧!下面指战员早就急了……”
“我心里何尝不急!”陈昌浩的语气有些硬。“我和徐总指挥都向国焘提过,国焘说:打松潘没有问题,只要组织问题解决了,就立刻打!”
“组织不是已经解决了吗?国焘同志不是就任了总政委吗?”张闻天的语气也硬起来了。
陈昌浩和缓了一下,笑着说:
“国焘同志早说了,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地位,是要整个的组织与现实的情况相适应嘛!”
张闻天又沉默了。他望了望当年的这位同窗,这位年轻的弟弟,在肚子里叹了口气。
双方的意思都已表达,双方最重要的话——争取对方站到自己一边——都没有讲出口来。即使讲出口来也不会发生作用。于是双方都放弃了努力,重新又谈起在莫斯科学习时的生活,那个一开始就谈了颇长时间的话题。
午饭是棒子面饼子和几样简单的蔬菜,这在当时情况下已经是最高的规格。吃饭时各人想各人的心事,交谈的都是无关紧要的话,不过避免冷场罢了。最后分手时,陈昌浩捧了一块当地出产的粗呢衣料,笑着说:“洛甫同志,你把这个送给刘英吧,再往北去还是用得着的。”张闻天也不推辞,让警卫员接过去了。
张闻天在归途上不免心中懊丧,暗中感慨道:如果路线上发生分歧,即使再好的朋友也无济于事。这样一路想一路走回到了索花寨子。毛泽东正在村前踱步,手里拿着树叶子裹起的卷烟。
“怎么样,洛甫,谈得如何?”毛泽东停住脚步,带着期待的神情。
“不佳!”张闻天摇摇头,叹了口气,“有些人就是这样,只晓得追随个人,心目中没有党,没有真理。”
毛泽东的心凉了半截,急问:
“打松潘的事,他可同意?”
“陈昌浩说,打松潘他是同意的,但是,要等中央调整了组织再说。”
毛泽东一听急了,他把烟蒂一甩,露出了怒容:
“张国焘不是总政委了吗?他还要调整什么组织?”
“他们的意思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都要调整。”
毛泽东激怒了。他习惯地卡着腰怒气冲冲地说:
“这是讹诈!是利用党的困难进行讹诈!”
“这自然是讹诈,是政治讹诈。”
“张国焘不打,让一、三军团打!北进是谁也挡不住的!”
毛泽东的性格,正象棉里藏针。他平时谦恭温和,具有较强的克制力;但是也有克制不住的时候,那时就如火山爆发,要大大燃烧一场。今天他的双眼闪着火星,样子也很怕人。
张闻天从旁劝慰道:
“泽东,我看还是从容商议吧。回头同恩来讨论一下再说。”
这时,从那边过来一支红军小队,约有二三十人。人人灰尘满面,军服褴褛。队伍里有人牵着一头乌黑的牦牛,驮着两个口袋,后面还跟着四五只羊子。看样子很象一支筹粮队从远处回来,个个脸上露出倦容。
毛泽东和张闻天正在观望,只见走在前面的一个腰挎短枪的青年跑了上来,打了一个敬礼。他光着两条腿,穿着一条短裤,脚上蹬着一双小小的草鞋。军衣褂子上掉了两个扣子,前襟也被荆棘挂得几乎成了布片。毛泽东端详着他那年轻秀丽的面孔,觉得好生面善,却又一时想不起名字,就问:
“你是谁呀?”
“毛主席,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樱桃!”说着,她的两只眼笑成豌豆角了。
“哦,你是樱桃?”毛泽东仔细一望,顿时惊呆了。真想不到那个十分美丽的姑娘,今天成了这样。她的乌亮的头发不见了,脸晒得黑中透紫,就象这里草原上的人们。更不知道她为什么穿着短裤,两条腿上满是一条一条的伤痕。全身上下,只有那微微隆起的胸脯,还有草鞋上两朵小小的红缨子,是作为一个女人的标志。想不到,真想不到当前的生活竟把我们的女同志变成了这样。毛泽东不禁一阵心酸,握着樱桃的手,顿时热泪盈眶,背过脸去,好半晌说不出话来。停了好久,才说:
“天这么凉,你怎么穿着短裤?”
“我们净爬大山、钻树林了。”樱桃笑着说,“我的裤子挂成了片片,我就干脆截去,给同志们包伤用了。”
“你的头发呢?”
“我的头发,”樱桃不好意思地说,“已经成了虱子窝了。以前我们女同志在一起,就互相捉,现在怎么办?我一怒之下,就统统剪了。这算什么,反正以后还要长的。”
她嘻嘻一笑。
红军小队迈着疲惫的脚步走过去了。驮着粮食的牦牛和几只羊子还在后面慢慢地走。张闻天顺手指着问:
“这些都是买来的吗?”
“是的。”樱桃答道。“买来这些东西多不容易呵!这次牺牲了好几个同志,金雨来同志也牺牲了……”
“什么,金雨来也牺牲了?是遇见藏军了吗?”
“不,是饿死的。”
毛泽东神色黯然,仿佛喃喃自语:
“为了一个人难填的欲壑,付出了多少代价!”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