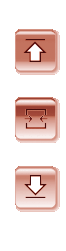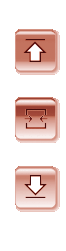|
|
|
|
第 十 一 章
|
火辣辣的阳光,逼射在签子门边。窄小的牢房,像蒸笼一样,汗气熏蒸得人们换不过气来。连一丝丝风也没有,热烘烘的囚窗里,偶尔透出几声抑制着的呻吟和喘息。
“吱——”
近处,一声干涩的蝉鸣,在燥热的枯树丛中响起来。
刘思扬忍住干渴,顺着单调的蝉鸣声觅去,迟钝的目光,扫过一座座紧围住牢房的岗亭;高墙外,几丛竹林已变得光秃秃只剩竹枝了,连一点绿色的影子也找不到。
远处久旱不雨的山岗,像火烧过一样,露出土红色的岩层,荒山上枯黄的茅草,不住地在眼前晃动。迟钝、呆涩的目光,又回到近处,茫然地移向院坝四周。
架着电网的高墙上,写着端正的楷体大字:
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
切莫执迷……
又一处高墙上,一笔不苟地用隶书体写着黑森森的字:
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
墙顶上的机枪和刺刀,在太阳下闪动着白光……他的眼前,像又出现了今天早上那辆蒙上篷布的囚车,沿着颠簸的公路,把他押进荒凉无人的禁区,又关进这座秘密的集中营的情景。一个多月以前,被捕时的经过,也清楚地在他的脑际闪现出来:那天晚上,他的未婚妻孙明霞从重庆大学来找他。深夜里,他俩轻轻拨动收音机的螺旋,屏住声息,收听来自解放区的广播。透过嘈杂的干扰声,他俩同时抄录着收音机里播出的一字一句激动心弦的胜利消息。然后,他校正着两份记录稿,用毛笔细心地缮写了一遍。到明天,这份笔迹清晰的稿件,便可以送交李敬原同志,变成印在《挺进报》上的重要新闻。抄写完稿件,孙明霞就把钢精锅从电炉上拿下,倒出两杯滚烫的牛奶,又把两份记录的草稿,拿到电炉上烧了。在寒星闪烁的窗前,两人激动而兴奋地吃着简单的夜餐,心里充满着温暖。手表的指针,已接近五点,再过两小时,又该是另一个战斗的白天。孙明霞丝毫没有倦意,正娓娓地向他谈述学校里近来的情况:华为离开以后,孙明霞接替了他的一些工作,她和成瑶又是要好的朋友,她们在一起工作得十分愉快……
就在他们促膝谈心的时刻,楼梯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刘思扬心头一惊,立刻把刚写好的《挺进报》的稿件塞进书桌暗装的夹缝里藏好……就是这样突如其来,事前连一点预感也没有,他和未婚妻孙明霞同时被捕了。
直到被审讯的时候,刘思扬才明白是叛徒甫志高出卖了他。叛徒不知道他负责着《挺进报》的收听工作,因此敌人没有从这方面追问,刘思扬决心把这当作一件永不暴露的秘密,再不向任何人谈起。
刘思扬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戴着金色梅花领章的特务头子和他进行的一场辩论——特务头子高坐在沙发转椅上,手里玩弄着一只精巧的美国打火机,打燃,又关上,再打燃……那双阴险狡诈的眼睛,不时斜睨着自己的面部表情。一开口,特务头子就明显地带着嘲讽和露骨的不满。
“资产阶级出身的三少爷,也成了共产党?家里有吃有穿有享受,你搞什么政治?”
自己当时是怎样回答他的?对了,是冷冷地昂头扫了他一眼。
“共产党的策略,利用有地位人家的子弟来做宣传,扩大影响,年轻人不满现实,幼稚无知,被人利用也是人之常情……”
“我受谁利用?谁都利用不了我!信仰共产主义是我的自由!”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无理的话,让党和自己蒙受侮辱,这是不能容忍的事,当然要大声抗议那个装腔作势的处长。
“信仰?主义?都是空话!共产党讲阶级,你算什么阶级?
你大哥弃官为商,在重庆、上海开川药行,偌大的财产,算不算资产阶级?你的出身、思想和作风,难道不是共产党‘三查三整’的对象?共产党的文件我研究得多,难道共产党得势,刘家的万贯家财能保得住?你这个出身不纯的党员,还不被共产党一脚踢开?古往今来各种主义多得很,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好好研究一下三民主义……”
刘思扬到现在也并不知道特务为什么对他说这样的话,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像别的同志一样遭受毒刑拷打。这原因,不仅是他家里送了金条,更主要的是,作为特务头子的徐鹏飞,他难以理解,也不相信出身如此富裕的知识分子,也会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因此,他不像对付其他共产党人一样,而是经过反复的考虑,采取了百般软化的计策。当然刘思扬并不知道,也不注意这些,他觉得自己和敌人之间,毫无共同的阶级感情。
“阶级出身不能决定一切,三民主义我早就研究过了,不仅是三民主义,还研究了一切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主义,但我最后确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真理。”
“凭什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那特务处长,居然颇有兴致地问。
“在大学里,我学完了各种政治经济学说。最后,才从唯物主义哲学,‘资本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找到了这个真理,只有无产阶级是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只有它能给全人类带来彻底解放和世界大同!”
“少谈你那套唯物主义哲学。你到底想不想出去?”特务的声音里,仍然带着明显的惋惜之意:“你又不是无知无识的工人,我现在对你的要求很简单,根本不用审问,你们的地下组织已经破坏了!你在沙磁区搞过学运吧?你的身分,还有你的未婚妻的身分,甫志高全告诉我了!他不也是共产党员?他比你在党内的资历长得多!但他是识时务的人,比你聪明!”
“要我当叛徒?休想!”
“嗯?你是在自讨苦吃,对于你,我同意只在报上登个悔过自新的启事。”
“我没有那么卑鄙无耻!”
“嗯,三少爷!路只有两条:一条登报自新,恢复自由;一条长期监禁,玉石俱焚。”
刘思扬记得,他当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对方的威胁,并且逼出了敌人一句颇为失望的问话:
“你想坐一辈子牢?”
“不,到你们灭亡那天为止!”
“好嘛!我倒要看看你这位嫩骨细肉的少爷硬得了多久?
出不了三个月,你敢不乖乖地向我请求悔过自新!”
“向你请求?休想!”
就这样,结束了敌人对他的引诱,于是他被关进一间漆黑而潮湿的牢房。再次被提出去时,已经天色漆黑,似乎被押过一片草地,还碰到一棵树,也许是个有花草的庭园,接着,又进了一条漆黑的巷道。几个人和他并排走。耳边听见一阵吆喝,“举枪!”后来就是“砰砰”几声刺耳的枪声,在巷道深处回响。他想再看这世界最后一眼,面前仍是一片漆黑,什么也望不见,黑暗中,他和一些人高呼口号……可是,子弹并未穿过他的胸膛,原来是一场毫无作用的假枪毙。又押回牢房时,他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和一个青年工人关在一起。工人叫余新江,也是被甫志高出卖的。从此,两个人成了同甘共苦的伙伴,互相支持、鼓励,直到今天早上,囚车又把他和重伤的余新江押进这秘密的集中营。
从被捕以后,再没有见过明霞。除了假枪毙那天晚上,听见过她高呼口号的声音。不知此刻,她关在什么地方,也许和自己一样,押进了这座集中营?
刘思扬从风门口微微探出头去,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他的眼睛发酸。他忍受着酷热和喉头的干燥,左顾右盼,两边是一排排完全相同的牢房。他记得,他和余新江关进的这一间,叫楼上七室。在这间十来步长,六七步宽的窄小牢房里,共了二十来个人,看样子都是很早就失去自由的人,也不知道这些人当中,是否有自己的同志和党的组织。楼下也和楼上一样,全是同样的长列牢房。一把把将军锁,紧锁着铁门,把集中营分割成无数间小小的牢房,使他看不见更多的人,也看不到楼下,只能从铁门外楼栏杆的缝隙里,望见不远处的一块地坝,这便是每天“放风”时,所有牢房的人可以轮流去走动一下的狭窄天地。
地坝里空荡荡的,在炭火似的烈日下,没有一个人影……
对新的集中营,他还不熟悉,保持着某种过分的拘谨。对这里的一切,他宁愿缓缓地从旁观察、了解,而不肯贸然和那些他还不了解的人接近。这就使他虽然生活在众多的战友中间,却有一点陌生与寂寞之感。他自己一时也不明白,这种感受从何而来,是环境变了,必须采取的慎重态度,还是那知识分子孤僻的思想在作怪?
太阳渐渐偏西了,可是斜射的烈焰给闷热的牢房带来了更燥辣的,焦灼皮肉的感觉。
高墙电网外面,一个又一个岗亭里,站着持枪的警卫。佩着手枪巡逻的特务,牵着狼犬,不时在附近的山间出没。
目光被光秃的山峦挡住,回到近处;喉头似火烧,连唾液也没有了,这使他更感到一阵阵难忍的痛苦。“出不了三个月,你敢不乖乖地向我请求悔过自新!”徐鹏飞的冷笑,又在耳边回响……向敌人请求悔过自新?刘思扬咬着嘴唇,像要反驳,又像要鼓励自己,他在心里庄重地说道:“一定要经受得住任何考验,永不叛党!”
回头望望,全室的饮水,储存在一只小的生锈的铁皮罐子里,水已不多了,然而谁也不肯动它,总想留给更需要它的人。刘思扬又一次制止了急于喝水的念头,决心不再去看那小小的水罐。
他的心平静了些,勉强挤出一点聊以解渴的唾液,又向对面的一排女牢房望去。这时象要回答敌人的残暴和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似的,刘思扬心底自然地浮现出一首他过去读过的,高尔基有名的《囚徒之歌》,他不禁低声地独自吟咏起来,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却逃不出牢监,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
挣不断千斤锁链!
就在这时候,一阵轻微的清脆的歌声,传了过来,牵动了刘思扬的心。声音是那样的熟悉,吸引着他向对面的女牢房凝目了望。在一间铁门的风洞旁边,意外地看见了那一对睽别多日的,又大又亮的眼睛!孙明霞的嗓音,充满着炽热的感情,仿佛在他耳边低诉:这才值得人牵挂——就说他是个穷人也罢,
有钱岂买得爱情无价?就说他是个犯人也罢,
是为什么他才去背犯人枷?…………
随着清脆的歌声,那对火热的目光,久久地凝望着他。刘思扬清楚地看见孙明霞头发上扎着一个鲜红的发结,这时他象放下了一副重压在肩上的担子,心情立刻开朗了。明霞就在这里!两个人共同战斗,同生共死,使他感到一阵深深的安慰和幸福。
“水!……水!”
身后传来一声声干渴难忍的低喊,昏迷中的余新江又醒来了。刘思扬的眼光留恋地离开了对面女牢的铁门,转过身,回到周身被汗液湿透的余新江身边。余新江半昏半醒地仰卧在楼板上。他的双手又把衬衫撕开了,胸脯上露出正在化脓的刑伤,那是炽热的烙铁,烫在皮肉上留下的乌黑焦烂的伤斑。他张着焦裂的大口,一次次吐出一个单纯的字:
“水!……水!”
刘思扬的目光,再次扫过屋角,那储水的铁皮小罐,就放在那里。他下了决心走过去,提起水罐,可是水罐已经变得很轻了,只剩下最后几口。刘思扬茫然地望了望这间象口闷热的铁箱似的牢房,人挨人,挤在一起,但他们都强自忍耐着,不肯把小罐里的水倒光。刘思扬迟疑了好久,才从小罐里倒出一点水,回头看看满脸烧得通红的余新江,又犹豫地慢慢加上几滴。
一个靠近墙角的人,两腿肿胀,乌紫发黑,双手捂住下巴,噙着杆黄泥巴烟斗,闷声不响。这时抬起头来,随眼望望余新江,又望望刘思扬,他挣扎起来,夺过刘思扬手上的小水罐。
“他发高烧,才受刑下来,多给他喝口水,不要紧嘛!”
说着话,那人张开嘴,露出几瓣大牙齿。随着说话的动作,嘴上咬着的那根装着竹管的黄泥巴捏成的烟斗,上下晃动着。他把罐里的水,咕噜咕噜全倒进刘思扬拿着的碗里。然后把罐子往墙角一扔,两手比画着说:
“点点大个罐罐,一泡牛尿都接不完!”
刘思扬端着半碗水,感激地望着面前这个率直的农民模样的人。他望着那人吸惯叶子烟的焦黄牙齿上挂着的一缕缕血丝,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你的嘴流血!”
那人摇了摇头,坦然地说:“牙龈烂了,手脚也……”
刘思扬痛苦地皱着眉头:“这是坏血病,营养不足……”
“这里哪像我们乡下,青菜萝卜齐全罗,咋个不得这些怪病嘛。你看,连烟都没得抽的!”
说着,他们抬起余新江汗湿的头。一滴水刚刚碰上嘴唇,舌尖便伸了出来,双手又不住地抓着喘不过气来的胸口。
刘思扬和那人对视了一下。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似乎都在说:要是还有水该多好!可是看看倒空了的水罐,两人都沉默着。刘思扬随手拿起自己的西服上装,举在余新江身畔,权且遮住从签子门缝中直射进来的斜阳的毒焰。那人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柄废纸贴成的破扇,递了过来。刘思扬便放下衣裳,用扇子给余新江扇来一阵阵带有浓烈汗臭的热风。
“你是从农村来的?”刘思扬望着对方的空烟斗,烟斗的泥巴磨得亮亮的,却没有烟火烧过的痕迹。
“乡巴佬哇。我叫丁长发。家住川西新津县三汇场,一抹平阳的好地方呵,就是地主恶霸多了点!”
“我叫刘思扬。”
“听说过罗,他叫余新江嘛。”丁长发接口说道:“你们是重庆大码头的,到这渣滓洞集中营里头,开初几天,怕不大惯适?你看,硬是比县份上的班房恼火。”丁长发吐口长气,又说道:“嘿,没得烟抽。老子做个烟杆,叭几口过过瘾!”
刘思扬苦笑了一下:“没关系,过些时候,就习惯了。”
“这个余新江,是个工人,长一手老茧。坐两年牢,你屁股上也要长牢茧嘞!”丁长发又咧开嘴巴,爽直地笑了笑,转身坐回原处。
在沉闷的气氛中,破扇子嗦嗦地发出单调的声响。刘思扬的目光,不经意地打量着对面的墙壁。他的目光忽然停滞了,手里的破扇子,也停止了摇动。墙角上刻画着一些纵横交错的字迹,几行显眼的暗红色的字,扣住了他的心弦:
中国共产党万岁!吕 杰 绝笔
是鲜血写成的字!刘思扬心里不禁浮起一阵异常庄严的感情。他不知道吕杰是谁,可是吕杰写下达几行绝笔时那种光芒四射的思想感情,他完全能够理解。有一天,当自己为真理而奉献生命的时候,能像吕杰这样毫无愧色地迎向敌人的枪口,讲出这样的话吗?刘思扬问着自己,又进一步借着阳光,贪婪地搜索着墙角的各种字迹。在吕杰绝笔的旁边,是谁用指甲深深地刻画出一条条的痕印,这又表示着什么呢?刘思扬一时猜不透它,目光向旁移动,一处耀目的字句,立刻映进了他的眼帘: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是谁写下了这样透彻的警句?刘思扬不禁问着自己。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刚刚大声读完这首洋溢着战斗激情的诗篇,刘思扬忍不住急切地询问:
“这是谁写的诗?”
“我们军长!”一个洪亮的声音,应声答道:“叶挺将军!”
刘思扬一回头,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向他走来。和他洪大的声音相适应的,是他的军人气派。他穿一身整洁的灰布军衣,不管天气多热,领口的风纪扣,总是紧扣在脖子上,他不像其他的人,只穿短裤,却穿了一条长长的军裤,衣袖高高卷起,露出一双黝黑的手臂,头上端正地戴着一顶军帽。
“我是新四军的。军长在楼下二室写过这首诗,我把它抄在墙上给大家看。”这位新四军战士,毫不隐瞒他的行为,继续说道:“我叫龙光华。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我在中原军区参加突围作战,挂了彩。”他解开军服,露出右肩上一处巨大的伤疤,“醒过来已经被俘了。我叫反动派补我一枪,他妈的,却踢了我一脚!我们被俘的十一个人,有的伤重牺牲了。有的一路上被反动派折磨死了。就剩下我们王班长和我两个,今年才押到这里。我们王班长关在楼下二室,就是我们军长住过的那间牢房。活不出去就算了。要是活了出去,再端起机枪,我要叫反动派吃够革命子弹!”
来到这间牢房的最初几小时,除了照顾重伤的余新江,除了观察这集中营的环境,刘思扬很少和同牢房的人们谈话。他觉得自己的衣着太好,又没有受刑,难免要引起别人对他的怀疑,甚至遭到歧视。可是,现在,他的感情渐渐变化,想和这豪爽的军人,以及那直爽的农民多谈两句,了解一下情况,以便日后寻找狱中可能有的党组织。刚想到这里,一个特务摇着一把蒲扇,从签子门边晃过,接着便传来一阵开铁锁的响声。
“楼五室,出来放风!”
楼五室没有脚步走动的声音。
“放风!”
还是没有动静。
“喊你们出来!”
“楼五室怎么啦?”刘思扬把头探出风门,看见特务正摇着蒲扇,在楼五室门口吆喝。
“好几间牢房,都病得没有人起来放风了。”背后,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说。
“楼六室放风!”特务干涩地叫了一声,又在开动铁门。刘思扬退回余新江身旁,心里猜想着:大概楼六室没有完全病倒,有人出去了,所以特务没有再怪声嚎叫。
过了一阵,铁门上的锁叮当地响了,特务打开了楼七室的牢门。
“出来放风!”
丁长发缓缓地移动一下身子,揩揩汗水又坐下去。满屋子的人,都没有想站起来的动作。只有龙光华,走到放便桶的角落,伸手去提那桶装得满满的粪尿。
“让我来吧。”刘思扬从未做过这样的苦役。此刻他要求着自己,努力习惯新的生活,也希望逐渐接近同牢房的战友。
他丢下扇子,自告奋勇地走上前去。
“好吧,你去倒尿桶,我去找水!”龙光华拾起扔在墙角的小水罐,大步走出牢房。
刘思扬抓紧便桶上的粗绳,用力往上提,额角上冒着汗,手臂颤动着,他卷了卷苦麻而不灵活的舌头,积聚起全身力气,踉跄着把便桶提了出去。下了楼,沿着高墙,走过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地坝,墙角里的野草和苦蒿也枯萎了,他不知道龙光华还能从哪里弄到一点水回来。
厕所里到处撒着恶腥的竹片,纸块。在这些竹片、纸块上面,沾连着一片片黑色的血块,一摊摊酽痰似的粘液。绿头苍蝇,营营地飞扑;密密麻麻的蛆虫,蠕动着身子,一堆挨一堆地爬着……
刘思扬倒过便桶,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头脑像要胀破似地膨胀着,嗡嗡地响,手脚也麻木了。他站不稳,依在墙边,昏昏沉沉地过了好一阵。这一个多月以来,他住在二处的黑牢里,不见阳光,受着折磨,身体比过去衰弱多了。他挣扎着,艰难地走出厕所。
狭窄的地坝,这回变得特别空旷起来。楼梯也变得又高又陡,刘思扬走了两步,就觉得耳鸣目眩,再也无力走动了。
一间间锁死的牢门,在眼前晃动……
“你怎么啦?”龙光华赶上来,问了一句,从他手上接过便桶。回到牢房,他把水罐朝墙角一扔。大声骂着:“一点水都找不到,他妈的反动派,真做得出来!”
刘思扬定定神,又回到余新江身边。牢房里的人们,挨个地横躺着,困难地扭曲着身子,在滚烫的楼板上,发出一阵阵难忍的喘息。
“他妈的!”龙光华的眼睛冒出怒火:“渴死了,我们也不缴枪!”
屋角里,一个秃顶的老头子,皱着眉梢,艰难地撑起上身,向牢房四周看了看,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突然伸手捂住胸口,咯咯咯地咳了起来。他的喉管里堵塞着一块东西,上下不得,把脸憋得通红,接着变成苍白。嘴唇也青紫了,气喘越急促,呼吸就越发艰难了。
这边的丁长发和龙光华,被急促的喘哮惊动了。两个人赶快走了过去,一个吃力地扶住老头子,另一个用溃烂发黑的手轻轻地给他捶着背。
一股浓烈的血腥气,从老头子口里喷涌出来。他的口张得大大的,两只白眼珠呆直地望住签子门,昏过去了。
过了一阵,老头子才苏醒过来,翻着两只白眼,直瞪着低矮的屋顶。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睁大了眼睛。
“老大哥,你还是喝口水吧。”旁边有人请求着说。说话的人似乎还不知道水罐早已空了。可是刘思扬马上又听见那人补充了一句:“我在碗里,给你留了一口。”
“这阵好多了。”老头子细声回答,微弱的语音,拖得很长很长,他慢慢地说:“水——留——给——伤——员——”
是吃饭的时候了,室外传来一阵混合着焦糊与霉臭的味道。可是刘思扬除了口干舌燥,毫无饥饿的感觉。出去提饭桶的龙光华,在牢门口大声喊道:
“同志们,吃饭了!”
刘思扬抬头看了看,饭桶里面尽是乌黑的碎石似的硬饭粒,他卷了卷麻木的舌头,涌出一种厌恶的感觉,扭回头,再也不愿看那饭桶。
龙光华把饭桶撂得咚咚响,想惊醒所有昏睡着的人。可是,人们像早就知道桶里边的东西似的,隔了好久,还是一潭死水般的沉寂,没有人抬起头,甚至不愿睁开眼皮看一看。
龙光华站在那里,眼圈遽然红了,一眶热泪,突然涌上这豪壮军人的眼帘,他挪开步子,站到老头子身边,恳求地说:
“两天了,大家一点东西不吃!老大哥,身体是我们革命的本钱呀!”
被称作老大哥的病弱老头子,困难地支起上身,依着墙,喘息着,他的声音里,出乎刘思扬意外,竟出现了一种坚定不移的刚毅气概:“大家起来吃饭……大家都吃一点……”语音里带着激动的颤抖:“好吧,先给我舀……”
满屋昏睡的人渐渐睁开了眼睛。
刘思扬迟疑着,走了过去。他挖开干硬的饭粒,给老大哥舀了大半碗,又把筷子递给他。老大哥吃了一口,喘着气,脸色也变了,又捶了捶胸口,才勉强咽下去。接着,他用筷子敲敲碗,“大家……都吃一点……别叫敌人小看我们!”
望着老大哥的动作,满屋的人都勉力坐起来。丁长发最先露出笑脸说:“给我舀嘛,我吃一碗!”
又一个人像接受任务似的举起手,毫不犹豫地喊:“我来半碗。”许多人递过碗来,“也给我一点……”“我吃小半碗……”“我也……”
刘思扬强烈地感到,这些声音,都是忍受着痛苦,咬着牙关迸出来的。此刻他还不知道,狱里的缺水,完全是敌人有意制造的。因此,在极度干渴之下的吃饭,竟成了一种战斗,一种不屈服于迫害的战斗。顽强的斗争意志和不屈的决心,鼓舞着人们听从老大哥的劝告。刘思扬一个一个给大家舀了饭,自己也勉强咽下几口干硬霉臭的饭粒。他又给仍然昏迷不醒的余新江留了半碗……看见大家都放下碗筷时,他忽然冲动地站了起来,提着饭桶在室内绕了一圈,龙光华朗声叫道:“再给我舀!”又干脆添了大半碗,另外的人,谁也不再伸过碗来。刘思扬只好把大半桶剩饭,送到牢门外去。
院坝里摆着一排饭桶,都装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人动过。
刘思扬目不转睛地盯住成排的饭桶默默站着,心里翻动着一阵复杂而痛苦的感情。他不知道这种迫害,将要继续到什么时候。
黄昏,在郁闷的寂静中悄悄来临。
特务拉开铁门,反复查看每间牢房,单调的点名的呼号声,像凶残的野兽,在荒山野谷中嚎叫。夜空繁星闪烁,天边卷起一片乌云。又黑又闷,屋顶像一口铁锅,死死地扣在头上,叫人透不过气。蚊虫嗡嗡地夹杂在呻吟声中,一群群地,呼啸着,穿过铁签子门缝,潮水似的涌了进来。赤条条地躺在楼板上的,被灼燥、闷热、刑伤和病魔折磨倒了的,连血液都快要干涸的人们,听任蚊虫疯狂地进攻,连挥动手臂驱赶它们的力气都没有了。
刘思扬勉强躺在火热的楼板上,不知过了多久。
半夜里,屋脊上传来了呼呼的风声,闷热的牢房清凉了一些。远处,闪灼的电光,渐渐近了,听得见沉闷的雷声。突然一声惊雷,刘思扬被震醒了。
“梆!梆!”
一阵竹梆声在耳边响起,一处岗亭敲过,另一处岗亭又梆梆地敲响。被惊雷震醒的刘思扬,默默地听着那巡夜的梆声,一声接一声,无休止地敲着。
“梆梆梆!梆梆梆!……”
“梆梆梆!梆梆梆!……”
梆声突然急促起来。
“听,又要提人!”黑暗中是谁紧张地说。
电光闪闪,又是一声炸雷!
狼犬嚎叫着,像从远处猛扑过来。隔壁牢房的铁锁响了一声,接着,传来推开铁门的哗啦啦的巨响。
“5013号!出来!”
“5013号!”
听见这声音,刘思扬扑到铁门边,从风洞口伸出头去,在狂风呼啸,电光闪亮的瞬间,瞥见一个身材瘦长的人影,从容地跨出牢门。立刻,一副闪光的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
强烈的电闪,忽然照亮了楼口。铐上手铐的人在强光照射下,跨下楼梯,又向前走。在对面一间女牢门边,他突然站住脚,像铁铸的塑像似的崛立在狂风和闪电里,似乎要等待和谁告别。正在这时候,一个头发长长的孕妇,披着带血的长衣衫,突然出现在女牢的风门口。她伸出了双手,隔着铁门,紧紧抓住那个身材瘦长,戴着手铐崛立的人。
“他们是谁?”有人在问。
“不知道,昨天才从云南押来的。”黑暗中有人应了声。
……女牢风门边紧握着的双手分开了,远远地分开了。戴着手铐的人,霍地回转身,高举双臂,在震耳的雷鸣中,向所有的牢房昂然呼唤:
“同志们,永别了。解放那天,请代向党和同志们致敬!
共产主义万岁!”
滚滚雷声中,又是一阵耀眼的闪电,刘思扬泪汪汪的双眼,看见了长发面向墙角站着,他的指甲在对面的墙头,趁着电闪又深深地刻下一道清楚的痕印。刘思扬明白了,他刻画的那一条条痕印,正是无数次秘密屠杀的铁证。这时透过雷声传来几声枪响,接着便是一阵令人心悸的狼犬的嚎叫。
粗大的雨点,狂暴地撒落在屋顶上,黑沉沉的天像要崩塌下来。雷鸣电闪,狂风骤雨,仿佛要吞没整个宇宙!
丁长发的指甲缝里嵌满了石灰粉屑,捏成了拳头。
“他妈的!”龙光华摇着铁门咬牙切齿地喊:“给我一支枪,我杀完这群野兽!”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