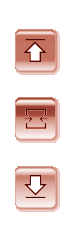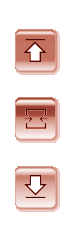|
|
|
|
二一 反脸无情
|
六月底,何福荫堂的管账二叔公何不周到省城去跑了一趟。他选定了一个星期天的日子。这一天的天气热得不行,他自己的身体又胖得不行,因此他决心连一步路也不走,雇了一只那种叫做“四柱大厅”的木船,自己躺在上面,让艇家把他划到省城去。一路上的村村、树树,水水、天天,他都让给艇家去赏玩,自己闭着眼睛,打一会儿呼噜,又咂一阵子油嘴。其实说他睡得很舒畅,也是冤枉了他。他只是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地躺着不动,在那里反复想着胡杏这桩该死不死的怪事儿。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大人物象袁世凯、龙济光、张作霖,极其威武,极其令人崇敬的,却慌慌失失地死掉了;可是象胡杏这样的臭丫头,死了也不值个烂桔子,却偏偏活了转来。他想到这里,不免在心里又骂又叹道:“呸!好不知羞!还铰了辫子呢!我看你索性剃光了头,当师姑吧!这世事也真是——不平的事儿总断不了有呵!”坐了半天船,又坐了好一阵子黄包车,他才算到了三家巷。这天却巧,何应元、何胡氏、何守仁都在家。因为事关机密,他们把他让到头一进南边那个华贵的大客厅里,由最漂亮的使妈阿苹出来奉了茶,掩上房门,才和他说话儿。省城的人都穿着轻软雪白的熟绸,摇着鹅毛扇;乡下人却穿着香云纱,摇着“油纸弓”。一黑一白,对衬十分鲜明。闲叙了老半天,何五爷才问起胡杏的事儿来。何不周见主家问,就叹口气说:“唉,真是好人不长命,祸害几千年呢!”跟着就把五个月来胡杏病危,胡柳吵闹,周炳服侍,工人罢工,一直到胡杏命不该绝,逐渐痊愈的情形,也不管别人知道的、不知道的,也不管从前的信中提过的、没提过的,一概从祖宗十八代讲起。讲了约莫一个时辰,才把话说完了,又加上说道:“这真是好心不得好报,好柴烧烂灶!这边老五侄哥、老五侄嫂、大侄孙少爷送那贱骨头回家,谁不知道你们的心呢,是想叫她断气之前,骨肉团聚一番呵!是再好也没有的好心肠呵!可是那贱骨头没有死,这就坏了。那些穷鬼不逞之徒,就说起不干不净的话来了。什么黑心烂肝呀,连棺材钱都想省掉呀,吃人不吐骨头呀,什么好听的都有了,倒好象无情无义的,是你们这边了。这真是好人难做——弄巧反拙呀!”何五爷立刻指正他道:
“二叔,你们就是不读圣人诗书之过。什么弄巧反拙!”
何胡氏想了想道:“只怕那个阿杏是死了。这个是妖精托世的!”
何不周哼哼哈哈地呻唤了老半天,才又说道:“要不是有那十大寇在那里为非作歹,单凭周炳一个人,他也救不活那贱骨头!这十大寇就是八字脚,那是审都不用审的!近来稽查站打死了一个共字号,听说就跟那十大寇有牵连。人家说得千真万确呢!可是咱有什么办法?人家十大寇有你们那边的亲家管着,咱们管不着。只为有陈家护着他们,连稽查站都不敢认真动他们呢!依我看,咱们不如把农场的土地收回来。那就一了百了,什么都了了!”
何应元正在思算着,踌躇不决。何胡氏捂住耳朵,不爱听这些事情。何守仁一直不做声,到这时却开腔了。他说:“陈家他们是新派。他们一天到晚,攻击我们是旧派。我还惹得起他们?只怕咱们堂堂县长,也惹不起他们呢!”
何胡氏只管自己说自己的道:“我们那个身娇肉贵的倒进了癫狂院!人家那么一只烂货倒白白地好起来了!真便宜了她!”她底下的话没说出来,可是谁都明白:当初以为她准死无疑,说了不要了;这阵子她却好了起来,想要也要不回来了。何守仁觉着事情没法办,只是摇头。何五爷看见这样,就教训他道:
“亏你还是个当官作吏的角色!你光摇头干什么?凭摇头就把事情办好么?咱们就该当机立断,把她要回来!咱老二也不是一辈子住癫狂院的。有一天回家来了,没个人伺候他成么?咱们当初是说了不要,可那只是一句话。她的卖身契还在咱手里,这就大有文章可做。契约、契约——就是恐口无凭,才立此为据的呀!”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何不周告辞回家。对于当老子的那种老谋深算,洞察世情,何守仁钦佩得五体投地,心里想:“姜就是越老越辣,一点不假!”何不周走了之后,一家人还没有散,何守仁的大舅子陈文雄从外面闯了进来。这外号“外国绅士”,又经常被人称做“独创家”的洋行经理如今快到三十了,正是英年有为的时候,最近却遭了一点小小的不如意。一千九百二十六年,英国人让他当了兴昌洋行的经理,是为了他能够对省港大罢工。起一点破坏的作用。他自己也知道,英国人办事,是讲求实效的。可是到了一千九百三十年,人家干么还要请他当经理呢?于是英国老板找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借口,把他开除掉了。这几天,他正在进行着十分紧张、十分剧烈的活动,准备另外搞一些什么名堂。今天,他一走进客厅,就大声叫嚷道:
“亲家老爷!亲家奶奶!二姐夫!你们都在这里摇鹅毛扇子,看样子,又要搞什么阴谋诡计了吧?”从那说话的狂劲儿看来,他今天的心情极好。
何应元把刚才商量要回胡杏的事情对他说了一遍。陈文雄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也真是,就钉着要一个人。纵然她比区桃还漂亮,又能值几个钱?给守义兄弟另外买一个用用就是了!”后来他又转了口气道:“不过,不谈这些小事情了吧。我有一件正经要紧的大事,来找你们。”何应元、何守仁爷儿俩听了,都有点不痛快。何守仁给他两句听听道:“什么正经要紧的大事?光景不外是这个洋行、那个洋行!”陈文雄点头大笑,使唤何应元听不懂的英文说:“塞尔屯利!塞尔屯利!”何守仁接着说:“这真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只有英国人才有这么狠的心,只有英国人才有这么毒的手!要是我,我真做不出来!”陈文雄哼哼地冷笑道:“这是战争,不是做诗!什么叫做商战?不过我倒不在乎这些。不跟英国人做买卖,我可以跟日本人做买卖。英国老板不雇我,我就自己当老板。英伦三岛和扶桑三岛,在我看起来,都是岛而已!”何守仁说,“你总是乐天派。”陈文雄耸了一个欧洲的肩膀,说:“我过来惊动你们,就是为了这桩大事。我爹不知怎样,心血来潮,说要创办一个‘庚午俱乐部’,把省城所有有名有姓的人物,都包罗在内。看他的意思,是想邀请大家投资,办一个专做东洋货的大商行。另外,还想筹办一些别的实业,象纺织、染印这一类的东西。他那计划之大,筹算之精,我看了都头疼。主体是那东洋商行。好象连名字都有了呢,好象叫做‘东昌行’呢。你们何家也来俱乐部玩玩,投点资,怎么样?”何守仁不做声,只拿眼睛望着爸爸。何胡氏听得不耐烦,就站起身,拍拍屁股走了。何应元不动声色,轻轻摇那花白干瘦的脑袋。过了一会儿,这才冷酷严峻地回答道:“工商业投资嘛,按照我们的家规,是沾都不沾的。这叫做不熟不做。按理说,我也知道你们找钱容易,也很稳当,可是我不想找那个钱。我也不明白,一会儿美国货是劣货,一会儿日本货是劣货,一会儿英国货又是劣货,你们说不定哪天一高兴,又要抵制了!”陈文雄也不相强,就说:“投不投资,那是闲事。你爱买房子,买地皮,只管买你的房子、地皮。参加庚午俱乐部,那才是要紧大事呢!”何应元父子答应了参加俱乐部,陈文雄才满意地走了。客人走了之后,何应元对那教育局长教育道:“你看,这不是活活的一个东昌行大经理的身分么?还要办实业呢!放着现成的花旗布、红毛布、东洋布,既多又好,你穿一辈子都穿不完,他却想创办纺织工厂!陈家的事儿你猜得准?你拿钱去入股吧,你拿钱去打水片吧,哼!”剩下给何守仁做的事儿,只有点头一桩了。
经过两三天的筹划,何家决定派出大奶奶房里最机灵的使妈阿贵,去震南村“迎接”胡杏“回家”。按照何五爷的训示,这桩事儿应该当做一桩大事来办。第一,要以礼相迎;第二,要点明胡杏的身分,是二少奶的身分;第三,要让胡杏光光鲜鲜,欢欢喜喜地回来。不用说,除了中学生何守礼之外,何家大小、上下人等,都明白这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儿。虽说按世俗的眼光看来,何家山高树大,谁不想挨挨靠靠,别说当他家的小媳妇儿,是巴之不得,就是再下贱的事儿,也有人抢着干呢!——可是胡杏,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阿贵听说主家要她去接胡杏,也一时没了主意,立刻到厨房里找阿笑、阿苹两人商量。到了晚上,又在大门外的白兰树下,找陈家的使妈阿发、阿财、阿添三个一道斟酌。阿贵对大家恳求道:“我干什么事儿,就撇撇脱脱,说做就做。惟独这一回心大、心小,不知去好、不去好。众位姊妹给我出出主意吧!”这时候阿贵已经二十八岁,尖尖嘴脸,那刁钻的劲儿,仍然不弱于年轻的时候。她们这六个人之中,年纪最小、住年妹出身的阿添,今年也二十七了,不过大家都认为她的懵懵懂懂,没分没数,跟十年前、她十七岁、当住年妹的时候没有两样。当下她首先发议论道:“人家说胡杏心灵,我说胡杏心塞!是我年纪大些,别人不要我罢了。如果何家要我,我宁愿嫁给那疯子!有名有分,一辈子穿金戴银,我怕什么?”最狡诈的使妈阿财挤挤眼睛说:“可不!这正是:有人辞官不愿做,有人漏夜赶科场呢!”为人势利,今年已经四十八岁的使妈阿发慨叹道:“论相貌,胡杏比得上天仙。要说脾气,那真是再温柔、再随和也没有的了!就是年纪,也不多不少,正正十六。这样的人儿,你打锣也找不着。可是就这一样:对何家就是不服,就是强!这也只怕是前世的冤孽呢!”何家三姐房里最老实的使妈阿笑说:“这样的事儿,你怎么好开口?人家病了,快要断气了,你才把人家赶出去,说什么一刀两断;如今人家好了,又象一朵花一样了,你又要人家回来当媳妇儿了。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天下哪有这么横蛮的理儿!要是我,我才不去!”看来阿笑的话是正理,大家都驳她不倒,也就不做声了。阿贵说,“笑姐既然这样说,我也不去了。留给大奶奶自己去吧!”何家二娘房里最漂亮的使妈阿苹虽然只有三十一岁的年纪,可她是二娘房里的,老爷跟大少爷的意旨,她总是先摸着几分,因此说话就有分量。当下她摇摇头说:“不去行么?你受人家的二分四厘银子,人家叫你做事,你不做!”于是有主张去的,有主张不去的,分成了两派嚷嚷。后来还是阿笑让了步。她说:“阿贵,你平素机灵,这时候怎么笨钝起来了?有那非去不可的话,你只当玩耍,也就去上一回就是了。我倒要提醒你一句:你要见机行事,切莫太过认真。能说就说几句,不能说就拉倒。横竖不关你的事儿,别叫人耻笑到你自己的头上才好。”大家都觉着朝这么办好,事情就决定了。
何家准备下的礼物可真不少,有吃的,有穿的,有戴的:两个大金漆盒子,一盒鸡蛋卷,一盒南乳小凤;两个布,一个黑竹纱,一个白柳条;两个首饰盒子,一个装着一只玉镯子,一个装着一副朱义盛金耳环。另外还有一个大红封包,里面封了二十块钱西纸的利市。以上这些,都是送给胡杏的。此外,又给胡源送了一把家用双料蓝布伞,给胡王氏送了一个软缎珠花包头,给胡柳送了一条象牙鸡心西金项链,给胡树、胡松每人送皮带一条、“足安居”的双底竹纱袜两双。小姑娘何守礼听说有人要去接胡杏表姐回来,十分高兴,也跳出跳进地叫嚷着,又拿一张做手工用的绛红蜡光纸,包了十个双银角子,要送给胡杏表姐买东西吃。东西收拾停当,阿贵又查看通书,挑选出一个上好吉日,才穿戴整齐,打着赤脚片子,拿扁担网络挑起礼物,走到西濠口,雇了一只小艇,朝震南村不慌不忙地缓缓划去。一早动身,过午就到了震南村的槐冲南渡口。阿贵挑好东西,一路走,一路向人打听胡杏家在哪里。等她走到胡杏家门口,全村都知道省城何福荫堂有人送礼来了。
恰巧胡源、胡王氏、胡柳、胡杏都在家。阿贵一见他们都认得的,就开口叫亲家老爷、亲家奶奶,又管胡柳叫柳姨,十分嘴甜;见胡杏体态娉婷,容光焕发,就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二少奶。胡源、胡王氏、胡柳见阿贵来得突然,叫得肉麻,不知道怎样对答才好,惟独那胡杏听见阿贵这样称叫,心窝一阵绞痛,脸上气得灰白。跟着,阿贵把礼物摆开来,一面摆,一面说,什么好听的话都说完了,那礼物也就摆满了一堂屋。最后,阿贵才说出来意:何家老爷、大奶奶、二娘、三姐、大少爷、大少奶、小姑姑都惦记着二少奶,想看看她,想找个高明的大夫给她瞧瞧,想接她回省城去住几天,好好地把身子保养保养,如此等等。胡王氏听了,一句话也答不出来,只顾在胡杏床上坐着擦眼泪。胡源拿手扶着天堂,反复叫道:
“那怎么成呀!那怎么成呀!那怎么成呀!”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含糊不清的。究竟说礼物不能收呢,说胡杏不能回去呢,还是说何家不该来要胡杏呢,谁也听不清楚。乱了一阵子,胡源和胡王氏又洗米、生火,给阿贵做饭,还叫胡柳上街市去买菜。胡柳刚走出巷口,胡杏又追了上来,两姊妹一面在田基上走着,一面商量对付何家的办法。最后,决定胡柳买了菜,去农场叫胡树、胡松弟兄俩回家;胡杏上小帽冈震光小学去请周炳来走一遭。商量妥当,两人分头行事。在胡家的破烂堂屋里,那些辉煌夺目的礼物仍然象个杂货摊似地摆开,左邻右里,大人娃娃,都联群结队地来看新鲜。对于那些玉镯子、金耳环、珠花包头、鸡心项链,个个都摸摸捏捏,爱得不忍释手。趁着胡柳、胡杏不在跟前的机会,阿贵一面喝茶、抽纸烟,一面把何家的恩德跟何家的威势给这两位亲家说得十分清楚,让他们好好地拿主意。最后阿贵说:“要是我对得上这么一门亲家,要我修行三辈子,我也乐意呢!”听了阿贵的话,胡源只是愕然地楞着眼睛,胡王氏只是重新擦着眼泪,都说不出一句正经话来。不久,胡柳买了菜回来,给阿贵炒菜、开饭。正吃饭间,胡杏也回来了。阿贵偷眼望望她,只见她一脸冷冷的威严,摸不透她的心思。刚吃完饭,周炳、胡树、胡松都到了。对于胡树、胡松这两个年轻小伙子,阿贵并不放在眼里;可是对于周炳,她却有着好感,同时也有敬畏之意,因此另眼相看。一见周炳个子高了,骨胳大了,英气逼人,象个大人的样子,也就亲亲热热地叫嚷道:“炳哥哥,炳哥哥!三年没见啦!你可好啦!跑了多少地方啦!快回三家巷看看大家啦!”周炳做出一种男人的沉着姿态,微微笑着,简单说了说这几年的情况,又问何家的阿笑、阿苹,陈家的阿发、阿财、阿添诸人安好。正说着话,急脚松等得不耐烦,就没头没脑地插嘴问道:“是什么鬼打了我们二姑?她怎么一下子发起善心来了?”
经他这么一提,话儿又落到胡杏身上了。阿贵把刚才说过的话,又对大家重复说了一遍,末了还加上说:“老爷吩咐过,要我们大家尽我们的礼,还要二少奶做身干干净净的衣服,欢欢喜喜地回去。依我看,他们财主家既然回心转意,亲家老爷这边也赏个脸给我们底下人,应承了吧!大家亲家上头,有什么三言两语的,不是弥弥缝缝地也就过去了?”这种言词,老实忠厚的胡松听了,很不受用。他拍了一下面前的矮方桌子,瓮声瓮气地说:“什么回心转意?什么弥弥缝缝?谁是你家的亲家?谁是你家的二少奶?人都要断气了,你家才不要的,如今人活转来了,你家又悔了,又要人了!怎么能这样反脸无情?哼,人不说人话!”阿贵瞅瞅大家的脸色,见所有的人都怒目而视,正在为难,周炳开腔道:
“阿贵姐,你素来机警,这回却上了那两只老豺狼的当!有话不会叫他们自己来说?你来挡灾?连二叔公何不周都不敢出头呢!你问问左邻右舍,看人家怎么说的?你再回去问问你们大少奶,看什么叫做妇女解放?什么叫做无产阶级解放?你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你怎么不向着受压迫、受剥削、受欺负、受侮辱、受折磨的穷人、苦人?就算你帮理不帮亲吧,理也不在那边嘎!”
阿贵听了周炳的话,就顺水推船地说:“世界上的事儿呢,也没有个定准的。碰到这样的机会,有人还求之不得呢!总之,这不关我的事儿。我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说得好呢,说不好呢,有你们两家在!”胡王氏觉着一个劲儿责备阿贵,有点过意不去,就接过来说:“是咯,是咯。阿贵姐好心好意,我们有不知道的道理?看目前这样子,事情也实在难。就劳烦阿贵姐回去说几句好话,只说孩子任性,不肯回去,也就罢了。不落家的媳妇,世上有的是呢!小杏子又不是下凡的天仙,又没有本事,脾性又臭,希罕她什么?何家的门户,要娶媳妇,还怕娶不来一百个?也只当好心的二姑、二姑爹做做善事,放放生就是了!”阿贵见胡王氏口软,就紧逼一步道:“话是怎么都好说的。只是亲家奶奶,你也知道古语有云: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如今何家又是官、又是富,正是当时得令,势大财雄。你们惹翻了他,是你们好呢,是你们不好?这你总该垫高枕头想一想呵!”胡柳拿起那条鸡心项链,朝阿贵面前一扔,说:“把这条婊子项链拣回去吧,我不受这么肮脏的礼物!告诉他何家的人,我们什么都不想!要想,让他们想去吧!你只要问问他们,说过一刀两断的话来没?看过《马前泼水》的戏来没?水既然都泼在地上,还能重新收起来么?”阿贵冷笑一声道:“柳姨,论起才情,我说不过你!可你千桩想得到,万桩想得到,就有一桩想不到:二少奶还有张卖身契,拿在人家手里呵!”胡杏一听卖身契三个字,登时忍耐不住了。只见她圆圆的莲子脸儿拉长了,大大的眼睛竖起来了,左脸上那深深的酒涡儿跳动起来了,血色一直泛滥到眉梢下面了。她拿起盛金耳环的首饰盒子,乒令一声摔碎,嘴里说道:“卖身契!”又拿起装玉镯子的首饰盒子,乓郎一声砸烂,嘴里说道:“卖身契!”又将两个细布扔在灶台底下,又将两盒细点倒在黑泥地上,还将那包红封利市,用木屐踩了又踩,然后指着满地的礼物骂道:
“拿老爷的心去喂狗,狗都不吃!拿奶奶的肝去喂狼,狼都不闻!你回去告诉他们,我宁愿上刀山,下地狱;跟猪狗一个窝儿,跟豺狼一个洞儿;再不然每天挖一块肉,每月剥一层皮,也别指望我会乖乖地回他何家,跟那些青面獠牙的恶鬼一道过日子!什么卖身契不卖身契,我才不在乎。我卖身也只能卖一辈子,还能卖两辈子?上一辈子的我,已经是死掉了!便宜了他们,连棺材都没施舍一副呢!这一辈子,我又活转来了!这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叫他们不要欺人太甚,不然我做鬼也不饶他们呢!”
阿贵低声细气地说:“那是陈年的老账了。如今人家一番好意,却不该反脸无情,恩将仇报。难道小姑姑阿礼,也使的坏心肠么?”
胡杏将那包绛红蜡光纸包着的十个双银角子揣进怀里,说:“既是阿礼表妹一番好意,我且收下,剩下的那些阴司货物,你替我挑回去,砸在那两只老狗脸上,叫他们留着上祖坟使唤吧!他们也没有什么恩。有的,只是仇!从前压迫我、剥削我、欺负我、侮辱我、折磨我,是仇!如今拿这些钱财物件来羞辱我,也是仇!告诉他们,不是我反脸无情,是他们反脸无情;这样的冤仇,我怎样报都不过分,报十辈子也报不完呢!”
周炳看见这十六岁的小姑娘眉宇间俊俏英武,做起事来干净撇脱,不觉又敬佩,又感动,眼睛里都含满了泪水,阿贵讨了个满脸没趣,吟吟沉沉地自言自语着,拾掇起那一担破烂东西,溜出震南村,无光无采地回广州去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