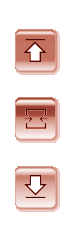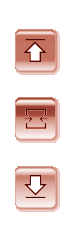|
|
|
|
三六 女英雄
|
震南村的人心烦意乱地又捱过了一个月,到了阳历四月了。胡源的伤势虽说一天比一天有起色,但仍然不能随意走动。眼看清明已过,禾秧还没插下去,不免长嗟短叹,十分着急,那天一早,胡柳、胡杏姊妹俩吃过早饭,就挑上秧箩、秧篸,先去秧地,拔起秧苗,接着就到鬼地脚、她们那块水田里插起秧来。胡柳原是插秧的把式,震南村是有名的;胡杏回家这一年多,原先丢生了的手艺也重新拾了起来。只见两个人弯着腰,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在田里插着,插得又快、又齐、又匀、又直,好象一对画家在宣纸上纵情挥洒一样。天空阴暗,飘着小雨点,一层薄薄的雨粉铺在她们的头发上。在她们旁边的几块水田里,还有七、八个姑娘,疏疏落落地在那里插秧,这里面有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等人。这些人既不象平时那样唱歌,不也象惯常那样说笑,都闷声不响地一个劲儿干诡。突然之间,胡柳听见田基路上有粗鲁的男人笑声,好象还不止一个人。自从上回四个团丁来逼着要胡杏回省城之后,胡柳心里就分外警觉,听到什么地方有陌生男人的声音,她一定要全神注视。这时她抬起头来,一眼就望见田基路上,果然有七、八个穿灰色军服的,象是县里的保安队那样的人物,正在对着这边,叽哩咕噜不知道说什么。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胡杏也抬起头来。她却看见那些不怀好意的灰家伙里面,大半是徒手的,只有两个一高、一矮的背着长枪。有一个背枪的高个子正拿穿了草鞋的脚丫子踢她们的竹帽,把那两顶竹帽踢得飞上了半天。胡杏生气了,离得远远地大声骂那灰家伙道:
“喂!你瞎了眼了!怎么连你姑姑的雨帽也认不得了!”
另外有一个背枪的矮个子,也高声向她们吆喝道:“嘿!
你们谁是胡杏?”
胡杏说,“你找我呢!”。胡柳说,“你别理他。”随即在泥水中迈前两步回答道:“她不在这里。你找她干什么?”其中一个声如破罐的人说:“你多嘴什么!你叫什么名?”胡柳说,“用不着你问!”又有一个喉咙很窄的人说:“我们不是来找胡杏的。我们是来抓胡杏的。她犯了案!你们谁是胡杏,快说!”她们没答话。又有一个声音象猪叫的人说:“你们谁是胡杏,我们抓谁!你们不说,把你们一齐抓走!”听说那些灰家伙要抓人,田里的姑娘们都放下农活,站了起来,慢慢地从四面八方走过来,七嘴八舌地咒骂那些人强横霸道。其中有两个姑娘,一个叫何好,飞身跑回村里,向胡柳家里报信;一个叫胡执,飞身跑上大帽冈,找胡树跟胡松两兄弟来解围。这时候,有四个灰家伙拿了绳索,下了水、两个、两个地朝胡柳、胡杏进逼。在水田的泥泞里面,那四个人却不是她两个人的对手,一滑一跌,弄得满身泥巴,却摸也摸不着她俩。那两个背枪的只是站在田基上咤呼,不肯下水。另外两个徒手的也跳进田里,帮着兜截。三个追一个,在田里乱转。旁边的姑娘们一面咒骂,一面高声呐喊,给胡柳、胡杏助威。不大一会儿工夫,田里的秧苗都叫踩得稀巴烂,陷到泥土里面去了。忽然之间,胡柳看见胡杏叫三个人围在当中,已经无路可走,十分危急,嘴里直叫唤:家姐!家姐!”她奋不顾身,在田基上捞起一根农民叫做“竹升”的竹杠,朝那个正准备伸手揪胡杏头发的保安队打下去,把那家伙打得狗叫一般直嚷;“哎哟!哎哟!疼死人了!你们快开枪呀!快开枪呀!”胡柳打了那人之后,还来不及把竹升收回来,背上已经着了一拳,差不多要摔倒在田里。她咬紧牙关,使尽全身的劲儿,回身一扫,正中那人胸膛,蒲达一声,倒在水里,却没想到又有另外一个人,也捞起一根竹升,朝胡柳头上打来。胡杏一嚷,胡柳把头一偏,打在脸上,鼻子、嘴里都流出血来。胡杏和其他姑娘们见保安队动手伤了人,便一齐捞起家伙,有竹升的拿竹升,有扁担的拿扁担,也不管人家有枪、没枪,向那些保安队攻击,一个个象下山的猛虎一般。胡柳平时温柔淡定,从来没伤害过别人的,这时杀得性起,横冲直撞,闪避腾挪,竟是英勇非凡,象学过武艺的男子汉一般。
“你们把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姑姑跟你拼了!”
胡柳这么一嚷,众姑娘们也跟着嚷起来。那些保安队虽是野蛮,虽是男子,叫这些娘子军奋勇一冲,竟冲得东倒西歪,束手无策。胡柳头发散乱,满脸流血,手脚青肿,衣服破烂,平时水汪汪、亮晶晶的两只柔媚眼睛,这时红光闪闪,杀气腾腾,那恬静的颜容,骤然之间,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同时,在这事机紧迫的一刹那之间,她又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她觉着伤她妹子的是这些人,打她爸爸的是这些人,害死何娇妈妈何龙氏的是这些人,杀死区桃跟周金的也是这些人。她又觉着,她一竹升打出去,她那满腔的仇恨就顺着竹升流出去,——那股神力,简直不知道从何而来!胡杏、何彩、何兴、何旺、胡带、胡养、胡怜七个姑娘见胡柳带头,猛烈冲杀,也就一个个地跟上去,捅、扫、挑、打,浑身的劲儿都从血管里涌将出来。但是不幸得很,何旺首先受伤倒下了,胡怜也跟着受伤倒下了。敌众我寡,形势十分危急。胡柳也觉着天旋地转,不过还拼死撑持着。这时候,胡王氏披头散发,从一条田基路上飞跑而来,何好紧跟在后面。在另外一条田基路上,胡执领路,胡树、胡松、陶华、马明、丘照、王通、关杰、邵煜、区卓九条好汉随后,手里拿着铁笔、铁尺、铁锄、铁锹各种武器,一声不响地赶来增援。到了鬼地脚,胡树一马当先,举起三尺长的一根加粗铁笔,双脚一跳,跳进泥潭似的水田里,一直奔向那背枪的高个子,嘴里大喝道:
“这里是什么的地界,你们敢来踩秧苗!缴枪!”
保安队素来知道震南新村的农场工人厉害,听说缴枪两个字,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又加上那许多赤卫队英雄,一齐象旋风似地朝他们卷来,哪里招架得住!斗了一顿饭工夫,那些灰家伙一个个肿眼、歪鼻子,一双双瘸腿、拗胳膊,却又不敢开枪,只得抱头鼠窜而去。周炳听见消息,赶到鬼地脚,满眶热泪地走到胡柳身边的时候,她已经支持不住,突然昏迷过去了。大家将受伤的姑娘们搀的搀,扶的扶,背的背,抬的抬,一同回到村子里。周炳横抱着胡柳,在后面慢慢地走着。胡杏紧跟在旁边,拿手帕擦家姐脸上不断往下滴的鲜血。走了一阵子,胡柳悠然苏醒了。她浑身无力,只望了周炳一眼,就又闭上了眼睛。周炳十分痛心,紧紧地搂着她,吻她脸上的伤口,又安慰她道:
“打得好!打得好!你不单救回了妹妹,还显出了咱穷人的威风!你是一个真正的赤卫队员!比有一些男子汉更配当赤卫队员!”
胡柳在浑身热辣辣的,针刺般的痛楚当中勉强笑了一笑,这一笑,又甜蜜,又端庄,又娇柔,又矜持,完全恢复了一个女孩子的本色。胡杏在一旁,听见周炳这么说,心中十分高兴。可是忽然一想,就噘起嘴道:
“那么我呢?我打不得么?我不配当赤卫队员么?”
周炳力气大,他横抱着胡柳,看起来十分轻松,一点也不吃力,但是他又要十分小心地望着路面,避开哪怕是极小、极小的坑坑坎坎,以免胡柳受到哪怕是很轻、很轻的颠顿。这样,他的眼睛就不能望胡杏,只用他的声音回答道:
“你要革命,自然是对的。可是我跟你说过三件事,你都记得么?”
胡杏斩钉截铁地说:“记得!”
周炳问:“第一件?”
胡杏回答道:“要永远、永远、永远跟着党走!”
周炳鼻子里唔了一声,又问:“第二件?”
胡杏挺起胸膛说:“要使尽所有的气力夺取政权!”
周炳说:“是呀。你看咱们受的许多折磨,都因为咱们没有政权!第三件?”
胡杏拿两个拳头并在一起,又慢慢地朝两边分开,表示她正在使用很大的力量,要拉开一样什么东西,结果还是拉不开的样子,嘴里同时说道:
“要有这个——韧劲儿!”
后来她又增加道:“受了打击,不灰心;受了毒刑,不害怕;受了挫折,不泄气!照你那样说,——百折不回!”
周炳用嘉许的眼光对她笑了笑道:“不错,你全懂得了!小杏子,记住今天的事儿,也记住从前的事儿!你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为什么还不能当一个赤卫队员?能!能!区卓和你一般年纪,他能当,你为什么不能!”
胡杏听了,仰起头,挺起那本来已经很高的胸膛,步伐也加大了。
几天以后,他们打退了保安队的消息传到了三家巷。这消息在那里着实引起了一番极大的骚动,谈论的人们都吐出舌头,缩不进去。那天是星期六,外面的酒局虽然不少,何守仁因为心情不快,都一一推辞了。他很早就回了家,老太爷何应元也在家,父子俩开了一瓶白兰地酒,弄了几样清淡的菜,在家吃晚饭。呼罢,使妈们收拾了碗盏,泡上了细茶,一家人坐在饭厅里闲谈。何应元喝了几盅酒,牢骚满腹地开言道:“如今的世道已经是乱而复治的时候,怎么还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事情出现呢?那胡杏,论宗族,她是这里的小辈;论法律,她是这里的丫头;论情理,她是这里的小媳妇;她怎么能违抗这里的意旨,赖在家里不来呢?无他,圣贤的道理衰微就是了。所以不尊孔。,不读经,治世就永远不会出现!”何守仁也喝了几盅,也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加上他自从当了官儿以后,也学会了拍桌子、砸板凳的,于是他就拍起桌子来道:“哼!治世!没有法治,那里有治世”我是学法律的。这方面的事情,用不着瞒我!胡家那些刁民,农场那些土匪,还有咱们隔壁周家那位美男子——,嘿嘿,美男子,他们的行为是些什么行为?看:毁弃文书,捣乱乡府,破坏婚姻,抢劫粮食,焚烧房屋,殴打兵丁。——这是目无法纪!这是大逆不道!这是造反!如果真想维护法律尊严,这些人都该处以极刑!”说到这里,他用尽平生之力,往桌子上一拍,连茶壶都跳起三寸高。所有的人听见极刑两个字,都觉着有一把钢刀架在脖子上,面面相觑。在大奶奶房间里,二少爷何守义正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照片。他虽然从癫狂院回了家,但仍然语言颠倒,神志不清,听见砰訇一响,就吓得魂不附体,哇哇直叫,跟鸭子的叫唤一般。后来,何守仁又接着往下说:“可惜不是所有的法官都明白事理。他们总是找一些借口来推卸责任。什么证据呀,民怨哪,余地呀,宽容呀,总之是不肯依法判罪。是不是想敲我们的竹杠?谁也不知道。——可是除了这些混蛋以外,社会上也还有一些好心人,——不叫他们做好心人,能叫你们什么呢?他们满脑子都装着人道、博爱、自由、平等,把五四以来的响亮口号,整天挂在嘴唇边,同时斜着眼睛厉我们,说我们残暴、自私、专制、封建,说我们不符合他们的理想,经常袒护着那些践踏法律的刁民和土匪!这真是叫人感慨无量!”陈文娣听得明白,何守仁所说的好心人,有她自己一份,但是她不想在这时候插嘴,只是笑了一笑。小妹子何守礼年少气盛,一听就冒了火。她今年一十四岁,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满脑子正是装着人道、博爱、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并且恰恰认为这些东西是最神圣,最尊贵、最美丽的东西。她唰的一声站了起来,尖削的脸孔冲着天空,急地辩护道:
“大哥!话不能这么说!人道、博爱、自由、平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何守仁冷笑道:“来了,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不可侵犯!谁侵犯了你了?”
何守礼抗声道:“没侵犯我!光没侵犯我不成!灌醉人家,强迫人家嫁给疯子二哥,这人道么?把人家打得死去活来,一碗、一碗地吐出血来,这博爱么?人家快死了,就打发回家,说一刀两断,不收下不行,人家活转来了,就要人家回来,不回来不行,这自由、平等么?蓄婢、纳妾,一些人当主人,另外一些人当奴隶,这又自由、平等么?”
何五爷正待发作,何守仁已经跳到何守礼面前,指着她的鼻子问道:“那么,你想怎么样?”
何守礼一点也不退让,稚气盎然地说:“我不想怎么样。
我想家庭革命!”
那教育局长挥动干瘦的胳膊,往下就是一掌。啪的一声,正打在他妹妹那鲜花一般的脸上,骂道:“混帐东西!小共产党!”何守礼挨了打,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的亲生母亲、三姐何杜氏一头豹子一般跳了出来,也给了那教育局长一巴掌。何守仁也顾不得风采官威,就和自己的庶母扭缠厮杀起来。一时全家大乱。陈文娣赶快拖住小姑姑,离开饭厅,走出大门,回到隔壁自己的外家,才算喘了一口气,恰巧那天晚上,陈文雄、周泉,孩子国栋、国梁,老太太陈杨氏都在家,也刚吃过晚饭,坐在楼下客厅里闲谈。陈文娣进得门来,一坐下,就讲起刚才的事情。何守礼瞪大两只失神的眼睛,不哭也不笑,样子怪可怜。陈文雄听了,气愤填膺,正准备安慰她们几句,忽听得隔壁何家大奶奶何胡氏高声尖叫道:
“什么?脖子还硬过钢刀?我什么都不在乎啦!也不管阴功,也不管积德;也不管前世,也不管来世!活的要不回来,死的也要!出口气就行了!”
陈杨氏听得清楚,连忙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
陈文雄见大家都望着他,等他发话,就做出挺身而出的姿态,仗义执言道:
“野蛮!封建!”又用英文插进了一句:“亲爱的,不是么?”那是对周泉说的。等周泉点了点头之后,他才说下去道:“你可以千方百计地找钱,你可以照自己的意志尽情享乐,你在残酷的竞争当中有时也免不了损人利己,你有权利踏着失败者的脊梁走向成功之路,但是你不应该忘记文明和人道!文明和人道——一条界限。一条善恶之间、美丑之间、人兽之间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说,阿礼,我同情你!我支持你!我甚至崇拜你!二妹,还有我的小鸽子,你们看:我们的实际一天天多了,我们的理想一天天少了,愿意或者不愿意——我们是从幻想的乐园里被放逐了。当年换帖的时候那些美妙的词句,如今很少人谈起了。我们曾经把三家巷膜拜为圣地,如今回想起来,不免哑然失笑了。但是,新星出现了,新人诞生了,新锐之师长成了,这就是她:密斯何守礼!她是我们的美丽而慈善的公主!她是五四理想的化身!她是三家巷的精华!”
除了陈杨氏和国栋、国梁听不懂之外,大家都叫他这番话迷住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