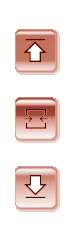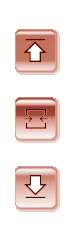|
|
|
|
第一章 王强夜谈敌情
|
到过枣庄的人,都会感到这里的煤烟气味很重,煤矿上那几柱大烟囱,不分昼夜的“咕吐、咕吐”喷吐着黑烟,棉絮似的烟雾,在山样的煤堆上空团团乱转。附近人家的烧焦池也到处冒着烟。还有矿上的运煤车和临枣铁路的火车,不住的向天空喷着一团团的白云。这四下升起的浓烟密雾,把枣庄笼罩起来,人们很难看到晴朗的蓝天,吸到清新的空气,走到哪儿都是雾气腾腾。风从山样的煤堆上吹来,带着煤沙到处飞舞,煤沙细得打到人的脸上都不觉得。人们从街上走一遭回来,用手巾往脸上一抹,会看到白毛巾上一片黑灰。白衣服两天不洗,就成灰的了。下窑的和装卸煤车的工人,在露天劳动的脚夫,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整天在煤里滚来滚去,不仅手脸染黑了,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他们也不习惯时常去擦身和洗衣,因为很难洗得清爽。就这样,他们一年到头手脸黑,穿的黑,有钱人就叫他们“煤黑”。
旧社会有多少不平事!正是这些“煤黑”创造了枣庄的财富。那山样高的煤堆,是他们从深黑的炭坑里挖出来的。又是他们把煤炭装上火车,运往四方,供给工业的需要,和万家住户的烧用。可是这些财富都被老财们掠夺去了,被卑视和受苦的却是这些“煤黑”。日本鬼子占领枣庄以后,夺去了煤矿,许多有钱的先生们,在鬼子的刺刀下为敌人服务。又正是这些“煤黑”们,扛起了枪杆,成立了游击队,打击敌人。我这部小说就是写这些“煤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怎样对敌人展开轰轰烈烈的英勇斗争,他们在敌占区的枣庄、临城,津浦干线和临枣支线铁路两侧,把鬼子闹得天翻地覆,创造了很多英雄事迹。这是后话,现在暂且从头谈起:
鬼子来了以后,中央军跑了,共产党组织了一批煤矿工人,拉到北山里,和八路军游击队汇合,坚持鲁南山区的抗日战争。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和掌握枣庄及临枣支线敌人的情况,司令部派了两个精悍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这两个队员一个叫刘洪,一个叫王强。刘洪坚决勇敢,王强机动灵活。他们都是枣庄人,过去在煤矿上干活,由于自小生长在这里,他们对矿上和铁路上都很熟悉,还练出扒车的本领。他俩被派回枣庄后,山里的斗争就残酷起来,刚成立的八路军游击队,不仅时常遭到敌伪的袭击扫荡,而且还受到当地封建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排挤。在敌伪顽的夹击下,这支年轻的游击队经常吃不上,住不下,不得不四下分散活动。因此,有半年的时间和刘洪、王强他俩失掉联系。以后西边开来八路军一一五师两个主力团,打开了山里的局面,山里游击队才站住脚,司令部才又派人到枣庄和刘洪、王强联络。
这天傍晚,枣庄的烟雾显得更大,天黑得仿佛比别处早些。煤矿上和街上的电灯亮了。四下的烧焦池的气眼都在呼呼的窜着火苗。远远望去,枣庄像刚开锅的蒸笼。煤矿公司大楼上和车站票房上的太阳旗,像经不起这里的烟熏火燎似的,在迎着晚风飘抖。西车站上守卫的日本鬼子的刺刀,在电灯下闪闪发光。
西车站下沿,就是枣庄的西郊了,这里有一个陈庄,百多户人家,大都是下窑的工人,和车站上的脚夫,还有几家炭厂。这庄除了炭厂烧焦卖,各个住家也在烧,因为烧焦是死利钱,一百斤煤能烧七十斤焦,一斤焦能卖二斤煤钱。七十斤焦就能买一百四十斤煤,所以烧一百斤煤的焦,净赚四十斤煤。男人们下窑去了,女人们虽然忙着家务,但也会抽空在小屋旁边挖个坑,填上煤烧起来。天黑下来,这个小庄子,到处都冒着烟,地上到处都喷着火苗。因为这里和车站只隔一道小沟,车站上有鬼子,所以天一黑,街道上就没有人了。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从庄西进来一个人影,绕过两个焦池,来到一家大门前,他把门推开,走进院子里。
“老王哥在家吗?”
“谁呀?”一个浓眉方脸的人,从有着灯光的西屋里走出来,他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眨着黑黑的小眼,向院子里的来人望着。在黑影里,他看到是一个穿着农村服装的人。“我!从南乡来的!”客人走过来,一把抓住主人的手说,“老王!你不认识我了么?”
王强嘴里咕哝着:“是谁呀!”把头伸到对方的面前,仔细打量着,又把他拉到灯亮处再一看:“咦!”他扬着浓浓的眉毛,咧着嘴巴狠狠的咦了一声,双手抱住了对方的臂膀,把客人拉到屋里。
“啊呀!原来是你呀!老周!你怎不早说呢?真想不到呀!……”
显然王强对老周的到来,感到说不出的惊喜。忙从袋子里掏出香烟,自己用火点了两支,把一支递到老周的嘴上,看看家人正在吃饭,他便拉着老周的手说:
“走!到那边炭厂小屋里去!咱们好好拉拉,回头找到老洪,咱们痛快的喝一气!”
两人出了门,摸黑向右走了十多步,在一个栅栏门边停下。老周往里一望,这是一个四周围着短墙的小炭厂。中间有个炭堆,旁边有些筐筛铁铲等工具。院子四周靠近短墙的地方,有几个焦池在熊熊的烧着。所以这里显得烟气特别大。老王开了栅栏门,他们走进一间矮小的黑茅屋里。
王强点上了灯,说:“这里还僻静些,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找老洪去,马上就回来!”
老周知道这老洪就是刘洪,因为在一块时候长了,叫顺嘴了,就把刘洪叫成老洪了。虽然刘洪和王强的年纪差不多,可是都叫他老洪,这里边也包含着尊重的意思。他俩被派到枣庄来以后,原是由刘洪负责,因为老洪没有家,所以将联络点设在王强家里。
老周问:“老洪住在哪儿?”
“就在这里。”王强指着东边那个地铺说,“我们两个,都住在这里。有时我也到家去住。”说着就出去了。
老周看看这小黑屋,确有两个地铺,临门一张小桌,两条粗板凳,屋子当中砌着一个火炉,窗台上有些锅碗盆罐一类的东西,显然他俩也是在这里做饭吃的。他和老洪、王强过去在山里,曾在一个连队里作过战。他看到这些摆设,想到刚才王强乌黑的面孔和满身的煤灰,他感到对方真成了一个道地的枣庄人了。老周不由得回想起在山里一道打游击的时节,初进山时,老洪、王强他们的脸也是黑的,以后用山沟的水渐渐的洗干净了,由于常睡草铺,衣服上的煤灰味换上枯草味了,只是在密密的布纹里,还有着些看不出的煤灰,直到换上了军装,身上才完全看不到煤的痕迹了。唯一的就是眉毛黑,只有在那眉毛中间还隐藏着些微微的煤污。现在为了执行党的任务,他们又生活在这煤灰里了。
外边的夜没有山里宁静,火车在轰隆隆的响着,远处还隐隐的听到矿上机器的嗡嗡声,老周想到过去他们在一块的生活,他很想马上看到老洪。记得队伍一拉进山里,老洪就是连里出色的班长,以后被提拔为排长。他有着倔强的性格,个子虽然不高,可是浑身是劲,只要见到他发亮的眼睛一瞪,牙齿一咬,就知道他下了决心,任何困难都会被他粉碎。有一次他们被敌人包围,他用一挺机枪掩护了整连的撤退。他趴倒在坟头上,打倒了十多个敌人,最后灵活地避开敌人的火网,安全的追上队伍。老周想到这里,他真想马上见到老洪,心里才感到松快。
不一会,王强回来了。一手提着瓶烧酒和一大荷包熟牛肉,另一手提了一手巾烧饼,放在桌上。
“找不到老洪!一到天黑,你别想摸着他的脚迹!”王强斟了两杯酒说。“咱不等他吧!你也许早饿了,一边吃着一边拉吧!”
“外边……”老周警惕的向门外望了一眼。
“没有什么!我进来时,把栅栏门扣上了,老洪回来会叫门的。”王强说着把门掩了,并笑着问老周:
“你啥时回来的?山里怎么样?”
“我回来四五天了,”老周把声音放低些说。“咱们山里的队伍已经整编,义勇军改为苏鲁支队,从枣庄拉出来的煤矿工人支队,编为三营,还是我哥周震当营长。因为鬼子常到山里扫荡,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部队,又常给我们摩擦,所以部队流动性很大,一方面防鬼子,一方面还得防这些反共的龟孙。你知道咱这个部队刚成立不久,武器还不齐全,活动的地区又小,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来,通过我哥哥的关系,在家乡活动。因为他在这一带威信很高,咱们三营又都是这一带的人,地方群众关系也好,我们计划在南山一带秘密的建立起一小块抗日根据地,以备咱们部队遇到紧张情况时,可以跳过来隐蔽的休整一下,再投入战斗。要知道敌人在山里扫荡的越残酷,插到这敌据点附近,就越安全呀!”
“对!”王强连连点头说,“应该在南山一带开辟一下。以后咱们的三营过来,老洪和我也可以在火车上搞些东西,接济接济部队。说实话,屯在敌据点里也真想咱们的部队……”
听到王强说要搞火车接济部队,老周正嚼着一块牛肉,他笑着说:“那再好也没有了。山里的部队的确很困难呀!部队派你和老洪回来,好几个月没有音讯,司令部很担心,生怕你们遭到危险。……”
王强摇了摇头说:“没啥危险。只怪我们没有和上级联系上。可是,我们有啥法子呢?我和老洪都不识字,又不好找人写信,我们去吧,又不知道部队住在什么地方。”
“我这次出山,司令部特别叮咛我找你们联系,看看你们活动的情况怎样,还嘱咐如果你们和山里直接联系有困难,就到西南山边小屯去联系,我家就在那里,离这七八里路。我那里经常有交通①和山里联络。我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和你们接上头,了解下你们活动的情况,好向山里作汇报。”“这太好了。过去我们和山里断了信,可把人憋死了呀!像两个没有娘的孩子似的,我和老洪老蹲在一起喝闷酒。这一下可好了。今后有啥事,就到小屯去找你们和山里联系吧!”说到这里,王强兴奋起来了,他举起杯子说:“干一杯!”两人就一饮而尽。
-----------------
①抗日时期称联络员为“交通”。
他们一边喝,一边谈。老周的脸色已有些红红的了,可是王强的脸色没有变,只是一双黑眼里有点水漉漉的。老战友分别大半年了,乍一见面有说不出的高兴,尤其是在这敌人的据点里会见更不容易,再加上王强和山里失掉联系,现在接上关系的兴奋心情,所以两人就越喝越有劲。老周的酒量比不上王强,可是也喝的不少。接着他就吃烧饼。饭后,两人点上了烟,隔着小窗,望到外边,天已阴起来,老周转过头来说:
“老洪怎么还不回来呢?”
“他可没个准,常常到半夜才回来。”
“那么,你就先谈谈吧,你们到枣庄后,这几个月来的活动情况怎样?”
“还是等老洪回来谈吧,啥事都是他领着干的,我又说不好。”
“你先就知道的谈谈,老洪回来再补充一下就行了。老王,就我个人说,也很愿意早听听你们在这里的情形,老王,开始吧!”
“怎么个说法呢?又从哪谈起呢?”王强愁得抓着头皮说。“咱这些老粗,叫干点什么还可以,要是叫用嘴说,那就难了。”“随便谈谈吧!想到哪就说到哪。先说,你们从山里回到枣庄,怎样安下了身,还有敌人的情况,你们进行了哪些活动。”老周笑着说。
“好!”王强咳嗽了一下接下去,“先说怎样安下身么?那还不容易,我俩都是枣庄生的人,自小在这里长大,老洪虽然没有家,可是早年咱在一块下窑,他常住在我家,像我家的一口人一样,这事村里人谁都知道。所以没几天,我们都弄来了‘良民证’。
“住下以后,找个什么营生来干呢?年轻人没有正当职业掩护,是会惹起怀疑的。过去我俩下窑,现在鬼子又开了工,正用人,一去就行。可是老洪和我商量了一下,我们都不愿意去干,要说往年下窑苦,四块石头夹一块肉,现在鬼子可更狠,他只要你多挖煤,可不管你的死活,一不小心,轻则皮鞭抽,重则刺刀捅。鬼子在公司四下设着岗,谁敢动一动,就机关枪嘟嘟。说到工钱,少得顾不上吃。过去一些老下窑的都不去干了。逼得鬼子没办法,从山里和河北抓来成千的俘虏,到矿上作苦工,四下安上铁丝网,每天只给几个黑窝窝头。老洪那个烈火般的脾气,他哪能受那个气呢?同时我们到这里的任务,还是偏重干军事方面的。下窑被困在里边,什么都不能做。左思右想危险多,好处少。所以我俩决定不去搞那老营生了。
“干什么呢?老洪说:‘吃两条线!’白天在这小炭厂名义上当伙计。晚上,他就去约合一班子人,扒鬼子的火车。说起吃两条线,你恐怕有些不懂。你知道火车道的铁轨不是两条么?两条线就是铁路的意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就吃这两条线呀!往年下窑出苦力,顾不上生活,挖的煤像山样高,一列列火车日夜不停的往外路运,大肚子赚的钱数不完,福享不尽,难道我们瞪着眼望着用自己的双手挖出来的煤炭,像流不尽的水样的运出去,而我们就老实的饿着肚皮么?我们饿极了,就扒上火车,弄下几麻包烧烧,或者去卖几个钱维持生活!难道这不应该么?说起这班扒车的人,都很有种,飞快的火车一抓就上。老洪扒的最好。有时在火车上遇到押车的车警,就得拼命。有次老洪被车警用炭块打破了头,直到现在脸上还留下一块黑疤。他急了,以后上车就带着刀子,他说刀子有两个用处,可以割断麻包上的绳子,又可以捅车警。这一来押车的车警软了,因为这些家伙都怕死的。经过车上一些人说合,以后这班子扒车的,送几个钱给他们,他们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打马虎算了。这班穷兄弟都很服帖老洪。因为他勇敢、讲义气,扒车又扒得好,能为穷兄弟们撑腰。遇事,老洪一叱呼,说干啥就干啥,像一群小老虎似的。这次回来,他又想起搞火车了,他说:‘搞鬼子的更应该!’老洪的意思是想领着这一班子人打鬼子。老洪就这样住下来了。
“我呢?开始和他们一道搞车,可是想想,这也不是个长远办法。以后我就利用我父亲的关系,到车站上去干了脚行,推小车运货出苦力。因为我父亲过去在车站上下大力干脚行,以后当过脚行头,现在老了,不能干了,经他一说我很容易的就上去了。开始老洪不同意我干,他说:‘你干那个有啥意思呢?出力受气,还是扒车来得痛快,你没钱我给你。’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因为我在车站上干活消息灵通,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动静,而且车站上装卸货时,货物都经我的手,每一趟火车装的什么东西,我都知道。遇到机会我就告诉他们,他们去搞车,一搞一个准。……”说到这里,老周打断了王强的话,连声叫道:“好!好!”他听到他们搞车的情形,听得很入神。过去他们在山里打游击,有时闲下来,也谈谈在枣庄时的情况,也听说他们会扒火车,可不知道里边还有这些详情。老周望着王强接上一支烟,听他说下文。
“以后脚行的活就更多了,鬼子在站台对过,开了一个国际洋行。就像中国的转运公司一样,可是又不大像,因为它的权力很大。枣庄煤矿所有运出去的煤,从外边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得经过这个洋行。商人往外发货,都得向他们要车皮。
“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的。他们都是在侵华战场上打伤的军官,不能随军队杀中国人了,就下来做买卖,吸中国人的血。听说大掌柜是一个大尉。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鬼子是怎样将中国的财富,煤、粮食,不分昼夜的往外运,像淌水似的。多心痛呀!接着又把些熊东洋货源源不断的运进来。这一切都是经过我们手装卸的。三个杀够中国人的日本掌柜的,养的胖胖的。他们有薪水,从奸商手里大把捞钱,还克扣我们脚行。照例,外来的货到站一落地,每件就是落地税一毛;脚行运到货栈定价一毛,洋行抽两分;从货栈出站交给商人,也是一毛,洋行还得抽两分。就这样一件货到站,他们要抽一毛四分,这些都是鬼子掌柜的额外收入。每天运下那么多货,他们还不发财!洋行成立不久,由于货太多,他们从站上脚行,抽出五十辆常备小车,每天到洋行听候使用。我被抽上了,编队的时候,选二头,因为大头是鬼子担任,由于我父亲过去是老脚行头,大家都推我作了二头。每天领着小车队给鬼子装卸货!”
说到这里,王强皱着眉头,对老周说:
“老周!你说,我过去在山里咱队伍上当班长,现在竟给鬼子脚行当起二头来了。这不是笑话么?”
王强说着,又从瓶里倒了一大杯酒,狠狠地灌下去。老周发觉他的脸色很难看,知道他心里不舒坦,便安慰他道:“为了工作才这样。”
王强点点头,大声的说:“要不是为了工作,谁干这个!”老周说:“你们不但干得对,而且把自己安置得很好。老洪那一伙能扒车的,将来组织起来,在火车上很有用;你在车站上,和鬼子打交道,了解敌人的情况,这也是很要紧的。那么,现在谈谈敌人在枣庄的情况吧!”
“说到鬼子么?”王强骂了一声“奶奶”,又说下去:“大部分住在公司里,车站上。洋街住着鬼子的宪兵队。现在又正在南马道一片空地上修大兵房,看样子还有大批的鬼子要来。枣庄街也成立了维持会。汉奸每天办保甲,十家连环保,一家出事九家受累。居民都领良民证。鬼子整天出来,在街上抓人。夜里冷不防就查户口。大队的鬼子,三天两头出发,到山里扫荡,一回来就绑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起初送到宪兵队审问,一进去很少能活着出来的。以后捉的人干脆送到南马道大兵营了,那里四下用电网铁丝网围着,光见用汽车往里边拉,就没见出来的,枪毙了,也得有个响声呀!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在夜里经常听到凄惨的叫声。以后从一个翻译官口里漏出来:这些运进去的中国人,都叫洋狗咬死,刺刀穿死。鬼子在夜间把捉去的中国人绑在木桩上,给鬼子新兵练刺刀,训练洋狗。那里有几十根木桩,挖了好几亩大的土坑,穿死,咬死就扔进去,撒上一层土,再扔进一批,又添上一层土,你说鬼子多残忍!……”
王强说到这里,他的眼红了,里边像有一团火在燃烧。他愤愤的提起酒瓶又倒了一杯,像喝白水一样喝下去。他干咳了两下,又接着说:
“还有,煤矿上有个医院,鬼子占了改作军用医院,给负伤的鬼子治疗。原来在这医院的中国大夫大部分被撵走了,都换上日本医生。中国人也留用了几个,不过都驱逐到外边住。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睡觉。开头这些中国大夫还没觉得什么,可是以后渐渐注意一件事,就是早上一去上班,总见手术室地板刚用水洗过,可是墙角,手术台脚,没擦洗的地方还残留着血迹。天长日久都是这样,中国大夫感到很奇怪,难道鬼子每天晚上都开刀动手术么?可是病房的鬼子开刀的并不多呀!没过多久,这个谜就被附近的老百姓揭开了。每天夜里都有汽车到医院来,天快亮的时候,汽车又开走了。有一个老百姓偷偷的隔着窗户往外看,只见开来的汽车,装的都是绑着的中国人。他心里想,鬼子难道还有好心肠连夜的给中国人看病么?可是天快亮,汽车开走时,车上却不见人影了,只见那么多麻袋包,血顺着麻包往下流,里边装的什么呢?原来鬼子把捕来的中国老百姓,供鬼子大夫作活的解剖。你说日本鬼子狠不狠,毒不毒!……”
王强砰的一声,捶了下桌面,酒杯子被震得跳起来,他被怒火烧红的眼睛里泛着泪水,望着老周。老周的脸色铁样的严肃,沉重,他的心被王强所讲的鬼子的残暴所激怒。他想到鬼子在山里扫荡时抓来的根据地的老百姓,原来都是这样悲惨的死在这里。小黑屋里沉静下来,只听到外边矿上的机器的嗡嗡声。就在这沉静的夜里,也许鬼子又在大兵营、宪兵队、医院里残暴地屠杀着中国人。王强沉默了一会,又说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是个中国人,能平心静气么?老洪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鬼子这样屠杀中国人,他还受得了?我们出山时节,带回了一棵十子连的手枪。我们人少枪少就小干,一有机会,我俩夜里带着它,去摸鬼子的岗哨,混过去,打倒就跑。鬼子戒严、查户口,他能查出个屁?我们都是本地人,又在夜里人熟地熟,他有什么办法,就这样,我们也干了几回,消消肚里这股闷气。白天我还是照常到站上,领着小车队在洋行值班,和那三个鬼子掌柜的打交道。可是自从我知道那些黑夜里的屠杀以后,我见了鬼子掌柜的心里就冒火,心里说:‘我啥时候杀了你们这些龟孙,心里才解恨!’一天,老洪对我说:‘老王,咱们干了他们吧!’我说:‘行!’老洪叫我侦察一下,在一天夜里,老洪约了人就把这三个鬼子军官杀了!”
“啊!杀了么!”老周沉闷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当然杀了!老洪干事从不拖泥带水,他说杀哪个,还跑得了么?”
“好,好,杀得痛快!”老周听了王强说半天鬼子屠杀中国人的残暴,心里一阵阵发沉,像坠了上千斤的石头,这一听杀了三个敌人,才出了一口气。
“说杀了三个是假的,”王强笑着说,“杀了两个半,有一个没杀死,第二天又活了,这只怪我,惹起以后不少麻烦来。”“你说说,你们怎么去杀的!”老周想听个详细。
“是这样。”王强慢慢的说下去:“我不是小车队的二头么?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左右,站上的货车都装卸完了,大伙都换班回家了。可是我还得去跟鬼子三掌柜金三结帐。当天装多少件,卸多少件,工友该分多少钱,我领了再发给他们。就这样我和三掌柜金三混得很熟。有时晚上结完帐,他也留我坐一会,给我一支烟,递我一杯茶,拍着我的肩头笑着说:‘王的,你的好好的干,以后我提拔你大大的!’我知道这是他拉拢我,好让我俯首贴耳的为他们效劳。我就应付着说:‘谢谢,太君以后升官大大的!’他听了也高兴的哈哈大笑。平时我也帮他扫扫地,倒倒茶,把他的屋子收拾一下。日子长了,到各个屋子里出出进进,鬼子也不避讳。有天晚上,是个机会,我和鬼子三掌柜结帐结得晚了,大约有十点多钟,大掌柜、二掌柜都睡下了,这个矮胖子的金三打着呵欠也想睡,我装着收拾东西推延着时间。等三掌柜也睡下了,我把电话机偷偷的搬到离床远些的地方,就把大门倒挂上走了。
“当晚我找到老洪,把情况一谈,他说:‘干!’我说:‘行!可是枪呢?’有三个鬼子,我们两个人一棵枪是够搞的。搞不利索,洋行对过就是站台,站台上驻着鬼子,并有流动的哨兵,是容易出危险的。老洪说:‘枪不够,用刀砍!再找个帮手就行了。’我俩商量着去约彭亮。他平时也和我们一道扒车,很勇敢,他一口答应了,愿意和我们一道去。三个人一棵短枪。三把大刀对付三个鬼子,一个人打一个正好。可是又一想,洋行离站很近,枪一响,站台上的鬼子听见,用机枪堵住门怎么办?商量了一下,进去都用刀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放枪。我头里领路,夜十二点以后,我们就到洋行去了。
“他们在一个拐角黑影里等着,我悄悄的摸到门口,把大门弄开,让他俩偷偷溜进去,我用手指着南屋,南屋的门是往两边拉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开法,我上去,把门用力往两边一拉,拉开了,屋里的电灯还雪亮。我一愣,老洪带着彭亮早跃进去了。只听得其哩格叉,鬼子一阵乱叫,等我跳进去时,两个鬼子已被他们砍翻了。另一个鬼子用被子裹着头,滚到地上乱叫。我急了,夜深入静,声音传得很远,不能让他叫下去。我跑上去,对着裹被子的鬼子照头照胸打了两枪。枪一响,我们就溜走了。我们汗流满面的跑回家里,听听车站上,并没什么动静。原来,在屋里打两下手枪,外边听不清楚。所以车站上的鬼子并没有发觉。事办得倒还利索,很痛快。这三个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的日本鬼子军官,总算没逃出中国人民的手掌。
“可是,我躺在床上,又一寻思,一个心事缠得我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怎么办?去上班还是不去呢?不去吧!准惹起怀疑,平时都是一早按时到车站上值班,怎么就偏偏这夜出了事就不来了呢?不用说,不等吃早饭,就要被抓去了。反过来一想:去吧!杀了鬼子,心里总是一个事,一露出不自然,就出毛病。最好的办法是晚上逃出去。可是这一跑可就证实了,家里人准受连累。连夜和家人一道跑出去吧?鬼子四下有岗,不好出去,天已快亮,也来不及了。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就去找老洪,要他给拿个主意。我就是有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拿不定主意,要是灾祸真临到头上了,我也能对付过去,就是在事前事后多犯寻思,老洪说我太犹豫。可是我一见老洪的眼睛一瞪,也就有信心了。所以我一有磨不开的事,就找他商量。一见到他,老洪说:‘这点小事,你嘀咕什么呢?他又没有抓住你的手,怕什么?’我说是呀!他说:‘这三个鬼子还不该杀么?’我说该杀呀!他就说:‘那你明天就理直气壮的上站去,啥事不要怕,越怕越有鬼上门!’老洪的话也对呀!他这一说我心里踏实了。第二天一早,我像没事人一样到车站上去。
“在站上,我点了点人数,小车队的人都来齐了。我说:‘走!到洋行去看看,今天运啥货!’小车吱吱呀呀的都到洋行来了。一看,大门半开着,我心里有数呀!平时都是小车在外边等着,我一个人进去找三掌柜。这次我约了几个人一道进去。我先带他们到帐房。这里没有一个人,我坐下来,叫他们:‘到南屋里去看看三掌柜的起床了没有!’他们都到南屋去了。只听一阵啊呀声跑回来:‘二头!鬼子叫人杀了!’我故意装着不懂,问:‘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说:‘鬼子掌柜的不知叫谁杀了。’我急忙站起来说:‘真的么?哪有这种事!跟我去看看!’他们都要跑,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可是被我喝住了:‘事到跟前,你们跑还行么?一个都不准跑。’我就往南屋走去。其实不看,我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过一进门,却使我大吃一惊。大掌柜、二掌柜都死了,可是鬼子三掌柜却满头是血的坐在炕上。原来夜间我进去打他时,他早吓得蒙着头,裹着被子在地下滚,使我的枪没打准。头上那一枪,只在头皮上穿了一道沟,胸部的那一枪,由于他一滚,子弹从肋骨间穿过,却没打中要害,当时他是昏过去了,天亮时苏醒过来。由于他蒙着头,我没能打死他。可是也正因为这样,他也不晓得是我干的。所以我一眼看到他坐在炕上,虽然心里吃惊,可没敢流露出来,就假装惊慌的急忙跑上前去,叫着:‘太君!怎么了呀……’三鬼子说:‘夜里来了土八路,王的!你打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宪兵队,报告洋行出了事,又打电话给医院,叫派人来。不一会大队鬼子开来了,机关枪四下支着,鬼子端着刺刀围住院子,宪兵队进南屋检查,这时有些脚夫都偷偷的溜跑了,可是我硬拉几个人,在院里院外忙着,医院的汽车来了,我帮着把鬼子三掌柜抬上汽车,他临上汽车,看到我累得满头大汗,拍着我的肩说:‘你的好好的,我医院的出来,干活大大的……’我说:‘好好的,干活大大的!’送他进院了。……”
老周完全被王强谈的杀鬼子的故事所吸引住了,一听到鬼子送进了医院,他才松了一口气,说:
“真危险呀!以后没有什么事了吧?”
“没有什么事?”王强眨着小眼笑着说,“危险的事还在后边呢?你往下听吧!”他又接下去说:
“我在回来的路上,狠狠的吐了两口唾沫,心里说:‘奶奶个孙,鬼子才真是为钱不要命哩!’当我开始看着他满头是血,坐在炕上的时候,他样子很泰然,好像眼前的两具尸首,和他自己身上的伤,并不算什么似的,一点也看不到难过的样子。当时我就奇怪,也许是这些鬼子军官,打咱中国,杀人杀得太多了,手上的血也沾多了,看见血不算回事。可是等我送他上汽车,听他说干活大大的,我心里才明白了。原来洋行里大掌柜和二掌柜的权力很大,赚钱很多,三掌柜的官最小,常作杂活,不被重视。所以这一次他没被打死,满脑子金票的飞舞,代替了伤口的疼痛。他完全被一个欲望所占有,大掌柜、二掌柜的死,不但没使他难过,相反的却感到幸运,因为他的伤好了,就有希望作洋行的大掌柜了,今后可以大把的抓金票,发财。要当大掌柜,就离不开这班脚夫替他出力。他临上车要我好好干,就是拉拢我,要我今后为他出力。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想鬼子总不会甘休的。准要开始捕人了。我也特别警惕。因为平时打一次岗,第二天就戒严,查户口,逮捕人,闹那么大动静。这一次白白丧失了两个军官,就会拉倒了么?不会的。可是一天,二天,三天都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车站上的鬼子像没事似的,每天还要我们装卸货。开头几天,有些胆小的,从那天见到鬼子的尸体后,就吓得不敢来了,怕受到连累,因为是我们一早发现的,容易惹起鬼子的疑惑。可是后来,看看没有什么事,就都又推着小车上站了。第四天人到齐了。我们一早正在车站上搬运货物,突然鬼子的骑兵包围了车站,四下架起了机关枪,我们所有的脚行,都被赶上了汽车,一直拉到宪兵队去了。“我在汽车上,看看所有被逮捕的人,只有我一个是参加这次事件的。我心想这次可完了。到了鬼子的宪兵队,不死也得剥一层皮。人们一提到宪兵队,头皮都会发麻。一进去,我们都被关进一个大院子里,地上铺着煤渣,鬼子端着刺刀,逼着大家脱下衣服,跪在煤渣上听候审问。每个人的膝盖都被尖利的煤渣刺得血呼呼的流。我是二头,还没等脱衣服,就被第一个喊去审问。鬼子宪兵队长亲自问案,旁边站着中国人的翻译官。宪兵队长问我:‘你的二头的?”我没鞠躬,只点了点头,回答说:‘是!’惹怒了旁边的翻译官,他想对鬼子讨好,给我一个下马威,只见他飞起一脚向我后腿踢来,并用手向我前胸一推,想把我甩个倒栽葱。可是我眼快,急用手向上一架,右腿猛力往后一蹬,只听扑通一声,翻译官仰面朝天甩到地上。我愤愤的低声骂他:‘你是不是中国人?’翻译官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正要去抽东洋刀劈我,被鬼子宪兵队长拦住:‘你的不好,滚的!’骂了翻译官一句,就拉我到屋里去了。他很客气的把我让到椅子上坐下,说:‘刚才翻译官的不好,你的不要见怪;洋行的事,你的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宪兵队长翻了一下白眼,不相信的摇了摇头:‘你的二头的,洋行常常的在,这事你一定的知道。’他的眼睛狼样的盯住我的脸。我用眼睛迎着他说:‘我真的不知道。’鬼子的脸马上沉下来,在屋里走了一遭,然后站在窗前,指着玻璃窗外边一群跪着的人,对我说:‘他们里边谁的干活的,你的知道?说了没有你的事。’我摇摇头说:‘太君!那天晚上,我住在家里,没在车站上,我哪里能知道是谁干的呢?我不知道。”我这第三个不知道,使这个宪兵队长暴跳起来,拍的一声,捶着桌子,茶杯被震翻了。他刷的从腰里抽出洋刀,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我的心一凉,耳边听到他叫着:‘你的二头,不知道,要杀了杀了你的。’我心里说:‘反正完了,’就又摇了摇头。可是,他的刀并没有砍下去,因为他问不出什么,是不会轻易杀了你的。
“这时,外边又进来一个鬼子,宪兵队长就怒冲冲的出去了。这新进来的鬼子满脸笑容,在我旁边坐下,从桌上茶盘子里,拿了两块茶点,送到我的面前。我说:‘我不吃!’他说:‘你要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不然,你要吃苦的有!’我说:‘我不知道,能硬说知道么!’鬼子冷笑着说:‘你愿意吃苦头,那么,好!’他向外边咕噜了一声,两个武装着的鬼子进来了,手里拿着绳子,站在我的两边。眼看就要动刑了,鬼子发怒的问我:‘你说不说?’我说什么呢?看看马上就要吃苦了,这时,我突然想起鬼子三掌柜的,我要用这个没被我打死的对头,来为我挡一阵了,行不行就这一着了,我就理直气壮的对鬼子说:‘太君,就这样吧!我再说你也是不相信的,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三掌柜金三就明白了。我是好人是歹人,他很清楚。出事的那天早上,我到洋行里去,还是我发现了这事情,又是我给宪兵队打电话报告的,我又打电话给医院叫来汽车,汽车来了,还是我把三掌柜抬上汽车,送到医院里。这一些事是真是假,可以调查。这事要是我干的,我还敢大清早到洋行去么?我说这话如有一点假,可以打电话到医院去问问,三掌柜会告诉你底细的。’不知怎的,也许是急了,当时我很能说话,一气说下去。鬼子听了以后,顿了一下,仿佛认为我说的有些道理,果然,立刻从桌上拿起电话听筒,打起电话来了。我听出电话里有三掌柜的回声了,我的心在跳着。他们叽咕了一阵,鬼子把听筒放下以后,脸上有了笑容,很快的走到我的跟前来,握着我的手说:‘你的好人大大的,三掌柜的说你很好,好,你回去,没有你的事!’
“就这样,我就出来了。我一边抹脸上的冷汗,一边心里说:‘被抓的那些脚行,他能问出个什么呢?杀人的已放走了,他们这些人才真是不知道哩!’还不是空折腾一阵子,又都放出来。这些人虽然受了点罪,可是那两个鬼子军官,终究是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了。杀鬼子的事,就是这样。”
老周一气听完王强和老洪杀鬼子的故事。当他抬起头来,才感到天很晚了,听到外边呼呼的风声,风里夹着雨点,打着窗纸,远远的传来了隆隆的春雷声。他刚才完全沉浸到故事里去了,一阵紧张,一阵高兴。最后他对王强说:
“老王!你真行!机动灵活,随机应变!”
“不!”王强说:“行的不是我,而是老洪,枣庄哪次杀鬼子的事都少不了他,都是他领着干的。……”
王强的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到街上“拍拍”响了几枪。王强急忙站起来,低低的说:“出什么事了么?”接着又听到外边轻轻的扑通一声,一阵急遽的马蹄声,从小屋后的短墙外响过去。王强赶紧吹熄了灯,小屋顿时变得漆黑。王强低声对老周说:
“鬼子的骑兵过去了,约莫又是在追捕人!”
他的话刚出口,小炭屋门吱吜一声开了,闪进一条黑影,王强问:
“谁?”
“我!”火柴擦的一声油灯点亮了。他俩看到灯光下,站着一个人,正是老洪。他比王强个子稍矮些,可是浑身都是劲,两只眼睛亮得逼人,他袖子上有片鲜血,手里提着矮枪,胸部不住的起伏着,王强问他:
“老洪!你怎么了?”
老洪点上一支烟,狠狠的抽了一口说:“刚才我打了鬼子一个门岗,叫鬼子的骑兵追来了。”
当老洪看到老周时,惊喜的上前,紧握着手问:“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傍晚就来啦,已等你半天了。”
王强把老周来的情况,谈了谈,老洪连连点头:
“这太好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