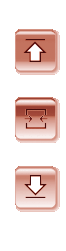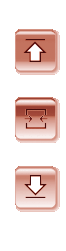|
|
|
|
二、折磨
|
空气越发干热,太阳毒辣辣的像火烤一般。天空晴的瓦蓝瓦蓝的,连一丁点云彩丝都没有。花草树木庄稼都晒蔫了,把叶子卷缩起来,看看都要干死了。有些老年人天天仰头望天,磕头许愿,只盼风娘娘送来云彩,雨娘娘给下场透雨。年轻人们可把老天爷的八辈都骂了。他们不服气,黑夜站着岗抢着浇地,老年人也跟着干。井水被打的剩了泥浆,滹沱河底和村头的大水坑底干的裂了缝。人们难过地唉声叹气,空着肚子含着眼泪,还得天天给敌人送钱、送面、送肉、送鸡蛋,修碉堡……敌人的活动一天比一天紧,几乎每天头明半夜地包围村庄,找女游击队长,抓人抢粮,把人都快折磨死了。看看天将正午,张大娘端着一个盛了才磨的玉米糁的簸箕从磨棚里走出来。一只老母鸡也跟着跑出来,用嘴在地上刨了两下,没有找到什么吃的,发愁似地咕咕叫着蹒跚地向草棚子里去了。大娘的脸消瘦了。她难过地望望天空,心情恍惚地向槐树底下走去。秀芬、小曼走来,一块坐在槐树底下,擦着脸上的汗。秀芬见大娘低下头用衣衿擦眼泪,就忙问道:“大娘,怎么回事?快说给我吧!”说了亲切地去扶着大娘的胳臂摇着。
大娘抬起头来吁口气,苦笑着说:“没有什么,不过一时想起大雨那孩子来了。”
要在往日,小曼早跑到娘怀里去撒娇哄娘了,现在她却低头在地上划着字,一声也没有言语。秀芬看着也觉纳闷,不由地轻轻推了小曼一下。小曼抬起头来,明白秀芬那眼神是在责怪自己,便说道:“昨天黑夜我跟娘商量,我要要求到区里参加抗日工作。一说离开家,娘就不痛快起来。”
大娘忙插话道:“你爹为掩护县委机关被鬼子打死了。你哥参军是我送他走的。你才多大一点年纪?又要离开娘……”大娘说着心里难受,说不下去了。
秀芬忙劝道:“大娘,别难过,大雨哥在大部队上比咱们这里还好呢。咱们区里县里同志们谁不知道你是一心为党的好同志啊。”
小曼一下立起来冲着娘说:“娘,难道你是喜欢一个没出息的闺女吗,我要那样你不觉着丢脸吗?”
大娘一下抬起头来,眼睛湿湿的,看看小曼和秀芬说:“娘说过拦你的话吗?只要你凤姐不嫌你小没用处,你就去吧,反正你们也是在一起的。”
小曼一下跑到娘跟前,蹲下把头扎在娘的怀里。搂着娘正高兴呢,觉着脖颈上落下两滴水点,不,这一定是娘的眼泪。忙抬起头来用手给娘擦了一下脸颊上的泪痕,正要安慰她几句,娘却用热手抚摸着她的头说:“把小武子他们从黑屋子里叫出来吧。这就晌午了,我看敌人也不会来了。”
“好,我就去!”小曼说着跳起来冬冬地向后院跑去了。
秀芬想跟大娘说些别的话宽宽心,便看着这在烟熏火燎的墙壁上盖着新顶的屋子向大娘问道:“有工夫咱们得再往房顶上糊层泥,不然一下雨会漏的吧。”
大娘仰脸看看火一样的阳光,摇摇头说:“只要老天爷下场透雨,哪怕漏倒了房我也愿意呀!”
秀芬倒真发起愁来了,看着大娘说:“这村有好多家要出外讨饭吃去啦。还不下雨,嗐,怎么办呢?”
说着小曼跑了回来,在衣衿里兜着才从树上采来的榆叶,一面走着抓起一把塞到嘴里。又着急地说:“别说话啦,快去看看凤姐吧,她烧的直说胡话。”
大娘哟了一声说:“早晨不是还好好的吗?”
三个人赶紧往后院走去,急忙来到许凤住的屋里,只见许凤盖着棉被躺在炕上,黑发蓬松,脸瘦的露出了颧骨。她闭着眼睛,嘴唇直动,说着听不清的梦话,脸蛋红艳艳的。大娘轻轻坐在她身边用手在她额角上一摸,热的烫手,不由地嗐了一声。
许凤这些日子天天黑夜参加挖洞。前几天夜里她累的浑身流汗,从洞里上来,坐在院里叫凉风一吹就病了。她这个人有个怪脾气,有点病从来不说,也绝不哼呀唉的叫苦。又带着病参加了这次袭击,累的病更重了。勉强拖着千斤重的腿走回张村来,不吃不喝,只觉得头疼欲裂,浑身恶寒,躺在炕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今天冷的浑身直抖,觉得头胀的不知有多么大,身子像是在旋转,房子像是飞上了半天空。她迷迷糊糊地觉得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空中飞舞着嚎叫着。她觉得自己来到了野地里,黑云沉重地压在树梢上,一声霹雷,狂风暴雨夹杂着冰雹猛打下来。狂风拔倒了大树,地下满是陷脚的淤泥,她拚命跋涉着,倾盆大雨浇在身上,冷得浑身哆嗦,牙齿咬得咯哒咯哒直响。好容易蹚出泥水,敌人的骑兵舞着明光耀眼的战刀又追上来了。她使劲跑,可是怎么也跑不动。她闪过敌人的战刀,举枪射击。她喊叫一声醒来,心还突突地跳个不住。慢慢地睁开眼一看,只见大娘、秀芬、小曼、武小龙、郎小玉、陈东风他们一群人都挤着立在炕下边,静静地望着自己。有人轻轻地叹着气。许凤竭力打起精神,微笑了一下说:“别结记我,不碍的,快去,你们快去挖洞!”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闭上眼,又说起胡话来:
“哪儿也别去,战死啦,情况……绝对不!……不后退!
……”
人们一个跟一个走了。秀芬和小曼喂许凤喝了水,吃了药,给她盖好被子,放下竹帘子,轻轻地走出去了。窗上的阳光全部被阴影吞没了。许凤渐渐清醒过来,浑身不那么疼了,可还是头旋,蒙蒙眬眬地听着窗户外边有人说话,她注意地听着。
一个声音尖细的女人说:“这一回八路军真完啦,咱们八分区的司令员和政委都叫鬼子打死啦。”
“在哪儿啊?”
“在肃宁县……”
“好些干部逃亡啦,有到天津去的,也有到北平去的。”“大封锁沟快挖成啦,两丈多深,三丈多宽,直上直下的,掉下去就上不来,听说还埋了地雷呢。”
“唉,公路跟蜘蛛网一样,汽车来回直跑,不有数不清的岗楼,你一动弹人家就看的清清楚楚的啦。”
“藏也藏不住,躲也躲不了,大部队也不会回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枣园据点不是叫领良民证吗?”
“是啊,还得挨个的到枣园去照像哩。好几个村都去啦,咱们村张立根可不叫去。汉奸王金庆把联络员福臣大伯给打坏了。”
“不去也不行啊。这一回来的几个汉奸特务头子,都是本地人,谁家的锅台在哪儿他们都知道。明个一个乡住上一个清乡队,三四十个人,一色的盒子枪,谁挡的了哇!”
“唉,老天爷呀!怎么生在这个年头啊!”
“许凤还在你家藏着吧?”那尖嗓女人在问张大娘。
张大娘干脆地回答:“是啊,在这儿哩!”
“还不快点叫她走哇!赶明儿搜出来可受连累。”
许凤听到这里,心里好生难过,光想翻身坐起来,看看是谁,可是动不了。只听张大娘说:
“叫她上哪儿去?就是她不在俺家吧,俺也是个抗属,俺娘儿俩又都当过干部,她在不在俺家里还不是一样吗?就是有汉奸向敌人报告了,把俺娘儿俩抓去,顶多也不过是个死。孩子他爹已经叫鬼子打死了,俺也不想当亡国奴活着。该死就跟许凤一块死。要死不了啊,那可就由不得他们了!”大娘说到这里用鼻子吭了一声。
许凤听着忍不住鼻子一阵酸楚。
“唉,这话说的也是啊。”不知是哪个老太太声音颤抖地说。
又是那个女人的尖细的声音:“这些话可别叫许主任知道了啊,她挺厉害的……”
大娘笑了一声:“我说这个干什么?你放心吧,她不会把你当做汉奸办的。不过你的嘴可得严实点!”
“放心吧,她婶子,咱也不是那种人哪。”
那女人正叽叽喳喳地说的欢呢,听见一声咳嗽,张立根吹着口哨进院来了,那女人吓的说了声:“俺走啦!”跟着是冬冬冬的跑着小颤步的声音,似乎是向大门去了。
院里静了片刻,大娘嗐了一声说:“立根,这是什么环境啦,你还天天在街上大摇大摆,吱吱地吹口哨。你呀!你呀!”张立根笑了一会儿,严肃认真地说道:“我是得大摇大摆。你知道么,我在街上这么一摇一摆,那些动摇派就稳住了,投降派就吓得不敢动手动脚了。”
大娘听着噗哧一声笑了,说了声:“对,到这工夫就是得硬点!你得注意,几个党员也在背地里说,完了,抗日看不见头了……”
立根说:“连有的支部委员也主张别跟敌人硬斗了,这怎么得了。晚上开会就是对这种思想展开批评,你得准备发言……”
谈话声越来越小,好像走到别的地方商量什么去了。许凤听到这里,心里得到很大安慰,心情一舒畅,便不知不觉睡着了。一会儿恍恍惚惚地听着又是一个老太太说话的声音:
“找一块姜给她弄点开水喝吧。”
“要有点糖多好。唉,这年头!”
“她是发疟子吧?吃了秀芬找来的这药也许能好了。”
许凤被人扶着吃了药,喝了水,又闭着眼睛躺下,觉得有两只手伸过来轻轻地摸着自己的前额,那样温存地揉捻着。她忽然感到这是慈爱的母亲在守着自己。她多么想摸摸娘的手,把头枕在娘的怀里呀。她伸手去摸着那双手,喘息地微微睁开眼一看,原来是小曼家邻居张老奶奶,满是皱纹的干巴巴的脸上,带着慈爱和忧愁的神情。
老奶奶见她醒来,小声地问道:“觉得轻些了吧,闺女?”
许凤舔舔烧裂了的嘴唇,嗯了一声,振作精神微笑了一下。
老奶奶抚摸着许凤说:“她凤姐,敌人才又打东村过去啦,可吓死人。这日子可怎么算了头!还是送你回家吧。不是我顽固落后,可咱县里的人一个也不见了,八路军大部队都没影啦,你个闺女家能怎么着。你说是不是,她大娘?”老奶奶冲张大娘看着,白发苍苍的头不由自己地摇了摇。
张大娘只唉了一声,没说什么。
老奶奶又说:“病好一点了,还是送她凤姐回家吧,省的叫她娘在家里惦记着。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要有个好歹可怎么着。她凤姐要像人们说的打鬼子的那女队长那么壮实,也还罢了,可她身子骨儿这么细弱,怎么行啊!”
张大娘只在旁边哼哈答应着,也不想多跟老奶奶说什么。许凤只觉恶心头眩不想说话,睁睁布满红丝的眼睛,又昏迷过去了。忽然,她又像迎着大风跨上骑兵团的骏马飞奔起来,秀芬和小曼也飞驰过来了,无数战马犹如怒涛席卷大地,周明那明朗严肃的面孔一闪而过……胡文玉却勒马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她追他,喊他……叫他回来……天空黑云乱翻,震耳的霹雷,好像从地底下迸发出来的,又隆隆地向四外滚去。四外是黑雾沉沉,一阵寒风暴雨打在身上。她悲痛,她愤怒,她呐喊着……突然,许凤觉得有人摇自己,睁眼一看,看秀芬和小曼坐在自己身边。小曼拿了一块热气腾腾的湿毛巾来,在自己脸上试了试,才给许凤擦脸。秀芬又端了热粥来,许凤肚里也想吃东西了,便扶着小曼坐起来,把粥吃下去,觉得身上轻爽多了。小曼郑重地对许凤道:“凤姐,等你病好了,我想求你一件事。”
许凤忙问:“什么事?你说吧!”
秀芬直冲冲地接口说:“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她要求入党,我愿意当她的介绍人。”
许凤笑了一下,把小曼搂起来,脸贴脸地亲着她。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