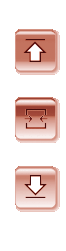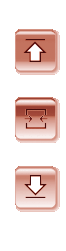|
|
|
|
五、沉沦
|
猛烈的爆炸声震得窗纸咕哒哒直响。胡文玉目瞪口呆地立在炕下,向窗户望着,惊疑地听着。爆炸声停止了,枪声也渐渐地听不到了。他还在失神地瞅着窗户发愣。灯光跳动摇闪,照在他的脸上,他沉思着,这些天出人意料的突变把他陷在痛苦和彷徨迷惘里边了。他一直在思虑,解也解不开,摆也摆不掉。现在他呆呆地立着,心又回到大扫荡那天的情景里去了……
那一天,他只听见炮弹在身边爆炸,子弹在头上飞鸣,前后左右发生了什么,根本没有看清。他从地上爬起来,在烟尘里不顾一切地向漫地里飞奔。突然郎小玉一下按倒了他,他伏在地上,不知是怎么回事。
答……答……答……叭,叭,叭……
密集的弹流从头顶上扫着麦穗射了过去。郎小玉又拉了他一下:
“政委,快爬,快爬!这边的敌人过去了,可以突围。”
胡文玉按郎小玉指的方向爬去,听着旁边麦田里哗啦哗啦直响,不知多少人惊慌地爬起来跑了。伪军在后边喊叫着:
“站住!敢跑!”
“举起手来!过来!”
在后面响了几枪,一定是在打逃跑的人了。胡文玉藏不住了。光想立起来,又不敢立起来,犹豫一会,慢慢抬头一看,敌人并没有追过来。他向前爬了一段,立起来就跑,刚一翻过古洋河堤跑了不远,就见东、南、北三面白光闪闪,日本鬼子的自行车队又圈上来了。河堤上出现了挎战刀的鬼子军官,举着望远镜在瞭望。他没有办法,只好向敌人包围圈里走去。一摸腰里,皮带和驳壳枪都没有了,记不清什么时候丢了。哎呀呀!衣袋里还有一支钢笔和一个小笔记本,他趁着身边有几个庄稼人遮着,把钢笔和笔记本丢在路边的粪堆上,用脚一踢埋了起来。抬头一看,只见北旺村街头上黄压压的都是鬼子和被迫来“欢迎”敌人的惊慌的人群,几面小旗在晃动。同时传来打人的砰拍声和喝骂声。胡文玉一步挪不了四指地走着。正在心慌意乱,忽然响起紧急的哨子声,鬼子们驾起摩托车狂奔起来。这时他才发现东北上枪声激烈,远远望去,漫野尘头飞滚,直指平大路方向。一定是骑兵团突破包围了!这是敌人没堵住,又增调快速部队追击了。
“看啊!是咱们的骑兵!……快跑啊!”有人这样喊。
和胡文玉一起走的几个人都撒脚奔跑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一起跑的人都不见了,剩了胡文玉一个人在头里猛跑。看看到了段村村头,糟了!村里乱攘攘的都是敌人。
“站住!举起手来!”
三个伪军挺着刺刀逼上来了。他被带着往村西那个大柏树坟地里去。在右边一块洼地里二十多个青年被赶下去,鬼子的机枪像刮风一样一阵扫射,青年们都躺倒了。
“看见了吗,这是因为他们领头逃跑,都是八路!”伪军对胡文玉冷笑了一声说:“皇军要看中了你,也许凑数把你一块干了呢。”
胡文玉听着心里猛地凉了半截,见一个鬼子向自己走来,小腿肚子就抖起来,心里想:难道就这样像开个玩笑一样打死我吗?忽听后边喊叫了一声,伪军用枪托打了他一下,带他回头向坟地的矮土墙边走去。他以为就在这儿杀他呢,浑身晃晃悠悠的一脚高一脚低,已经吓的走不动了。听着伪军喊了一声,面前出现了一个大连鬓胡子黑胖脸高个子的伪军军官,手里玩弄着驳壳枪的皮穗子,仔细地盯住胡文玉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我叫赵白,是赵庄的,赵文卿是我大伯。”胡文玉背诵着预先准备好的口供。
伪军军官渐渐露出了笑容,坐到矮墙上,用枪穗子抽打着黑亮的高统皮靴,浮土像烟一般扬起来。他一指对面那个树桩说:“嗯,请坐!”又对那几个伪军摆一摆手说:“去吧!”
伪军们走了。胡文玉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得坐在树桩上。伪军军官掏出烟卷来,自己吸着一支,又递给胡文玉一支说:“吸吧,别客气,你是文卿的侄子,为什么我没有见过你?我就是大队长张木康。”
“我净在北平混事,这次回来看看家,昨天去串亲,就赶上扫荡了。”
他发现这个伪军军官,好像并没有恶意,一点也没追问找岔,却像老朋友一样只扯赵青家的事,听起来他比胡文玉还知道的多,甚至连赵青五六岁以前的事他都知道。只听他又突然问道:
“你是文业哥的大少,你是属什么的来?”
胡文玉哪里注意到这个,只好胡诌道:“属马的。”
伪军军官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会,黑胖脸狞笑着露出白牙,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道:“我知道你是谁了。”接着叫来几个伪军,一挥手:“带走!”
……
胡文玉就这样在残酷混乱的扫荡中失踪了。赵青在被群众用抬架抬回家来之后,曾经派人到处打听胡文玉的下落。看来没有指望了。不料隔了几天之后,一个黑夜里胡文玉突然来到了他家里,十多天不见,竟然瘦损憔悴的不敢认了。胡文玉一见赵青,就把他怎样冲出敌人包围,怎样跑到平大路附近的李村,怎样累的吐了血病倒了,在一个老大娘家隐蔽了几天,说了一遍。赵青见他蓬首垢面,精神不支,说着话儿直是咳嗽,就劝他先在家养养病,再计议怎么工作。随即叫了妹妹小鸾来,吩咐她好好照顾胡文玉。正赶上他爹赵文卿老头子也从天津回家看望,也介绍相见了。一家人对胡文玉十分热情,把他安顿在这严密的东跨院北屋里住下。胡文玉受尽惊骇,突然得到了休息和安慰,似乎应该振作起来,不知为什么心情却十分不安。日夜瞪着大眼睛出神,偷偷地唉声叹气,特别是一听到传来枪声,就惊魂不定地跳起来。
往事像噩梦一样压在他心头,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呆呆地立了一会,嘘了一口气,拿起烟斗来,慢慢装上烟,在灯火上吸着,不由地又想起赵青的爹赵文卿来。赵文卿胖胖的高个子,亮光光的秃头顶,满脸都是笑纹,穿着串绸裤褂,黑呢鞋,金表链在胸前扣子上系着,手里玩弄着名人书画的折扇,风度翩翩。赵青把胡文玉介绍给他,他打着哈哈,自我表白说:
“我是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国难当头,只好学陶朱公自食其力,经营点商业,这是不得已呀,哈哈哈!请,请!
……”
胡文玉被让到桌边坐下。桌子上江西大花瓷盘里,盛着热气腾腾的肉饺子。小鸾坐在炕沿边上在剥蒜瓣,她那一团火似的眼睛,不住地瞟着他。赵青的姨娘小美,打扮得妖里妖气,叼着烟卷,一口天津话,不停地向做饭的老太太挑三捏四的。
于是在恭维的笑语声中,一起吃起饺子来。
“不要紧,你就在我这里住着吧,我保险什么事都不会出。”赵文卿笑着,用白手绢擦着秃头。
胡文玉回味着当时的情景,心里也奇怪起来。过去只知道他是个买卖人,现在看并不那么简单。他为什么单单在这时候回来呢?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胡文玉坐在炕沿边,磕了烟斗又装上一袋吸着。
这赵文卿是个三百多亩地的地主。“七七”事变前是这一带办教育的绅士,国民党的县党部委员,当过大乡长,开过银号,事变后发行过小票子,还开过烧锅、杂货铺、运货栈,又是来往天津的大行商。他秘密地勾结着一批流氓土匪,所以在这一带很有势力。他为人八面玲珑,笑里藏刀,善于投机取巧,只要有利可图,见缝就钻。不管什么人,只要跟他一接近,就免不了要吃亏。财主就得叫他刮点钱,穷人就得给他白出力。还得叫你笑在面上,苦在心里。因此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大烙铁”。共产党八路军一来,他立刻打出抗日的旗号帮助收枪,改编义勇军,并且叫儿子赵青也参加了游击队。实行合理负担之后,他一算账不合适,立刻又把土地分给穷苦的亲友自种自吃,脱掉了负担,又落了人情,暗中却又白得些租子。自己落得清闲自在,来往天津经营商业。他就这样表面上很开明,实际上脚踏三只船,和国民党、日伪军都保持着联系,等待时机恢复他的势力。为了表现进步,把雇工都辞退了,只留下亲族中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嫂子给料理家务,名义上是白养活她,当然工钱是没有的。他这套手腕确实骗过了好多人。又加赵青参加工作后入了党,一直表现得很积极,就更没有人再去怀疑他了。
胡文玉虽然对赵文卿有些怀疑,但想到赵青是个干部,又是党员,心也就踏实了;再说由于心情不好,便装做有病,口头上虽不断和赵青说要出去转转,赶快恢复工作,可是今天推明天,总也出不去。他整天价藏在东跨院什么人也不见,只跟小鸾、小美泡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根本不知道许凤派人来找过他。听到的都是坏消息,说什么:部队全垮了,干部们死的死逃的逃,谁也联系不上。又听说敌人三个村安一个据点,驻二十个清乡队……他听了这些就已经抬不起头来了,偏又听说许凤被敌人俘掳去了。这一下对他是再严重不过的打击,使他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胡文玉精神变得萎靡颓丧,举动迟缓,意志消沉,那种蓬蓬勃勃的锐气,都丧失净尽了。现在他从红漆迎门桌上拿起镜子来,在灯下照着,摸摸自己那苍白的脸颊,灰心丧气地放下镜子,一骨碌躺在炕上,瞪起那空虚无神的眼睛,出神地喃喃自语着:
“唉!完啦,一切都完啦!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哪?”
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摧折了篷舵的破船,无目的地在汪洋大海里漂流着,一切希望都毁灭了,现在只是等待着沉没,死亡,可又非常害怕死亡。他胡思乱想地拍打着自己的前额。
这时屋门轻轻地开了,赵青扶着双拐冬冬地走进来,他没有招呼就悄悄地坐在八仙桌旁边的椅子上。胡文玉抬头看了他一眼,仍旧伏在炕桌上,用铅笔在一张纸上胡乱写着字。赵青起来凑到炕桌边,就灯火上吸着烟卷,看见胡文玉在纸上乱写着:
“茫茫的长夜呀,我已等不到天明,一切都成了泡影,战斗,有何用?怒海狂涛你吞没我吧,吞没我吧!你已经吞没了她,我也应该沉没,沉没,沉没!……”
胡文玉见赵青来看,忙将字纸一团,在灯火上烧着了。
赵青猛吸了两口烟,对面坐在炕桌边,唉了一声说道:
“真出乎意料之外,鬼子这一次还能有这么大的兵力来对付咱们冀中!看起来,形势越来越严重了。”赵青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天津寄来的《庸报》递给胡文玉。
胡文玉接过报纸,展开在灯光下看着。问道:“哪儿来的汉奸报纸?”
赵青笑道:“好多村都收到了天津寄来的报纸、宣传品,还有这玩意儿。”赵青说着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叠纸说:“是敌人自动寄来的,根本不收费。”
胡文玉又接过那叠白光光的道林纸一看,竟是一套彩色的春宫画,旁边印着反共标语,看着摇了摇头。赵青叹口气说:“你看看报上的消息吧,真没有想到鬼子还有这么大力量。太平洋战场英、美还是一直失利,连东南亚许多国家也被鬼子占领了。我们这里恐怕将和东北一样变成日本鬼子的后方基地哩。听说重庆方面的代表也正跟鬼子秘密谈判。因此,鬼子能够集中全部力量来搞我们各个根据地。我们各个边区都受到很大损失。如此下去,结局不知道将要怎么样呢。”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
胡文玉呆呆地听着,唉了一声说:“看来我过去真是盲目乐观主义!这次大扫荡这么厉害,也全出乎我的意料。嗐,局面是真严重啊!”
赵青点点头说:“国际形势也对我们不利,现在莫斯科被围,列宁格勒朝不保夕,德军还在南线不断突进,斯大林格勒已经陷入重围,红军牺牲很大,一旦失守……”
胡文玉翻过报纸的第一版,突然发现了触目惊心的大字标题:“皇军赫赫战果,共军冀中主力全部被歼,沧州道全境治安强化。”
他呆呆地看着,已听不清赵青还在说什么,就觉得惶惶惑惑六神无主,浑身像泼上了一盆凉水,从头顶直冷到脚跟。
他心里乱七八糟地寻思着。
赵青又加上一句说:“我们不能闭着眼睛瞎干了,应该好好想一想啦!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可以避免牺牲的方法救国吗?”
胡文玉托着腮只是看着灯火沉思着。好半天才喃喃地说:
“不是派人找县委去了吗?等着看县委有什么指示吧。”
赵青悠长地嗯了一声说道:“县委,好吧。不过你也应该主动地把工作安排一下嘛!”
胡文玉一听,竭力打起精神说:“对!我这不是正在起草一个工作计划吗?我虽然病着,可是我决心很快地把工作恢复起来,得马上出去了解一个情况,首先得派同志去掌握各村的维持会。再提拔一些干部到区里来工作。你也赶紧把失散的队员找一下……”说了激动地大口吸着烟,在屋里踱着步,显出了沉思焦虑的样子。
“找寻队员的事,我正在办。你身体不好,还是休息休息吧。”赵青说着,用小白手绢擦擦脸颊,温和地点点头走出去了。
胡文玉思绪如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抗日,革命,为什么?他茫茫然,魂儿又回到了那豪华的家,看到了那绿树、红楼……忽而他又幻想着内心的追求……他厌倦地躺在炕上吸烟,无聊地向空中吐着烟圈,看着那一串烟雾和顶棚的花纸在灯光闪烁中变幻着,仿佛出现了一匹骏马,上面坐着一个将军,又有一座宫殿似的高楼大厦,周围各样的花草,古树参天,湖水泛着波光,一群人恭顺地向将军鞠着躬。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将军,翻身下马,把缰绳递给随从,和一个美女携手并肩地说着话,往那幽静的花园里走去。正幻想着,听见一个女人轻轻咳嗽了一声。胡文玉抬头一看,是赵青的妹妹小鸾走进屋来。她穿着一身素净的淡蓝裤褂,粉盈盈的圆脸露出矜持的神情,像一枝出水的荷花,袅袅婷婷地走到面前站定,递给胡文玉几本书说:“你不是要看书吗?我给你找了这两本来。”
胡文玉接过来一看是《西厢记》和《金瓶梅》,在灯下随手翻阅着。小鸾挨近他坐下也凑过去看,两人摩肩擦臂久久地挨着。小鸾低声细语地说:
“再巴巴结结地赖着跟你说回话吧,环境这么残酷,说不定哪会儿谁就死了,像你这会儿死了也算一辈子!”
胡文玉听着叹了口气。
小鸾更凑近胡文玉温柔体贴地微笑着,给胡文玉把衣领整了整,小声地说:
“我跟爹吵了一架!”
“为什么?”
“他叫我到天津去上高中,我坚决不去。我要抗日,我要工作。再说,他哪里知道我的心早被一个人牵住了,哪怕那个人不理我,哪怕我为他死在这里,我……”她说不下去了,低下头掏出手绢擦着眼睛。
“你是说谁?”
“谁?”小鸾抬起头来怨恨地盯住胡文玉,颤声说:“横竖你知道,我知道。”
胡文玉心慌意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他呼吸急促,脸涨的通红,一下子把小鸾搂起来说:“我对不起你!”
小鸾突然忿忿地把他推开,一阵风似地跑出去了。
胡文玉脸上热烧火燎,神魂颠倒地往外遛出来,毫无目的迟缓地走着。这时月亮才升上当空,在月光下整个院子静得毫无声息,只有树阴花影悄悄移动着。赵青家这院落在赵庄是数一数二的好房舍,一套青堂瓦舍的大四合院,通过一个月亮门就是胡文玉住的一座幽静的东跨院,院内宽宽敞敞,绿槐成荫,夹竹桃石榴树葱茏地掩映着窗台,藤萝葡萄搭成花架凉棚,很是讲究。
胡文玉烦闷地走出月亮门来,在院里呆立着。石榴花枝在月下微风中拂擦着小鸾的窗台。灯光把小鸾的影子投射在窗纸上,她在绣着什么。只听她小声地叹口气,哼起悲哀的曲调来。她的声音是那么凄凉又那么哀怨动人。胡文玉轻轻地走过去,痴呆地扶着花枝,凝视着地上的月光,侧耳听她唱,光想流下泪来。
胡文玉仰首望望天空,长出一口气,拨开花枝,走到藤萝花架底下坐在凳子上,默默地吸着烟斗胡思乱想起来:“为什么才发现小鸾这么好?她多么风流,多么漂亮,她一定是又爱我又恨我,我对不起她!”他想着恍恍惚惚地像是又穿着西装皮鞋在北平的柏油马路上走着,右臂挽着一个漂亮的穿高跟鞋的女郎,她就是小鸾。恍恍惚惚带着她坐车回到了家里,又看见了那沙发、地毯、粉红色的电灯罩、淡绿色的丝绒窗帘,灯下闪耀着小鸾的笑盈盈的红唇,粉盈盈的圆脸和她那无限幽怨、似恨非恨的眼神……胡文玉一年来,一直用冷淡的态度对待小鸾的追求,几次把小鸾写给他的情书连看也不看,就撕碎了。现在他忽然感到那些忠诚、节操都是无用的了。他立起来,推开小鸾的屋门,一闪进去,窗上两个人影抱起来,灯光突然熄灭了。
胡文玉从小鸾的屋里悄悄蹓出来时,已经是早晨五点多钟了。
胡文玉离开小鸾回到自己屋里还不到两个钟头,赵青就扶着拐杖走进屋来,板着冰冷的面孔,两眼向胡文玉射出寒凛凛的光芒。胡文玉看见赵青用这样的眼神看自己,心就虚了,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赵青坐在椅子上,单刀直入地问:
“你跟小鸾这是怎么啦?”
胡文玉红了脸,张口结舌地正想抵赖。赵青一挥手,说道:
“别赖了,小鸾都跟我说了。胡文玉同志,你想想这有多么严重。一个共产党员,生活腐化,这不是小事,这是一个品质问题。”
胡文玉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了。
“再说,你这样怎么对得起许凤同志!你爱着许凤,许凤也爱着你,就不该,嗐!想不到你……”
赵青激动地吸着烟,胡文玉低头不语。静了一会儿他突然像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急手架脚地在自己衣袋里翻找起来,可是什么也没找到,似乎失落了什么东西,又不敢寻问。他脸色突然煞白,一会又涨得绯红,鼻子尖上沁出汗珠,呆呆地向窗户望着,叹口气,颓萎地坐了下来。赵青却只是吸烟,冷静地观察着他。看了一会,也不言语,立起来想走。
胡文玉忙立起来拦住赵青恳求道:“求你无论如何要给我保守秘密。”
赵青叹口气道:“家丑不可外扬。这是你们俩自己的事情,我也犯不着多管。”接着,又用阴森森的眼光看着胡文玉道:
“至于能不能保守秘密,一切全在你自己。”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