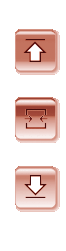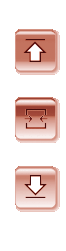|
|
|
|
四、狼窠
|
赵青一觉醒来,睁开眼睛看看,已经后半晌,窗户上的阳光还有两道窗棂。院里静静的没有人声,只有扁豆架上的蝈蝈,吱吱地叫一阵歇一阵的,夹杂着麻雀的喳喳声。他照着镜子摸摸自己的脸蛋,一咧嘴做了个鬼脸。穿好了衣裳,洗了脸,跑到院里看了一会花,又回到屋里,微笑着,用手拧了个响啪,从墙上摘下胡琴来笑眯眯地拉着。他暗自谋算着,打下李铁,叫自己的人当上队长,再打下许凤去,那时候就会满有把握地当上区委书记……正自高兴地想着,姨娘小美轻盈地走进屋来。她今天打扮的十分妖艳,头发梳的黑亮,穿着短袖白绸小汗衫,拿着小团扇,一阵风似地走到赵青跟前,格格地笑着说:“你爹个老家伙天不亮就走了,你怎么把他弄走的?”
赵青笑着说:“很简单,昨天我告诉他说:县公安科要抓你哩。他一听吓得像个二傻子,再也站不住脚了,忙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快走吧,没有信你可不要回来。”
小美吃吃地笑着问:“那他怎么说?”
赵青说:“他说,好,我走,能走的了吗?我说不要紧,我叫人送你,连夜到天津去。就这样。”
小美对着窗户坐在凳子上,举着小镜子照着。用尖细嫩白的手指抹擦着眉毛,哧哧地笑起来说:“你爹昨天晚上非逼着叫我跟他一起到天津去。”
赵青叹口气说:“白劝你半天,你还是不跟他走。”
小美呸了一口说:“这年头儿,妇女也兴自由了,一辈子不见他个老不死的才好!”
这时听小鸾在外边说:“老胡来啦!”小美忙跑出去看。
胡文玉这几个月轻易不到小鸾家来一趟,非来不可时,来了也总是设法快点儿走掉,光怕被人发现他和小鸾的关系。无奈小鸾全不顾体面,死缠住他不放,胡文玉也只好听着她摆布。这一次可不同,胡文玉一来就朝小鸾屋里走。小鸾这几天,自以为着着胜利,乐的魂儿飘飘的。天天只准备着县政府的通讯员来领她去工作呢。今天正乐得哼着小调子,对着镜子,研究自己怎样打扮更庄重朴素一些。听见脚步声是胡文玉来了,以为他是来接自己去县政府哩。不由欢叫了一声迎出来。见胡文玉闷着头朝屋里走,又忙跟进屋来,亲昵地叫了声:“老胡来啦!”胡文玉就扑上去,一下子抱住小鸾,把她按在炕上,一言不发,狠狠地捶起来。小鸾还当他闹着玩呢,又是哭又是笑,紧往炕角落里躲。小美见了,忙上去拉着:
“老胡,这是怎么回事?”
胡文玉打得不耐烦了,住了手,走到一边,装上烟斗吸着,指着小鸾说道:“妈的!你爱我,咱们就算结了婚,你是我的老婆,立刻拾掇东西跟我走!”
小鸾跳下炕来,擦着眼泪,又掩饰着得意的暗笑,娇声娇气地问:“上哪儿去?你说吧!我这不是正拾掇着准备走吗?”
胡文玉嘿嘿地笑起来:“上哪儿去?上北平!你不愿意去吗?”
小鸾吃惊地问:“上北平?你不干啦?”
胡文玉浑身颤抖地说:“不干了!少废话,快点儿拾掇!”
赵青在屋门口出现了,一挥手,小鸾、小美赶紧躲了出去。赵青沉静地用严厉的眼光看着胡文玉,掏出烟卷来吸着,同时递给了胡文玉一支。两个人吸着烟,沉默地坐着。赵青用低沉而亲切的声音问道:
“心里不痛快?工作谈了吗?”
胡文玉激动地吸着烟,没有言语作声,只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两股白烟像箭一般从鼻孔里喷射出来。
赵青又问道:“担任什么职务?”
胡文玉突然一声冷笑:“宣传干事!哈哈!宣传干事!”他把烟卷摔到地上,用脚狠狠搓了一下,插着腰望着窗户笑起来。
“怎么?你这是什么意思?”赵青也突然厉声地问。
胡文玉回头用愤恨的要厮杀的眼光对着赵青,用鼻子吭了一声:“什么意思?大丈夫合则留,不合则去!”赵青猛然立起来,往前凑了一步:“胡说八道!往哪儿去?我不能再容忍你!咱们到县委去谈谈,我要把你的一切都揭出来!”
胡文玉脸色煞白,把手枪掏出来,冲赵青一递说道:“要去你就去,把枪也带去!我退党,我不干了,再管不着我了吧!”
赵青不接他的枪,低声道:“怎么啦,你昏啦,你是在跟我发脾气还是怎么的?”
胡文玉把枪放在桌子上道:“跟你发什么脾气!我是不干啦,我受不了,我不是个任人摆弄的木偶!”
赵青叹口气坐下,沉思着,不时用冷森森的眼光观察一下胡文玉,又掏出一支烟来吸着。胡文玉匆忙地拾掇了衣服,包上一个包袱,向外边叫道:
“小鸾,你来,咱们谈谈。”
小鸾走进屋来,她正在梳头,抿着嘴露出嘲笑的挑战的笑容。胡文玉一手插着腰,一手把小包袱往炕边上一摔:“怎么着,你要做我的老婆就跟我走,要不,咱们就算完。”
小鸾盯着胡文玉说道:“看你那个样,要走也得叫我拾掇拾掇呀。”
“那就快点!”胡文玉坐下,冲赵青一伸手,要过一支烟来抽着。
小鸾慢腾腾地拾掇着,好一会儿谁也不吭声。胡文玉忍不住了,催道:
“快点呀!”
小鸾反而停住手坐下说道:“不,我不走,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胡文玉气的立起来,看看小鸾,又看看赵青,看看屋门口的小美,提起小包袱往外就走。踏出屋门,回头说了句:
“后会有期!”
“你回来!”赵青严厉地吼叫了一声追上去。
小鸾、小美也跟着追出去。几个人在院里挣扎了好一会儿,总算把胡文玉拖回屋来。赵青叫小鸾、小美出去。
屋里剩下赵青、胡文玉两个人。胡文玉完全变了样子,脸色青白,满眼红丝,充满了迷惘恐怖的神色,萎顿无力地坐在凳子上,两手抱着头,伏在迎门桌上低声地说:
“我心里充满了仇恨,我要杀人!要杀人!”
赵青小声说道:“希望你冷静点,这话可以说吗?”
胡文玉嘿嘿地冷笑了一声,逼近了对着赵青咬牙小声说:“你这伪君子,你他妈的装得正大光明,偷偷地跟你小妈妈睡觉。哼!什么东西,你也够个共产党员么!?”突然一抬头,用疯狂的眼睛看着赵青道:“你不是有手枪吗,你要不念咱们的交情,你可以打死我,趁我还没有到枣园去,以免将来我把你们杀光!快开了枪去请功啊。”
“呸!我想不到你会堕落到这样,叛徒!”赵青说着嗖地一转身,拔出手枪。
胡文玉惊恐不安地立着,看着赵青那无情的面孔,那黑森森的枪口,他骇怕了,脸上立刻冒出汗珠。他向后退着,一下瘫软地坐在凳子上,两手抱着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瞥见赵青把手枪又装回枪套里,平静地说:“我也太冲动了,唉,你好好想想吧,到底应该怎么办?”
胡文玉只是低着头,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去擦着眼泪,好久才抬起头来,眼睛红红地说:“我真昏了,不该这样,组织上还是信任我的,只要努力工作,也许有一天我会抬起头来的。”
赵青这时却冷笑了两声说:“不见得吧!”说着从衣袋里拿了一个小本子,掀开了取出一个名片来,递到胡文玉面前。胡文玉接过来一看是张木康的名片,上边还签着一行字儿。他看着愕然失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个名片使他又想起了那可怕的时刻……
那是大扫荡那天,胡文玉在段村村头被伪军抓住,押着走了三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他开始被审讯。一连几次,他都一口咬定姓赵,别的什么也没说。于是敌人把他带到一个高大宽阔的砖房院里。院里十分清静。走进一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屋子,就见张木康坐在太师椅上,黑胖脸上露着假笑,龇出一口白牙,毒箭似的眼光紧盯着胡文玉。
“请坐!胡政委!受了委屈吧!对不起!”说着,让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胡文玉心里一惊,看样子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他没有答言。
“你可以相信,任何人都不知道我和你见过面,日本人更不会知道。我不想留你在这边,你可以回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将来你感到有必要的时候,咱们也许会一起共事的。现在我请你在这里签个字。”
“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不签字!”胡文玉壮了壮胆大声说,可是同时小腿也抖了一下。
张木康平静地说:“我尊重你的选择,给你三个小时,也就是说到晚间十二点整,你要做出决定:或者是枪决,或者是签字。”说完就出去了。
胡文玉呆立了一会儿,坐在木椅上。椅子对面的方桌上,放着一架陈旧的座钟,一盏油灯。张木康把要他签字的自首书放在桌上。夜,静得令人可怕,一切喧哗都停止了,只有座钟嘀嗒嘀嗒机械地响着,时针不停地走着。胡文玉面对着时针坐着,计算着。忽然,他感到一阵彷徨涌上心头,好像一切都摇晃起来。他想起了在家里时那豪华享乐的生活和他逃出家庭的情景。他现在忽然明白自己根本没有准备为革命去死,可是现在却真的就要死了。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血污的尸体。他又感到四周一团漆黑,时针已经指到十一点半了,离死亡还有三十分钟。他脸上流着汗珠,衣服被汗水湿透了。黄色的灯光照着他那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他抖动着双手,拿起自首书,又放下。他的脑子里出现了问号:“我为什么要死?我干革命是为了什么?”他不能回答自己。时针已经毫不留情地指到了十一点五十五分。突然,门开了,张木康站在门口,看了看手表,从牙缝里迸出一种残忍威胁的声音:
“你怎么办?决定了没有?”
胡文玉茫然地站起来,不知怎样好了。座钟嘀嗒地响着,只有一分钟了。两个凶恶的特务提着枪进来了。
张木康又说话了:“只有一分钟了!你必须立刻决定!”他说着把钢笔递过去。
胡文玉突然像掉在海里的人抓住救生圈一样抓住了钢笔,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张木康接过去,看了一下,笑着拍了拍胡文玉的肩膀:
“我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我现在就送你走。为了你行动方便,请你穿上这件大褂,戴上这顶帽子。这是我签了字的一张名片,你好好藏着,在必要时候拿出来让他们看一下。”
胡文玉接了名片,穿好衣服,跟在张木康身后通过岗哨,走出了村头。
“好!我们一定为你保守秘密。”张木康的黑脸上浮着狞笑和胡文玉握了握手。……
胡文玉这才明白,原来这张名片是和小鸾发生关系的那一晚上,被她拿去了。他想着心神惶惑不安,不由地啜嚅着对赵青说:“反正我不是特务!”
赵青突然笑起来说:“不!你不但是特务,而且是真正的国民党特务。”
胡文玉震惊地张开了嘴,望着赵青。
赵青狞笑着一挤眼说:“是的!你已经跟我们一起干了不少破坏共产党的事业,他们不会饶过你的。再说,你已经干上了,就由不得你了!”赵青说着递给胡文玉一支烟卷,给他点着火吸着。胡文玉渐渐抬起头问:
“那么你是?”
赵青笑着喷出一口烟说:“我?事到如今,也只好对你公开了。我是本区的国民党书记长,正正经经的地下工作者。你呢,虽然以往你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可我已经给你请了委任状在这里了,看!”赵青递给他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白纸。
胡文玉接过来打开一看,只见一张石印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兹委任胡文玉为特派专员”几个核桃般大的字,旁边还盖着一颗朱红的大印。他惊奇得瞪着眼睛,狠狠地吸了两口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赵青笑道:“没什么奇怪的。以你的才能,只要忠心报效党国,前途比我要大得多。我也不想冒你的功。这几个月,靠着你的帮助,我们已经掌握了十多个村的共产党支部,并且在这些村的游击小组里,建立了咱们的秘密武装。这是许凤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发觉的。这可是大大的功劳啊!你知道么,国民党中央实行'曲线救国',已经派遣九十万国军投降日军。两边这么一合流,天下还不就是咱们的!叫共产党去流血、去牺牲吧。到时候咱们得了天下,你老兄立下汗马功劳,说不定还可以到南京见咱们老头子呢。那时候,随你要什么吧,金钱、美人、名誉、地位、高楼大厦、汽车、洋行……就是许凤吧,如果你喜欢她,你就娶她做姨太太好了,有什么困难!
哈哈……”
听赵青说着,胡文玉脸上,一会儿恐怖,一会儿惊慌,一会儿迷惘,真是瞬息万变。他觉得这几年自己好像做了一个梦。现在梦给惊醒了,梦中的那条路,生生的给打断了,再也接不上了。他又觉得自己在赵青布置好的染缸里洗了一个澡,染了一身黑,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赵青真阴险!为什么自己以前一点也没看出他的形迹呢?赵青真是个狠毒的猎手!自己已经落进他的网里,还脱得了身吗?不行!他就是放了你,你往何处去?还不是成为李铁他们的俎上肉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男子汉大丈夫,不甘,不甘!……他又向赵青要了一根烟吸着。吸着,想着,手微微地有些颤抖。思前想后,觉得也只有赵青给安排了的这条路可走。胡文玉好像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出路,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抬眼看了赵青一下,自语般轻声说:“我服你!我就是还不明白,既然你是干这个的,为什么大扫荡时还要冲啊,冲啊,弄得挂了彩呢?”
赵青笑道:“挂彩个屁!那是演戏嘛。你看我腿上有伤疤吧?”说着,撩起裤腿让胡文玉看。
“那么你杀死那个义勇军独立旅长的事,难道也是假的吗?你脸上不是还带着叫他砍伤的刀疤吗?”
“这个事可是不得已而为之。你知道,那个独立旅长是咱们的人。开初我们一块拉起了一支义勇军,本来要委他当书记长,后来见他不可靠,又委了我。他气愤不过,要把队伍拉着去安平投吕正操司令。你想这怎么得了。我只好先发制人,找县游击大队,说他要投降日寇当汉奸。我叫游击队秘密包围了独立旅,我又自告奋勇去找他。在谈话中间,趁他点火吸烟的时候,我就开了枪。不防他身边有一把刀,中了枪之后,他还给了我一家伙。倒也好,从此留下了这块光荣的革命标记,比金牌还吃香。”
赵青大笑着拍拍胡文玉的肩膀,胡文玉惨淡无声地苦笑了一下。随后赵青坦率地跟胡文玉商议对付李铁、许凤他们的计划:赵青争取控制这个区,作为根据地;胡文玉和小鸾打入县委,发展力量。胡文玉忧虑地把许凤和他谈话的经过说了一遍,担心许凤叫他向组织上坦白,是发现了他自首的秘密。赵青沉吟片刻,仔细分析了一回,认为不可能被发现。她可能是指的男女关系方面的事。胡文玉这才放宽了心。这时小美、小鸾又进来,一起说笑起来。
赵青从墙上摘下一把胡琴,调好琴弦,拉着西皮倒板,点点头冲胡文玉说:“来,唱一段乐乐吧,你不久就要离开这儿到县委会去啦。”
“唱什么?”胡文玉懒洋洋地眯起眼睛。
“来,唱一段《坐宫盗令》。”
胡文玉点着一支烟卷,倒背着手在当屋踱着方步,小声地悠扬地唱着,抒发着不得志的心绪。
正唱着,葛三一步踏进屋来,冲赵青挤挤眼说:“把杜助理员叫来了。”
赵青急忙放下胡琴走了出去。小鸾把麻将牌拿来哗一声倒在桌子上,葛三留在屋里和小鸾、小美、胡文玉说笑着打起牌来。等了好一会儿,听着赵青和杜助理员又说又笑地从西院北屋里走出来,客气了几句,杜助理员走了。赵青回来走进隔扇门口向葛三一招手,葛三赶紧提了枪跟赵青走到院里。赵青附耳向葛三说了几句话,葛三就匆匆地迈着大步紧跟上杜助理员走了。这时太阳已经点地。
赵青的媳妇寒露从娘家来了,一进门碰上杜玉良跟葛三往外走。寒露见杜玉良神色不对,也没多问就悄没言声地走进院里来。见赵青正在院里仰着脸立着吸烟卷,寒露也没叫他就笔直朝自己的屋子走去。赵青一看是她,忙笑着过来跟她说话。他们俩的关系,从结婚以来,就是这么不冷不热的。论人品,寒露也还算漂亮,就是为人端庄沉静,不苟言笑,也念过三年小学,识文断字的,但是赵青不爱她,嫌她一点也不风流。特别是和他姨娘小美勾搭起来以后,跟寒露更加冷淡起来。可是寒露娘家是绝户头,老两口就守着这么一个闺女,有一份不多不少的财产,离着只二三里路,又近便,将来总可捞到手,因此赵青从来也不得罪她。她愿来就来愿走就走,也不去管她。她不在家倒也省得碍眼。寒露在娘家村里也是个村干部,不像别人好欺负,赵青一家子,也就不敢多招惹她。别看寒露冷眉冷眼地不大说话,连小美那么泼不讲理的人。也避着不敢多跟她打照面,只盼她快点回娘家就一顺百顺。想着寒露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公公想她。从娶过寒露来老头子就存心扒灰,只因寒露又正派又机警,总不得手。再一个是作饭的大娘想她。因为只要寒露一来就像一鸟入林百鸟压音,谁也不敢吵了。她也有个知心人说说话,也没人敢明目张胆地欺负她。有什么好吃的寒露总想办法给她送去。寒露也常惦记着去看大娘,心里怪可怜她的。
赵青跟寒露说着话,见寒露越发像一枝春雨洗过的梨花,清新素淡,倒有心跟她亲近起来,便竭力温存地说:“这回住几天再走吧。”
“不,拿几件衣服,明天就走。”寒露淡淡笑了一下,一点热情都没有,反正对她来说赵青是可有可无的。她对他们这家人除了恶心以外,很少有别的感觉。离婚又办不到,不光爹娘坚决反对,连区、村干部们都不同意。她就这样忍着,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会离开这个肮脏地方的。
“不要走。你不知道我多想你呀!”赵青过去拉她的手,两人来到屋里,说了一会话,天就大黑了,赵青打火链点着灯。
寒露看着赵青问道:“娘怎么样?”
赵青愁眉苦脸地说:“嗐!这几天总是闹病。我才去看过了,她睡着了,我看你先歇歇吧。”
寒露说:“我去看看她吧!”
寒露来到后院里,就觉冷冷清清,一股阴湿的气味。进屋叫了声“大娘”,没有听到答应。轻轻掀开门帘一看,不由得吓得往后一退,大娘半边脸歪在尿盆子里,已经死了。
“他们真的治死她了!”寒露自语着,一阵恐怖,浑身一抖,心里一阵难以抑制的愤怒直冲头顶,光想闯到前院去跟赵青、小美他们打一架。紧走了两步又站下,沉思着,脸上流下泪来。“他们为什么要治死她?”这个问题在她脑子里盘旋起来。
大娘的死,寒露是怎么也猜不透的。本来赵青是出名的和气。人们到他家来,只要赵青在家,就会看见他对大娘必恭必敬地问寒问暖,关心得十分周到。大娘在街上走路,只要赵青看见,总是上前搀扶着,有说有笑。有好的东西总是买点,说是带给大娘的。那么好的侄儿为什么会治死大娘呢?难道说怕她把小美跟赵青勾搭的事说出去吗?不会的。虽然大娘出名喜欢到处说话,这事她可绝口不提。大娘还劝过寒露:“家丑不可外扬,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吧!”那可是为的什么呢?
寒露怎么也猜想不到。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拂晓,枣园的敌人包围了赵庄,把群众都赶到大场上去开会。大娘把赵青藏起来,就到街上去了。可是她不放心,又回到家里来看看。刚一进院,就听见一群人在后边跟进来了。她赶紧藏在茅房里,偷偷看着,只见几个人留在大门外,一个大个子伪军军官进了院,把大门插上了。她认得那是伪军大队长张木康。他插了门,就照直向北屋走去。她轻轻地跟进北屋,掩在隔扇门后边,就听见张木康叫道:“赵青!赵青!”
“进来吧!”赵青一掀门帘迎了出来。
大娘奇怪:赵青为什么会跟张木康搞在一起,两个人偷偷地见面,究竟商量什么东西?这样想着,她就蹑手蹑脚地躲在门边听着。
“怎么样,咱们见面对你有危险吧?”
“不要紧,这个办法好,一点也不会暴露。老是偷偷摸摸的。我实在也有点不耐烦了。我正在想法把许凤、李铁挤走,除去这个眼中钉。全部情况我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咱们马上计划一下,给他们来个里应外合、一网打尽。我就可以把全区都掌握起来了……”
大娘这时喉咙发痒,抑制不住咳嗽了一声。噗隆一声门帘一掀,赵青、张木康跳出来,一看是她,赵青不动声色地说:“大娘,你老人家真是!快到外边去。”
张木康走后,大娘带气问他:“张木康来干什么?不明不白的。青儿,你可不能干这种断子绝孙的缺德事啊!”赵青装着笑脸哄她:“这是组织给我的秘密任务,有什么缺德!”大娘半信半疑地嘀咕说:“什么秘密任务,明日个许凤来我问问她!”赵青心里一惊,脸上还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问吧。可除了许凤,对谁也不许讲!”当天夜里,大娘吃了饭就肚子疼,病得起不来了。赵青又给她取药来,吃下去,就关上门走了。大娘一个人在屋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感到渴得不能忍受,一头扎进尿盆子里死了……
寒露想了一会儿,越想越蹊跷。她没有声张,悄悄退出来,关上了门。
“哈哈……”
这时就听见前院里传来一阵男欢女乐的笑声。
寒露毛骨悚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