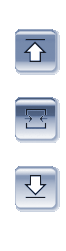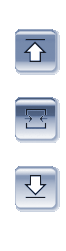| |
| |
|
钟表盛会
|
|
机械钟
发明机械钟的困难在于怎样才能使一个比房屋还小的轮子与地球同步转动并连续运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轮子就成了一个微型地球,并且可以告诉人们时间。如今,时间与地球旋转的快慢已无关系。
这种机械技术的实现,是人类社会的最大进步之一。今天,钟表已无所不在。机械钟发明于公元8世纪的中国,但是直到公元1271年,罗伯特斯·安格列卡斯才在他的书中告诉我们,在欧洲,“工匠们正在试图制造一个能与地球公转一致的轮子,但是他们失败了。如果此项创造得以成功,它将是一架相当精确的钟表,其计时精度比任何星盘或其他天文仪器都要高”。
欧洲于公元1310年在借鉴我国机械钟的基础上,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国机械钟是由商人带到欧洲的,同一世纪传入欧洲的还有黑火药、拱桥建造技术、铸铁和印刷术等项发明。
我国古代的皇帝认为其是天神下凡,他的一举一动都要与占星术相符。皇位的继承人不一定就是皇帝的长子,在我国历史上,由第四子或其他后裔继承皇位的史实屡见不鲜。那么,皇储究竟是怎样选择的呢?皇储的选择过程包括对候选人受孕时辰的星位占卜 (占星学认为,人的生辰应以受孕时间计算,而不是生日)。为在可能受孕的时候安排皇后和贵妃与皇帝同房,皇帝的内侍必须准确地推测出合适的时间以安排皇帝的房事。从公元前2世纪的《周礼》中,可一窥有关皇帝性生活的惊人内幕:
“名份低的女子宜先,名份高的女子宜后。贵人81人按九人为一组,九个晚上,在同一寝宫。嫔妃27人,分为九人一组,三个晚上。妃子九人和贵妃三人各为一组,各一个晚上。皇后单独一人一个晚上。在每个月的第 15天,这个顺序就完成了。此后,重复这种做法,但顺序倒过来了。”
皇帝身为天子,充满着强盛的阳气,阳气乃男子之元气。但皇帝的阳气尚需阴力与之匹配,阴力乃是女子之元气,以求阴阳平衡。满月之夜,阴力最盛,此夜需皇后与皇帝同房,以其阴力服侍皇上,此夜是受孕的最佳时间。余下的嫔妃,分组陪皇帝度过月缺之夜,以便集中她们各自的阴力来补充月缺之阴力不足。由此看来,皇帝一生的大部分夜晚,都是由九个嫔妃陪伴度过的。
假如一个王子被选做皇储,占星者们就需追溯到他受孕的精确时间,绘制星图,据此推测每个彗星、新星及其他天文现象。如果天象形状表明,该王子是一个强健的统治者,一个勇士等等,那么他将赢得皇位。因而,如果长子是处在灾星或死亡之星的星象影响之下出生的,他很早就会被排斥在皇位继承人之外。
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当时发明机械钟的背景。看一看皇位继承规则实施得如何?从公元9世纪的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一诗中可感受到诗人对皇帝荒淫生活的感叹:
“每夜九个嫔妃,皇后则满月时两夜。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典,是女史以朱笔记下的这一切情况……但现今两宫3000女子争宠,一片混乱。”
显然,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并非都很合适,无能的王子也可能中选,那是因为对他的受孕时辰没有精确的记载。为此,必须发明计时钟。公元725年,计时钟诞生了。
我国虽然发明了第一架机械钟,但其他形式的钟表却并非我国发明。自巴比伦时代起,漏壶就已产生。古代先人间接地从中东居民那里得到了这种最早的计时器及最早的天文仪。并且改进了很多种漏壶,其中包括一种用水银代替水的便携式“停表”,它具有相当的时间精度。我国漏壶采用天平或称而不是在壶里插浮竿——“箭”的方法来表示时间刻度。这些方法是对外国发明的钟表的改进。表盘是由希腊人和罗马人发明的,公元前1世纪建筑学家维特拉维斯曾介绍过这个发明。
世界上第一架机械钟是由唐朝高僧、数学家一行设计制造的。这架钟实际上是一架附有报警装置的天文仪器,而不是一架简单的机械钟表。据《旧唐书·天文志》记载:
“(浑天仪)按圆天的形象制作,上面按顺序示出28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水流入穴中而使轮子自动旋转。一日一夜,使之转动完整一圈。此外,在浑天仪外边,装有两个轮圈,上栓日月,使其按环形轨道运行。每天,当浑天仪向西转一圈,太阳就向东行一度,月亮则向东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转29圈之后则日月相会。当浑天仪转365圈时,太阳就转完整的一圈。他们做一个木柜,以其表面作为地平,因为该仪器有一半处于地平之下。它能准确地测定黎明、黄昏、满月和新月,迟延还是加快。再则,在地平面上立有两个木人,其前面分别置一钟一鼓,钟自动敲响以示小时,鼓自动击打以示已过一刻钟。
“所有这些运动都由柜中的机器进行,各项运动决定于轮、轴、钩、联锁杆、制动装置和锁合装置,互相抑制 (即擒纵机构)。”
因为这架仪器还能显示黄道,所以当时人们对它的精巧设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公元725年这架仪器制造完成时,它被称为“水运浑天”,置于武成殿前以供百官参观。公元730年的会试曾出过论述新天文钟的命题。该文继续写道:
“不久后,铜铁制作的这种机构开始生锈,不能自动旋转。于是放置在集贤院,不再使用了。”
从以上叙述可以认为,第一架机械钟是水钟向完全脱离水力的欧洲纯机械钟的过渡。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一行的钟是一架漏壶 (水钟)。它只能说明第一个用于钟表的擒纵轮不是靠重力落体或弹体,而是由水力驱动的。这与漏壶中的浮标随壶中的水 (或水银)面一起升降是不一样的。在机械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古代人民以水为动力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钟都是靠水力推动的水钟,因此很自然地把水作为动力了。永不停息的水流被看成是天体的永动,正如苏颂在公元1092年叙述自己的改良钟时所述:
“驱动机构采用水力的原理总是相同的。天体运行不息,水流也是如此。因此,如果使水以极高的均匀速度倾注,那么天体和机器旋转运动相比就不会有什么差异和矛盾;因为不息跟随不停。”
一行钟的工作是靠一个以轮代桨的直枢轮带动的,在枢轮边缘的轮辐上安装有水斗。因为这些水斗靠漏壶流水将其注满,因此说,一行钟是以漏壶为动力的机械钟。当其中的一个水斗被注满后,它本身的重量足以使枢轮克服擒纵轮的限制,转动一个刻度,各种按序排列的齿轮将把上述的运动传递给时间指针,以此循环往复。正如古书所述,时钟的零部件还有轴、钩、销子、连锁杆等。我们将从下面对苏颂钟的全面描述中看到这些东西的组合。
一行的钟是一个简单的计时装置,运行并不稳定,与其说是一部上乘的机械,不如说它标志着一种伟大思想的实现。正是因为一行钟为未来的钟表发展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前景,才使人们对一行同时代的机械产生了兴趣。一行钟的前景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得到证实。一行在发明一行钟两年以后就去逝了,他未能在有生之年制造出第二代一行钟。
如同水钟一样,一行钟易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冬季时需在钟旁生火温水,以防冻结。而水银钟则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水银在地球上的任何气候下都不会冻结。因此,此后出现在中国的大钟用水银代替水,以此解决了冰冻问题。宋朝张思训于公元976年制造了一座大钟,此钟做工精巧,以水银为动,是继一行钟之后对钟表的又一次重大改进。尽管一行钟已在公元 906年佚失了。
张思训的大钟要比一行钟大得多,也远为复杂。据《宋史·天文志第一》记载:
“一个三层的塔式结构,每层三米多高,所有的机器皆藏于内。顶部圆形,象征着天;底部方形,象征着地。下面设置有低轮、低轴和框架基础。还有横轮、固定于旁路的竖轮,以及侧轮;将它们固定于适当位置的轴承;一个中央制动装置和一个小的制动装置(即擒纵机构)装有一个主传动轴。有七个假人,左边摇铃,右边打钟,中间的一个敲鼓,清楚地指出已过去的时刻。每昼夜(即24小时),机器整整转动一圈,那七个假人围绕黄道移动其位置。还有12个木人每两小时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一次,拿着执辰牌,指明时刻。昼夜的长短由明暗中逝去的多少刻钟的各种数字来确定。在机器的上部,有天顶件、上齿轮、上制动装置 (擒纵机构),上抗反冲销,天梯形齿轮传动箱 (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个链式传动装置,要不然就是不久后苏颂为他的钟而发明的),框架的上梁,以及上连接杆。浑大仪上分布着365度,以示太阳的运动、月亮和五个行星的活动;以及紫微宫(北级区)、28宿和大熊星座;赤道和黄道表示寒暑进退取决于太阳的运动,钟的动力是水,这种方法是由汉代张衡经一行流传下来的……但是,由于冬天时水部分地冻结,其流动大大地减缓了,所以机器失去了准确度,寒暑无准。因此,用水银作为代用品,就不再有差错了。”
上述所有的努力为中世纪我国制造出最大的一座钟作了充分准备,此钟即是苏颂于公元1092年制造的“水运仪象台”。有关苏颂钟的基本细节目前已广为人知,因为苏颂所著《新仪象法要》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该书介绍了设计、建造大钟的全部细节。最近人们发现该书中的某些插图用公元976年张思训钟以及那里在苏颂钟之前的钟非常相似。今天,在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还可看到一个仍在运转工作的苏颂钟的现代仿制品。当然,这些仿制品都是根据苏颂《新仪象法要》描述的插图建造的。
苏颂钟实际上是一座有10余米高的天文钟台,类似于张思训钟。但苏颂钟的台顶有一个靠动力驱动的巨大的铜制天文仪——浑仪,它是被用做观测星球位置的。台内的浑象同台顶的浑仪运动一致,二者能不断地互相比较对照,使浑象上球面星座位置和浑仪所观测的天象相吻合。据说,设在台内示范天体的浑象与台上的浑仪就“像两个半球吻合成一个球体一样”。
在台前部,是五层的木阁,每层木阁都有门,门中有木人按时轮流出来敲锣打鼓摇铃报时。报时装置与浑象、浑仪的转动同由一个巨大的时钟机器来驱动。
这个巨大的时钟机器通常由一个巨大的带有幅条的直立水轮组成,每根幅条的端部都装有水斗,漏壶水直入水斗,当水斗注满水后,水轮转动一个刻度。在水轮上装有一个卡子,它阻止轮子逆行。就轮子向前转动而言,每转动一个斗,就等于一刻钟。
事实上,苏颂钟在当时的京都开封从公元1092年开始使用直到公元1126年北宋朝灭亡。此后,它被运到北京重新组装并重新运行了很多年。苏颂钟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苏颂的政敌曾经要毁掉这架大钟。此事我们可从公元1140年米弁所著的《曲海旧闻》中得知:
“到绍圣初年(公元1094年),大臣蔡汴认为,苏颂的浑仪钟应该毁掉,因为它属于元祐年间(仅两年以前)之物。当时晃美叔是秘书少监,因为他非常饮佩苏颂的仪器的精确度和美观的结构,所以极力反对蔡汴的观点,起初他的努力是成功的。他求助于林子中,子中与宰相章惇商谈,因而免于销毁。但在蔡京兄弟掌握政权以后,没有人敢于反对销毁苏颂的机器。多么可惜!”
个人间的恩怨和政治派别的不同能够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机器发明毁于一旦。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苏颂的著作连同书中的插图、注解才得以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苏颂钟可能是人类在中世纪的最卓越的机械创造,其原理传入欧洲后,导致了两个世纪后机械钟在西方的发展。
能演戏的钟
苏州博物馆曾经展出过我国古代艺人制作的一架打点摆钟,叫“铜人敲钟水法音乐钟”。这座钟到了指定的时刻,钟内会突然奏起悦耳动听的音乐。在音乐声中,小铜人手里拿着鎯头,掀开帘子走到正中间,自动敲钟报时。这时候,钟盘上部好像从高山顶泻下了瀑布,也好似下起了倾盆大雨。盘下有条小河,流水潺潺,一只只小船扬帆而过,演了一出美丽的报时剧。这座会演出的钟,诞生在明末清初,距今大约300多年。那时没有机床,单凭手工制作,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我国的钟表艺人还制造过一架楼阁式的“群仙祝寿问乐钟”:小楼阁共分两层,上层有3个小人,下层有八仙。到了一定的时刻,上层楼门自动打开,小人出来报时并奏乐,下层八仙转动,看上去好像在祝寿,也像在演一台木偶戏。
300多年前,有个奥地利人叫奥古斯丁·迈耶尔堡。他在公元1661~1662年间住在古老的莫斯科,后来写了一本游记,介绍了当时克里姆林宫的斯巴士克塔钟。
斯巴士克塔钟是莫斯科的“大汤姆”,向全城人报时。但是,它报时的方法十分奇特:钟面转动,指针一直不动,钟面上的哪个数字对着正上方的指针,就是几点钟。看!它的指针像个光芒四射的小太阳,固定在墙壁上,正在钟面的上方。
可奇怪的是,钟面上的数字是从1到17的,迈耶尔堡的游记里是这样介绍的:
“它从日出到日落指示白天的钟点。……俄罗斯人把一昼夜分成24小时,但是却按照太阳 ‘在场’或‘不在场’来计算时间。这样,从日出的时候算起,接着打一点钟,之后继续打到日落。以后又从夜晚第一点钟开始计时,一直到天亮……最长的白天,时钟可鸣报到17点,而那时的黑夜,只有七个钟点。”
你看,300多年前俄国人计算时间有多么麻烦。当然,和法国的亨利一样,在斯巴士克钟塔里也住着看钟人。每天晚上,斯巴士克钟塔打钟了,整个城市也跟着打起钟来:“每一条街上都配备一个更夫。每天晚上,他们听钟声得知时间,钟打几下,他们就敲泄水槽或板子几下,使人们在听不到钟声的夜晚也不会失去警觉。这简直是全城的更夫在演戏。
住在钟塔里的看钟人有时喝醉了,斯巴士克钟就会乱打点,于是,全城就乱了:店铺里的伙计会提前关门,衙门里的录事也借机溜回家。
到18世纪时,彼得大帝命令在克里姆林宫上安装从荷兰订购来的大钟,斯巴士克塔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城市大钟
早期的机械钟都是又高又大,往往要为它建个钟楼。英国伦敦议会大厦钟楼上的大钟,取名“大本”,它是在公元1859年第一次发出钟声的。大本重12吨,直径为2.7米,高2.3米。这座钟是本杰明·霍尔当工程局局长时建造的。本杰明身材高大魁悟,人们亲昵地叫他“大本”,后来,干脆用
“大本”来称呼这座大钟了。这座钟走时准确,也不像大汤姆那样闹出笑话。在1913年以前都是用手工上发条来推动“大本”走动的,后来改用了电动机。
我国北京,早在明清时代便通过钟鼓楼打鼓敲钟向全市报时了,那时是用漏壶计时。北京鼓楼里设有铜刻漏,据说,在清乾隆年间就不用刻漏了,而改用“时辰香”(火钟)了,香一烧完便打更。后来,在西交民巷口的楼顶上由外国人建了机械钟,至今还走着,不过这座楼已是中国银行的了。民国初年,北京一度改为每天中午12点放炮一声叫“午炮”。午炮一响,老百姓全都对表。40年代初,北京当局在前门、王府井、东单、东四、西四等主要繁华路口分别建立了所谓标准钟。这些钟的表盘是圆形的,两面都有指针和字盘,外壳与底座都是铁做的,用地脚螺丝固定在各路口便道的拐角处。这些钟不会自鸣,要有人定时来为发条上弦。解放前,由于管理不善,标准钟各走各的,东单的钟是10点,王府井的也许就是11点,西四的因为忘了上弦指的却是5点。
解放以后,在北京火车站、西单北京电报大楼的建筑物上安装了巨大的钟表,后来又在王府井等处安装了新式钟表。
1958年建成的北京火车站(北京东站),站外的钟楼上安有大钟,售票处、站台、候车室里也安有大钟,它们走得完全一样,而且里边没有摆。原来,北京站的钟是一套“子母钟”。在安静的房里有一座精密的摆钟——母钟。母钟的摆有节奏地来回摆动,每隔一分钟便向外输送一股电流。子钟的肚子里有一套装置,跟电铃的锤子一样,一接受电流,就动一下。你如果仔细看看北京站的钟,就会发现,它上边没有转个不停的长秒针,那分针也不是在均匀缓慢地转动,每到关键的一刻,那分针就会突然跳动一格。在 50年代,世界各大城市的火车站、飞机场里都安了子母钟装置。
在西单附近的北京电报大楼上,有一座钟,它不但会自鸣报时,在夜里还会发光。据考证,最早在钟上安照明设备的是英国伦敦弗利特大街圣剑桥大教堂,当时没有电灯,在钟的四周安了12盏瓦斯灯。我们电报大楼上的钟灯却不同,它的表针和数字里都是发光的电灯,在老远的地方就能看清楚是几点钟。
代替挂摆
钟大了是不方便的,人们总希望有个随身携带的钟表。用发条当动力以后,钟总算从沉重的重锤下解放出来了,可以做得小些了,可以做成能移动的了。
最早能携带的钟表,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他命令工匠为他做了一架比较小的钟,可以装在箱子里,用马驮着到处行走。一个名叫马丁·格雷的仆从,专门为国王看管马匹和时钟,国王到哪里去游玩,马丁就牵着驮钟的马跟在后边。马丁总要提醒自己,一是别忘了喂马,二是别忘了为钟上弦。因为马丁干着马夫兼“钟夫”的话计,路易十一每天要赏给他5块钱呢!
怎样才能把钟做得更小巧呢?很明显,用挂摆来计时,钟就不能做得很小。
于是,不少人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根据摆的原理,改进一个钟表的构造呢?你看,那钟摆总是一忽儿左,一忽右地摆动,每一次运动都在重复着上一次的运动。想一想,在我们周围还有没有类似的运动呢?
找一根弹簧 (用皮筋也可以),在弹簧下边挂一个小锁头,把弹簧挂起来,拉一下小锁,怎么样?小锁头上上下下地跳动起来了。仔细观察一下,它每次振动的时间总是差不多的,这就是它振动的固有周期。
用这样的弹簧就能当摆。国产的一种“逍遥钟”,它的摆就是个上下振动的螺旋型弹簧。那摆锤是件工艺品,它的样子可以多种多样,但是,重量是不能改变的。
要是在老虎钳子或者其他工具上夹住一个钢片,用手拨动它一下,它也会左右振动起来,同时发出嗡嗡的响声。小钢片自由振动一次所用的时间,也是一定的,这是它的固有周期。用这种自由振动不是可以来计量时间吗?
依据这个原理,几百年前的钟表工人制造出了摆轮游丝装置,代替了伽利略发明的单摆。今天使用的小闹钟、怀表、机械式手表的心脏都是摆轮游丝。
游丝是一根螺旋形的弹簧,一头安在摆轴上,另一头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摆轮是一个圆圆的金属轮,牢固地安在摆轴上。摆轮一转,摆轴就转,摆轴一转,游丝卷紧,游丝一紧,就产生了弹力阻止摆轮再转。摆轮只好慢慢停下来,接着便又在游丝弹力的作用下向相反的方向摆动。当摆轮转到平衡位置时,游丝没有弹力了,可是摆轮却像个刹不住的大车轮,依然转着,这一下又使游丝反卷。那游丝不甘心反卷,便又产生反方向的弹力,使摆轮渐渐停下来,回过头,冲向平衡位置。当摆轮冲到平衡位置时,游丝又一次失去弹力,再一次被摆轮卷起……。这样下去。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摆轮游丝系统将永远摆动下去,而且,每摆一次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正像那来回摆动的单摆一样。
用摆轮游丝装置代替钟摆,在钟表史上是一次飞跃,它的起点就是闪光的思考:“能不能改变一下摆呢?”
从水钟到机械钟
大约在1000多年以前,希腊人制造了较为精巧的水钟。它的结构是这样的:贮水壶上部一侧有个小孔,多余的水可以从这个小孔溢出,这样就能保持固定的水平面,保持恒定的压力。水从贮水壶下部的小孔流出,注入受水壶。受水壶内有一浮舟。浮舟上装有“护钟神”——箭竿。受水壶中的水达到某一高度时,通过虹吸管使水注入旋转的平衡轮 (它由于自身的重量而转动),驱使一列齿轮转动,从而按照昼夜的长短把计时用的鼓状圆筒带到新位置。随受水壶水面高度的变化,“护钟神”就在圆筒刻线上指出时辰。这些刻线是不等长的,有些还是斜的,以便指示出冬季里一天的时辰。
我国古代对水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最著名的例子是北宋初年 (大约公元1086年)苏颂设计制造的“水运仪象台”。
水运仪象台高三丈五尺六寸五分(约12米),宽二丈一尺,是一座上狭下广的三层木结构建筑。全台由水斗、木轮、钩状铁拨等组成传动系统。它用水作动力,是一架复杂的天文仪器。它的计时部分原名“昼夜机轮”,是一具精巧的水钟。在这里,苏颂使用了相当于现代钟表中的擒纵器的一系卡子和枢轮杠杆装置,通过大小齿轮的啮合控制水斗转动和枢轮运轮运转速度。整个计时部分共有五层木阁:第一层是昼夜钟鼓轮。轮上有三个不等高的小木柱(起凸轮作用),可按时拨动三个木人的拨子,拉动木人手臂,一刻打鼓,时初摇铃,时正敲钟。第二层是昼夜时初正轮,轮边有24个司辰木人,表示12个时辰的时初、时正,相当于24小时。该轮上的24个木人随着轮子转动按时在木阁门前出现。第三层是报刻司辰轮,轮边有 96个司辰本人,每刻出现一人。第四层是夜漏金钲轮,可以拉动木人按更序法钲,报告更数,并且可以按季节调整,以适应昼长夜短的变化。第五层是夜漏司辰轮,轮边设38个司辰本人,木人位置可按季节变动,从日落到日出按更序排列。
苏颂主持制造的这架水运仪象台,不仅继承了我国汉、唐以来的天文学和机械学上的成就,同时还有创新。昼夜机轮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它所用的擒纵装置也被公认为世界上机械钟的祖先。
但是,苏颂等人的这项发明并未得到封建王朝的支持和鼓励。当时有一位翰林曾以阴阳五行说来非难和阻挠仪象的制造和安装。他胡说什么宋朝是以火德称王于天下的,这个仪象台名为水运,不是国家的吉兆,因为水可以克火。他的奏折送到皇帝那里,皇帝就听信谄言,命令把“水运”二字,取消,改名为“元祐浑天仪象”,并让把它安放在京城(今河南开封)西南角,因为据他们说,西方属金,南方属火,金火夹攻,可以镇住水。这实在是愚昧、荒唐!
后来,金兵攻陷开封,北宋灭亡。这架杰出的天文钟为金兵缴获,移置于北京。但由于战祸连绵,秩序紊乱,至使这一重大发明未得推广、应用,停滞达百年之久。
苏颂的水钟可以说是一种最早机械摆轮,是已知以机械运动的周作为计时标准的早尝试。由于是通流水计时,而不是过机械装置本身运动计时,因此,可以把它看做从定流水守时到机振动守时的过渡。
随着十字军征,中国时钟制造术传到了欧洲,刺欧洲人去制造类似装置。当然,一个聪明人,一旦知道某种东西是怎样做出来的时候,他常可找到自己做这种东西的办法来。从严格的专业意义上说,水钟和机械钟的根本差别仅在于,前者涉及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水从孔眼中流出),而后者则由一个不断重复的机械运动来控制。我们不是说欧洲人大约在13世纪发明的机械钟,特别是擒纵装置完全是照抄中国的。它们之间有区别,例如欧洲人不用枢轴和定时杆,而用心轴和冕状齿轮控制时钟机构的运动。但他们所依据的原理来源于中国,这是中外科学史家大多承认的事实。
英文里的“钟”叫 clock,它源于法文 cloche,意为“铃”。铃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很可能正是根据齿轮和摆动连杆制成的摇铃机械,吸取中国的擒纵装置,创造了欧洲早期的机械钟。
机械钟的发明是使将昼夜划分为等长的 24小时制在欧洲得到普遍承认的决定性一步。意大利的米兰于1335年设立了公共钟,按一天24小时报时。
早期机械钟的钟速取决于驱动轮,而驱动轮又受到动力机构中摩擦力变化的影响,因此精度很低,每天要差一刻钟以上。
把1小时划分为60分,1分划分为60秒是在1345年左右提出的,当时是为了表示一个月蚀的周期。但这只限于理论计算,没有进行实际测量,迟至17世纪中叶,机械钟还只有一个指针,钟面上也只有小时和四分之一小时的刻度。
由于缺少计量短时间的精确方法,所以尽管机构钟已经问世,科学时间概念的发展仍然受到严重阻碍。
摆钟的传说
对改进早期机械钟作出重大贡献的,是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他发现了摆的等时性原理。
摆的均匀摆动是人们继滴漏之后发现的一种真正的人造周期运动。从17世纪早期起,西方的工艺家们便把它运用到时钟上,作为稳定的“定时器”,使机械钟能够指示出“秒”,从而把计时精度提高了近100倍。
通常,人们往往喜欢给科学上的发现和发明笼罩上一层故事色彩。譬如,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发现了引力;阿基米德洗澡时,从身体在水里的上浮发现了浮力定律;爱因斯坦根据建筑工人从高空脚手架上摔下时的感觉发现了广义相对论;等等。伽利略发现摆的等时性原理也被编成了故事广为流传。
通常的传说是这样的:伽利略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去比萨教堂做礼拜。微风吹来,使挂在天花板上的大吊灯来回摆动。伽利略注意到,链条一般长的两盏青铜吊灯,来回摆动的时间好像一样长。他凝视吊灯,终于发现:摆的快慢与摆锤大小和重量无关,而取决于摆的长短;摆长相同时,摆动一周的时间相等。同时,他还想到利用摆来调节时钟,并动手做了第一台摆钟。
这个故事加上传说,已经渗透到时钟发展史中去了。但是,这多少是有些不真实的。它差不多是小说家的虚构。
这个故事最早来自于伽利略的一个学生V·维维安尼的记述。后者是伽利略传记的撰搞人,也是伽利略的一个崇拜者。
在伽利略死后,物理学和天文学都有很大发展,超过了枷利略生前时代。维维安尼为了扩大他老师的影响。编辑了第一部伽利略著作选集,还特别写了一本富有传奇色彩的《伽利略传》。在这本书中,维维安尼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伽利略在中学时代就做出了上述发现的故事。
后来,这件事越传越奇,它成了科普作家发挥想象力的一个绝妙题目。其实,这只是维维安尼的一种艺术创作。事实上,伽利略对摆感兴趣开始于他对重力效应的某些研究过程中。当他想到用摆控制时钟时,他已是一位老人,而且近乎双目失明了,根本不是在中学时代!
世界上第一个做出摆钟的人,是天才的荷兰科学家C.惠更斯。
在惠更斯制造的摆钟里,有一个重锤起动器。它通过一个伞形齿轮。伞形齿轮受摆轮心轴控制。心轴由摆带动,并同一根L形杆子相连。摆样从L形样的孔内穿过。为了控制摆杆的摆动,惠更斯设计了一块挡板,由它使摆的摆动转向。
单摆的摆动不需要其他装置驱动,而主要靠重力驱动。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时钟的精确度。
当然,摆钟里的摆杆是金属制品,它的热胀冷缩将影响摆的周期。由实验知道,100米长的不锈钢金属杆,在温度变化5.6℃时,会使一天的时间减慢2.5秒钟。不同的金属还有不同的膨胀系数。随着这些问题的发现和逐步解决,大约到17世纪,摆钟就已经相当完善了,它在一个星期里的计时误差只有几秒钟。
摆钟开辟了精确计时的新时代。它不仅提高了测量物理时间的精确度,而且可以看作是一种均匀划分固定时间间隔的手段,类似于把有限长的连续直线划分成大量等长的线段。因此,机械钟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时间的类几何均匀性和连续性的认识的发展。
航海计时
科学是生产力。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科学的发展又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这种相互约束的关系,在时间计量中表现得也非常清楚。
在生产水平粗放的古代,人们用滴水 (更早还有用燃烛、漏砂、落石)等方法测量时间。后来,由于冶炼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机械钟和摆钟。这些进步不仅反映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人类科学文明史的每一个进程。
17世纪以后,航海事业蓬勃发展。海员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需要精密时计。对海员来说,精密守时钟犹如生命线,没有它便难于知道船只的位置,就有触礁沉船的危险。
为什么时钟对海员如此重要呢?因为测量地球上任何一点的经度离不开时间。
海上船只的地理位置,是用它的经度和纬度来表示的。测量纬度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太阳和恒星的高度不仅随季节变化,也同观测者的纬度有关。海员只要简单地测定他所在地太阳的高度,或者北极星到地平面的夹角,就可以求出这一地点的纬度。在17世纪,任何有经验的水手都能以零点几度的精度测出船只所在地的纬度。
当时,欧洲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曾出巨额奖金,悬赏征求解决测定经度方法的人。159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三世出1000克朗悬赏费。荷兰国王悬赏10000佛罗林。法国后来出价10万里弗。由此可以看出解决测定经度方法是当时十分迫切的问题。
在英国,1707年发生了一次特大航海事故。当时,一支由海军上将C.肖维尔率领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由于搞错经度而撞上了锡利群岛中的一个小岛。结果,4只舰艇和2000名水兵 (包括舰队司令C.肖维尔本人在内的所有军官)统统葬身海底。英国政府对事故进行了长期调查之后,于1714年悬赏2.0000英镑 (在当时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富翁的数字),征求能以半度的精度测定地理经度的人。英国发表的官方公报是这样说的:
“兹颁发两万英镑奖金给予那些发明任何一种可以随时在海上决定经度方法的人。如果这种方法在往西印度航程中试验的结果与实际的经度位置相差在三十英里之内的话,将授予他两万英镑奖金,如果相差在四十英里,可得一万五千英镑;如果相差在六十英里内可得一万英镑。”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科学家和有技术的工匠就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使这项工作取得十分可观的进展。
科学家相信,至少在理论上,测定经度的方法是存在的,这多少同测定纬度一样,也取决于对太阳和恒星的观测。太阳和恒星的相互位置不随经度变化,但在东西方向有差别,这就是时间。
如果有一只船停在英国京都伦敦的格林尼治,船员在正午将自己的时计同格林尼治天文台时计对准,然后向西行驶。结果他会发现,船上的时计是下午3点 (格林尼治时间)了,但太阳的位置看上去仍然是正午。
因为地球自转一周是24小时,地球经度变化为360度,所以船上的时间与格林尼治时间每差1小时就是15度。这样,海员就可以由这个时间差知道他处于格林尼治以西45度的地方。
那么,怎样让海员在出发时知道格林尼治时间呢?办法很简单,只要在醒目的地方安置一座大钟就行了。当时人们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现在你要是去伦敦,还可以看到,在该市的威斯敏斯特高塔上有一具大得出奇的时钟。它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各有一个直径几米的钟面,分针长三米半,它跳一格(一分)是15厘米,表示分的数字每个都有75厘米高。英国人把这个大钟叫做Big Ben(大本)。它高98米,建于500多年前。当初建造的本意就是为了让海员出发时对时的。
但是,要测定经度,单知道格林尼治的时间还不行,船上还必须有一个能精密守时的钟。由于船在运动,冷热、干湿变化很大,不同纬度的地方有不同的重力差,当时要造出足够精密的航海钟是困难的。但是,生产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动力。这样的钟终于造出来了。
第一个造出这种时钟的人是英国的约翰·哈里森。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从小就喜欢工艺劳作。他费时近40年,于1769年制成了一只航海时计。1761年,哈里森的儿子约翰·威廉带着这只时计,从朴茨茅斯港出发,远航牙买加,作测量试验。
航行的第一停靠站是马迪拉岛。按照以往经验,朴茨茅斯港到马迪拉只有9天航程。但第9天,船员们仍看不到马迪拉岛。这时,船长用老方法估算,船的位置是西经13度51分;然而,威廉用新的时计计算却是15度19分,并预言第二天就能望见马迪拉。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马迪拉果然出现在船员们面前。如果按船长计算的方位改变航向,那他们就根本到不了马迪拉。船员们高兴地狂欢起来,一下子就把船上的啤酒渴光了。
因为马迪拉只有白酒卖,没有啤酒,于是船长决定在马迪拉不停,直驶牙买加。到了牙买加,同当地的经度值相比,威廉用新时计测得的结果不仅没有超过半度,而且只差百分之二度。
约翰·哈里森要求获得政府颁发的20000英镑奖金。
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大概是出于慎重吧,英国政府只答应分批支付,直到1773年哈里森80岁时才最后付清。哈里森在拿完全部奖金后的第3年就与世长辞了。
英国政府的这类“慎重”或许就是造成时钟发展史上一段有趣记述的根由:在时钟发展史上,第一只航海时计是哈里森制造的;但航海时计的发明人却不是哈里森,而是法国人勒·鲁瓦。后者在哈里森同时代采用了不同于哈里森的原理,也制造了相当精确的航海时计,并且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及时承认。
对于这个严格说来不敢相信自己国人创造能力的当时的英国政府,人们应该总结出一些怎样的教训来呢?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