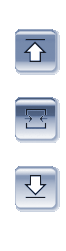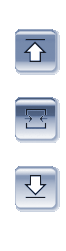| |
| |
|
艾密尔·费舍
|
|
违背义愿
“简直让上帝也没法子,他把库房当成化学实验室了。买了一本施托加德的化学教科书,就在那儿配起什么混合物来,闹得库房一会儿冒出一股呛鼻子的怪味,一会儿又是嘭地一声爆炸。好几回,他都从‘实验室’蹦出来,头发燎了,手也烫了,一脸污黑。您能想得到吗,我想,他常偷偷摸摸到化学老师那里去。总而言之,我们这位可爱的艾密尔干哪行都好,就是别再让他做生意了”马克斯怨愤地向岳父老费舍“控诉”着小舅子在公司的所做所为。
艾密尔·费舍是费舍家业的唯一继承人,可是年轻的费舍根本不愿在分公司经受父亲所谓的“锻炼”,他负责的帐目一塌糊涂,担任分公司经理的姐夫马克斯,被他气得只会乱翻白眼。木讷的艾密尔仍然在帐本上偷偷地计算着化学式子,马克斯劝诫了无数次,毫无效果。
“他仍是那么吊儿郎当,唉!看来,这孩子没有经商的才干。只好让他去上学吧!”费舍老先生说罢,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叹气。独生子,唯一的指望啊!可是又无可奈何,或许是命中注定吧,只要艾密尔·费舍做个正派的人,也就得了。父亲的决定使儿子异常高兴。
1871年,19岁的艾密尔来到波恩大学就读。功课不难,但大学却使他很失望。从春天到夏天,他只可以听听课,根本没有机会进实验室,教师的课讲得枯燥无味。秋天到了,艾密尔总算进了实验室,可这里和他想象的实验室相距甚远,没有导师的指导,也没有有趣的课题和组织者,当他用了两周时间,才完成一个化合实验时,那儿的助教却异常惊奇地说:
“这纯粹是虚构的结果,您的溶液里什么也没有!怎么会有镍呢?这钾又来自何处?统统是胡来,再好好去做上两周吧!”
艾密尔脸红心跳,他感到寒心,他似乎对化学绝望了,他准备试试物理,可是堂兄恩斯特苦劝他坚持努力,继续下去。还是颇有密尔的另一位堂兄文高见,他叫奥托·费舍。
“转学吧!去维也纳!世界之大,何处不可学习,要出去闯闯才会甘心!”
到慕尼黑
1872年秋,艾密尔和奥托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他们同住一个房间,一起学化学。
化学教授阿道夫·拜尔的学识和师德,深深地吸引了他们对化学的兴趣和尊重。拜尔也十分关心年轻的学者,他请他们到自己家做客,倾心交谈,拜尔勉励他们苦心钻研。
在拜尔教授的指导下,艾密尔开始撰写关于荧光素合成问题的博士论文。这时,化学对于艾密尔来说,再也不是枯燥无味的东西了,他的研究工作充满生机,饶有兴趣。拜尔反复告诫他,科研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大自然创造出许许多多活的有机体,而这些有机体又是由千百种物质构成的。要了解这些物质首先要研究它们,然后还要把它们合成出来!只有把它们成功地合成出来,一个科学家才能说是把这项研究工作有头有尾地完成了。”
荧光素的研究进展顺利,艾密尔更加着迷地工作着。有一天,他试验成功了苯肼,拜尔充分肯定了这一化合成果,并告诉他以最先进的方法继续研究下去。
1875年夏,拜尔应邀去慕尼黑担任化学教授,艾密尔加紧博士论文的写作,在斯特拉斯堡完成了论文答辩。“秋天,我们去慕尼黑吧,在那儿可以受到拜尔教授的亲自指导。”艾密尔向奥托建议,奥托一口答应,但奥托提出的条件是先去维也纳玩上一个夏天。
维也纳,无论是它本身,还是那里的市民,特别是大学,使这两个年轻人为之倾倒。他们到处浏览,欣赏着维也纳“音乐之都”的艺术。艾密尔这个音乐迷,大受感染。维也纳的生活十分愉快,可秋天在即,兄弟俩恋恋不舍地回去了。在家休息了几星期后,他们准备前往慕尼黑。然而,此时慕尼黑伤寒病流行,父母反对他们去那里。艾密尔毫不动摇:他应该在拜尔教授领导下继续研究苯肼,而这只有在慕尼黑的实验室才能办到,最后父母终于让步了。
“你已经长大成人,该怎么办能自己作主了。我已经尽到了父亲的义务,替你在银行存下一笔款子,数目同给你姐姐们作陪嫁的一样多。你随意支配吧。”父亲说。
“谢谢父亲,光利息就够我用了。在慕尼黑我要用全部时间在拜尔教授的实验室工作。我想告诉您,苯肼的合成及再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确有意义的工作。”10月,兄弟俩人按期到达慕尼黑。慕尼黑的条件的确优越,他们在有机化学实验室埋头干了起来。
在苯肼研究的基础上,艾密尔进一步研究了粪臭素。在拜尔教授的启发指导下,他终于闻到了烧瓶中冒出的第一股臭气,这股气味连大马力的抽风机也吹不散。
“喂,艾密尔,这是什么?你好像是连整个街道的马粪都给搜罗来啦!”同行们被恶臭熏得直捂鼻子。
“成功啦!可成功啦!臭啊——。”艾密尔兴奋得全然不顾大家的嫌恶之情,谁也听不进他那欣喜若狂的话。大家熄了各自的燃烧炉,争先恐后地从实验室跑出去,因为室内臭气冲天,可艾密尔却毫不在乎地继续工作。
他坚信,借助苯肼这个化合物还可以有新的发现。他的衣服、头发和皮肤上满是粪臭素的气味,他毫不介意,继续进行试验。可是,无论他上街、吃饭、看戏,不管到哪儿去,这股气味总是紧紧伴随着他。
艾密尔是个音乐迷,可在剧场,粪臭素把他搞得狼狈不堪。一天,他刚坐在剧院的座位上,邻座的人们就掏出了手帕,还捂着鼻子咬耳朵,女士们则抗议似地掏出香水瓶来。
“谁把这个马■给放进剧场来了?”有人喊道。
艾密尔脸红了,他连忙离去。回到宿舍认真地洗澡,换了衣服,但令人厌恶的臭味仍紧随不散。
“没关系,”拜尔教授安慰着,“搞科研是要付出牺牲的,这还不算是什么重大的牺牲。你已经做出了贡献。”教授沉吟片刻,又说:“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你的研究总结一下,准备材料发表。我们这里也要设置副教授职务,我愿意看到您也能成为副教授。”
1878年,26岁的艾密尔获得了副教授的学衔。他还按惯例作了一次“讲演”,其实与其说是“讲演”不如说是上台背诵讲稿,艾密尔实在不会讲演。
艾密尔继续在拜尔教授的实验室里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这时他已是教授,也是分析化学教研室的主任,他还指导学生们的实习和研究活动。
的确,实验室是他的用武之地。他才思敏捷,爱钻研,善于在复杂的研究工作中确定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善于推动研究工作并取得预期的结果。这时,艾密尔的成就已经闻名于世,博得国际的赞誉。他应爱尔兰根大学的邀请,去担任那里的化学教授,他必须乘火车前往。
火车中途到纽伦堡,车厢的单间里进来一位美丽年轻的姑娘,一位看来是她父亲的老人陪着。老人自我介绍,他是爱尔兰根的科学家盖尔拉赫教授,从事医学。艾密尔也作了自我介绍。其实,他们早已相互耳闻。
老教授的女儿阿格涅斯细心地倾听着他们的谈话。她怎么能想到,这位萍水相逢而且大她许多的人,几年后竟会成了她的丈夫。
艾密尔只顾与盖尔拉赫津津有味地交谈,几乎没有留意这位美丽动人的女伴。虽然,他常参加拜尔夫人那里济济一堂的集会,却完全不善于同女性打交道,尽管他通晓音乐、戏剧、绘画,可是和女性相处,总觉得有点儿拘束。
被科学研究吸引得入迷的艾密尔,根本无暇考虑家庭和个人私事。实验室就是他的家,科研就是他的幸福。可是,每逢晚上他独身一人时,就愈来愈想念火车上的那位阿格涅斯。在爱尔兰根的集会上,他们不只一次地相见,彼此也熟悉起来,艾密尔越来越感到没有她,自己便寂寞无助和空虚无聊。
1887年末,也是在一次聚会上,艾密尔终于向阿格涅斯·盖尔拉赫正式求婚。当天晚上,大家祝贺他们订婚。次年2月他们在爱尔兰根举行了婚礼,此时,他已36岁。
在不幸中前进
1888年末,艾密尔的大儿子出世。
尽管娶妻生子给艾密尔的生活带来变化,但他那紧张的研究工作却一直没有停顿过。这位伟大的实验家提出并改进了有机化合物的许多合成与分析方法,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继咖啡和甘糖的合成之后,他又和助手一起进行了天然糖类的较复杂的、多阶段的分步合成,即合成了甘露糖、果糖和葡萄糖。这些成就使费舍首次赢得了国际荣誉。1890年,英国化学学会授予他戴维奖章,马普萨拉协会推选他为通讯会员。同年,德国化学学会邀请这位科学家到柏林,去做关于糖类合成与研究方面的学术报告。
艾密尔所作的研究,以及他在阐明若干类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方面所做的种种尝试,和他提出的有机化合物的分类法,博得了各国化学界的高度评价,他应邀参加了日内瓦有机化合物命名会议,在整个化学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
科学的成就使他欢欣鼓舞,可是家庭的不幸却使他越来越痛苦。严寒威胁着孩子们的健康,他知道医学并非万能,他特别为孩子们担心,可是更可怕的是,阿格涅斯生下第三个儿子后,一病不起,直到1895年去世。艾密尔痛苦万分。沉重的打击并没有使艾密尔灰心丧气。他把儿子托付给一位女管家,又继续埋头工作。他开始研究蛋白质这个大课题,但是作为构成活细胞基本材料的蛋白质,竟是何等复杂和多样啊!研究它们的特性又是何等艰巨的任务。
阐明糖类结构,合成葡萄糖、果糖及其他糖,确实是有机化学中的最重大的发现。由于他的创造性成就,1902年,整整50岁的艾密尔荣获最高奖赏——诺贝尔化学奖。
蛋白质的研究,单调、烦琐并且十分艰辛。但经过四年的实验,1906年,在德国科协举行的一次包括著名科学家参加的例会上,艾密尔报告了氨基酸、蛋白质和合成多肽方面的结果,他阐述了他创立的多肽学说原理,即蛋白质中氨基酸之间是通过肽键联结的。这一成果震惊了科学界,全人类亦为之欢呼。
几天后,《维也纳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试管中合成蛋白质!》的文章,此文如星星之火,点燃了报界。记者们编辑们纷纷撰文,认为地球上人类食物的供应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他们幻想着煤炭石油将被制成精美可口的食品。艾密尔的发现,的确像脂肪的发现一样,使人类战胜自然的历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未来的任务会更加艰巨。
艾密尔的生活又出现了苦难。入伍的小儿子阿尔弗列德,染上伤寒死去了,接着,二儿子也病逝他乡。艾密尔本人的研究工作也是困难重重,由于化学试剂不足,实验停顿下来。他开始埋头著书。
在撰写著作时,他每每回首往事,便想起那些新奇的发现、有趣的事情,想起他尊敬的师友。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把一生贡献给了化学事业,有许多人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他给每个人以应有的评价,他想向每个人表达出自己的谢忱。于是,他最后写成了自己的回忆录。
一切都在预示着科学繁荣时代的到来,可是,艾密尔·费舍渴望工作的意愿却惨然落空了。癌症夺去了他的最后一丝精力,他从容地安排了后事,将自传修改完毕,安然地闭上了眼睛。时间是1919年7月15日,享年67岁。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