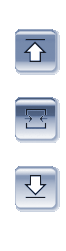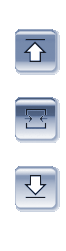| |
| |
|
郑作新
|
|
白鹇的发现
1960年春天,郑作新登上了四川省的峨眉山。
峨眉山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我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这里山峦迭秀,林木茂盛,气候温和,风景秀丽,一年四季游客不断。这里的生物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吸引了不少专家来考察。郑作新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郑作新在考察中,来到一位老乡的小茅屋休息。在茅屋的一个角落里,郑作新发现了一只美丽的鸟。他仔细一看,不由得怔住了:原来,这是一只少见的雄性白鹇!它的头顶仿佛戴着一顶华贵的帽子,红红的冠子后面,披着几绺蓝黑色的羽毛,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泽;腹部的羽毛是蓝黑色的,跟背部和翅膀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棵长长的白色尾羽,使它的身体显得修长而又俊美。
郑作新知道,白鹇是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共有13个亚种,都生活在我国的云南、广东、广西、海南岛以及东南亚的柬埔寨、越南的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的高山竹林里,峨眉山从来没有发现过。于是他感到奇怪:这只白鹇是从哪里来的呢?该不会是游客从外地带来“放生”的吧?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郑作新和他的助手们在这一带山区中又捉到了几只白鹇。这说明,它们不是被人从外地带来的,而是在峨眉山土生土长的,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居民”。可是进一步想,峨眉山的白鹇和生活在南方的白鹇有什么不同呢?它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许多问题在郑作新的脑海里回旋。
考察结束了,郑作新带着白鹇的标本,回到北京,把它们放在自己的标本桌上。在这以后的几年中,只要一有空闲,郑作新就对它们进行观察,可是并没有发现它们和南方等地的白鹇有什么明显的差异。郑作新对科学工作并不草率,仍旧继续观察。一次,他把白鹇翻过来,从脖颈看到胸脯,又从胸脯看到腹部和尾羽,连每个细节都不肯放过。突然,郑作新惊讶得几乎叫起来,原来,这只白鹇的两侧尾羽是纯黑色的,而南方白鹇的两侧尾羽却是白色的,中间夹杂着深色的花纹,两者完全不同。又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对比,郑作新还发现,这几只白鹇的背部、肩部和翅膀上的黑色羽纹,也和南方白鹇稍有不同,但由于差别很不明显,很容易被人忽略。
在动物分类学上,“种”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同一种的动物,由于地理上的隔离,如果发生一些差异,那就叫作“亚种”。比如说,人们原先知道,白鹇这一个种共有13个亚种。郑作新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峨眉山的白鹏和生长在南方各省的白鹇并不相同,它是一个新的亚种,并把它命名为“峨眉白鹇”。这样,白鹇一共有14个亚种了。
郑作新把这个发现写成论文,和有关的同志联名投登《动物学报》。论文发表后,郑作新还把它寄给了民主德国的著名鸟类学家施特斯曼教授。国际学术界确认了这个发现。
几年以后的一天,郑作新突然接到了美国芝加哥博物馆鸟类研究室主任特雷勒教授的一封信。信中说,早在1930年,就有一个名叫史密斯的鸟类学家,在峨眉山采到一些峨眉白鹇。他还把一些标本带回芝加哥博物馆。遗憾的是,史密斯不曾作细致的研究,没有发现它和南方的白鹇有什么不同。一直到了60年代,特雷勒教授对这些标本进行研究时,才发现了这些白鹇的独特之处,并且做出了和郑作新完全相同的结论。特雷勒教授认为,这个新的亚种产在中国,应该用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而在当时的中国鸟类学家中,最有名望的是郑作新教授,因此给它定名为“郑氏白鹇”。特雷勒教授把自己的论文寄给英国的一份鸟类学杂志,而这个杂志的编辑部又把文稿转寄给施特斯曼教授审查。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巧合!施特斯曼教授看过以后认为,郑作新的发现和命名都比特雷勒要早,所以按照国际上有关动物分类及命名的规定,这个新发现的白鹇亚种还是采用了郑作新所定的名称,叫作“峨眉白鹇”。
事情过后,施特斯曼教授给郑作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前在许多问题上,中美的看法很不一致。可是我至少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你们都认为峨眉白鹇是一个新的亚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领先了。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
郑作新为祖国、为人民赢得了荣誉。
在某些人看来,这件事似乎可以结束了。而郑作新却不这样认为。他想把峨眉白鹇的发现和白鹇的起源与进化问题联系起来,做一些理论上的探索。
郑作新发现,在白鹇的14个亚种中,有半数以上的亚种产于云南省的南部和附近一带。这说明,云南南部是白鹇的分布中心,很可能就是白鹇的起源地。另外,除了峨眉白鹇以外,还有两个亚种的雄鸟的尾羽外侧是黑色的,它们一个产在海南岛,一个产在柬埔寨,和峨眉白鹇一样,都在白鹇主要分布区的边缘。
这些情况能说明什么呢?郑作新经过反复思考,得出了新的结论。他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白鹇生活在我国的云南南部一带,那时候,它们的尾羽全是暗色的。后来一部分白鹇进化得快一些,它们尾羽的底色渐渐演变成白色。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使它们在生存竞争中处于优势,逐渐占据了起源地。而另一部分白鹇进化得慢一些,它们的两侧尾羽仍然是暗色的,处于相对的劣势,因此受到比较发达的同类的排挤。它们之中有的被淘汰了,有的被迫向其他地区迁移。它们之中的一支——峨眉白鹇,从云南南部出发,沿着横断山脉的峡谷向北迁移,来到了峨眉山区,在这里定居下来,直到今天。生活在海南岛和柬埔寨的白鹇也是这样。
这就是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排挤观点。郑作新在研究白鹇进化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这个理论,已经受到了国内外生物学家们的重视。
寻找家鸡的祖先
1961年,郑作新带领几位年轻的鸟类学工作者,又一次奔赴云南南部一带,寻找家鸡的祖先——生活在野外的原鸡。
在我国,家鸡饲养有很悠久的历史。可是,中国家鸡的祖先是怎样被驯化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欧美各国和日本的有关书籍中,都一致地写道,中国家鸡是从印度引入的。
这种说法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达尔文·在他的著作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说,“鸡是原产西方(这里西方是指印度)的动物,在公元前1400年的一个王朝时代,引到了东方中国。”由于达尔文的巨大威望,100多年以来,大家都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就连我国的农业教科书也这样介绍。
然而,勤于思考的郑作新却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他想,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不能驯化中国的原鸡,非要远由印度引进呢?他很想把这个问题调查个水落石出。
首先,郑作新想搞清楚,达尔文是根据什么下的结论?他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发现,达尔文在著作中提到,他的根据是一部公元 1596年出版、1609年印行的中国科全书。至于这部书的名字,内容是什么,作者是谁,达尔文都没有提起。
郑作新一头扎进了科学院图书馆的古书堆里。他发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巨著《本草纲目》是在1596年出版的,可是翻遍全书,也没有找到关于家鸡引进方面的记载。而在1609年印行的书中,比较著名的只有《三才图会》。《三才图会》的内容十分广泛,篇幅很大,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鸡有蜀鲁荆越数种。……鸡西方之物,大明生于东,故鸡入之。”
很显然,这段文字就是达尔文提出论断的根据。可是,郑作新通过分析后认为,这里所说的“西方”,不是指的印度,而是指位于中国西部的“蜀、荆等地” (即今四川、湖北一带)。于是,一个大胆的、崭新的推断在他心中产生了:中国的家鸡不是从印度引进的,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用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原鸡驯化的;由于达尔文的疏忽,造成了一个人云亦云、流传百年的错误!
然而,如果没有事实根据,推断是不能作为科学的结论的。因此,原鸡是否曾产于中国?原鸡是否现在还在国内生活?就成为摆在郑作新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在风景秀丽的云南西双版纳,郑作新和助手们肩挂摄影机,手提猎枪,终日在原野和密林中奔走。一天黄昏,他们突然发现,在200米开外的原野上,有两只美丽的原鸡。原鸡的外形和家鸡十分相像,雌鸡披着一身铁褐色的羽毛,在前边疾走,雄鸡是栗红色的,头顶镰刀状的羽毛,紧跟在后。在夕阳的映照下,它们的身体闪烁着耀眼的光泽。原鸡的视觉和听觉都很灵敏,它们一发现有动静,雌鸡迅速躲入草丛,雄鸡惊恐地飞起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助手赶忙用枪把它们击落,留作供研究用的标本。
郑作新和助手们没有满足。他们还想抓些活的原鸡。又经过许多天的奔波努力,一天,他们在一个山寨旁的河谷里,发现了16只正在觅食的原鸡。它们的觅食习性和家鸡很相像,到了夜晚,有几只胆大的,还跑入村舍,和村民饲养的家鸡玩耍、交配呢!郑作新经过几天连续的隐蔽观察,最后确定,它们就是原鸡,就是中国家鸡的祖先——古代原鸡的后代!
从云南回来以后,郑作新还广泛地查阅考古方面的著述。他发现,我国考古学家曾经从中国史前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找到了鸡型的陶制器皿。这也是古代中华民族饲养家鸡的有力证明。综合各方面的考察和研究的结果,郑作新提出了“中国家鸡的祖先是中国的原鸡,是由中国人自行驯化的”的结论。这个结论很有影响,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后来,郑作新在提起这件事时,很有感慨地说过,搞科学不能迷信权威,对权威的错误也要认真纠正。当然,达尔文是伟大的,我们对他的功绩是肯定、推崇的,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啊!
1966年,郑作新正好60岁。正当他以花甲之龄,奋力挥动着翅膀,向更高的科学高峰冲击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有人胡说什么“鸟类是资产阶级玩赏的对象,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研究鸟类学,就会变修变色、亡党亡国”,郑作新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遭受了不应有的冲击,长时期被隔离反省。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巨著《中国鸟类分布名录》也被无理压制,拖延了好几年才得以出版。
1976年,罪恶滔天的“四人帮”终于倒台了。郑作新和全国人民一起,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潮之中。尽管他已经70多岁了,然而他不服老。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笑容满面对别人说:“你们总爱问我多大年岁。告诉你们吧,我今年72岁,过年就73啦。可是我要把73岁当成37岁过,这正是我的黄金时代啊!我要活到2000年,工作到2000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的双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眉宇间总是洋溢着青春活力。他一天也不停地忙碌着。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鸟类情况,满足各国鸟类工作者的需要,郑作新花费了几年时间,在自己50年鸟类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写成了英文版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这部1200多页的巨著,概括了中国有史以来发现和记载的所有鸟类,于1987年出版后,受到了世界各国鸟类学家的热烈欢迎。为了表彰郑作新的杰出成就,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学会授予他“1987年美国自然资源保护成就”奖。
30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着《动物学报》主编的职务。他还和其他鸟类工作者们一起,编写《中国动物志》的鸟类部分,共14卷。现在,《鸡形目》、
《雁形目》以及《雀形目》中的前三卷已经出版,其余各卷也在编写之中。几十年来,郑作新完成了14部研究专著,30多种书籍,上百篇科学论文,200多篇科普作品……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著作等身”,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著作很多,撂起来有他本人那么高。用这句话来形容郑作新,真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为了及时了解鸟类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郑作新不顾年迈体弱,又一次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在黑龙江省西部风景秀丽、渺无人烟的扎龙自然保护区,他们对丹顶鹤进行考察;在碧波荡漾、浩渺无际的洞庭湖上,他乘着一叶扁舟,深入到水草丛生的湖心深处,研究野鸭、豆雁等鸟类的习性……同时他痛心地看到,近些年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环境逐渐被污染了,有些人不懂保护鸟类的重要性,滥捕乱猎。各种动物,包括鸟类,保护生物,保护人类的家园。在他和各界人士的倡导下,群众性的爱鸟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起来。
……
由于郑作新在鸟类学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中国鸟类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长。1984年,中国动物学会也推举他为理事长。国际鸟类学界也很尊重他,推选他为英、美、德等国鸟类学会的通讯会员。1979年,他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雉类学术论讨会上做报告,并被推任世界雉类协会副会长,后来又被选为会长。
郑作新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然而他不愿休息,因为要做的事太多了。在他看来,鸟类研究就好像是一座宝库,是永远挖掘不完的。他经常用一句话来提醒和勉励自己:“时间有限,生命有限,不能浪费。”每天早晨动物研究所开门,经常是他第一个走进大门。天还没有全亮,他的办公室窗前就亮起了灯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