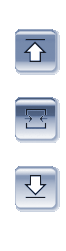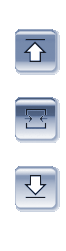| |
| |
|
女核物理学家
|
|
兴趣的由来
很少有人知道,把“核裂变”一词引入科学词典的人是一位妇女——莉泽·迈特纳博士。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妇女是第一个认识到原子可以分裂并且释放出巨大能量——原子能的人。由于她的开拓性的工作,一个原子能的时代开始了。现在,我们有了核反应堆,可以用来发电,可以把放射性同位素用于医学和工业,以及不幸的是,可以制造可怕的原子弹。
莉泽·迈特纳是菲利普·迈特纳和黑德威格·迈特纳的女儿,1878年11月7日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虽然父母两人笃信犹太教,但是他们的八个孩子却都施行了洗礼,被培育成基督教徒。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孩子们在那些反犹主义盛行的日子里受到保护。
莉泽·迈特纳当学生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在1902年发现镭的报道,从而对原子物理学发生了兴趣。由于一心想从事物理学这一专业,她在1901年进入维也纳大学。这件事听来容易,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人们一定记得,在那个时候,教职员和学生中间有一种反对妇女上大学的强烈情绪。确实,当时一名女大学生在人们心目里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为了不使自己偏离自己的目标,莉泽终于在1906年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能做到这一点的第一批妇女之一。
毕业后的一段时期里,迈特纳博士仍呆在维也纳,并对放射性这一新科目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个兴趣后来形成为她终身的工作,引导她打开了原子能领域。但是,在那个时候,科学工作和进步的中心是柏林,而不是维也纳。很多伟大而著名的科学家聚集在柏林,把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吸引来。因此,1908年,莉泽·迈特纳来到柏林,在举世闻名的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博士指导下学习理论。(普朗克博士开创了对现代物理学有着重大意义的量子理论,为此,他于1918年获得诺贝尔奖金。)后来,迈特纳博士成为普朗克博士在柏林大学的助手。她在这个位子上干了3年。
在跟随普朗克博士工作期间,迈特纳博士遇到了奥托·哈恩博士,以后,她同哈恩博士合作了30年。哈恩博士当时正在寻找一名物理学家来帮助他研究放射性的化学。然而,由于时代的偏见,妇女是不能在化学研究所工作的,而哈恩博士就是在化学研究所进行他的工作。因此,哈恩博士和迈特纳博士就在一个地下室里找到一间木匠的工作房,他们就在那里设置了他们的实验室。作为化学家,哈恩博士的兴趣在于发现新的化学元素和它们的性质;而迈特纳博士则关心这些新元素的放射性。两个人在放射性领域里都做着开创性的工作。
为了比较容易地理解迈特纳博士的工作和她的贡献,这里最好把一些用过和将要用的名词说明一下。首先,一切物质都是由被称做分子的基本单位组成的,而分子又是由被称做原子的基本单位组成。原子的中心是一个原子核,周围有许多电子围绕着它转。原子核内部是质子和中子。质子是物质的粒子,带有正电。电子带负电。中子是中性粒子。由质子和电子结合在一起组成。还有另外一些粒子存在,但现在我们暂时不涉及到它们。
某些化学元素放出粒子或射线,从而变成其他元素,这样的元素被称为放射性元素。大约有19种元素天然具有这种放射粒子的性质,因而被称作是天然放射性的。举例来说,镭和铀就是这种元素。其他一些元素,当把它们置于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里的时候,可以通过用高速原子粒子轰击的方法使其具有放射性。放射性元素可以放出α粒子或β粒子或γ射线,或者它们的结合体。一个α粒子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 (氦原子的核)。β粒子是来自原子核的电子,是一个中子被分离成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的结果。
γ射线与χ射线非常相似。α粒子没有多少穿透力,一张纸就可以把它挡住。β粒子穿透力较强,但可被薄金属板挡住,此如一块薄铝板。γ射线具有巨大的穿透力 (甚至超过χ射线),只有铝和混凝土才能把它挡住。
放射性是法国巴黎大学的安托万·亨利·贝克雷尔在 1896年偶然发现的。他给这一过程起了名字。这件事情是在威廉·伦琴于1895年发现X射线之后不久发生的。这两个发现加上另外一些发现,比如J·J·汤姆森在电子方面的研究和马克斯·普朗克对量子放射性质的研究等,引来了现代物理学的时代。对放射性研究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是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他们在研究天然放射性沉淀物时发现了镭。
科学家们用α粒子、γ射线、中子和质子把一种元素变为另一种元素,从而制造出人工元素。例如,1919年,欧内斯特·卢瑟福在他在英国的实验室里用快速的α粒子 (从镭中得到的)轰击氮,氮变成了氧。发生的反应如下:
氮+α粒子→氧+一个质子
用这个方法,卢瑟福发现了质子。1932年,在卢瑟福实验室里工作的詹姆斯·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他用α粒子轰击化学元素铍,使铍变成碳,同时放射出一个中子。
铍+α粒子→碳+中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托·哈恩和莉泽·迈特纳正在紧紧追踪着一个新元素。然而,随着战争的到来,哈恩博士被应征入伍。迈特纳博士志愿充当奥地利军队中的一名X光护士。她仍然是奥地利的一个公民。只要情况允许,他们就继续他们的合作。到战争快结束时,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们向科学界宣布了一种新的化学元素——他们把它命名为镤。
永不停息的追求
1918年,迈特纳博士被任命为负有盛名的威廉皇家学院物理系主任。她被责成组建一个物理放射系。她在那里拥有优良的研究设备和一批助理人员以及学生。她着重研究自然的和人工的元素嬗变,那就是α粒子、中子和其他原子的炮弹轰击一种化学元素,使其变成另外一种不同的元素。
迈特纳博士继续她的放射性元素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工作报告。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特别是柏林的科学家,对于这一令人兴奋的核物理学新领域非常感兴趣,并且满怀热情地进行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辉煌的进展。质子和中子以及人工放射现象都已经被发现了。1934年,迈特纳博士和哈恩博士再次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他们对意大利的恩里科·费尔米的工作特别感到振奋。费尔米用中子轰击像铀这样的重元素,得到了比铀还重的新元素——超铀元素。他们重做了费尔米的实验以证实他的结果,获得了成功。如果要让科学界承认这种结果,这种证实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天,迈特纳博士和哈恩博士正在他们的实验室向铀原子核发射慢速中子,希望得到一种新的超铀元素。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更确切地说是令人迷惑不解的,他们发现了有钡的存在,而在实验开始以前,这种元素并不存在。钡的重量比铀轻得多 (原子数指的是一个原子核中的质子数目,原子量包括原子核中的质子加中子的数目)。他们原先希望的是发现一种比铀重而不是比铀轻的元素,他们对这个奇怪的结果无法作出解释。
迈特纳博士一生中的巨大悲剧发生了,正当她处于就要完成也许是本世纪最有深远影响的科学发现——发现铀原子可以分裂的边缘时刻,她被迫离开了哈恩的实验室。由于纳粹占领了奥地利,她的奥地利国籍已不再能使她在德国受到保护了。她从来没有隐瞒过她的犹太血统。1938年3月,当反犹主义在纳粹德国达到狂热程度时,迈特纳博士不得不逃走。她已被柏林大学解除了教学职务。她借口想度一个星期的假期,乘火车前往荷兰。在侥幸地躲过了纳粹巡逻队之后,她偷偷地越过了荷兰国境线。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获准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进入荷兰,因为她的奥地利护照在纳粹占领下已经不再有效了。当她离开德国时,只有哈恩博士一人知道她将永远不会回来了。
迈特纳博士从荷兰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在那里,她和她的朋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尼尔斯·博尔及他的夫人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此后不久,她接到邀请,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新诺贝尔物理研究所工作。与此同时,哈恩博士正在德国继续关于轰击铀的实验,结果得到的仍然是较轻的元素。他担心是否自己在实验中搞错了,于是,1939年12月他写了一封信给在瑞典的莉泽·迈特纳,信中包括他的实验的所有细节以便供莉泽进行专门分析和使用。她一遍又一遍地读了这封信,心思完全被信的内容占据了。当时她确信,铀原子确实已被分裂,并且在之一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她把信给她的侄子、物理学家奥托·弗里施看,两人于是重新进行这种实验,以证实其结果。迈
2特纳博士运用著名的爱因斯坦方程式E=mc,计算出:用一个中子轰击一个铀原子核释放出的能是 2亿电子伏特,即等于同等数量 TNT炸药爆炸力的2000倍。
威廉·L·劳伦斯在1940年9月7日的一篇杂志文章中对她的工作是这样描述的:“她正体验着一定是和哥伦布当年的感觉相类似的那种感觉。她和哈恩博士意外地碰上了本时代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他们已经踏上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也许将引导他们到达 ‘原子能的希望之乡’的彼岸。”
1939年1月16日,迈特纳博士和她的侄子奥托·弗里施把他们的研究报告投寄给英国著名的杂志 《自然》。这篇报告在大约三个星期之后发表,其中含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段话:“因此,这种情况看来是可能的:铀原子核的形式只有很小的稳定性,所以,在被中子俘获后,可能将自身分成两个大小大致相等的原子核。这两种原子核将互相排斥 (因为两者都带有大量的正电)并且将能得出总计大约2亿电子伏特的动能。”核时代已经开始了!正是迈特纳博士把铀原子分裂成两个较小的和不同的原子的现象描述为核
“裂变”,从而给科学词典中增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
当迈特纳博士把她发现原子裂变以及从而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情况通知丹麦的物理学家尼尔斯·博尔时,他非常激动,以致差点错过了去美国的轮船。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把这一消息转告给恩里科·费尔米和其他人。这一发现被迅速证实,原子弹的竞赛开始了。
反对战争
虽然迈特纳博士从未想到她的发现会被置于破坏性的用途上,并且她本来会极力反对这样做的,但是,无论是盟国还是德国都看到了将这种发现用在军事目的上的可能性。在美国,国防部执行了“曼哈顿计划”,在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的指导下制作原子弹。在德国,许多科学家卷入了具有同样目的的工作。
1945年8月5日,当第一颗原子弹投掷在日本的广岛市时,人们创造了历史。关于是否应当使用原子弹问题的争论——赞成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今后大概将长时间的持续下去。迈特纳博士反对使用它,尽管受到邀请,她拒绝用它的研制去做任何事情,也不再在核裂变方面进行更多的工作了。在广岛被炸的两天之后同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的一次广播谈话中,迈特纳博士说:“我希望,通过若干国家的合作,将有可能使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并且防止我们已经经历过的那种可怕的事情再发生。”
投掷在广岛的炸弹是一颗铀弹,它毁灭了整个城市。紧接着投掷在长崎的炸弹是一颗钚弹,也是在“曼哈顿计划”中被研制出来的。关于原子弹的消息完全出乎迈特纳博士的意料之外,她说:“我感到吃惊,它竟然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制造出来。这一发现发生在战争时期真是一件不幸的事件。”从此以后,她经常尽力使自己的工作不与原子弹发生联系。她在战后不久同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喋喋不休地议论我。我并没有设计任何原子弹,我甚至连它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它在技术上是怎样搞的。我必须强调指出,在我做击碎原子核的工作时,并没有想到要生产致命的武器。你们不能因为从事战争工作的技术人员利用我们的发现而责怪我们科学家。”为了表示她希望世界合作和把科学上的巨大发现用于和平的目的,迈特纳博士说:“妇女负有巨大的责任,她们必须竭尽所能来设法防止另一次战争。”她长期以来是一个赞成国际合作以防止把原子武器用于破坏性目的的人。
1945年10月,迈特纳博士被选为瑞典科学院的外籍成员。这个荣誉在该科学院200年的历史中只赠给过另外两个妇女——1748年当选的是一位瑞典妇女,1910年当选的是居里夫人。
1946年,迈特纳博士来到美国,做为一个客座教授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天主教大学呆了一年。她是一个讲话和气、经常面带笑容的妇女,英语说得很好,但带有很重的口音。1947年,当她69岁时,她退休了。之后,她继续在皇家工程科学院的实验室里工作,那里正在与瑞典原子能委员会合作,建立一个核反应堆。
1958年,迈特纳博士搬到英国与她的侄子和侄女们住在一起。那时,她的侄子奥托·弗里施博士是剑桥大学自然哲学系的主任。她继续出去旅游、讲课和出席音乐会 (她终身爱好音乐)。但是,年龄已开始使她的活动大大减少。1966年,迈特纳博士与从前的两位同事哈恩博士和费里茨·斯特拉斯曼博士分享了原子能委员会赠给的5万美元的恩里科·费尔米奖金。她那时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虚弱了,难以去维也纳领奖,因此,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格伦·T·西博格亲自到英国剑桥把奖金送给她。1968年10月27日,再过几天就是她90岁生日,迈特纳博士在一家小型私人医院里去世了。同她在研究工作中合作了30年的奥托·哈恩博士于同年7月去世,比她早3个月。
为什么莉泽·迈特纳博士从来没有因为她在打开原子时代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金呢?这对许多科学家来说仍然是一个谜。许多人贡献并不大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才冠群雄的女数学家
冲破世俗
埃米·诺特,1882年出生在一个以喜好钻研学问著称的犹太人家庭,父亲马克斯·诺特是爱尔朗根大学的教授,曾为代数几何的发展作出过许多重要贡献。马克斯的犹太家史和数学家气质对小埃米产生了深刻影响。
1897年,诺特考入爱尔朗根女子学校。当时的欧洲,妇女仍受到多方歧视,世俗的人们认为:女子是不能学习数学,也是学不好数学的。女子学校主要不是培养为社会服务的人才,而是培养合格的家庭主妇。因此,课程大多以家政、宗教为主,并辅之以钢琴、跳舞等必修的技巧。小埃米生性朴实无华,不爱虚荣炫耀,除了对开设的语言课外,对上述课程一概不感兴趣。在学校的大多数时间里,小埃米独自抱着厚厚的数学书籍,算呀,想呀,对同学们善意的讥笑和戏弄毫不在意。尽管诺特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较高的造诣,但在中学毕业时,也仅获得当一名语言教师的资格。是呀,世俗的人们怎么能放心让一个女孩子去教数学呢?小埃米面临着第一次选择:或听从命运的安排专心当语言教师,或向世俗挑战走自己的数学研究之路。小埃米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我要继续深造,我就不信女子不能学好数学!知子莫于父。老诺特早已发现埃米潜在的数学天赋,对女儿的选择更是双手赞成。可是到哪儿去深造呢?要知道,当时的大学是禁止女子学习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影响好不容易地给小埃米争取到一个旁听生的名额。小埃米高兴极了:不管旁听不旁听,只要有机会学数学就行!就这样,小埃米作为一名没有学籍的学生,大大方方地坐在教室前排,认真地听讲,如饥似渴地学习。后来,她勤奋好学的精神感动了主讲教授,竟破例允许她与男生一样参加毕业考试。于是,小埃米又成了一个没有文凭的大学毕业生。
诺特并不在乎那些写在纸上的文凭,她认为,学到真正的本领才是重要的。当时,数学研究的中心在德国,而德国研究的中心在哥廷根。“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大学毕业不久的诺特来到了哥廷根大学。在这里,她又旁听了希尔伯特、克莱茵、闵可夫斯基等数学大师的讲课,感到大开眼界,大受鼓舞,越发坚定了献身数学研究的决心。
不久,爱尔朗根大学传来了允许女生注册学习的消息。诺特激动极了,
“漫卷诗书喜欲狂”,当即返回家乡,作为仅有的两个女生之一堂堂正正地跨入校门,并以优异的成绩成为第一位女数学博士。从此,诺特逐步走上了完全独立的数学研究道路。
诺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人宣告:女子是同样可以学好数学、研究数学的!因此,诺特的求学道路和光辉成就成为鼓舞妇女向数学高峰攀登的力量源泉。
哥廷根大学的“编外教授”
诺特生活在公开歧视妇女发挥数学才能的制度下,她通往成功的道路,比别人更加艰难曲折。
诺特在不变量理论方面的修养及表现出的才能,使正沉迷于相对论研究的希尔伯特和克莱茵为之钦佩。1915年,诺特接到哥廷根大学的邀请。此时,诺特正处于困境之中:父亲退休,母亲病故,求学的弟弟被迫从军,女子又难以谋到职业。她迫切需要寻找工作,至少解决个人的温饱问题。能在希尔伯特、克莱茵身边工作、研究更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因此,当接到邀请之后,诺特毫不迟疑地迁居哥廷根,但是,好事多磨,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希尔伯特本想为诺特争取讲师资格,这以诺特取得的成绩而言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哲学院的教授们出于对妇女的传统偏见,极力反对诺特执教。一个荒唐的理由声称:“当我们的士兵从战场上回到大学。发现他们将在女人的脚下学习,他们会怎么想呢?”希尔伯特十分厌恶这种语言,他反唇相讥道:“我不明白候选人的性别何以会成为反对她当讲师的论据。先生们,别忘了,我们这是大学,而不是澡堂!”大名鼎鼎的希尔伯特也无法改变多数人的偏见,只能以他的名义开课,诺特讲授。
不过,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先生们,很快就为自己的错误决定羞愧得无地自容。因为仅仅只过了几年的时间,这位遭到歧视、只能以别人名义代课的女性,就用一系列卓越的数学创造,震撼了哥廷根,轰动了整个数学科技界,跻身于20世纪著名数学家的行列。诺特首先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给出了一种纯数学的严格方法,提出了统一的数学概念,现今被物理学家称之为诺特定理的工作,已成为相对论、基本粒子物理学某些方面的基石。后来,她又从不同领域的相似现象出发,把不同的对象加以抽象化、公理化,并用统一的方法进行处理,其经典性论文《环中的理想论》揭开了抽象代数现代化的新篇章。诺特也因之被誉为“抽象代数之母”。
诺特的杰出成就及希尔伯特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使诺特在清一色的男子世界——哥廷根大学取得了教授称号,然而只是一种“并非雇员的编外教授”。这是特意为诺特设置的一个奇特的职称,它似乎意味着哥廷根既不好意思无视诺特深刻的创造工作,又不愿彻底放弃对妇女的歧视。作为一名编外教授,无固定工资收入,而只能从学生的学费中支取一点点薪金、来维持其极其俭朴的生活。
传统的偏见和肤浅的见解使诺特没有得到应该享有的待遇。由于薪金太低,同事们发现,诺特总是在同一时间,在同一饭店里,坐在同一个座位,吃着同一种廉价的饭菜。对此,诺特没有怨言,甚至无暇去回味生活的甘苦。她经常说:“名利、金钱、地位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我的事业!”诺特是科学史上少有的几个真正视功名如粪土的人,平静地接受各种挫折和委屈,全部身心投入到数学研究和教授学生的工作之中。这就是哥廷根大学中没有薪水的“编外教授”,而原因就在于她是一位女性!
桃李满天下
诺特以杰出的思想和纯真的心灵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学生吸引在她的周围。她孜孜不倦地研究,又慷慨大度地奉献,是一个完全、彻底为学生服务的人。
尽管诺特不具备一个优秀教师的先天素质:她课堂组织能力差,表达欠丰富多彩,讲课技巧一般,但她热情、真挚、无私,把自己通过扎实的研究而形成的卓越的思想,尽心尽力地教给学生,深受学生爱戴和尊敬。诺特喜欢“散步教学”,即与学生在散步时共同讨论教学内容和感兴趣的课题。她把尚未最后定型的想法告诉学生,让他们同她一起讨论。她从学生那儿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共享生活的乐趣;而学生则从与她亲密无间的交往中获得伟大的才智和创造性思维的启迪。到20年代末,诺特周围已经形成了哥廷根内部的一个数学中心,而诺特实际上成了哥廷根数学集团的中流砥柱。诺特像慈母一样、引导着大批青年人走上数学研究之路。
1924年至1925年间,荷兰的范德瓦尔登来到哥廷根,这是一位具有独立见解但还尚未成熟的年轻数学家。当他把自己在代数几何方面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呈给诺特时,诺特看出了这位年轻人的非凡才华,但她又不能不直言相告:这些成果几年前就已由别人得出,且结果更为广泛。为了让范德瓦尔登及早了解代数几何的最新成果,她把自己的文章送给他参阅。此刻,范德瓦尔登不仅看到了诺特的工作对他进一步研究的价值,更看到了诺特赤诚无私的心。他很快地掌握了诺特的思想,并加以精辟透彻的解释,并成功地讲授了“一般理想论”的课程。后来,他又在诺特和哥廷根过去讲义的基础上出色地完成了《代数学》的著述。从此,诺特的抽象代数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诺特的学生遍及世界各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当时法国数学界人才空缺。一战”期间,法国政府把大学生全都赶上了前线,结果给法国的科学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破坏。“一战”后,一批法国优秀青年不满足法国数学界沉闷、保守、落后的局面,纷绘到国外求学。魏依、丢东涅等先后来到哥廷根,从师于诺特。诺特的抽象代数成果使这批青年如醉如痴,他们为这门新学科的公理结构所倾倒,影响了布尔巴基学派的思想。
日本先后有多人追随诺特学习研究。他们回国后组织了日本的抽象代数学派,推出一批日本代数学派的领头人物。在中国,诺特的思想最早由曾炯之博士传人。曾炯之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诺特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但由于曾炯之先生过早去世,使中国失去一次迅速普及抽象代数的机会。
诺特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她没有政治偏见。1923年,莫斯科大学的亚历山大洛夫和乌利松来到哥廷根,并进人以诺特为首的数学圈。对于这两位来自苏维埃政权的学者,诺特始终给予热情的关怀,建立起坦率和真诚的关系,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并曾一度赴苏讲学,深刻影响了前苏联的拓扑学研究和群论研究。
诺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和学者,而且还是位伟大的女性。正如外尔所言:“她热爱人民,热爱科学,热爱生活;爱的是那样热烈,那样衷心,那样无私,又那样敦厚——一个非常敏觉的、又是女性的灵魂所能具有的一切。”诺特终生未婚,但她作为一代宗师,桃李四方。
难灭的赤子心
1932年,诺特的科学声誉达到了顶点。在这年举行的第9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诺特应邀作了长达1个小时的大会发言,它显示了诺特研究方向的彻底成功,鲜花和掌声献给了这位善良、仁爱的女数学家。
然而,巨大的声誉并未改善诺特艰难的处境。在不合理的制度下,灾难和歧视像影子一样缠住了她。但她对祖国给予她的不公正待遇始终宽大为怀,没有丝毫的计较。相反地,诺特十分关心祖国的前途与发展,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为祖国增添一份荣誉。
诺特曾认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向何处去的讨论,主张社会正义和人类平等、希望德国能在理性、公正、人道的基础上重新组建。诺特的政治态度是纯洁和坚定的,在德国国内狂热的复仇和扩张情绪泛滥的时候,她始终保持着真正的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但是在那歧视妇女、“改良人种”的年代,一位犹太女子的呐喊又有什么用呢?诺特在研究、讲学之余,默默地祈求自己的祖国早日摆脱这场厄运。
但一场更大的打击和灾难又降落在诺特身上。在德国法西斯眼里,犹太民族是下等民族,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随着一大批犹太籍科学家的被迫出走,哥廷根数学中心彻底垮台。诺特被当局禁止参加一切科学研究活动,最后连她的“编外教授”、讲座和微薄的薪金都被取消了。“活着就要研究,就要讲学!”1933年10月,诺特在一片勒令的叫嚣声中,含泪告别了希尔伯特,告别了哥廷根大学。
诺特漂泊到达美国,在朋友和学生的帮助下,诺特终于在异国他乡有了一个较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爱因斯坦曾评论到:“这不仅使她生前在美国找到了珍惜她的友谊的同事,而且有了一批令人欣慰的学生,他们的热情使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过得最为愉快,也许还使她获得了一生中最丰硕的成果。”的确,那时诺特正处于创造力的高峰,她的想象力和技巧达到了最高点。她以新的统一的纯粹概念方式,逐步建立了非交换代数及其表示理论;她及其合作者证明的“通常代数数域上的每一个单代数都是狄克逊意义下的循环代数”的结论,仍是代数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标志。
尽管“德国的新统治者对她终年累月所从事的不谋私利和重大意义的工作所给予的报答,就是将她解雇;这使她丧失了维持简朴生计的手段和从事数学研究的机会”,但诺特始终热爱祖国,流亡中更是心系祖国,她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在理性、公正、人道的基础上重建和昌盛啊!尽管她在美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比在国内好得多,但诺特仍然关注哥廷根的事业和发展,并时刻准备着响应哥廷根的召唤。即使是在病榻上,在肿瘤手术的间隙里,也念念不忘她的祖国,不忘哥廷根,盼望着有朝一日重振哥廷根的雄威。但意想不到的手术并发症无情地夺去了她的生命,时间是1935年4月14日。就这样,这位有着完美人格的、才冠群雄的女数学家带着未竟的心愿离开了心爱的事业。
诺特一生清贫,在歧视女性的时代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待遇,然而,她百劫不悔、至死不渝,“以她那刚毅的心情和生活的勇气,坚定健康地屹立在我们的星球上。”今天,公开限制妇女发挥才能的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但诺特的人格和精神仍将激励千百万人为科学献身!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