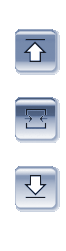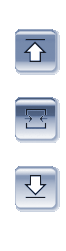| |
| |
|
徐光启
|
|
科场失意
徐光启是我国明朝著名的科学家。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奋著述,尤精晓农学。他还是一位沟通中外文化的先行者。梁启超在剖析中国学术史发展进程时,曾经深刻指出:“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笔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又说:“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如果说“第一次”接触的代表人物是玄奘的话,那么,
“第二次”接触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便是徐光启。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1562年4月出生于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里。年幼时,家道业已衰落。父亲徐思诚,一贯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常以助人为乐,悠闲地学习阴阳、医术、星相占候及佛、道之说。母亲钱氏,是位贤惠的“儒家女”,勤于早晚不停地纺纱,并经常给徐光启讲述当年倭寇之患的故事,加之评论当时主事官员的得失成败。
徐光启的童年是贫困而丰富,平静但不寂寞的。他曾在龙华寺读书,传说有一天馆师外出,他与同学玩耍且各言其志。有的说:“我欲为富翁”,有的说:“我欲为道士”,徐光启则说:“是皆不足为也。论为人,当立身行道,治国治民,崇正辟邪,勿枉为一世。”由此可见,他从小就怀有大志。8岁时,有一次,他曾顽皮地爬到塔端,一不留神跌到塔顶的铁盘里,正当人们感到惊慌时,他却很快地爬起并且为被他惊走的鹳鸟所吸引,又好奇地去寻找鸟蛋,早已忘却了危险。还有一次,他爬到高塔去捉鸽子也摔到地上,当人们被吓得大叫的时候,他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手中的鸽子,若无其事,透过这些小事,不难发现徐光启小时就有着好奇、勇敢的个性和对自然界的浓厚兴趣,这些正是他日后致力于科学研究的重要因素。
徐光启生存的年代,正值明代王朝急剧衰败和崩溃的前夜。此时,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后期,先后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文学家、探险家、哲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徐光启长大成人后,因家庭环境不好,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科场中求取功名。当时,这对读书人来讲,是所谓最公平、最具吸引力、也是最被看重的一条路。参加这种科举考试的目的是要取得“进士”资格,以便获得朝廷委任高级官职的机会。徐光启20岁时正式递补为可以领俸米的“廪膳生员”,第二年即开始参加乡试。明朝的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叫做“大比”。他曾先后五次参加乡试,不料,每次都以落榜告终。仅此,整整耗费了他15年的宝贵光阴,而屡试不中对徐光启的折磨和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这期间,为了养家糊口,他曾在家乡和广东、广西等地设馆教书。
1596年,徐光启在广东韶州教书时,有一天信步走到护城河西,他早就听说有位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住在这里。他走进利玛窦的屋舍,看到中堂墙上供奉的天主画像,神情栩栩如生,不由得肃然起敬。又见到屋内陈列着许多从欧洲带来的各式钟表、天文算术仪器、三棱镜、西洋乐器及欧洲名城的建筑图画等,越发激起了他的好奇心,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当时,因利玛窦已移往南昌,这里由另一位意大利神父郭居静主持。他亲切地接待徐光启,话题无非是围绕屋内的东西——科学与宗教。这次会见,使徐光启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科学与宗教,尤其是郭居静的谈吐留给他极深的印象,更令他希冀早日见到名闻遐迩的利玛窦。
研究西洋科学
1597年,35岁的徐光启,千里迢迢从广西桂林到北京赶考,这是第六次。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考上了,并以第一名中举。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焦竑,他对焦竑的知遇之恩,无疑是万分感激的。中了举人,在科举任用考试中,等于只是通过了地方初试,只能获得中下级的官职;要想成为可进受爵禄的“进士”,还须通过中央的考试,即“礼部会试”。徐光启抱着极大希望,先后两次参加“礼部会试”,又都落榜了。
1600年春在南京,徐光启初次见到利玛窦,二人谈论得十分投机,他热情称颂利玛窦:“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同时,对天主教的印象更为深刻。1603年在郭居静、罗如望两位教士主持下,他加入了天主教。
1604年,在他42岁时,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了进士。又经殿试,他考了第52名,列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当皇帝点翰林时,他又被点上第四,成为“翰林院庶吉士”。总计他在科场的经历,举人考了6次,进士考了3次才考中,一共花费了23年的时间,真可谓大器晚成。
徐光启在北京接受一连串考试时,常去会见业已在北京4年的利玛窦。到翰林院供职时,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从此,徐光启正式迈入了吸收西洋文化的学习里程。他对利玛窦十分推崇和赞许,曾说自己“生平善疑”,只有利玛窦能消除他对各种问题的疑惑。他认为利玛窦学问渊博,“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所谓“修身事天”即指他要传的宗教,“格物穷理”则指的是科学。为了便于学习,他在利玛窦的教堂旁边,租了一间屋子。他学习西洋科学的范围很广,天文、历法、火器、数学等,凡是利玛窦掌握的、实用的科学知识,他都认真地学习。徐光启有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就是喜欢作笔记。凡有参考价值的东西,都随手记下来。他发现利玛窦早先所著和所印的中文书籍,很受读书人重视。为了让中国的士大夫了解西洋人是如何地在尽心研究学术,是怎样地寻求确实的理由去证明一些理论,他向利玛窦提出了翻译科学著作的建议,对此,利玛窦十分赞同。经过商议,他们决定从《几何原本》入手,因为这本书中的理论和证明,十分明了,可以使中国读书人一新耳目。
1606年秋天,年已45岁的徐光启,开始和55岁的利玛窦合作译书。他每天到利玛窦的住处,都要工作三四个小时,一边学习,一边翻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即使一个词的翻译,为了准确,他也要反复推敲。“几何”这个词,就是他根据英语的音和义翻译出来的。费了一年多的工夫,经过三次易稿,徐光启终于用明畅的文笔译完前六卷。本来,他要求利玛窦继续译完全书,但因利玛窦忙于传教工作,只得暂告一段落。于是,两人各作了一篇序,便将译好的六卷刻板付印。徐光启在 《序》中指出:这种“度数”之学,在我国三代以前本来很发达,可是全被秦始皇烧毁。而汉朝以来的人,
“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虚发无效,或依拟形似。如持萤烛象,得首失尾”。大多成了半调子。他认为这本 《几何原本》是“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用它可以“补缀唐虞三代之缺典遗义”,把失传的古学补起来。徐光启对此书寄予厚望,他在《序》之后写的《几何原本杂议》中提出:“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强调该书“能令学者去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他还预测“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这充分反映出他要以西洋科学赋予中国古学以新的生命,使失传的古学复活,使误传的古学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的高度热忱。
《几何原本》作为徐光启潜心研究西洋科学的第一个具体成果,它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璀璨夺目的一页。在这之后,他和利玛窦又合著了《测量法义》一卷,自己又写了《测量异同》、《勾股义》各一卷,成为《几何原本》的接续之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明确指出勾股法则是治河、治水要取得成功的不可偏废的法宝,应把这些测量技术推广到治水、治田上面去,从中足以看出他的聪明睿智和科学头脑。由于徐光启大量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大门由此打开了!
《农政全书》和 《时宪历》
徐光启在大量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还特别关心农事,十分热爱农业科学。他在许多反映个人政见的文章中,始终认为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归根结底都要靠兴农事、行垦荒才行。他对农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且亲自耕作、实验,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上升为理论。
比如甘薯,当时由菲律宾传入中国,只在福建沿海少数地区种植。许多人相信古来传统的风土之说,认为什么地方生长什么作物是固定的。徐光启最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他请人从福建引入甘薯种子,在上海和江南一带多次试种,经反复试验,终获成功。他还试种女贞、乌臼。女贞树可以取白蜡,乌臼可以榨取臼油造蜡烛,还可以染发、造纸。同时进行过西洋种葡萄法以及新种接木的实验,养桑蚕,留意各种农事的方法。他全面研究过棉花的品种、选种、种子贮藏和播前处理、播种时期、施肥等技术问题。他还研究在我国北方大面积种植水稻,均获得成功。徐光启在农事上,除了自己躬身试验以外,还十分注意四处访问有经验的老农,有心得就随时作笔记。多年来,积累了丰富有用的资料,为他日后编著《农政全书》奠定良好基础。
1612年,他请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讲述,自己笔记,编译完《泰西水法》六卷。这本书介绍了17世纪初欧洲一些水力学原理,包括西洋的水利器具及水库工程方面的知识。他推荐用书中方法可以做到:“江河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无不可资为用,(而且)用力约而收效广。”译成这本书,也是他计划搞西北垦荒实验的前奏,因为在他看来,垦荒的先决工作就是要解决水利灌溉问题。
1613年,他称病引退到天津,开辟了一个有800亩麦田的实验农场,作为他搞“西北治田”实验的基地。他除了结合中国传统方法的优点实验西洋水利法以外,还继续试种别人认为风土不宜的作物,收获颇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实验过西洋制药水的方法。他虚心向洋人学习“西国用药法”——“药露”。为此,他让上海的家人到各方搜集需要的中药药种,自家种植,他自己也在天津种。
1625年,徐光启退隐之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增订、批改以前所辑《农书》上,经过勤奋钻研,日夜笔耕,终于在1627年完成了《农政全书》的初稿。全书共60卷,50多万字,引录了229种历代文献。这部书是集各书之大成,再加上他在北京、天津、上海进行农业科学研究的成果,编辑而成。全书分为12章,即: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农政全书》的主要内容是由三方面材料构成的。第一,是我国历代的农业文献,包括他翻译的《泰西水法》;第二,是各地老农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它是徐光启长期同农民一起积累的结晶;第三,是他自己对农业的专门论述,这是全书的核心部分,而且最为精彩。比如,在除蝗虫一节中,写了作者在多年的农业实践中,痛感蝗虫对庄稼危害巨大,为此曾花费7年时间调查蝗灾,翻阅我国自春秋以来历史上111次大蝗灾的记载,并观察蝗虫由子变蝻,由蝻成蝗的过程,最后提出了从灭卵入手治蝗的科学主张。
《农政全书》是我国较早的农业百科全书。它是研究我国农业史最重要、量珍贵的参考资料。300年来,这部书不但在国内一再出版发行,而且在国外也备受青睐。
徐光启融会中西科学,取得的另一突出成绩,表现在研究天文历法方面。具体来说,就是修订历法。
1629年,他在67岁时,奉崇祯皇帝之命督修历法。当时明朝推行的“大统历”乃太祖洪武年所定,实际上就是元朝郭守敬所订定的授时历。当郭守敬在世时,它就曾发生过错误,推算日月食已经不准确了,加之后世因循守旧,当然一错再错。后来,虽然多次有人提议改革历法,均未被采纳。1629年5月的日食,掌管观察天象的钦天监推算又发生明显错误,对此,崇祯皇帝十分震怒,于是便根据礼部奏疏,准由徐光启督领修历事。9月13日又下谕给徐光启,指示其修历原则:“西法不妨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用人必求其当,制象必核其精”;要他“阐千古之历元,成一朝之巨典”。徐光启接谕今后,即在北京设立“历局”,组织人力,开始了规模宏大、集思广益的修历工作。
徐光启虽以古稀之龄从事修历工作,可是他并未选择捷径,而是采用了最困难、最麻烦、也最具远大眼光的方法,即不但要建立新历法,还要述说其所以然,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此,他把修历的重点工作放在译书上面。他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由此看出,他对吸收西洋先进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在修历中,徐光启还非常重视国内外在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他曾把自汉朝以来68次修改历法以及293次日食预报与实际发生日食的误差,做了认真统计和研究。他还大胆引进了欧洲的时辰钟和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对天象进行精密观测,精心绘制了一幅《全天球恒星图》。这些研究。可以说已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他经常登上观象台观测。一次。为了测算冬至的时刻,在测验天文仪器时,不小心从台上失足坠下,腰和膝部都受了伤。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工作,不遗余力。
1631年正月,他第一次向皇帝进呈译好的历书;8月,第二次进呈历书;转年4月,第三次进呈历书。1633年,71岁的徐光启未及修完《崇祯历书》,便卧病不起了。他在去世的前几天,特地向皇帝推荐另一位学者——山东参政李天经接掌历局,以完成未竟事业。当年11月8日,这位勤劳俭朴、刻苦钻研、功盖华夏、献身科学事业的著名学者,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旅程。
徐光启精心研订的这部历法,直到清兵入关后,才正式公布使用,定名为《时宪历》,即是我们俗称的“阴历”。事实上,中国的阴历,并不是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应当指出的是,在我国历代改历工作中,只有徐光启这次采用了西方阳历的基本观念,作为一切推算的根基。这在中国,等于是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改革。可见,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