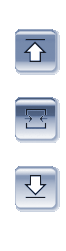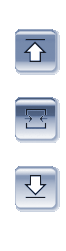| |
| |
|
王淦昌
|
|
像老师那样
1982年的一天,在江苏省常熟县,一位派出所的同志领着几位外地来客,走街串巷,来到一座木板房前,来客中的一位老人,端详着这修缮过的房屋,激动地连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他来探望深深怀念的生他养他的故乡。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常熟县枫塘湾。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中医,他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13岁的时候,母亲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肺病,又故去了。只有外婆疼爱他,供他上学。
1920年,他随一位远房亲戚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他在小学的时候,对解趣味数学题着迷。在中学,他最感兴趣的课仍是数学。教数学的周培老师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鼓励学生自学,在课外组织开展数学自学小组活动,王淦昌是小组的活跃分子。在周培老师的指导下,他在中学里就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1925年,他考进了清华大学。
清华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从 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招收一年级学生,王淦昌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学生。清华大学是用我国政府每年缴付美国的庚子赔款办校的,经费比较充裕,设备条件是国内其他大学不能比的。而化学系的实验条件在学校里又是佼佼者。王淦昌一进清华,就迷上了化学。他在中学时没有接触过多少化学实验,现在他一进实验室就显得异常活跃。石蕊试纸的颜色变化使他惊奇;关于元素和化合物性质的各种实验,他都认真去做;化学元素周期表,他背得烂熟,他觉得化学真是有意思。
可是,一年之后分系的时候,王淦昌既没有考虑从小就喜欢的数学,也没有进化学系,而是选择了物理系。
原来,清华大学物理系是由实验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 (1898~1977)创建的。他很重视为学生打下牢固的基础,亲自给学生讲普通物理课。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提了一个有关伯努力利方程的问题,王淦昌很快给出了答案,叶先生很高兴。下课后,他把王淦昌找去了,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并对他说:
“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叶先生引人入胜的讲课,对王淦昌的特殊关怀和鼓励,使王淦昌对实验物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爱上了实验物理,决心要打开实验物理的大门。
后来,我国另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吴有训从美国回来,叶企孙就请他到清华大学来主持近代物理课程。吴有训很注意培养提高学生进行实验物理研究的本领。他在教学中,注意到王淦昌对实验的特殊爱好和操作能力,他也喜欢上这个勤奋、好动的学生。他自己是通过实验工作接受近代物理学的,他也希望用同样的方法,来培养、帮助王淦昌。1929年6月,王淦昌大学毕业了,吴有训把他留下来当助教,并且给了他一个研究题目: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目的是要研究北京附近气象因素对大气放射性的影响。这项研究当时在国内还不曾有人做过。王淦昌在吴有训的指导下,查阅了大量资料,然后进行实验。每天从早晨9点到11点,重复着那一套繁琐、艰苦而又需要一定技巧的实验,同时记录下当天的温度、大气压、风速、风向、云的性质与分布等。从1929年11月到1930年4月,一共6个月。这真是对青年科学家的一次考验,王淦昌坚持下来了,得到了北京上空大气放射性与气象条件的相互关系的大量数据,写出了论文。
是叶企孙、吴有训这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把王淦昌引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王淦昌对物理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他在浙江大学当物理系主任的时候,新生入学,他都要亲自去欢迎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他对新生们说:“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她研究的对象。她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十分有趣味的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多么使人鼓舞啊!他也像他尊敬的老师那样,把一批批学生,引上了物理学的征途。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50年4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1年被任命为副所长主要领导宇宙线的研究工作。1954年在云南落雪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很快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注意。
1956年秋天,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并且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
自从1930年英国科学家狄拉克首先从理论预言存在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逊利用云雾室从宇宙线中发现正电子以后,实验物理学家一直在寻找各种粒子的反粒子。如果所有的粒子都有反粒子,这将证明微观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对称性,粒子与反粒子——正与反——的对称。各种介子的反粒子已经确证了。1955年美国建成60亿电子伏质子加速器,用这台加速器很快就发现了反质子,接着又发现了反中子。到1957年,摆在实验物理学家面前的一个挑战性课题,就是寻找反超子。这时候,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一台能量更高的加速器还在建设中,而联合原子核所一台能量为10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就要建成了,在能量上可以占几年优势。王淦昌根据这个情况,果断地把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作为小组的主要研究课题。
联合所的加速器是建成了,但是配套的设备如探测器、测量仪、计算机等都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经过研究,王淦昌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首先,他考虑到反超子的寿命很短,要想比较可靠地捕捉到这类粒子,用能够显示粒子径迹的气泡室作为主要探测器比较理想。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又选择了技术难度比较小,建造周期比较短的丙烷气泡室,他们自己动手,建造了气泡室,用π介子作为炮弹,在加速器上进行实验。王淦昌把握着研究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时地嘱咐组员们在观察气泡室拍摄到的照片时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1959年3月9日,终于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
王淦昌小组的工作,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1972年,杨振宁教授回国访问时对周恩来总理说:联合原子核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1982年,王淦昌和丁大利、王祝翔荣获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物理学家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以身许国
1960年底,王淦昌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任期满了,他就要回国了。
一天,他特地来到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慎重地把一个存折当面交给大使,说:“请你收下,转交给祖国人民吧!”这是他在联合所工作4年,节衣缩食积存下来的,共有14万卢布(旧币,折合新币14000卢布)。他想,祖国和人民正在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这笔钱虽然不算多,但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祖国的一份心意。
看了这个故事,读者可能会想,王淦昌是教授,工资高,一定有很多钱吧。他的学生曾经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师的薪水很低,王老师又在病中,生活艰苦,营养不足。有人私下议论:王老师是28岁当教授的,抗战前,应该拿高薪,那时候物价也比较低,发的是硬币银元,师母也善于节俭治家,估计会有积蓄,为什么生活这样艰苦呢?后来揭开了这个谜,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早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为了支援抗战,王老师和物理系仪器管理员任仲英一起,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捐废铜烂铁,给政府造抗日枪炮。而王老师是既出钱又出力,把他结婚时的金银首饰和家里积攒多年的银元都捐献了。王淦昌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的学生。
王淦昌的夫人是一位家庭妇女,子女又多,靠他一个人的收入,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有一颗非常可贵的赤子之心。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常常以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勉。总是想着国家,想着别人。他40年代的一个学生,在1957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在十年动乱中,因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有一段时间断了生活费的来源,王淦昌知道后,就给这个学生写信,要他安心做好《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生活费由他负责。以后,他每月按时给这个学生寄30元生活费,直到他知道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问题确实解决了,这才放心。在那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这样做是要冒受批挨斗的危险的。
1982年,因为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他们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王淦昌得了3000元奖金。他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原子能研究所职工子弟中学,作为奖学金。他说,他是想为娃娃们的父母减轻一点负担,使他们为原子能事业更好地工作。这也体现了老一代科学家对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寄予极大的期望。
1959年6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企图把我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建设核工作。
为了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技术难关,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有关部门,集中到了北京核武器研究所。
1961年3月的一天,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健步登上二机部大楼,在二楼的部长办公室里,刘杰、钱三强正在等着他哩。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他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这个决定对王淦昌来说,就是要他从熟悉的、并且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研究工作,改做他不熟悉的应用性工作。他脑子里一下就联想到40年代初期,国际上有一批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他,没有多想,没有犹豫,随即愉快地表示:
“以身许国。”
汽车离开了二机部大楼。王淦昌陷入了沉思:“3天?”他想起了刚才刘杰同志向他转达的周总理的口信: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我们的祖国,需要更加强大。是啊,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并且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不就是祖国的强盛吗?他深深地感到,党和国家对自己是多么信任,寄托着多大的期望啊!第二天,他就到核武器研究所上班了。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地为这神圣的事业奋斗了16年。
王淦昌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领导工作。开始,爆轰物理实验是在离北京不太远的长城脚下进行的。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没有试验场地,是借用解放军的靶场。王淦昌和郭永怀来到了靶场,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指挥安装测试电缆、插雷管,直到最后参加实验。一阵阵“轰”、“轰”的爆破声,震撼着古老的长城,一年中,他们做了上千个实验元件的爆轰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获得内爆的重要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天,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去工作。那时候,基地刚刚开始建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喘气。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王淦昌仍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讨论问题,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一次实验都获得成功。
就在这一年中,王淦昌到广州开会,见到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副总理作了一个握紧拳头,然后猛地展开的手势,问王淦昌:“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王淦昌满有信心地答道:“再过一年。”陈毅副总理高兴地说:“好,有了这个,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就更硬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轰轰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过了两年8个月,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这里面有王淦昌的心血,人们称他为核弹先驱。他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1969年,王淦昌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在这期间,他又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
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上级明确要求,务必在国庆20周年前打响。并且要求保证成功,保证安全。当时,王淦昌已经年逾花甲,又是处在动乱时期,要担负这样重要的任务,要促生产,可真不容易啊!
他亲自深入车间,和工人同志们谈心,到职工宿舍,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的实干精神,支持着王淦昌满怀信心地去完成试验任务。
王淦昌在严重缺氧的高原上,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身体渐渐支持不住了。同志们要求他说:“王老,你歇歇,让我们去跑吧!”但是,有高度责任感的王老,仍坚持要亲自到科研生产第一线去。他说:“任务那么紧,项目那么多,有一项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试验。”后来。因为缺氧气喘,实在跑不动了,就在办公室接上氧气袋,坚持工作。
由于时间紧,工程量大,地下坑道里的通风设施比较简陋,氡气浓度不断增长。王淦昌听到这个情况,很为在地下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健康担心,立刻组织人员进一步监测,他分析原因,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仍有一些同志心里不安,几次找王淦昌反映。王淦昌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说明情况,并恳切地要求道:“希望大家发扬我院优良传统,加紧工作,缩短在洞内停留的时间。”最后,大家都提前完成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而王淦昌一直坚持在洞内,和大家一起工作,直到最后才撤离现场。
王淦昌领导同志们按期完成了国家试验任务。却因为他坚持科学态度,说了实话,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又因为同志们提出“对在洞内工作的同志保健应有所改善”的要求,王淦昌答应向党委建议解决,又被当成搞
“活命哲学”,怕苦怕死的典型。一顶顶帽子扣到他头上,他却泰然自若,用沉默予以抵制。开完批判会,一回到住地,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75年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前,同志们把准备工作做好了,满有把握地向王淦昌和其他领导作了汇报。王淦昌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坚持要进洞作一次最后的现场检查。当时,洞内回填工作已经进行,要进去比较困难,许多地方只能爬着进去,而且里面的光线很暗,大家一再说,可以保证工作的质量。他想到周总理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还是爬进洞内,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察看,仔细询问他不放心的问题,直到把每一个实验装置的结尾工作都看完了,才满意地说:“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永不知足的追求者
原子能研究所里静悄悄的。全所职工都在礼堂开会,王淦昌所长正在讲话。他,情绪微微有些激动。前不久,1979年12月1日,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宿愿终于实现了。他跟着共产党走过了30年的历程,他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现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作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实现“四化”更有直接的责任,我们必定要尽一切力量,争分夺秒地努力去完成各项任务。这就是一个新党员老科学家在新的形势面前作出的答复,也是对他所领导的全所同志发出的号召。
王淦昌看到实现“四化”,能源是重要的物质基础,而开发利用核能(核电站)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1978年,他和二机部的几位专家,利用国庆休假,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发展核电。邓小平同志很重视,派人找写信人座谈,听取意见。从此,他对核电就抓住不放了。率领考察团出去考察,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做报告、给有关杂志写文章,广泛地宣传核电。
1980年,中央书记处邀请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开设“科学技术知识讲座”,为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课,其中第三讲的内容是安排能源问题。王淦昌听说后,主动找科学院联系,提出应增加核能的内容。核工业部推荐王淦昌去讲。王淦昌认真准备,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反复修改讲稿,制作幻灯片,还进行了几次预讲。充分体现了他对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的负责精神。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淦昌兼了10多个职务,经常出去开会,但是,他的主要阵地,还是在原子能研究所。他亲自抓一个研究组,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研究室,进行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1982年,他把核工业部副部长的职务辞掉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辞掉了,把核物理学会理事长的职务也辞掉了。他说:“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何必自己一直担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他是不会辞掉的,就是科研,就是惯性约束核聚变。有一次他看了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电影后,非常高兴地说:
“巴甫洛夫活了90多岁还能坚持搞科研,实在太好了,我还可以搞好多年科研呀!”
聚变反应也是一种重要的核反应。海水里含有大量的氘,氘、锂等都是能进行聚变反应的核燃料。受控聚变一旦实现,将是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惯性约束是世界上公认很有希望的一种实现聚变的方法。早在1964年,他与苏联巴索夫几乎是同时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产生核聚变的设想,他向国务院写了一份建议书,很快上海光机所就开始从事强激光的研究。后来,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强流加速器产生的高能带电粒子束引发核聚变,花钱比较少,适合中国国情,有巨大的潜力,他就和科研组的同志一起,设计、建造这种类型的加速器,开展粒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工作。现在他又引导这个研究室把工作的重点转变到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上来,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王淦昌对科研上的成就就是这样永远不感到满足,对科学的探索永远不断地向新的高峰攀登。他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