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第八章 知时达务:梁启超与汪康年
|
|
十二岁的梁启超在考中秀才的第二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便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到广州拜师求学。他的老师先后有吕拔湖先生和陈梅坪先生,后来又有石星巢先生。石先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人到中年以后,他在写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还说:“此老旧学尚好,吾十五六时之知识,大承得自彼也。”(《梁启超年谱长编》,19页)
石星巢(1852—1920),广东番禺人氏,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他的情况,只知他本名炳枢,后改名德芬,星巢是他的字。同治十二年(1873年),即梁启超出生那年,他考中举人,先在广西任知府,后官至四川道员,不久,便返回广东老家,以教书为业。他的寓所建在广州城南的清水壕,被称为“石室”,又称“徂徕山馆”。这个名字应该是有些来历的,北宋儒学大师石介,奉符(今山东省泰安市)人,其境内有一座徂徕山,所以,石介便以“徂徕先生”自称。八百年后,石星巢以“徂徕”命名自己的寓所,当然不只是因为姓石,更主要的,还是追慕石介先生的学问和人格。
当时,广州城里有五大书院,分别为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名气都很大。他们的首席教授,人称山长,都是当地很有身份的学者,地方长官新来乍到都要先拜访他们,对他们是很尊敬的。梁启超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入学海堂读书,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离开学海堂,大约五年时光,他完全沉醉在知识的海洋里。先是插班生,后转为正班生,同时还在菊坡、粤秀、粤华等书院听课。在这里,他眼界大开,精神豁然,从而改变了从前“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的孤陋寡闻,“乃决舍帖括”。(《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页)什么是“帖括”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捷径》之类的教辅书。
学海堂是嘉庆年间的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他把有清一代的学术主流带到了岭南,广州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梁启超很快就成为学海堂出类拔萃的学生之一。他像阿里巴巴发现了藏宝洞一样,贪婪地汲取新的知识。但他又是个很不容易满足的人,他在多年以后说到自己的求学:“若启超者,性虽嗜学,而爱博不专,事事皆仅涉其樊,而无所刻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三十九,1页)
所以,当他听说了石星巢先生的人格、学问之后,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拜在石先生的门下。石星巢也是汉学一脉,所授学问不过训诂词章,但梁启超对石先生似乎有更多的好感,而石星巢也很喜欢这个聪颖而又勤奋的学生,称他为“卓荦之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中举后,石星巢写信给另外一个学生汪康年,希望他能在第二年春天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的时候,给予照顾和帮助。这样看来,梁启超结交汪康年,最初是由石星巢先生牵线介绍的。
师出同门,谊非寻常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人氏,中年以后自号毅伯,晚年又自号恢伯,最早翻译《茶花女》的林纾解释为“灰心时事也”。(林纾:《汪穰卿先生墓志铭》,见《汪穰卿先生传记》,5页)他和梁启超的缘分,真是不浅,不仅同出一个师门,而且还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同科举人。区别仅在于,他的考场在浙江,梁启超的考场在广州。他自光绪七年(1881年)求学于石星巢,执弟子礼,比梁启超早六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和梁启超同赴北京参加会试,这一年他三十岁,而梁启超只有十八岁,第一次出远门,所以,作为老师,石星巢请汪康年照顾他的这位小学弟,也在情理之中。
这次会试,梁启超与汪康年双双落选,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路线离开京城。汪康年选择去湖北,两湖总督张之洞请他做家教,教两个小孙子读书,不久又在自强书院给他安排了编辑的职位,还请他做了两湖书院的教员,其实就是张之洞的幕僚。在这里,他结识了很多张之洞身边及湖北官场上的人,大大增加了自己的人脉。梁启超呢?他在父亲梁宝瑛的陪伴下回了广东,准备继续读书。途经上海时,他买了一本徐继畬编纂的《瀛寰志略》,这是个世界人文地理的普及本,初刻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书中以地球为引子,先介绍东西两个半球的概况,然后,又按照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以及西方的民主制度,比如英国的议会、美国的独立战争等。对新知识充满好奇的梁启超,很快就被这本书吸引了,这时他才知道,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五大洲还有许多国家,他们也有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上海制造局翻译的其他外国书也让他感兴趣,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他也只能望书兴叹。这一年的秋天,他离开学海堂,拜在康有为门下,并与陈千秋等人一起,请康有为开馆讲学,成为万木草堂的学生,这才有机会读到更多的西方著作。他在万木草堂读书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发生了“公车上书”这件大事,从此,梁启超追随在老师身边,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万木草堂,学生生涯到这里便结束了。
这几年,梁启超与汪康年有过一些书信往来,曾把康有为之弟康广仁介绍给他,还托他代售老师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梁启超曾把这本书的印行比作“台风”,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清代学术概论》,78页)也就是说,人们奉行了两千余年的经典,从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一人敢违”,“无一人敢疑”(《新学伪经考》,2页),现在,忽然有个叫康有为的跳出来说,这些书都是伪造的,是赝品,是一钱不值的废纸。你想,他这么一说,不仅靠这些书吃饭的文人不答应,靠这些书为自己的权力提供合法性的统治者更不能答应。所以,该书印行不久就遭到清政府的封杀,书版被毁,发行也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代售该书应该还是有危险的,但汪康年没有推托,可见他们的交情绝非泛泛。不仅如此,梁启超在另一封信里还鼓动汪康年支持张之洞修铁路的主张。修铁路,开工厂,造轮船,这一直是洋务派所热衷的,他们很希望能在不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和立国精神的前提下,通过这些自强事业使国家强大起来。张之洞便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实际领袖。就像张之洞有时也大模大样地掏钱赞助开学会和办报纸一样,这时的梁启超却也对修铁路感兴趣,他对汪康年说,如果铁路能够修成,则中国“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0页)
光绪十八年(1892年),汪康年进京会试,中了第二十七名。发榜后,因突发足疾,行走不便,未能参加殿试,直到两年后,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才又入京补考,考了个三甲第六十一名。这时,梁启超也携家人来到北京,他在这里一直盘桓到十月,结交了不少贤者名流。这时,中日在朝鲜开战,李鸿章迟迟不肯调兵,外交又寸步不让,结果被迫宣战。黄海一战,中国海军战败,不久,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北京亦有风声鹤唳之感。无奈之下,梁启超将家眷送出京城,归省贵州,他也于十月六日离京南下,返回广东。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他与汪康年大约是见过面的,由于汪康年补考之后很快便离开京城,回了湖北,他们只能书信往还,交流各种信息,特别是中日战争进展的情况。这期间,梁启超还一再提起在京时多次讨论过的话题,即多方联络和发现人才,并说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年春天,梁启超再次入京,参加会试。这是他与科举的最后一次“调情”,此后便不再有科场入闱之事。这时,李鸿章临危受命,接替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前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求和,与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辽东半岛给日本,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消息传到北京,犹如一把尖刀插在中国人的心上,每个人都有一种心痛滴血的感觉。从四月十四日开始,几乎每天都有举子到都察院上书,反对朝廷签署和约。这时,聚集在北京的各省举子已有万人,大家群情激愤,康有为遂倡议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割地赔款,要求变法维新。“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13页)《任公先生大事记》也记载:“乙未公车上书,请变法维新。倡之者康南海,而先生奔走之力为多。”(《梁启年谱长编》,37页)这是梁启超直接参与政治运动的开始。由于公车上书的影响力,一时间,朝野上下,包括光绪皇帝,都有发愤图强的表现。所以,尽管有汪康年写信相邀,请他去上海商量创办《译报》之事,但他却被京城的形势所吸引,迟迟不肯动身。何况,北京这时也要办报了,他在五月间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顷拟在都设一新闻馆,略有端绪,度其情形,可有成也。……此间亦欲开学会,颇有应者,然其数甚微。度欲开会,非有(由)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同上,40页)
这封信在《汪穰卿先生传记》和《汪康年师友书札》中都被注明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其实是写于 1895年五月中旬,这里所说的办报,是指未办即夭折的《译报》。此外,所提到的开学会、编辑《经世文新编》,都是梁启超于 1895年在北京拟办之事。十月初,梁启超信中所说的学会即强学会在京成立,作为强学会的会刊,《中外纪闻》也开始随宫门钞(清代宫廷的官报。由内阁发抄,内容包括宫廷动态、官员升除等。因由宫门口抄出,故名。又称邸钞。)发送。到了十二月中旬,北京、上海的强学会先后被查封,报纸也办不下去了。这时汪康年又来信邀他到上海办报,他在离开北京之前写信给汪康年,抱怨:“南北两局,一坏于小人,一坏于君子,举未数月,已成前尘,此自中国气运,复何言哉!”对于办报,他没有异议,只是担心报馆“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惟命所适”,如果不成,他就打算去湖南了,“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右帅适在其地,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他知道汪康年与陈三立、邹代钧关系不错,还希望能为之事先疏通。(同上,53页)
共同创办《时务报》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3月抵达上海,参与《时务报》的创办。此前,他还收到了黄遵宪邀他来沪办报的信函以及康有为的师命。后来他在《三十自述》中讲到此事:“京师之开强学会也,上海亦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亦废。而黄公度倡议续其余绪,开一报馆,以书见招。”(《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7页)此时的梁启超,与黄遵宪尚未谋面,还谈不上什么交情,只是慕名而已。而梁启超最终选择上海办报,放弃湖南,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康先生并招出沪改办报以续会事”起了作用。(《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45页)
此时的上海,可谓风云际会。在康有为“一函两电”的催促下,去年十二月,汪康年力辞两湖书院之教职,已先期来到上海,接替康有为主持上海强学会的工作。而黄遵宪在朝廷的安排下,暂留江苏,处理教案及商务各事。他那时经常往来于上海、南京之间,恰逢上海强学会被迫停办,他本来并不热心此事—当初康有为来上海创办强学会,有十六个人加入,黄遵宪的大名亦赫然写在上面,却是由梁鼎芬代签的。但强学会被迫解散之后,竟然一蹶不振,不思再起,他觉得这是一种耻辱,所以,“谋再振之,以报馆为始倡”。(《人境庐诗草笺注》,1215页)他的这种想法与汪康年一拍即合,并得到了途经上海的吴季清与邹殿书的支持。他们二人都是维新阵营的知识精英,尤其是吴季清,与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的交情都很深,他的儿子吴铁樵与梁启超更是挚友。随着梁启超的到来,报馆的筹备工作更加紧进行,很快便有了一些眉目。梁启超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几个人“日夜谋议此事。公度自捐金一千元为开办费,且语穰卿云:‘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为股份,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46页)没想到,黄遵宪的这番话竟成谶语,随着《时务报》的发展,影响力的扩大,后来果然发生了要将《时务报》“据为汪氏产业”的纷争。
最初,《时务报》的开办经费只有强学会上海分会的余款一千两百元,以及黄遵宪和邹殿书的捐款一千五百元。当时,汪康年力主要办一张日报,梁启超和黄遵宪都表示反对,认为他只是“欲与天南遯叟争短长”罢了。天南遯叟即王韬,著名的改良主义政论家,黄遵宪的老朋友,那时他正在《申报》任总主笔。由于梁启超与黄遵宪的坚持,汪康年暂时放弃了办日报的想法,同意办一份旬报。但他并未完全打消办日报的念头,两年后,与《时务报》同名的《时务日报》还是在上海创刊了。不过,这是后话。此时,他们只能合力先把《时务报》办好。这份每月三期的旬刊,终于在七月初一日正式出刊,汪康年任经理,相当于今天的社长,负责财务经营管理;梁启超主笔政,也就是今天的总编辑,负责报纸的内容编排。出刊前,由梁启超草拟了《公启》三十条,并经黄遵宪改定,刊登在六月末的《申报》上,“署名公启者,先生(黄遵宪)暨吴季清(德。)、邹殿书(凌瀚)、汪穰卿(康年)、梁任公凡五人”。(《人境庐诗草笺注》,1216页)四五月间,这份《公启》还曾以小册子的方式,分送给各地的同志;到第一期创刊时,又印成单张夹在报内,阅报的读者都应该能够看到。
为了办好《时务报》,梁启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时务报》十天一期,每期三十页左右,“以石版印连史纸上,极清晰而美观。所载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内容,而域外报译,独占篇幅至二分之一强”。(《中国报学史》,103页)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两年里,这份报纸共出版六十九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梁启超应邀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离开了《时务报》。在此之前,除了中间有四个月去广东和武汉出差,其余时间他都在《时务报》辛勤笔耕。他后来回忆作为总编辑做了哪些工作:“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覆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46~47页)由此可见,一个总编辑的工作是多么繁重。事实上,由总编辑执笔撰写每天的社评或时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邓拓的时代,而梁启超实为滥觞。
时务报章天下闻
无论如何,《时务报》提供了一个比《中外纪闻》更加广阔的舞台,可以任他纵横其文字,驰骋其才华。那时他的西学新知,还是很有限的,他的旧学底子,用章太炎的话说,也很一般。但他消化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却是惊人的,他对媒体传播功能的领悟力也是不同寻常的,他又是个极敏感、极容易受到感染的人,所以,他的文字便有一种超强的魔力。胡思敬不是一个肯轻易说梁启超好话的人,却不得不承认:“甲午款夷后,朝政多苟且,上下皆知其弊,以本朝文禁严,屡兴大狱,无敢轻掉笔墨讥时政者,自《时务报》出,每旬一册,每册数千言,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所欲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行销至万七千余册,由是康门之焰张,而羽翼成,党祸伏矣。”(《戊戌履霜录》,见《戊戌变法》一,373页)胡思敬是个守旧之人,民国后还曾积极参与张勋复辟,对新派人物绝无好感,他是真的担心康梁如此嚣张,内外结党,会给朝廷带来明末那样的党祸。正因为如此,他对梁启超社会影响的描述,应该是可信的。
李肖聃称赞梁启超“作《变法通议》数十万言,其文出入魏晋,工丽大类范蔚宗(晔),亦效龚自珍为幼眇自喜之词,旁出陈同甫(亮)、叶水心(适)、马贵与(端临)诸人之风,指陈世要,一归平实,间杂激宕之词,老师宿儒,新学小生,交口称之。”(《星庐笔记》,37页)这段文绉绉的话也许有些费解,而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一文则说得比较明白,在他看来,梁启超所“著《变法通议》,以淹贯流畅,若有电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的达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畅言的政论。这一篇文字的影响,当然是极大。像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追忆梁启超》,67页)这当然也是因为,“当时民智之闭塞,士风之委靡,号称智识阶级者,下焉者日治帖括,上焉者鹜于训诂词章;而梁氏日以 ‘维新 ’‘变法 ’‘新民 ’‘少年’‘自强 ’‘救国 ’之说,大声疾呼,复以其间灌输世界智识,阐发先哲绪论。凡所著述,大抵气盛而文富,意诚而词达。加以 ‘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 ’,故一文之出,全国争诵,老师宿儒,犹深翘仰”。(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追忆梁启超》,115页)其实,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
清廷立朝近三百年,文禁甚严,屡兴大狱,敢于公开批评时政的人很少,敢于写成文章,明目张胆地批评朝廷,要求改制变法,抑制君权,伸张民权的人,就更少。由于甲午战败,国家危亡,大家心里憋了很多话,都不敢说。现在,梁启超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所以,朝野上下,先进保守,一时都为梁启超所倾倒。就连著名保守派人物,后来曾与叶德辉等人一起不遗余力地攻击康梁,要置他们于死地的湖南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也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年初手谕岳麓书院的学生,称赞《时务报》“议论精审,体裁雅饬,并随时恭录谕旨暨奏疏,西报尤切要者。洵足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38~39页)而湖南巡抚陈宝箴与两湖总督张之洞,更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全省所有书院以公费订阅《时务报》,并要求学生认真阅读。陈宝箴的要求不仅具体,而且想得也很周全:兹由本部院筹拨款项,属该报馆寄送若干分,发交各府厅州县书院存储,俾肄业诸生,得以次第传观,悉心推究。所有丙申年七月初一日开馆起,至十二月十一日,共十七册,均令补齐。嗣后每年,先由本省厘金项下筹拨报费,以便按月派送。(同上,39页)
在这里,除了要求全省各地书院都应订阅之外,已经出版的若干期也要求必须补齐。这说明,他们是很看重《时务报》的,也说明了《时务报》在读者中受到欢迎的程度。在这期间,《时务报》的发行量一度攀升到一万七千份以上,很显然,如果没有各地官员的全力支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做法不但开了中国公费订报的先河,还因此引起了各地年轻士子对新学新知的兴趣,以及民族国家意识的启蒙。所以说,“清末士气之奋发,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传,实与有大力焉”。(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见《追忆梁启超》,115页)即使张之洞,讲到《时务报》初创时的情形也不得不承认:“乙未(1895年)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籥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劝学篇》,88页)这也就是说,晚清士人之觉醒,民智之初开,风气之大畅,民间办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清朝末年改良变法的主体力量由在朝转向在野的重要标志之一。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感受力和“流利畅达、声气灏大”的新文体,成了那个时代领风气之先的人物,执舆论界之牛耳。著名报人、时政评论家黄远生甚至将他尊为“报界大总统”。
不过,梁启超在《时务报》的言论,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和不安,甚至不满。他的好朋友吴樵(铁樵)在致汪康年的信中,便提到《时务报》在武昌的一些情况:“南皮(张之洞)阅第五册报有讥南京自强军语,及称满洲为彼族,颇不怿。此层却是卓如大意处,樵知必力阻之。吾辈议论,当思非其时非其人不可发也。此时此人,当受之以渐,声闻不可以菩萨行告之,况佛法耶。以后此种吹求,恐天下发之者尚多,我辈羽翼未丰,断不宜犯此大阵。尚樵在申,必力阻之。卓如诚快刀砍阵,而此间讥之者亦不少。”(《汪穰卿先生传记》,57页)这里所说《时务报》第五期的文章,指的便是梁启超《变法通议》中《学校总论》那一章。根据汪诒年的说法,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批评“金陵自强军所聘西人,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引起张之洞的不满。查阅梁启超的文章,其中并没有汪诒年引述的这句话,但他在文章中的确批评了洋务派聘用洋人行新法的做法,特别提到“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局、汉阳铁厂之类,每年开销之数,洋人薪水,几及其半”;不仅如此,他还批评洋务派几十年辛辛苦苦做的这一切,是治标不治本,“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14~17页)所以,张之洞对他不满意是很自然的。
严复最初对《时务报》倒是大为赞赏的,他在其创刊一个半月时曾写信给汪康年和梁启超,认为“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已也”。并说以前他在欧洲的时候,“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此非取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余地已而。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嚆矢也”。他特意捐资一百元给报社,“区区不足道,聊表不佞乐于观成此事之心云尔”。(《严复年谱》,82~83页)但过了不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三月间,严复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赐书二十一纸”,不能算短了;而梁启超的复信也很长,有两三千字。严复在信中谈了四个问题,其一,叮嘱他下笔一定要慎重,因为,“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谬”(同上,87页),并提醒他言多有失,会给人留下把柄和口实;其二,变法难讲,应该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由甲及乙,由乙及丙,不可偏废;其三,由《古议院考》说到民主的传统,不必引述中国古事以证明西方有的中国也有;其四,孔子不是教主,儒学亦不是宗教,教不可保,也不必保。梁启超的回复,有讨论,也有辩解,或说明,“词气之间,有似饰非者,有似愎谏者”,但总的来说,他很感激严复对他的这一番教诲,“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母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母之外,无如严先生”。他说:“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谀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6~110页)
大声疾呼醒世人
《时务报》创立之初,汪康年所作言论也很激烈,他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文章,大讲民权的好处,“夫民无权,则不知国为民所共有,而与上相睽。民有权则民知以国为事,而与上相亲”。他还说:“若夫处今日之国势,则民权之行,尤有宜亟者。盖以君权与外人相敌,力单则为所挟,以民权与外人相持,力厚易于措辞。”(《汪穰卿先生传记》,55页)汪康年此言一出,竟引起轩然大波。梁鼎芬与汪康年是“至好”,亦作书表示反对:“弟(指汪康年)处华夷纷杂之区,耳目已淆,品类尤夥,望坚守初心,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此时神气清明,吾辈进言亦较容易,幸时时以斯自警,岂独吾之幸哉?”(《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99页)夏曾佑(穗卿)也曾谈及他对汪康年这番言论的看法。他在信中写道:“民权之说,众以为民权立而后民智开,我则以为民智开而后民权立耳。中国而言,民权大约三百年内所绝不必提及之事。”他又说,他并“不以言民权为非,而是以为此时提倡民权尚属太早”。(《汪穰卿先生传记》,56页)
这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应当看到,在《时务报》时代,求新求变的人是少数,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保守的、麻木的,还处于昏睡之中。这些醒来的人看到了现实的危险性,大声疾呼,希望能够惊醒周围的人,一起想办法挽救这个危险的局面。睡着的人反而觉得他们多事,搅了自己的好梦。而且,民众之中,原本多的就是惰性,容易接受“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且又自尊而敏感。虽然知道自己落后,有大不如别人之处,不然不会被小小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最终只能靠割地赔款来了结此事,但心里想想可以,有人说出来了,便一百个不愿意。如果有人进而提出要改革我们的弊政和旧习,学习日本及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更让一些人痛心疾首,辜鸿铭就曾用赞赏的口气写到傲慢的保守派:“已故皇家大臣徐桐,一位中国式领袖人物和满洲党的成员,说道:‘要亡么,要亡得正。’”(《清流传》,62页)更多的人则采取鸵鸟式态度,避之唯恐不及。这时的汪康年,似乎承受着比梁启超更大的压力,他的弟弟汪诒年曾指出:“故报纸初出,谤言日至,诃斥百端,殆难忍受。同人书札往还,咸以戒慎恐惧相勖,抑亦鉴于警世骇俗之论,不可以持久,惧其将一蹶而不可复振也。”(《汪穰卿先生传记》,57页)写信给他的人,除了前面提到的梁鼎芬、夏曾佑、吴樵,还有汪大燮、高梦旦、张伯纯、叶瀚、裘葆良、邹代钧、瞿鸿禨等许多当时的名流,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态度此时也有了相当大的转变,他在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全省各地书院必须订阅《时务报》半年之后,又发出一道指示,告知两湖地区各书院的学生,“上海《时务报》,前经本督部堂饬发院生阅看,以广见闻,但其中议论不尽出于一人手笔,纯驳未能一致,是在阅者择善而从。近日惟屠梅君侍御驳《辟韩》书一篇最好,正大谨严,与本督部堂意见相合,诸生务须细看,奉为准绳”。(同上,62页)
《辟韩》一文的作者是严复,最初发表于天津《直报》,文章对韩愈《原道》中的君主专制思想提出批评,倡导民权学说,认为这才是国家富强之道,他明确表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严复年谱》,76页)其后,严复将这篇文章连同《天演论》译稿都寄给了梁启超。经梁启超提议,《时务报》第 23册转载了严复《辟韩》一文。结果,“张之洞 ‘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 ’”,据说,大怒的张之洞自作《驳论》一篇,并以《辨〈辟韩〉书》为题,发表于《时务报》第30册,唯发表时用了屠仁守的名字。(同上,87~88页)严复的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正在杭州林启幕府的高梦旦的担忧,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指出:“《辟韩》一篇,鄙意大不以为然。所论君臣一节,尤不宜说破。变法之事久为人所不喜,内有顾瑗、杨崇伊,外有李秉衡、谭钟麟,皆以排斥异学为己任。君臣可废之语,既为人上所不乐闻,则守旧之徒,将持此以谮于上。不独报馆大受其害,即一切自新之机,且由此而窒。”他还进一步解释道,不是说作者道理讲得不对,而是因为,“以中国民智未开,既不足与陈高深之义,君权太重,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无益于事,徒为报馆之累,且并变法之可言者,亦将不得言矣”。(《汪穰卿先生传记》,58~59页)
高梦旦的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这番话与前面夏穗卿的那番话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希望办报人不要因小失大,重蹈强学会之覆辙。他们这些人,都非保守派,有人后来还成了革命党,但此时他们都很小心谨慎,都很爱惜《时务报》的前途。说到底,他们是把《时务报》看作自己的报纸了,愿意它“兢兢业业为之”,不愿它“轰轰烈烈为之”,“一切忌讳须加审慎,非不欲尽言也,虑炸弹之伤我报馆也”。(同上,61页)真的炸弹或未必有,但如果有人抓住把柄,上一道奏章,也许比真炸弹还要厉害。但梁启超并没把事情看得这么严重,他在给严复的回信中就曾表示:“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7页)而若干年后,王森然亦持同样看法:“平心论之,以三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先生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岂非豪杰之士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先生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近代名家评传》初集,198~199页)
事实也是这样,梁启超没有因为朋友们的批评、指责就有所收敛,他的文字依然保持着批判的战斗的精神,虽遭人非难,却并不动摇。汪康年的处境显然要比梁启超复杂得多,他曾经做过张之洞的幕宾和两湖书院的教习,还被张之洞聘为家庭教师,有这样一层关系,所以,对于张之洞以及张之洞身边那些朋友的意见,他不仅不能视而不见,还要给予特别的重视。他在《时务报》创刊之初发表的那几篇文章,已经引起张之洞的不满,梁鼎芬一再叮嘱他,“要在行之以渐,不可孟浪”(《戊戌变法》二,644页),“以后文字真要小心”(《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00页)。不久又发生了转载《辟韩》一事,张之洞这些人更不能容忍,梁鼎芬致信汪康年,毫不客气地说:“周少璞御史(讳树模,又字少模,时在两湖等书院讲学)要打民权一万板,民权屁股危矣哉!痛矣哉!纪香骢(名钜维,张之洞幕宾)与梁卓如必不干休(南皮诸人皆助纪)。文字将成,必要刻入板中。(此板不刻,必刻他板。)不刻,不复与弟相识。”(同上)这里所说的刻板,就是要求把他们所作批梁、批严的文章,刊载于《时务报》,并且以朋友绝交威胁他。不久,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同学徐勤(君勉)又在《时务报》第 42期发表了《中国除害议》一文,继续大谈民权,梁鼎芬写信责备他:“徐文太悍直,诋南皮(张之洞)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并且担心他在《时务报》中无权:“徐文专攻南皮,弟何以刻之,岂此亦无权耶?后请格外用心。”(同上,1901页)
汪康年也感觉很冤枉,叶瀚则写信劝他“多译实事,少抒伟论”,而且还说,“大约南皮(张之洞)是鉴于强学前车,恐若斯美举,再遭中折”,并希望他能体谅“南皮劝阻之意,其情极厚,似亦不可过却。在弟为此议,一望兄少为委蛇,无令大局中裂。又望兄多采方论,则病家或一旦发 ‘死马当活马医 ’之想,事转有济,亦不可知。总之,与其决裂于旦夕,不如求全于未然之为得计,而吾党存心则仍百折不挠,共济大局”。(《汪穰卿先生传记》,59~60页)其实,即便没有朋友们的苦口婆心,汪康年也完全可以理解张之洞的良苦用心。此后,不仅自己不再作民权民主之议,而且对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也一再横加指责,甚至妄加修改,搞得梁启超“窃不自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梁启超离开《时务报》赴湖南讲学时,他这个总编辑对报纸已经没有任何约束力。不仅人事变动不和他商量,而且,他要求发表的文章,甚至“告白”都迟迟不发。他对汪诒年说:“它日若竟是如此,令弟莫知所适从矣!”(《梁启超年谱长编》,99页)《黄公度先生年谱》也记载:“汪穰卿为张香涛(张之洞)之僚属,香涛初予资助,及见《时务报》论议新颖,且有民权民主之议,每授意梁节庵(鼎芬),贻书穰卿,以抑压之。穰卿至是不敢多言民权,且予梁以干涉。”(《人境庐诗草笺注》,1216页)不仅如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康有为在北京开保国会,张之洞在武昌听说了,大为惊恐,马上致电汪康年,告诉他“康开保国会,章程奇谬,闻入会姓名将刻入《时务报》,千万勿刻”。(《戊戌变法》二,644~645页)
由合作而积怨
很显然,张之洞犹如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一个楔子。梁启超与汪康年由融洽到隔阂,由分歧到矛盾,关系越来越紧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夹在中间的张之洞。早年的张之洞是个清流,与李鸿藻、张佩纶一样,喜欢以儒家教义为准绳,横议朝政,褒贬人物。中法战争中,张佩纶打了败仗,被革职充军,其他几位也分别受到处罚,只有张之洞得以幸免。以后的张之洞不再以清流的面目出现,他希望做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来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他不主张像李鸿章那样,一味地引进外国的军舰、大炮,但他也有所妥协,提出了著名的“中体西用”的理论。他愿意别人视他为维新党,所以,强学会在北京、上海成立之时,他都捐了银子,包括后来的不缠足会、农学会等,他也都有所捐赠,据说累计捐资高达五千两。《时务报》创刊,就用了上海强学会停办时剩余的银子。但他这个维新党,用严复的话说,并非真正的维新党,不过是个“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严复年谱》,120页)他以为,《时务报》既用了他的银子,就该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最初邀请梁启超到武昌,盛情款待,除了人人皆有的爱才之心,不能说没有讨好梁启超,欲将其收为己用的考虑。梁启超不为所动,张之洞退而求其次,这才利用汪康年,从内部入手,约束、抑制梁启超的言论。不久,他又在杭州、上海先后创办了《经世报》和《实学报》,目的就是要和《时务报》相抗衡,抵消《时务报》在读者中的影响。张元济当时曾写信安慰梁启超,“此皆例有之阻力,执事幸勿为所动也”,并斥责那些假维新党人:“所恨者,以爝火之微,而亦欲与日月争明,使为守旧之徒,犹可言也,而伪在此似新之辈。”(《梁启超年谱长编》,104页)
在此期间,康有为也成为梁汪交往中越不过去的一道坎。康是梁的老师,梁启超一直很尊敬他,言必称其师。康有为主张“尊孔保教”,他在上海创办《强学报》,甚至用了孔子纪年,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和反对。梁启超则追随其后,大肆鼓吹,也写了很多文章,在《复友人论保教书》中甚至提出成立“保教公会”,认为“居今日而不以报国保教为事者”,一定是不了解大局危亡之故。(《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11页)黄遵宪与严复都是欣赏梁启超的人,他们都曾力劝他放弃保教的主张。他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虽然也为康氏保教之说进行过辩解,认为:“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藉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110页)但他此后毕竟接受了严、黄二位先生的意见,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仅不再宣扬保教,而且反对保教,并因此和老师发生了分歧。
但是,对于康有为,他仍然以为是必须奉为师尊的,而且,康的学识、人品也是不容诋毁的。汪康年、汪诒年指责他借《时务报》宣扬康的思想学说,所谓言必称其师,梁启超明确告诉他们:“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康有为)。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未能征引(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梁启超年谱长编》,100页)他的意思是说,当初作《变法通议》,没有说明思想来自康有为,是考虑到报刊的发行,心里已经很不安了,其实谁不知道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如果说看到康有为的名字,就拒绝读《时务报》,那么看到梁启超的名字不是一样吗?早在《时务报》创刊之初,缪荃孙写信给汪氏兄弟,就认为梁启超不应将康有为的观点带到报纸中来。缪荃孙是固守考据、训诂的学者,他对康梁的今文学派自然是不能接受的。汪氏兄弟将来信中与梁有关的一段给他看了以后,梁启超回复道:“缪小山(缪荃孙)来书,舍弟节其大略来,已阅悉。弟之学派,不为人言所动者,已将十年……自信吾学必行,无取乎此,不徒为人之多言也。”他还嘲笑缪氏:“考据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吾以为今天下必无人更敢抱此敝帚以自炫者,而不意缪氏犹沾沾然,志得意满,谓其字字有来历也。”(同上,59~60页)
他们之间围绕着康有为而发生的争执与吵闹,一直发展到汪、梁公开决裂时,已经不可调和,在《创办〈时务报〉源委》一文中,梁启超把积压多时的愤懑一下子都发泄出来,他质问汪康年:“独所不解者,穰卿(汪康年)于康先生何怨何仇,而以启超有嫌之故,迁怒于康先生,日日向花酒场中,专以诋排为事;犹以为未足,又于《时务日报》中,编造谣言,嬉笑怒骂;犹以为未足,又腾书当道,及各省大府,设法构陷之,至诬以不可听闻之言。夫谤康先生之人亦多矣,诬康先生之言,亦种种色色怪怪奇奇无所不有矣,启超固不与辩,亦不稍愤;独怪我穰卿自命维新之人,乃亦同室操戈,落井下石,吾不解其何心也!”(《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48页)
还有一个人,在谈及梁启超与汪康年的关系时,也是不可少的,这个人就是黄遵宪。黄遵宪与汪康年久有嫌隙,后来几乎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梁启超则一直居中调和,想尽可能地维持这个局面。按照梁启超的说法,黄遵宪的为人,“讲条理,主简易,少应酬,其为人与穰兄性最不近,故每有不以穰为然处”。(《梁启超年谱长编》,97页)那么,汪康年又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脾性又如何呢?梁启超说他“应酬太繁”,他有个说法,必须吃花酒,才能“广通声气”,联络感情,所以,他每天“常有半日在应酬中,一面吃酒,一面办事”。(同上,47页)这种做派黄遵宪不仅做不来,而且不肯做。他甚至担心汪康年日日在上海滩的歌筵舞座中应酬,无暇掌管《时务报》的全局,于是建议让吴铁樵来上海,吴主内,汪主外。他还建议汪康年的弟弟汪诒年专门负责校勘和稽查,他并不知道,汪诒年现在所做的,正是他为吴铁樵准备的职位。他的这种安排很自然地让汪氏兄弟产生了误会,他给汪诒年写信,想尽力消除他们的疑虑,却由于他在此前一再要求请龙泽厚来上海,而龙泽厚又是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同学,更引起了汪氏兄弟的猜疑和不满。他们以为,黄遵宪和梁启超串通一气,就是想赶他们走。这几个人本来是有机会坐下谈一谈的,却阴错阳差,没有谈成,让误会变成了积怨。
黄遵宪是《时务报》的创办人之一,他倾注于《时务报》的心血,并不比梁启超和汪康年少。我们从他写给汪康年的几十封信中可以看到,只要是对《时务报》的生存、发展有好处,事无巨细,他都要不厌其烦地叮咛嘱咐一番。他最看重的,还是想给《时务报》馆建立一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他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不断强调,《时务报》是大家的事业,不是一家一户的买卖,“既为公众所鸠之资,既为公众所设之馆,非有画一定章,不足以垂久远昭耳目。故馆中章程为最要矣。此馆章程即是法律,西人所谓立宪政体,谓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中也。章程不善,可以酌改,断不可视章程为若有若无之物”。他对汪康年说:“公今日在馆恪守章程,公他日苟离馆,在公而任此事者,亦必须守此章程,而后能相维相系自立于不败之地。宪纵观东西各国谓政体之善,在乎立法、行政歧分为二。窃意此馆当师其意。馆中仍聘铁乔(樵)总司一切,多言龙积之(泽厚)堪任此事,铁乔不来,即访求此人何如?而以公与弟辈为董事,公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每遇更定章程,公详言其利弊发其端,而弟熟商参议而决之,似乎较善。”(《黄遵宪集》下册,463~464页)他的这一套想法,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设董事会,由董事会统领全局,再一个是立法、行政分开,有制定规矩、政策的,有实际操作的。这种制度设计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事实上,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很多私人企业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他的这种想法,并非心血来潮,报纸创刊时所定《公启》之第九款,就有这样的规定,在他不过是想落实这个规定而已。
但是,黄遵宪这些可能给中国报业制度建设带来巨大进步的设想,还是被汪氏兄弟深深地误解了,以为是人事替换的一种借口,因此对黄遵宪大为不满,并牵扯到梁启超,长期以来潜藏在《时务报》内部的各种矛盾,也随之公开化了,关于当时的情形,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源委》一文有详细的描述:以此两事之故,穰卿深衔公度,在沪日日向同人诋排之。且徧(遍)腾书各省同志,攻击无所不至,以致各同志中,有生平极敬公度,转而为极恶公度者。至去年(1897年)八月,公度赴湘任,道经上海,因力持董事之议,几于翻脸,始勉强依议举数人。然此后遇事,未尝一公商如故也。总董虽有虚名,岂能干预汪家产业哉!穰卿常语启超云:“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扰我权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公度一抗,则莫有毒予者矣。”此言启超之所熟闻也。自兹以往,正名之论大起,日日自语云:“总理之名不可不正,总理之权利不可不定。”于是东家之架子益出矣。去年一年中,馆中凡添请十余人,时启超在沪同事也,而所添请之人,未有一次与启超言及者。虽总办之尊,东家之阔,亦何至如是乎?(《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47页)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写在梁、汪二人撕破脸皮之后,固然有感情用事,不及深思熟虑之处,但所言却是可信的。严复曾在《国闻报》发表《〈时务报〉各告白书后》一文,他也认为:“梁君节概士,其言当无不可信者。”但他同时认为,梁启超的这篇文章,除了对《汪康年启事》中“康年创办《时务报》”一言有所辩驳,指斥他把众人集资的事业视若自家产业之外,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他说,问题不在于总理是否可以“独居创办名”,而在于总理能否以自己的工作证明可以胜任这个职务,“夫总理之名既正矣,总理之权既专矣,则宜视其事之何若”。那么,汪氏这个总理当得如何呢?严复认为,“自梁卓如解馆以来,而《时务报》之文劣事懈,书丑纸粗,大不餍于海内之望,如是则总理不胜任也。不胜任则宜自去,丈夫何妨溺死,乃拘游哉!任事以来,未尝照章清厘账目,以塞群责,设有谣诼,其将何以自明”?(《严复年谱》,124页)
《时务报》“党争”
如果说严复因为与黄、梁过从甚密而有先入为主之嫌的话,那么,来自陈庆年的记述是不是更能说明汪康年当时的想法和做法呢?陈庆年与汪康年一样,都是张之洞的幕宾,与梁鼎芬等一班朋友都走得很近,他的戊戌年(1898年)日记有几条与此事有关:三月十三日过访纪香骢(钜维),适汪穰卿在座上,少谈《时务报》,知今年销数较上年为少。旧主笔梁卓如(启超)久在湘中时务学堂为教习之事,不甚作文,近以穰卿添延郑苏庵(孝胥)为总主笔,卓如遂与寻衅,恐自此殆将决裂。彼等日言合群,而乃至此,可为发喟也。
三月十四日汪穰卿见过,言梁卓如欲借《时务报》以行康教(康长素〔有为〕为梁师,其学专言孔子改制,极浅陋),积不相能,留书痛诋,势将告绝。殊非意料所及,可叹也。
闰三月二十日闻康长素弟子欲攘夺《时务报》馆,以倡康学。黄公度(遵宪)廉访复约多人,电逐汪穰卿,悍狠已极。梁节庵(梁鼎芬)独出为鲁仲连,电达湘中,词气壮厉,其肝胆不可及也。
四月初一日闻节庵说,黄公度复电,以路远不及商量为词,且诬汪入孙文叛党,其实公度欲匈挟湘人以行康学,汪始附终离,故群起攘臂。爰发其隐情以复公度。公度嘱陈伯严(三立)电复,谓其徇人言逐汪太急是实,并无欲行康学之事云。(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见《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87~93页)
到了这个时候,《时务报》的内部之争,就明显地带有“党争”的性质了,至少汪康年周围的一些人是这样看的。双方都有些意气用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十一日,梁启超由长沙回到上海治病,马上给正在湖南的汪康年写了一封信,提出辞职。该信写得很像是最后通牒:“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他此时有些沉不住气,话说得就很决绝:“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二十五前后与弟一电(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并非弟用私人阻挠,此间已千辛万苦求人往接办,必不用康馆人也。)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弟开诚布公,言尽于斯,兄万不可作违心之言(但不愿辞,即不必辞),在此将就答应,到沪再行翻案。”但他还是希望《时务报》能够坚持下去,“《时务报》既为天下想望,不能听其倒败,故不得不勉强支持”。(《梁启超年谱长编》,103~104页)
然而,五月二十九日,御史宋伯鲁(芝栋)上《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据说此折是康有为代拟的,折中对《时务报》的工作大加赞赏,“两年以来,民间风气大开,通达时务之才渐渐间出,惟《时务报》之功为最多”。但是,由于梁启超“应陈宝箴之聘为湖南学堂总教习,未遑兼顾,局中办事人办理不善,致经费不继,主笔告退,将就废歇,良可惋惜”。因此他建议:“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责成该举人(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他还建议:“其官报则移设京都,以上海为分局,皆归并译书局中相辅而行。梁启超仍饬往来京沪,总持其事。”(《戊戌百日志》,197~200页)
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因为看到汪康年主持《时务报》工作期间,“尽亏巨款,报日零落,恐其败也,乃草折交宋芝栋(伯鲁)上之,请饬卓如专办报”。(《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49页)其实是想借朝廷的威力,将汪康年挤出《时务报》。此事见出康梁的局限和落后。没想到,皇上当天即明发上谕,请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处理此事,“酌核妥议,奏明办理”。(《戊戌百日志》,200页)孙家鼐与翁同龢同为光绪皇帝的老师,他受到中枢大臣们的影响,正想将康有为排挤出京,便利用了这件事。六月初八日,孙家鼐入奏上了《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他不仅请求批准宋伯鲁所奏,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而且拟请康有为赴上海接管《时务报》,督办此事。为此他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查梁启超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戊戌变法》二,432页)
针对宋伯鲁将《时务报》进呈皇帝御览的建议,孙家鼐借题发挥,他在奏折中写道:“仅一处官报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现在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皆有报馆,拟请饬各省督抚,饬下各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呈送都察院一分,大学堂一分,择其有关时事、无甚背谬者,均一律录呈御览,庶几收兼听之明,无偏听之弊。”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还乘机告了《时务报》的恶状:“《时务报》虽有可取,而庞杂猥琐之谈,夸诞虚诬之语,实所不免。今既改为官报,宜令主笔者,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宸聪者,一经查出,主笔者不得辞其咎。”(《戊戌百日志》,230~231页)
光绪皇帝当天即颁发上谕,同意了孙家鼐所奏。六月二十二日,孙家鼐再上《遵议筹办官报事宜折》,光绪皇帝又于当日颁发谕旨,请派康有为督办其事。但康有为并不情愿做这件事,他一直滞留于京城,不肯出京南下。汪康年则认为事关重大,光绪第二次颁发上谕的第三天,即六月二十四日,汪康年便在《国闻报》发表了《启事》,不仅声称《时务报》为他所创办,梁启超只是他聘请的主笔,还决定从七月初一日起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并请梁鼎芬为该报总董。七月初一日,黄遵宪五人连署在《国闻报》刊登启事,声明《时务报》为黄遵宪、吴德。、邹殿书、汪康年、梁启超同创于上海,推“汪君驻馆办事,梁君为主笔”。(《梁启超年谱长编》,132页)七月初六日,梁启超在《国闻报》刊载《创办〈时务报〉源委》一文,讲述了《时务报》的来龙去脉,以及两年来报社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矛盾纠葛。
其后,围绕《时务报》的归属所发生的各种争执,事实上已不重要。六月二十一日,《时务报》出了最后一期,第 69期;七月一日,《昌言报》第 1期出版,据汪康年所言,该报名称“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谕”,他也承认,除了总董改聘梁鼎芬,《昌言报》“一切体例,均与从前《时务报》一律,翻译诸人,亦仍其旧”。(《汪康年启事》,见《中国报学史》,111页)所以,过了一个多月,即戊戌政变后的第五天,慈禧便下令关闭了这家报馆。在她眼里,《昌言报》、《时务报》都是一回事,没什么区别。然而,严复在《〈时务报〉各告白书后》中讲了一段话,今天看来,却仍然值得人们深思。他指出,梁启超在斥责汪康年的时候,有一个道德制高点,即《时务报》本为公事,却被汪康年办成了私事。但是,“奏改公立民报为官报”,是不是为公呢?他说:“然则梁之所谓私者,正吾之所谓公;梁之所谓公者,正吾之所谓私。假使汪氏而私,是亦二私互争而已。公之名,断断非黄、梁二子所得居也。”严复的这一番话,不仅独到、深刻,而且非常公允,他揭示了被康梁所忽略的一个问题,即公众与公家的区别,按照《时务报》的民办性质,它是一份公众的报纸,而绝非一份公家的报纸。康有为所鼓动的改《时务报》为官报,其实是混淆了公众与公家的概念,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件事对维新人士的伤害是很大的,自从“争主维新以来,未有若此事之伤心气短者也”。(《严复年谱》,123页)
第二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日本与章太炎相遇,在章的撮合下,梁启超与汪康年恢复了交往,并时有书信往来。据章太炎记述,梁启超曾经问他,汪康年这个人到底怎么样?章回答:“洛、蜀交讧而终不倾入,章、蔡视木居士何如耶?”据说,梁启超听了章太炎的这番话,也很思念汪康年。但毕竟是不比从前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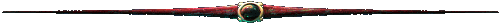
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书由“怅望祁连”免费制作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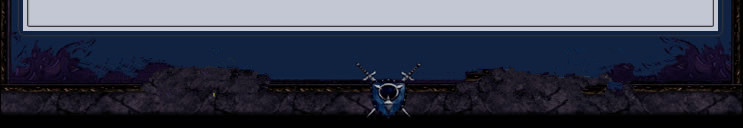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