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第十九章 寂寞身后事
|
|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告别了这个曾给他带来许多烦恼,又让他恋恋不舍的世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五十六岁。
2月17日,北平、上海同时举行公祭活动,以纪念这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了全部心血的伟大人物。北平的活动安排在广惠寺内,天津《益世报》为此出版了梁任公先生纪念专号,其中有《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一文,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广惠寺内佛堂均为祭联、哀章所布满,约有三千余件。据闻梁氏讣闻,仅择其素昔有关系者而送之。冯玉祥、丁春膏、商震、芳泽谦吉、籍忠寅、曹纕蘅、刘淑湘、丁文江等均送祭幛。男女公子思成、思礼、思懿、思达、思宁与林徽音(因)女士等均麻衣草履,俯伏灵帏内,稽颡叩谢,泣不可仰。全场均为喑呜之声笼罩,咸为所黯然。
是日到者甚众,除尚志学会、时务学会、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司法储才馆、广东旅平同乡会等团体外,有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张贻惠、林砺儒、瞿世英、杨树达、熊佛西、余上沅、蓝志先、任鸿隽、陈衡哲女士、沈性仁女士、江瀚、王文豹、钱稻孙、袁同礼等,门人中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约五百余人。(《梁启超年谱长编》,1206页)
《申报》也报道了上海追悼会的情形:
新会梁任公氏逝世后,已于前日(二月十七日)在北平广惠寺开吊,上海方面亦于同日假静安寺设席公祭,由诗人陈散原(三立)先生及张菊生(元济)先生等主持其事。昨日上午九时后吊客纷临,有孙慕韩、蔡元培、姚子让、唐蟒、叶誉虎、刘文岛、高梦旦等,不下百余人。学生及商界中人来者甚众。南京指导部某君与梁素昧生平,亦专来吊祭,并在礼场上声言:“论私益则知识及立志悉仰新会之启迪感化,论国事则振发聋聩为革命造基业,新会之功不亚孙、黄,故虽绝无交谊,特来致敬。”(梁启超在北平大殓时,有法界名人在广惠寺抚棺恸哭,言先知先觉,人人得而哭之,如梁新会者可谓不负中华民国矣。)(同上,1208页)
古人云,盖棺论定,入土为安。但梁启超却只能说是例外。
1929年9月9日,梁启超的遗体悄悄安葬于北平香山卧佛寺之东坡,其门生张其昀就显得有些不安,他注意到:“自梁先生之殁,舆论界似甚为冷淡。”(《追忆梁启超》,120页)他还担心:“梁先生与国民党政见不同,恐于近代历史不能为公平之纪载。”所以,他“北望西山,不禁为之泫然者矣”。(同上,125页)
张其昀的忧虑不是无缘无故的。对此,梁启超于生前便有预感和先见。他在1927年岁末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就曾提到:“几日来颇想移家大连,将天津新旧房舍都售去,在大连叫思成造一所理想的养老房子。”他甚至担心北洋政府的倒台,可能影响到女婿周希哲加拿大总领事的职位,安慰他官做不成也不要紧,还可以做生意。(《梁启超年谱长编》,1167页)
1928年6月10日,他写信给尚在欧洲旅行的梁思成,告诉他“北京局而(面)已翻新”,所以,先前所说他去清华任教的计划只好作罢,“该校为党人所必争,不久必将全体改组,你安能插足其间”?他劝思成到东北去,“东北大学交涉已渐成熟。我觉得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所差者只是参考书不如北京之多),况且东北相需甚殷,而清华实带勉强”。(同上,1179页)
6月23日,他又写信给女儿思顺,报告北京政局发生变化,北洋政府已被南京政府所取代,“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别人且不管,你们两位叔叔、两位舅舅、一位姑丈都陷在同一境遇之下(除七叔外,七叔比较的容易另想办法),个个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全家十几口,嗷嗷待哺,真是焦急煞人。现在只好仍拼着我的老面子去碰碰看,可以保全得三两个不?我本来一万个不愿意和那些时髦新贵说话(说话倒不见得定会碰钉子),但总不能坐视几位至亲就这样饿死,只好尽一尽人事。(廷灿另为一事,他是我身边离不开的人,每月百把几十块钱我总替他设法。)若办不到,只好听天由命,劝他们早回家乡,免致全家作他乡馁鬼”。(同上,1184页)
梁启超墓位于北京植物园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园由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走在其中像是进了一座庭院。(解玺璋摄)
他还说:“京津间气象极不佳,四五十万党军屯聚畿辅,(北京城圈内也有十万兵,这是向来所无的现象。)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不知他们何以善其后。党人只有纷纷抢机关、抢饭碗(京津间每个机关都有四五伙人去接收),新军阀各务扩张势力,满街满巷打旗招兵(嘴里却个个都说要裁兵)。”(同上,1185页)
不久,梁启超所预见的情况果然就发生了。新外长为了要替新贵腾新加坡的缺,牵连到加拿大总领事的人事安排,周希哲只好准备让位,惹得梁启超在给思顺的信中又一次大发牢骚:“现在所谓国民政府者,收入比从前丰富得多(尤其关税项下),不知他们把钱弄到那里去了,乃至连使馆馆员留支都克扣去。新贵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十万,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员官,真算得一种耻辱,不过一时走不开,只得忍耐。他现在撵你们走,真是谢天谢地。”(同上,1195页)
梁启超对国民政府侧目而视,国民政府对梁启超自然也不肯放过,北平特别市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做了一个针对“三一八”惨案的议决案,竟认为梁启超与此案曾有牵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乃至发生于数年前的这件惨案也被利用来做造谣的资本。当时,梁启超正在协和医院治病,为了说明真相,以正视听,7月7日,梁启超的侄子梁廷灿发表了《致北平特别市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书》,他指出:顷阅《民国日报》载贵委员会议决案关于三一八惨案有牵涉家叔之语,不胜骇诧。鄙人多年随侍家叔,于其日常起居,皆有详细日记,今因贵会议案所云云,与事实太相违反,不得不举出极简明而极有力之反证,郑重辨明。家叔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入春以后,忽罹重病,于二月十五日入德国医院疗治无效,三月二日出德国医院,三月八日入协和医院,住一楼三五号病室。九日医生检验一次,十一日检验一次,俱用局部麻药,十六日上午施用烈性药,全部麻醉,行剖割手术。施手术者为该院院长刘君瑞恒。十七、十八两日皆昏迷不省人事,十八日下午五六时间始渐苏醒。十九日下午,有问病者告以惨案状况。家叔奋气填膺,热度渐增,几陷危境。医生查知大怒,因此严禁探问者五日。此等事实协和医院有日记,某日某时某刻某秒病人作何状,一一记载,纤悉无遗。请贵委员会及普天下人凭常识推论,凭天理良心判断,以十六日正受麻药剖腹卧病之人,是否可以参预十八日上午发生之任何事件,此真不值一辩矣。贵会既以指导民众自命,鄙人殊不愿以不肖之心相忖度,谓其有意挟嫌,故入人罪;但据报纸所言,系一种正式决议。以堂堂一政党之议案,自不应为无责任而违反事实之言,以淆惑视听。为此专函抗辩,务请贵会派人向协和医院调查医案又日历,看鄙人所言有无一字虚伪差舛。(同上,1185~1186页)
这种凭空捏造的东西很容易被事实所驳倒,而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分歧却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12月1日,原清华研究院学生徐中舒、程璟、杨鸿烈、方欣、陆侃如、刘纪泽、周传儒、姚名达等致信梁启超,问候他的病情,同时说道:“客岁党军占领江南,南北之音问遂疏,师座因历史关系,为各方所注目,邮电往来常被检查,用不便径修书候。”(同上,1197页)这就是说,梁启超的往来书信是有可能被监控检查的。这些细枝末节足以窥视民国政府对待梁启超的态度。所以,梁启超逝世后,除了来自南京指导部的某君,无论北京还是上海,两地公祭现场,都见不到国民党方面的人,也少有他们送的挽联,是很自然的。当时,杨杏佛曾对徐志摩说,国府对于梁启超不能没有表示,并准备去南京找蔡元培等人商议,要在国府会议上正式提出。但是,由于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等人的坚决反对,此案也只能不了了之。梁启超的门生、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就曾以民国政府未能褒扬梁先生而深表遗憾,他说:“颇闻任公之殁,实曾有大力者建言政府,加之褒扬,格于吾粤某巨公而止。”(《追忆梁启超》,137页)这里的“大力者”即指蔡元培,而“吾粤某巨公”即指胡汉民。结果,直到梁启超去世十三年之后,即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三日,国民政府才颁布了褒扬梁启超的明令。对此,他的另一位门生吴其昌不无伤感地说:“读竟,泫然流涕。”(同上,403页)
言人人殊梁任公
这是因党见、政见分歧而导致的对于梁启超的轻视和冷落,虽然涉及到很少一部分人,但其影响却是长久深远的,尤其当国民党掌握了话语权之后,在以叙事建构晚清民国历史时,故意贬低梁的作用和贡献,丑化他,甚至用忽略和遗忘的方式,使他不存在,这些都是梁启超身后遭遇中最令人痛心的。
同为清华教授的吴宓对于梁启超身后的寂寞也曾感到不解:“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吴宓:《空轩诗话》,见《吴宓诗话》199页,转引自《追忆梁启超》夏晓虹后记,476页)说怪其实并不怪,王国维先生比较单纯,作为一个学者,他只在书斋里讨生活,性格上且落落寡合,与社会几乎不发生关系;梁启超就不同了,几十年风风雨雨,进进退退,几度出入于政治、学术之间,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无论人事还是国事,都牵扯到方方面面,各色人等,说好说坏都不容易,很多人说他“善变”,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梁启超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确实很难。
谭人凤是老同盟会员,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曾作过一部《石叟牌词》,开篇便说,他早年在思想上“感触于《时务报》者亦不少。故尝谓彼时之梁卓如启迪国人,功诚匪浅”。但“惜乎反复无常,甚至卖朋友,事仇雠,判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近康有为对人言,愿世人毋以我与某并称,我有所不为,某无所不为也”。(《石叟牌词》,2页)
这是来自敌对阵营的看法。湖南名士李肖聃在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时做过他的秘书,据说梁的有些文章还是由他代笔的,他对梁启超晚年的变化非常不满,认为“巨人长德,曲学阿世,且忍献媚小生,随风而靡。欧游心影之录,清华讲演之集,所以謏闻动众者,不惜低首于群儿,逐响于众好。而中国之文气日衰,圣风愈塞矣”。(《星庐笔记》自叙,1页)
他的意见大约代表了当时并不少见的固守传统文化不肯妥协的那一部分人的看法。而新文化的代表者胡适就从另一面指责他的“善变”,在一篇日记中胡适写道:“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追忆梁启超》,435页)
这种言人人殊,各持己见的情形,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梁启超太庞大了,以至于人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从某一角度出发去认识他的时候,看到的可能都是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我称之为盲人摸象式。郑振铎的看法与上述几位就完全不同,他说: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同上,88~89页)
郑振铎不是与梁启超交往很深的人,但他却可以说是梁的知音。丁文江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称赞道:“已经发表的论任公的文章,自然要算他第一了。”(同上,484页)
累变不离其宗
丁文江在给胡适的另一封信中还提到:“我听见人说,孙慕韩(宝琦)的兄弟孙仲屿(宝瑄)有很详细的日记,所以用思成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慕韩托菊生转交,请他借给我一看。”(《丁文江年谱》,333页)孙宝琦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与梁启超是朋友,他的弟弟孙宝瑄此时已不在人世,信中提到的日记,即后来出版的《忘山庐日记》。其中1907年5月20日记载:“饮冰梁氏,奔走海外十年,其言论思想,屡腾诸报纸。人有讥其宗旨累变,所谓种界也,保皇也,共和也,立宪也,开明专制也。始谈革命,继又日与革命党宣战。始谈公德,继又提倡私德。综其前后所言,自相反对者,不知凡几,岂非一反覆之小人乎?忘山居士闻而笑曰:不然。饮冰者,吾诚不知其为何如人,然据是以定其为小人,言者之过也。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为君子。盖小人知反覆也,因风气势利知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为反覆者不同。”(《忘山庐日记》下册,1043页)
梁启超对于自己的“反覆”“善变”也早有认识。他早年写作《饮冰室自由书》,就有一篇《善变之豪杰》,主张在宗旨不变的前提下,其方法可以随时与境而变。后来他作《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也有一番感慨:呜呼,共和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祖国;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自由。吾祖国吾自由其终不能由他途以回复也,则天也;吾祖国吾自由而断送于汝之手也,则人也。呜呼,共和共和,吾不忍再污点汝之美名,使后之论政体者,复添一左证焉以诅咒汝。吾与汝长别矣。问者曰:然则子主张君主立宪者矣?答曰: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吾知昔之与吾同友共和者,其将唾余,虽然,若语于实际上预备,则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86页)
梁启超的变与所以变在这里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他在晚年与学生们谈到变与不变,分分合合,不认为是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而是其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所决定的。他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见《追忆梁启超》,418页)这不是梁启超自夸,考察其一生经历,谁都不能否认这一点。陈寅恪于此看得很清楚,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指出: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寒柳堂集》,166页)
梁漱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
梁启超书法:忍辱精进负荷众生。这八个字表达了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任公先生是有血性的热肠人,其引用庄子内热饮冰的话,以饮冰自号,很恰当。他只能写文章鼓舞人,不能负担政治任务,其供他人利用是决定的。其卒自悔悟是有良心不昧者,以视康有为、杨度辈悍然作恶者,自有可原恕。(《追忆梁启超》,265页)
梁启超身后评价之难,固然与其自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有关,这恐怕正是徐志摩精心策划的《新月》纪念专号最终夭折的原因之一。胡适没有完成交给他的任务,怕也反射出其内心的矛盾。他在日记中写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然而他也看到:“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同上,433~435页)
寂寞身后事
胡适这样说固然有他的道理,而梁启超身后的寂寞寥落,又似乎和他的门生故旧往往早夭有关。蔡锷过早去世,已是很大损失;范源濂等亦先于他过世,徐志摩、丁文江、蒋百里更在其死后不久便陆续辞世;甚至他后期的学生,有些也未能保其天年,像清华研究院首届毕业的吴其昌,即梁启超的高足之一,只看他撰写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就不难想象他与梁氏相知之深,但他年仅四十岁即因劳累过度,身染重病而终至不起,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抱病撰写《梁启超传》,也仅得其半部,是为终生遗憾;他的另一个学生张荫麟,也是不可多得的史学人才,在新史学领域甚至梁、张并称,又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文学院四才子”,却因在战争期间患上肾炎症,缺医少药,病情日重,于1942年在遵义病逝,年仅三十七岁。梁氏弟子尚有不少,如徐中舒、王力、姜亮夫、陈守实、高亨、杨鸿烈、冯国瑞、陆侃如、何士骥、吴金鼎等,他们皆在学术界享有盛名,但在社会政治领域却影响很小,或完全没有影响。即使如张君劢、张东荪等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人物,三十年代以后也不可能再有更大的作为,已经没有人肯听他们说些什么了。丁文江曾在《大公报》上发表《公共信仰与统一》一文,希望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人把个人恩怨、各党利害放在一边,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都肯承认的最低限度的信仰,作为公共信仰,中国才有可能统一。但在国共双方打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的时候,谁又听得进这种劝告?
后面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很显然,梁启超身后所受冷遇的根本原因,就隐藏在这里。也可以这么说,他的思想和主张在那个时代让很多人感到隔膜,不可避免地采取疏离的态度,而且,他的救国方案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与其说他受到某些人的冷落,不如说那个时代冷落了他。梁漱溟曾在1943年撰文称,近五十年,中国出了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梁启超。”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同上,258页)他特别强调:“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他建议青年们读一读梁启超的书:“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同上,262页)
可惜,那个时代的青年已经很难听进他的劝告了。他们在越来越激进的革命理论鼓舞下,正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中去,哪有心思阅读梁启超的书呢?回想梁漱溟所说的近五十年,从1893年到1943年,乃至再向后推大约五十年,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舆论一直没有离开过“革命”,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调门越唱越高。梁启超最初也是革命论者,主张对旧世界采取破坏态度,至少他在1896年至1903年间的许多言论,是有反清革命倾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革命情结,梁氏还是其滥觞呢。但他很快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革命派,虽然他所反对的革命只是专以武力或暴力颠覆国家,推翻政府的狭义革命。他所主张的却是通过和平、渐进的制度或政体变革,或曰改良,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新生。此后他始终坚持这一点,无论是开明专制,还是君主立宪,所希望的无不是避免革命中的大规模社会动乱和流血,然而革命党没有这样的耐心,清政府也一再挑战人们的耐心,从而把更多的人变成了革命党,遂有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这时他所担心的,是革命将会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他尽了最后的努力,想要实现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但事实上已不可能。民国成立后,由于南方革命党与北方军阀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中国陷入了长期的纷争和战争。梁启超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实力和势力实现他的宪政理想,而他的愿望在袁世凯不断膨胀的权力欲望面前碰得粉碎,以至于他与蔡锷不得不在袁世凯宣布登基做皇帝之后举兵反袁,尽管他们一再声明此举为不得已,但实际上他们已卷入了自己一贯反对并努力避免的杀戮无度的军阀政治之中。
中华民国政府至少有十六年的时间来创建一个民主、自由、健康、有序的宪政制度,这也是梁启超始终为之努力的,尽管他在1917年府院之争后已从政治领域退守书斋,但他并未放弃与北洋政府的合作。直到二十年代初,他欧游回国之后,仍然对吴佩孚、孙传芳抱有很大希望,想通过联省自治、制定省宪、召开国民大会,来限制军阀的权力,促成民主政治,达到重建民族国家的目的。但此时已今非昔比,如果说民国前十年没有给梁启超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民国的第二个十年,已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军阀之间无休止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且不论,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则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梁启超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带来了新的希望,孙中山在绝望之中决心“以俄为师”,更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范畴之中。随着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中国革命获得了新的生机,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旧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均被动摇,革命风暴从城市向农村迅速蔓延,而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运动乘势而起,国民党对整个局势的控制已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毛泽东当时就曾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四卷本,12 ~ 13页)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并且发展为一种以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圭臬的更加广泛的社会冲突,梁启超以宪政为核心建立民主自由新国家的理想终成泡影。
重新认识梁启超
对梁启超的重新认识和发现应该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甚或九十年代,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梁启超的重要性以及他的政治、文化遗产才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谈论,所肯定。龙应台在2000年将要来临的时候写道:“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的重复?”(《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序,6页)她把第一次阅读《论不变法之害》的情形形容为“惊心动魄”,在她看来,梁启超这篇文章“所碰撞的几个问题正好是一百年以后中国知识界最关切的大问题之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让她大为感叹的是,“梁启超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所勾勒出来的难道不就是我们转进二十一世纪的此刻所面对的现代化以至于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吗”?(同上,10 ~ 11页)
龙应台对梁启超的阅读感受应该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发生在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从她所回顾的戊戌百年,到今年的辛亥百年,又过去了十几年,中国知识界最关切的问题,应该说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国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乃至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也即民主化。这些都没有超出梁启超政治遗产和文化学术遗产的范围。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承前启后的“新道统”或“新学统”,其主链即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或者还可以增加晚年陈独秀,在台湾还有殷海光和雷震,他们一代又一代一波又一波所不断追求的,归纳起来就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梁启超是将这些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也是其权威阐释者。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基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根本区别,前者所倡导的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后者所要建立的却是同化了各少数民族的单一大汉族国家。再看梁启超的民主主义,是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其思想底线,主张民权即国权,民权不能伸张,国权亦无从伸张。而孙中山晚年诠释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受到抨击,民权主义则受到“先知先觉”论、“国民资格”论的阉割,国民资格的获得必须以接受国民党训政并宣誓效忠党义为前提条件,于是,民国变成了党国,这真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不幸!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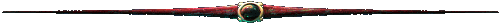
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书由“怅望祁连”免费制作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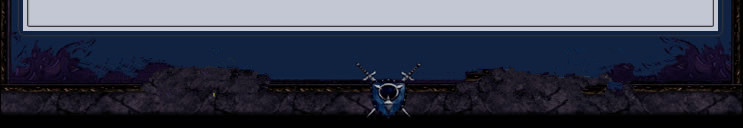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