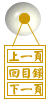一
于文光推开公司那扇铜把手的大玻璃门,坐进自己那部橄榄绿色的“摩瑞斯”
牌小轿车里,轻轻地发动了马达,方向盘略微向左一打,就开上了那宽平整齐的四线马路。
天气不错!不像是腊月天。
“还有三天就过旧历年了。”于文光对自己说,“这天气,倒有点像阳春二月。”
街上人车熙熙攘攘,比往常格外显得热闹而匆忙,大家都在忙过年。
他在红灯前面停下来,心里盘算着,前两天给读大一的儿子维立买的那件“开司米”大衣,说不定是太厚了一点。该另给他买件短的上装。万一过两天,天还这么暖,厚大衣就穿不着了。
想到维立,于文光就从心底浮上来微笑。这孩子,实在太好了!又用功,又聪明,身体又好,样子又英俊。见到维立的人,没有一个不夸奖。
“人生为的就是这点乐趣啊!”于文光欣慰地想。
维立的母亲去世得早,为了这个孩子,于文光没有再娶。男人抚养孩子可不容易!但是,一切也终于都过来了!
于文光是坚强的。
岂止坚强!他这一生,简直就没有一件事不成功的!二十年来,他为自己的前途,处处都是做着“抢摊”式的战斗。用赴汤蹈火、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在奋战的。
他知道,一生成败就看那身强力壮的几年,和是否善用了那股无视一切的冲力!他是认真在生活的。他没有浪费过一点岁月。真的没有!
他满意地看了看自己这部崭新的小轿车,挡风玻璃前,悬着一个绸做的小鸟,摇曳着。
要论在商场上看风色,那是要属于文光了!
他赚的钱,已经足够他好好地享受生活!
绿灯亮了。他把车子滑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决定到前面的百货公司停一下,给维立把前几天就看中的那件上装买回来。
“顺便买点精致的糖果和点心,给维立留着。”他想,总觉得维立还是个孩子。
维立在台中的大学里住读。放了寒假,该回来过年了。
“要是他母亲在世,看见孩子长得这样大了,不知该怎样高兴!她又是个勤快的女人,快过年了,为了让儿子过个快乐的年,她不知要忙成什么样子!”
想到那去世已经十一年的妻子,于文光有点黯然。妻真是一个好女人!那时候,自己没家没业,她却勇敢地嫁给他。
“苦日子可没少过啊!”于文光感慨地想,看了看把着方向盘的手。
那手上有一枚旧了的金指环。这指环,是他刚出来做事的那一年,省吃俭用积下来的,以后,战事逼近,就一直不再有余钱可以积蓄。
结婚的时候,他就用的是这枚指环,把它套在新娘的手指上。
那时,为买不起较好的戒指而惭愧,但新娘却是那样认真地把它戴在手上,片刻不离。直到她去世之后,他才把它从她手指上摘下来,戴在自己的手上,纪念他和她的爱情,也纪念他们所曾共尝过的艰苦岁月。
虽然现在他早已有条件买任何高贵的货色,但他却从来不打算再去买一枚真正贵重的戒指,来点缀他的豪华。
于文光对自己笑笑,把车子打向路边,停下来。
他抬头看了看百货公司的橱窗,前几天看中的那件短大衣还在。
“式样不错。质料也好。”他想,“虽然价钱贵一点,但是很值得,维立一定喜欢的。”
他下了车,走进了百货公司。
从那个年轻的店员手里接过那件短大衣,他对那店员说:
“这是给我的孩子买的,他现在比我还高了!”
他抬手比了比自己的头顶。
近来,每逢说到孩子比他还高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脸上流露着光彩。
店员奉迎地笑着:“您好福气!”
他笑了,说:“他在台中读大学,快回来了,回来过年。”
他买了那件短大衣。付了钱,往外走的时候,临时又回身走到二楼,买了一副围棋。
“维立的棋下得不错,过年没事,爷儿俩可以下棋消遣!”
二
于是,就到了旧历的大除夕。
于文光上午到公司去了一趟,回来之后,整个的下午,就都在家里和佣人老张忙着布置。
其实,家里整齐考究。所要下功夫的,无非是那些零星的点缀。
瓶子里的花和盆景,都是花店包办的。他自己特别又选了一盆水仙,点缀年景。
他又打电话叫这附近惟一的一家代卖原版唱片的电机行,送来几张古典音乐唱片。他选了一张《胡桃夹子组曲》,一张《天方夜谭》,维立曾说,他喜欢这些音乐中的东方风味。
孩子长大了,兴趣随着年龄在变。高中的时候,他喜欢西部歌曲和热门音乐。
上了大学,忽然热衷古典音乐起来。圣诞节的时候,他还为维立买了一套《弥赛亚》,这些,够维立在过年的时候欣赏的了!
维立从台中搭对号快车,9点多钟可以到台北。他要等维立回来一同吃饭。年夜饭是要合家团圆,一同吃的。
天已经黑下来好一阵子。
于文光关掉了收音机里的音乐,从袖木沙发上站起来,踱到落地窗前去,想看看天色。
落地窗的纱帘挡住了外面的星空,只见远远的霓虹灯在闪烁。
纱帘很考究,软软地垂着。近来,不知怎的,每看到这软软的纱帘,他就有一种辛福和安适的感觉。他喜欢他一手经营的这个家,而且越来越喜欢。
每当夜色深晚,他在驾车回来的途中,都时常会涌起这样一缕幸福温馨之感。
他是有家可归的。
回想这大半生,他流浪过、飘泊过、到处为家过;那时候,他倒从未觉得凄惶。
而近来,他却时常无缘无故地回想起那时候逐水浮萍般的岁月,而觉得有家是一种幸运。
他不但为自己觉得幸运,也为维立觉得幸运。他为维立安排了一切,只等他回来,过了一个快乐温暖的年。
他回过身来,踱到酒柜旁边去看那架镀金的德国制的小座钟。
9点15分。一点也没有错。事实上,他本用看就知道。从天黑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在看钟,不知看过多少次了。
老张轻手轻脚地在餐厅那边走着。于文光知道,老张一定早已按照他的意思,把那一排六个的铜烛台擦得雪亮,上面插好了红蜡烛,摆在餐桌的一角。
虽然天气并不太冷,他也仍然吩咐老张,在壁炉里升上了火。这样才有过年的情调。
维立大概马上就要到家了!
于文光想着,浮上了微笑。
他又在厅里踱了一圈,地毯是一位商界的朋友送的,是本地出品最好的那一种。
很厚,很密,上面织着桃花的图案。他说,他喜欢看这些桃花,红得那么娇嫩,那么年轻,而又那么使他想起自己小的时候。
他低着头,在地毯边缘那一排“二方连续”的桃叶图案上走着。
小时候,过完年,就是春天了,桃花总是第一个报告着春的消息的。
那时候的春天,怎么那么可爱呢?好久不想到小时候的事了!大概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忽然格外怀念起自己的童年吧。
他抬起头,看见老张已经把碗筷摆好,他走到餐桌旁,欣赏着那汕头抽纱的台布和成套的餐具,高兴地对老张说:
“把万经理送的那一套瓷的酒壶和酒杯拿出来!今天要喝一点酒。”
老张答应着,走了两步,又回过身来问:“今天喝什么酒?白兰地?”
“过年怎么喝洋酒?今天喝绍兴,要烫过的!”
老张答应着下去了。
门铃忽然响起来。
于文光不等老张出去,自己抢着跑去开门。
维立回来了!
于文光高兴地看着维立,这孩子,仿佛又长高了。
“爸!您好!我回来了!”维立的声音里充满着青年人的兴奋与活力。他的脸上,即使在夜色里,也透着光辉。尤其是那一双眼睛,又黑又亮,从里到外地灌注着精神。
“我在等你!冷不冷?”于文光问着。
维立一面笑着口答说:“怎么会冷?这个天气,怎么会冷?”一面往里走着。
他的脚步又长又快。手里提着一个旅行箱,仿佛没有提什么东西似的。显得那么轻便。
“我说开车子去接你,老张说,你一定和很多同学在一起,不肯自己坐车,我就没去。”
“可不是?”维立答,“何必接我?我们好几个同学一起回来的。大家挤公共汽车,说说笑笑的,才热闹。”
于文光听着维立那快乐的声音,看着维立那和自己一样高大的身材,笑着,和维立一同走进了客厅。
“好暖!”于维立把旅行箱交给老张,开始脱他自己的夹克,“这么暖的天气,还升火!”
“过年嘛!要升个火,才够意思!”
维立笑了,说:“爸爸您真是……”
于文光也笑着,望着儿子走进盥洗间去洗脸,又望着儿子容光焕发地走出来。
他说:
“维立!你来看!这套酒杯漂亮不漂亮!这花纹好古雅!”
维立走过来看了看,说:“嗯!真不错!”
“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要喝点滴!我特别教老张做了几色别致的菜,北方口味的。有栗子鸡,冬菜鸭,还有水晶肘子……咱爷儿两个慢慢地吃!”
维立愕然地抬头看着父亲,说:“您还没有吃饭?”
“我在等你!”于文光说。
“可是,我已经吃过了!”
“你吃过了?”
维立带着一点歉疚,说:“我和同学在火车上吃的。”
“你……”于文光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停了一会儿,才说:“你不知道今天过年?”
维立看了看父亲,笑道:“我知道!所以我赶着跑回来看看您。本来,我和同学们商量好了,明天一大早,直接从台中去横贯公路看雪。我说,我要先口来一下,还有几个同学也要先回一趟家,我们就一起回来了。明天一早再去。”
“明天又回台中?”于文光觉得自己生气起来,“那么,你何必回来?你就住在台中算了?何必要回来?”
“我回来看看您。”维立平静地说,“而且,台北还有些以前中学的同学也参加,所以我们决定买一家游览车的票,从台北出发,大家一起去,人多一点,才更热闹。今天晚上,我们十几个人,在同学家里有个聚会,大家通宵谈天。同学们好久不见,见了面,一定好开心!”
于文光愕然地看着维立问:“你说,你今天晚上要去同学家?”
“是的!我们在放假以前,就写信约好了!”维立说,“有王大夏、吕润德、方卫尧、郑家振、郭仲洁,还有……”
于文光看着儿子那一团高兴的样子,忍着自己要说的话,回身走到壁炉旁边去,停了一会儿,才说:“我一直在等你吃饭。”
“真对不起!爸爸!”维立歉疚地说,“我该在信里告诉您的。我也没有想到您会等我吃饭。”
于文光沉默着,背着手,注视壁炉中燃烧着的木柴。
维生看了看表,回头对老张说:
“老张,给我父亲开饭吧!时间太晚了。”
维立吩咐着老张,走到父亲身旁,学着父亲的样子,注视着壁炉里那熊熊的火光。
注视了一会儿,维立忽然说:
“爸爸!我陪您喝点酒好了。”
“不必了,”于文光说,“我自己喝也一样。”
维立看了看父亲,问道:
“真的不要我陪?”
“嗯”
维立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您最反对过年。”
于文光怔了怔,抬头问道:
“维立,你说什么?”
“我说,我小的时候,您不是常常抱怨妈妈不会享受生活?说她花了许多的钱,闷在家里,忙得昏天黑地,只为了过年。您说,有那些钱,为什么不出去旅行几天?
又开心,又有益健康!”
于文光看看维立,道:“我那样说?”
“当然!您怎么忘了?”
“年头太多了!”于文光说,“我不知道自己那时候是怎样想的!”
“不只是那时候。”维立说,“就是后来这些年,您也是不在乎过年的。在我记忆中,每年过年,您都是在外面的时候多,在家的时候少。”
“哦!”于文光摸摸自己的下颏,说,“那是因为业务的关系。我不得不耽在外地。”
“所以,您是创事业的人。”维生说,“我一向最佩服您的见解和生活态度。
我常常为我有您这样一位开明的父亲而骄傲。您不是那种守旧的、迂腐的人。您是创事业的,只有像您这样的人,才是创事业的!您的想法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所以,您比别人成功得快。”
于文光看看维立,说:
“你今天是怎么了?满脑子都是‘事业’和‘成功!”
维立笑了。带着一点青年人的羞涩,说:
“也许是因为刚做了大学生的缘故吧?您不知道,我们这一伙人把自己估价得多么高!今天我们一定是通宵都要谈理想和事业。虽然,我们开自己的玩笑说,那些都是吹牛。可是,吹牛是开心的事!是不是?爸爸!我相信,您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的。是不是?”
文光转过身来。注视着维立,好一会儿,才说:
“或许是的,我现在好像记不清了。”
“您不用说,我也知道。”维立没有看父亲的脸,他的眼睛专心地注视着壁炉中那一跳一跳的火舌,“您不是那种喜欢‘谈当年勇’的人,您的眼光是向前的。”
维立真诚地说,又加上一句,“您是创事业的人。”
文光看着维立,随着维立的眼光,也去注视壁炉里的一跳一跳的火光,那细细的火舌在黑暗的炉壁前面闪着,不知怎的,看来却有一种孤单寂寞而又乏累的感觉。
似乎它的燃烧和照耀都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消耗和徒劳。
维生沉默了一会儿,看了看手表,说:
“爸爸!我陪您喝一杯酒再走,好不好?”
文光往餐桌旁走着,没有回答。
维立斟了一杯酒,递给父亲,又斟了一杯拿在自己手里,就那样站着,向父亲举杯,道:
“新年快乐!爸爸!”
文光也举了举杯,绍兴酒带着它特有的浓郁和暖香,在那紫红色蟠龙花纹的小酒杯里微微荡漾。
小酒杯是瓷质高脚,是西式的,而蟠龙花纹却是中式的。文光尝了尝那略带苦味的酒,抬头看看维立,释然地说:“你去吧!别让大家等你!”
维立高兴地答应着,放下酒杯,回身到衣架那里去拿茄克。
“我给你买了一件新的上装,你要不要试试?”文光问道。
“不要了!我们明天去爬山,不要穿新衣服!”
“可是——”于文光又想说,可是今天过年,但是,他咽住了。他知道,维立完全没有把“过年”放在心上。
正如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不把过年放在心上一样。
于是,他看着维立拿了一些登山用的装备,走了。
三
于文光草草吃了几口饭菜,就放下了碗筷。这顿年夜饭吃得食不甘味!
早知维立要到同学家去参加什么“谈天通宵”的聚会,他就该答应万经理的邀约,去搓通宵麻将了!
而那时,他满心高兴地告诉人家:“我又不是单身汉!我儿子要回来过年!”
现在,他倒真有点“单身汉”的感觉。
“时间才10点半钟,做什么呢?”
“不如出去逛逛去!”于文光对自己说着,穿上外衣,坐进自己的车子。
马路上好静!从来也没有这么静过。除夕夜的10点半,店铺早就打烊,只有少数卖杂货的小店开着。
也没有什么行人。人们都回家过年去了!
平常开车,总是嫌路上人多拥挤。今天,他却嫌路上太空旷了。
“过年,应该热闹才对,而到处却都这么冷静!”
他不甘愿地望着,把车子拐了一个弯,开上了中华路。
中华商场也不再那么熙熙攘攘,马路倏然一下子显得宽多了!
他一段一段地开过了那排由违章建筑改建的大楼,霓虹灯管织成的广告在夜空下一闪一闪地向他唠叨着,“旭光牌,日光灯,”“国际牌,电视机,”“黑人牙膏”!
“高处不胜寒啊!”他想,同情起那些霓虹灯来。
于是,他来到了戏院。他把车子停在路旁,走上戏院的石阶。
晚场电影已经开演很久了。不知有几个观众。戏院门口一片萧条。
他茫然地在那里站了站,他知道自己并不想来看电影的。虽然他知道,今天的电影院里,一定有不少流浪汉,买一张票,跟着银幕上的幻景去喜怒哀乐一番,消磨年夜。他可不是那样的人。他从来不“杀时间”的!他一向是分秒必争,时间是宝贵的。他从未觉得生活空虚,时间难挨过。
他出来的时候,忘了带香烟,他停车下来,是想买一包香烟的。
但是,摆香烟摊的已经走了。
他四下里望着,只有一个卖茶叶蛋的老人,坐在小凳子上数钱。老人把一叠破烂的钞票,小心地折叠整齐,拉开茶叶蛋挑子下面的小抽屉,把钱放了进去。
这个老人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袍,脚上穿着皮鞋,皮鞋和棉施不大相称,正如这老人的相貌和他的职业不大相称一样,他相貌清秀,皱纹和风尘也没有完全掩去他不俗的仪表。
除夕夜还出来卖茶叶蛋?于文光对这老人升起一股突然的怜悯。
“他一定没有儿子!”于文光想,“否则,就轮不到他出来卖茶叶蛋,养活自己。”
“也许他有儿子。”于文光否定着自己,“而他的儿子为自己的前途,去外面创事业去了。于是,剩下他自己,在这风烛残年,靠卖茶叶蛋来维持生活。”
“就正如我在20多年前,离开老家,到外面来闯荡是一样的!”于文光想。
“那时候,好像也是过年?……哦!是腊月二十八。我大学还未毕业。那时候,正在抗战,同学拉我一同到后方去,我们已经计划了好久好久,于是,就那样,我们就去了!为了怕给敌人知道,怕被父亲阻拦,事先连一点消息都没敢给家里知道!”
“那时候——”于文光想,“真是就仗着年轻,什么也不多想。不管家里过年的时候找不到我,会怎样惊慌、伤心和焦急!”
“尤其是父亲。”于文光想,“父亲那时候四十多,将近五十的人了!他老人家是最疼我的!那时候,镇上已经很萧条,他老人家典房子卖地,供我上大学的!”
“做父亲的人们,大概总是寂寞伤心的!”于文光对自己说。又跟着就更正自己道:“应该说,做儿子的人们,大概总是不懂关心父亲的心情的!”
“父亲假如还在世,也七十多了!不知他怎么维持生活!”
于文光黯然地看了看那个卖茶叶蛋的老人。突然,一种没来由的激动,他走向前去,对老人说:“你这一堆茶叶蛋,一共卖多少钱?”
老人愕然望望他,说:
“你要买几个?”
“我说,一共多少钱?”
“哦!”老人仰起头来,认真地算着,“连煤火带作料,加上功夫,本钱就要八九十块,赚不了多少钱的!”
他点了点头,把钱夹打开,抽出4张100元,递给老人,说:
“都卖给我吧!”
“你要这么多?”老人疑惑地说。
“是的!带回去过年。”他说。
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从旁边找出一只篮子,说:
“幸亏刚才卖水果的送我一只篮子,可以装得下这些茶叶蛋。”老人把茶叶蛋装满了一篮,递给于文光。接过钱来数了数。
“不要这么多钱!”老人说。
“多的给你过年吧!”
于文光说着,接过那篮茶叶蛋,提在手上,沉甸甸的。
老人看着他,张大了他干瘪的嘴,眼睛里流露着惊疑和感激。
“回去过年吧!大家都在过年!”于文光说。
老人朝他点着头,“嗬嗬”地笑着,“先生!你也该回去过年!”
于文光怔了怔,点点头,说:“是的!我也要回去,回去过年。”
于文光提着那篮茶叶蛋,走到他橄榄绿色的小轿车旁边,想了想,打开车尾的行李箱,把那篮茶叶蛋放进去,然后坐进了车子。
“到哪里去呢?”他偏在方向盘上,望向都市的夜空。霓虹灯意兴阑珊地闪着。
“国际牌、电视机。”
“罗、邦、药、水。”
“硫、克、肝。”
它们闪给什么人看呢?街上人这么少?
闪给那些在电影院过年的人看。
闪给俯在方向盘上,而不能决定去哪一方向的人看。
问给卖茶叶蛋的老人看。
卖茶叶蛋的老人,今天算是做了一笔好生意。
好生意也抵销不了年夜的寂寞,假如他没有儿子的话。或者说,假如他儿子舍弃了他,而独自去远方创事业的话。
人上了年纪,就会害怕寂寞。
真是怪事!维立的话他在耳边响:“我小时候,您最反对过年。……花了许多钱,闷在家里,忙得昏天黑地。有那些钱,为什么不出去旅行几天……您不是那种守旧的、迂腐的人。您是创事业的……您是走在时代前面的……”
“走在时代前面的?”于文光俯在方向盘上,问着”自己。“也许是的!”
但是,他现在觉得自己好像那些孤悬在夜空的霓虹灯管。他是进步的、成功的、现代的、高高在上的!
然而,他宁愿自己是那些红红绿绿的爆竹纸屑,挤在地面上,热热闹闹的。
真是怪事!年轻的时候,老是向往着远远的天边。而现在,他总觉得脚下的地面才是温暖、安适和亲切。
“老了!”他叹了一口气,抬头挪动了一下近光镜。镜子里照见自己星霜微布的双鬓,和标示着岁月的鱼纹。
“老了!”他又叹了一口气。把返光镜移开,照向车子后面的夜街,脚上一着力,发动了马达。
回家去吧!
四
他真的在回家,在梦里。
梦里的年夜,大雪纷飞,好冷的天气!
仿佛那时候,他还在大学读书,赶回家去过年。
火车在白茫茫的平原上奔驰。
天是黑的,地是白的。雪片如鹅毛,扑向车窗。车窗紧紧密密地关着,雪就一层一层地积在那方形的窗棂上。
夜色如墨,车站玻璃上是水汽和积雪。车里的暖气不停地在被寒冷抵销,上升,又抵销。他把双脚放在那靠近车壁的暖汽管上,双手笼在袖子里。
“冷啊!过年是应该冷的。而且是应该下雪的,‘瑞雪兆丰年’啊!父亲一定又在呵着冻手,欣慰地笑哪!”
父亲在等他过年!他要赶回去,陪陪父亲,父亲晚景寂寞啊!
快吧!火车!快吧!
火车的汽笛在风雪中长鸣。那鸣声怎么那样凄凉呢?他在回家啊!
火车进站了!那“皇皇”的声音加大,速度慢下来了。
他站起身子,抬手拿下他的旅行箱,下车。
小站上,一片白茫茫。
站上的灯,还是那四面玻璃的老式煤气灯。收票员穿着黑色的棉制服,在寒风里收票。他是大表舅家的三表哥。
小地方,谁和谁都沾着亲戚。于是,他招呼着:
“你不是三表哥吗?你好啊?”
收票员抬眼看了看他,脸上没有表情。他怔了怔,难道他认错人了?不是三表哥!要不就是三表哥忘记他了。
疑惑着,出了车站,踩着大道上那半尺深的雪,于文光往镇上跑。
大道旁牌坊上顶着雪。
下雪最好,要不然,手里没有灯,就别想走路。大年三十,是没有月亮的。
是顺风,冬天下了火车,总是顺风的,他跑着,跑得比风还快。
进了南街,穿过中街,就到了北街。街上好静,不像是过年。
他恍惚想起,自己已经好多年没回来了,难怪这里一切都变了样子。从前过年的时候,他一回来,就看见家家户户都悬着灯,大门上贴着鲜红的春联。大门敞着,孩子们跑出跑进地放爆竹。他寻觅着,不知怎的,仿佛连自己家是哪一个大门都不记得了。
他慢下来,一家一家地辨认着,他知道,每年过年,父亲总是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的春联贴在大门上的。他家是坐北朝南的房子。
找不到那春联,却看见那里有一家黑色的大门虚掩着。他试探着推门进去,门洞里却点着一个“富贵吉祥”的风灯。他往旁边南屋里看了看,只见父亲佝偻着身子,在那八仙桌旁写“福”字。
他激动地站在父亲背后,强忍着欢喜的眼泪,他轻轻地说:
“写得真好!笔酣墨饱!”
老人家颤巍巍地回过身来,看着他,笑出一脸的皱纹。一面说:
“我就知道,你会赶回来过年的!我在等着你!”
他心里激动着,真想流泪,不知哪里来的眼泪。好像自己真是多少年没回家了似的,又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父亲的事似的。
“门上连春联都没贴,”老人家说,“等着你回来写哪!”
“我来写!”他答应着,放下小箱,呵着冻手,接过父亲手中的笔。写那每年都要贴的春联。
父亲把手揣在棉袖子里,在旁边看着他写。
他把笔在墨里蘸着,心里却搜索着那久已淡忘了的春联字句。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
他是记得的。还有呢?
仿佛门框上贴的是:
“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样”。
他看了看父亲,写下这两幅春联。
父亲在旁边笑着,回身去点他的旱烟。那烟草的气味在寒冷的空气里氤氲着。
那熟悉的气味使他想起了那古老的四合院的门楣上贴的那些古意盎然的“横批”。
“西园翰墨”,贴在西屋的。
“东壁图书”,贴在东屋的。
“上房贴什么呢?”他抬起头来问着父亲,“写‘三阳开泰’,还是写‘竹报平安’?”
父亲笑微微地望着他,想了想,拍着他的肩膀说:“今年写个别致的。”
“写什么呢?”他蘸着笔。
“写呀!写‘子孝孙贤’!”父亲说。
“子孝孙贤?”他疑惑地问。
“我年纪老了!心里不想别的,只愿合家团聚,享享天伦之乐!你写吧!”父亲哈哈地笑着。
他也笑着,把那“子孝孙贤”的横批拿起来,打算贴到上房的门楣上去。
也好像找了好久,才找到上房。
登着梯子爬上去,不知怎的,他却觉得上房好像是洋式的落地窗。他拿着“子孝孙贤”的红纸春联,在那横木上找来找去,总觉地位不合适。
是春联太宽了?还是横楣太窄了?
怎么贴,怎么不对劲。
那些贴着剪纸窗花的纸自呢?那阴阳瓦的房檐呢?
他在什么地方啊?
他觉得自己悬在空中,那梯子好像太高,太软,他站不稳,悠悠忽忽地往下倒。
哦!他在船上。他怎么会在船上呢?他倒下来了!
下面是海。
他拿着“子孝孙贤”的红纸春联,在海上浮沉着,一个浪头打来,那红纸春联就被冲走了!
他泅着水,伸手想去抓住那红纸,但海浪在把他向前推,那红纸在水中转了几转,就漂远了!
他挣扎着,海浪把他推拥着。
于是,他听见有人在他耳边说:
“潮流是向前,你抓不住过去的东西!”
他醒来了!
丽日当窗,昨晚他回来了后,合衣睡在床上,床边的收音机没有关。
播音员在播一节励志的插播:
“潮流是向前的,既然你无法抓回过去,那么,你还是继续向前吧!”
他释然地坐起来,自己身上盖着一条薄毯。这天气盖薄毯都嫌太热了呢!他推开薄毯,下了床,开始做他例行的健身操。
“要好好保养自己才行!”他对自己说,“这是个奋斗到底的时代。你要让自己一直年轻下去!否则,你就会被寂寞打垮!”
“而且,你要抓稳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你不能属于上一代,你的下一代也无法属于你!”
他拿起电话,拨给塑胶公司的卢经理。
“喂!老卢是吧?打高尔夫球去,好不好?今天大年初一,好晴的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