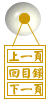一
每当我静下来,看着我国子里那片绿绿的草地和随处生长的小花时,我就想到多年前那个艳丽的女孩。那时我在×市一家广播电台做事,她时常在我节目完了之后去找我,或打电话给我。
她找我,并没有事情。打电话,也并没有事情。她说,只是想看看我,或听听我的声音。
我很忙,但是无论我怎样忙,我也仍尽量耽搁半小时,陪她坐一会儿,看着她,听她那简短而没有目的的话。
她说,她今年16岁了。她有着圆圆的漂亮的脸,黑黑长长的眉,浓密的头发,红红丰腴的嘴唇,和挂在唇边的那一抹淡淡的笑。
她很少抬起眼睛看人,而总是低垂着眼睑,让人看见她有力的睫毛。
我们的对话,多半是这样的。
“你来了?”
“刚来。”
“你好吧?”
“还好。”
“今天怎么样?”
“不怎么样!”
“有什么事吗?”
“没有。”
我找不出话来问她了。
于是,我们对坐着,我打量她,她低垂着眼睑,总是像在思索什么。偶尔才瞥我一眼,那乌黑的眼瞳实在太美,难怪她总把它隐藏在深浓的睫毛背后。
有好几回,她会突然对我说:
“我去看医生了。”
“哦?有什么病?”
后来,我就成了明知故问。
因为她总是告诉我,她的头发在脱落,或她的眉毛在掉
“我在生这种病,担心很快的我的头发和眉毛就掉光了。”
“不会的,每个人都有时会掉掉毛发;那是很自然的。”我说。
“不对,我不同。”
她很肯定。
我本来也不是医生,于是,我妥协下来。
然而,半年来,她的头发和眉毛还是那样乌黑浓密。
这次,她又来了。眉毛上涂着一点药膏。
“医生给我的。”她说。
“医生怎么说?”
“没怎么说。”
总是这样,她好像有意封锁我的问话似的。
我们沉默着。
我看着她粉白透红的圆脸,和那两道很长很密的眉毛,以及眉毛下面那两道朝上弯的眼睛的弧,宽宽的直鼻梁下面丰满的宽宽的嘴唇,微微地抿着,总像在抑制着她内心里随时都要迸发的那轻蔑的笑。
起初,我真以为她对我并不友好,就因为她嘴角那一抹抹不去的轻蔑。
但是,她那样喜欢见我,放下一切事情,不管风天雨夜,老远的从郊区的家,跑来找我,使我相信,她对我有一份我所不大了解的真诚。
这天,她就又一如往常的,那么默然地坐着,低垂着眼皮。
我不能总让空气这样冻僵着,于是,我找话来说。我说:
“今天听我的节目没有?”
“听了。”她瞥一眼我发音室的门。
“音乐喜欢吗?”
“很好。”
“你喜欢哪一类的音乐?”
“不一定。
“小提琴。”
“嗯。”笑意浓了一下,就抿去了!
我又感到无话可说。
半个钟头就这样过去。
我看了看表,说:
“太晚了,你该回去。”
“没有关系!”
“你妈会不放心。”
“她不管我。”她说。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只好暂时放弃了让她回家的打算,我问:
“为什么你妈不管你?”
“不知道。”
每次我想要明白她究竟有什么困难时,都是这样触礁。这次,我却多问了一句:
“你妈不喜欢你?”
“谁知道!”
“你家都有什么人?”
“爸爸妈……”
“还有呢?”
她停住了不答。
“没有别人了?”
她放弃了谈话,站起来,说:
“我要走了。”
刚才是我催她回去,这回我倒不便留她。
于是,我困惑地站起来,对她说:
“路上小心,天太晚了,以后不要时常往外跑。”
她没有说话。低着头往外走。
临下台阶的时候,她站定了脚步,垂着眼睑,说:
“我礼拜三来找你。”
于是,她回身走了。
天在下着小雨。
她慢慢地消失在黑暗里,怪凄凉的样子。
二
她时常来,我和电台的同事也习惯了她的来访。
慢慢的,我知道了她叫蓝费。她说,这名字不是她原来的名字。原来的名字是她母亲取的,她不喜欢要,自己翻字典,找出这个“葹”字来做名字。姓蓝倒是真的。
我问她,为什么要叫“葹?”
她说,她也不知道。
我说,总得有点缘故。
她说,也许因为这个字上有一个草字头。
蓝葹很聪明,只是不喜欢说话,有一天,她拿了一篇文章来给我看,说是她写的。写一只流浪的蝴蝶,最后给人捉去,夹在书本里的一个故事,很像一首诗。
她应该是上高中的年龄,但是,她并没有上学,她说,她身体不好。但我看不出来她有什么病。
看她穿的衣服,我相信她家里情形不坏。
不知她为什么不喜欢她的家?
三
这天晚上,又在下雨。
出了发音室,就又见蓝葹脸向外,站在走廊上。
“蓝葹,你来了!”
“刚来。”她说,移动她的脚步,走进了会客室。
习惯了她的沉默,我就也不再打算问她什么。
坐在那里,我写当天的播音记录表。
雨在外面哗哗地落着,春天的雨,显得很闹似的。
忽然,她叫了我一声:
“罗兰。”
“嗯?”我停止了写字,抬头应她。
她并没有看我,眼皮垂着,低低地说。
“你会不会有一天,不做这节目了?”
“当然会的。”
“为什么?”
“我总不能一辈子都能工作,我会老,电台会变更节目
“假如你不做这工作了,你去做什么呢?”
“哦!也许——”我想了想说,“也许我只好写写文章,或画点图画什么的!”
“那你还觉得生命有意义吗?”
“也许比现在差一点,不过,人总要活下去的,不管有没有意义,是不是?”
“我恐怕不是的。”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意义,他会去自杀的。”
我愕然地望着她。
她没有看我,自顾说道:
“我们家有好几个人都自杀。”她停了停,说。“好可怕!”我注意地看着,她的脸色苍白。
“不是吧?你说的不是真的吧?”
“是真的!我外祖父,我哥哥……”
“他们都死了吗?”
“有的死了!我叔叔没有,他被救了!”
“他们为什么要自杀?”
“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我想也许,他们是觉得生命缺少意义。”
“即使缺少意义,也不必去自杀的。”我说。
她抬眼看看我,露出她的眼眸,那眼眸,深黑如月夜潭水。但只是那么一瞬,她就又低垂下她浓密的睫毛,她说:
“每个人看事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反而没话可说了。
她沉默着坐了一会儿,忽然说:
“你能不能陪我出去走走?”
我说:“好吧!但是不能太晚,我陪你走到公路局车站,你回家。”
“你不喜欢和我在一起?”
“不是。”我说,“我怕你家里不放心。”
她抿着嘴笑笑,说:“也许有一天,他们会不放心,但不是现在。”
我们冒着雨,穿过夜街。她的花雨衣在雨帘里,在灯影里,我想到她笔下的那只流浪的蝴蝶。
四
我不大敢对她付出太多的友情,不是我吝啬,而是我不愿让她因为找我而时常迟归。当我发现我无法使她了解的时候,我只得说谎,当我接她电话时,我说,我必须早点回去,我有事。请她给我写信。
她写了信,她说:
“我知道你骗我,但你是善意,所以,我不怪你。我下星期一再来。”
五
下星期一,她并没有来,我只好回家。上了公共汽车,后面座位上有人拉了我一下,说:“这个位子给你。”我一看,原来是蓝葹。
“你怎么坐这班车?”我问。
她垂着眼睑笑笑,说:“你坐这个位子吧!”
“你到哪里去?”总是我在找话说似的。
“到前面。”
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在她让给我的位子上坐下去。
她左手抱着一叠书,右手拉着车子的皮套,白净丰腴的圆脸上,有三道弧。两道是眼睛,一道是嘴唇。她的黑发浓密闪亮,如锦锻,柔柔地覆盖住她浓密的眉毛。
我说:“蓝葹,你真像一幅画。”
她的黑眸往眼角一转,斜斜地扫我一瞥,又马上收回去,简短地说:
“真的?”
“我要找个朋友,把你画下来。”
“真的?”她还是那个表情,把黑眸隐藏在浓密的睫毛背后。
车子的声音很响,我没有再说话。我在桥畔那站下车,她也跟着我下车。
我忽然明白,她原说今天要来找我的。
以后,她就常常在公共汽车上等我,她知道我搭哪一班的车。有时天很冷,她也不在意。在寒风刺骨的夜里,我都有瑟缩之感,她却一直都是那么坦然地和我一同下了车,慢慢地在我身旁走着。有时,我实在不好意思就那样直接回家,而把她孤零零地扔在寒夜里,所以,我请她到附近的小吃店坐坐,叫一碗汤圆或馄饨,她经常只喝一点汤,就那样和我坐一会儿,我再把她送到车站,然后才回家。
有一天,她忽然叫我:“你不是说,想找人把我画下来。”
我说:“我一直这样想。”
“你去找吧!我希望看看我像什么样子。”
于是,我找来画家陈星。
“不要告诉他我是谁。”蓝布说。
“当然。”我说,“这一点,你不必担心。”
陈星画的画很快,他的画有一种朦胧缥缈的风格,他画的是蓝葹的半侧脸。漂亮的圆脸,黑缎般的浓发,有力的睫毛,隐藏的黑眸,嘲讽的嘴。
蓝葹看了,只笑笑说:
“哦!这就是我!”
“你要不要带回家去?”我问。
“送你好了。”她淡淡地说。
“你不要?”
她把眼光停留在那幅画像上,说:
“我也许可以自己画一张试试。”
“你也会画?”我问。
陈星在旁边听了,鼓励地说道:
“每个人都会画的,你不妨试试。”
蓝葹没有看陈星,淡淡地说:
“我画过。”
六
有好一阵没见蓝葹。雨季过去,春天就来了。
这天,收到蓝葹的信,她简短地写道:
“到我家里来一下好不好?我请你吃点心。
时间:星期六下午4点。
地址:第六区××路×号。”
不知为什么,我很想看看她,于是,我去了。
第六区是在×市的郊外,×路×号是一所医院。门口挂着蓝医院的牌子。但不像一般的医院,这所医院完全是住宅的模样。小小的院落,种着花木,日式的平房,前面一间是地板,其余则是“塌塌米”。
“请先挂号。”那个坐在药局里面的少年说。
一我不是来看病,”我解释道,“我是来这里找一位蓝葹小姐。”
“蓝葹?”少年疑惑地说,“没有人叫蓝葹。”
“她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我形容道,“圆圆脸,长得很美,她请我来的,说她住在这里。”我出示蓝葹的信给他看。
他看了看,猛省地笑笑说:
“哦!我知道了,她不叫蓝葹,她叫彩儿。你进来吧!”
我疑惑地跟着他往里走,经过那深深暗暗的走廓,他带我迈下这正面的房子,下了石阶,来到后院,往右一拐,见还有两间小小的房舍。纸窗木门,沿墙种着芭蕉。
少年把木门拉开一半,说:
“彩儿,有人找你。”
蓝葹从里面出来,说:“哦!你真来了。”
“你以为我不会来?”
“当然,”她抿抿嘴角,“我请的客人都不会来的。”
我看了看她。她一身家常打扮。春天里,她穿着一件浅蓝底子,粉红和鹅黄花朵的直筒宽腰身的洋装。胸前用丝带系着一个蓝色的蝴蝶结。浓浓的黑发比过去长了许多,垂在肩上,覆盖着脸颊的两侧,显得比平常瘦了些。
她看着那少年转身走回去,才笑笑说:
“让你知道我的真名。该死!”
“有什么关系?”我说,“彩儿不是很好听吗?”
“不好听也没有法子,爸妈给我的,我只得承受。”她说,侧过身子让我迈上那“榻榻米”的房间。
房间很小,只有4个“榻榻米”,外面是“玄关”,用一道纸门隔着。纸门上贴着许多浅粉红色的剪纸,很精细,剪的多是蝴蝶,也有些是花,或图案。
“是我剪的。”她说,“成天闲着,好无聊,只好剪纸。”
“剪得很好。”我说,“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民间艺术。”
她抿着嘴笑笑,说:
“什么事给你一说,就伟大。”
我也笑起来。今天的蓝葹比往常明朗些。
她让我坐在“榻榻米”上,面前有个矮几,上面摆着四个形状不同的日式小碗,那小碗,我很少见过。一个更青色的,是叶子形;一个紫红色的,是樱花形;还有两个黄色和绿色相间的,一个像船,一个则是方形。里面装着蜜饯、花生、小西点和糖。
“假如你不来,我就把它们喂蚂蚁。”她半真半假地说,“我妈说,我要请得到客人,那才是怪事。”
“为什么你请不到客人?”
“谁知道?大家都骗我。他们口头说来,其实他们心里不想来。所以,结果还是不来。人们拗不过自己的心的,是不是?”
我点着头,她的话真有道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想来。”她说,递给我一杯茶。
我倒任了怔,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替你说吧!”她不等我说话,就说,“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想来,对不对?”
我笑着,点了点头,说:
“也许可以这么说。”
她坐下来,低垂着眼睫,说:
“这样才证明你是真的想来,不是为敷衍我,或什么礼貌。人们只有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而做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
我惊愕地望着她,我说:
“彩儿!你不知道你有多聪明!你的话,简直是哲学。”
“哲学是什么?我不懂。”她说,拿起一粒花生剥着,“不过,你叫我彩儿,我倒很高兴。”
“应该高兴,那是你的名字。”
“不。以前我不喜欢它。在我认识自己以前,就被人强迫加在我头上,我觉得生气。”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他们生下来,就由父母命名。”
“所以,那是人的悲哀。”她说,“人们无权对自己先天的一切去决定取舍。
你喜欢,也得接受;你不喜欢,你也得接受。”
“所以,你早该喜欢彩儿这名字。”
“不,我一直不喜欢这名字,觉得它俗气。”她说,“直到你来做我的客人,并且叫我彩儿。”
“为什么呢?”
“因为这名字已经被我自己所选择的朋友认可。你使我知道,人们在不认识自己以前,所得到的东西,也可能变得有些意义。”
我有点不大了解地望着她。她抬眼看了看我,说:
“画了几张画。你要不要看?”
“当然要看。”我说,“我不知道你会画。”
“以前我只剪纸。家里的人个个烦我。现在我画画,他们可以减少扫除的麻烦。”
她一面说,一面站起来,由橱里取出一叠画。
“这张是我自己。”她说。
我看了看,那简直不是她自己!
画上的那个女人,头发蓬乱披散,脸上瘦骨嶙峋,眼窝深陷,嘴巴张开,仰着头,双手向天,似在呼喊。那褴褛的衣衫挂在身上,像被狂风吹卷。那是一张腊笔画。
我看看她,摇头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嘴角一抿,嘲讽地笑笑,说:
“有一天,我会变成这样子。”
“你太多幻想。”我说。
“是真的。”她淡淡地说,“我有一天会老,说不定会穷,也许受到什么打击,而变成疯子。或者会去自杀。”
“噢!不会,不会的。”我肯定地说,“你不能这样想。”
“我想不想都是一样。”她淡淡地说,“反正现在我不怕了。以前我是怕的。”
她把那张画拿开,给我看另一张。
那是一张古怪的画,画面上满布着一片桔黄的草,在右上角,却钉了一只已死的蝴蝶。
“那只流浪的蝴蝶死了。”她说,“我把它钉在荒草堆里。”
“你想得太多了。”我一面惊讶她画法的大胆,一面说。
“想不想都是一样的。”她说,“女孩子们也像这只流浪的蝴蝶、好时光会在流浪中浪费过去的。我们会变形,会死去,还不如蝴蝶,可以做成不变色的标本。”
她又给我看另一张画。这张画颜色很鲜明。蓝天绿野,点缀着几簇小小的花,她说:
“世界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大家野生野长。没有什么教养的礼数,每人依每人的方式过活,没有人说哪一样是正常或不正常。最多只不过是能活下去的活下去,不能活下去的就死掉,生死是很自然的事,怎样生,或怎样死,都是无关紧要的。”
她说完,把这张画拿开,露出下面的一张。这一张,她画得比较正常,是一个面貌端庄的中年妇人,微闭着眼,怀中抱着一个初生的婴儿在哺乳。那婴儿也闭着眼,很安详的样子,在旁边,她写了两个字的标题——“承受”。
“只有人类承受上一代的压力最多。”她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就已注定。”
“别的生物也是的。”我说。
她把图画一张一张地叠起来,收回壁橱里去。然后,走回来,坐在矮几的对面,低垂着眼睑,说道:
“也许你对。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再想那流浪的蝴蝶。自从我发现自己可以画画之后,我不再害怕我今生会怎样结局。事实上,怎样结局都是一样的。人生都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死亡’。‘死亡’是很公平的。分别只在你这一生有没有发现自己可以做出什么,一旦你发现了,你就不再害怕你将怎样结局了。”
我听着,蓝葹的这一番话实在很高深,高深得令我觉得意外,于是我说道:
“彩儿,你知道吗?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那差不多就是你现在所说的意思了。”
蓝葹笑笑,说:“我不懂你的话。我刚才也只是随便说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现在已经不再像那只流浪的蝴蝶,我可以定下来,做点事了。我不再想哥哥自杀或外祖父自杀的事。假如我注定要那样结局,我也只好接受,因为那是来不及选择,就已注定了的。今后,我将专心地画画。谢谢你做我的朋友,也谢谢陈星。他看过我的画,说我很有天分。”
“他看过你的画?”
“我寄给他看的。”
“你说不让我告诉他你是谁。”
“那是那时候。”她说,“现在不了。”
七
出了蓝葹的家,我直接去找陈星。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见他就问,“蓝葹找你学画了吗?”
“她不必学。”陈星正在自己裱画板,他一面用手抹平画板上的纸,一面说,“她是一个天才。她的画极富哲理,而有创造性,有一种神秘的美。那是绘画的最高境界。她把自己的人生观注入到画里,她的画充满着无拘无束的幻想和深挚的情感。”
“但是,她的——”我指指头部,“似乎有点问题。”
陈星笑着摇头,说:
“你被她骗了,根本没有那一回事。”
“但是——”我大惑不解地问。
“她的一切故事都是她自己编造的。”陈星说,“她外祖父并没有自杀,而且还健在,他是当地的一位名医,说来你一定也知道,施外科。”
“哦!施外科,我当然知道。”
“那位施医生就是她的外祖父。”陈星说,“她根本没有哥哥,所以,当然也不会有个哥哥自杀。”
“但是,她为什么要那样说?而且,你又怎么会比我更知道了。”
陈星把画板平放在柜子顶上,让我坐下,递给我一杯茶,他说:
“蓝葹乳名叫彩儿。那天,我一见她就认出了,她是以前的邻居。她的家,是个保守的家庭,世代习医,所以格外希望生男孩,而偏偏她母亲那一代就只生了她母亲一个女孩。无奈,只得招赘了她父亲蓝医生。”
“哦!原来她父亲是招赘。”
“是的,当时他们言明,如生女儿则姓蓝,如生儿子,则第一个要姓施,好继承施家宗祧。”
“那么,蓝葹是第一个,是女儿。”
“对了,所以,她母亲非常失望,不喜欢她,不理睬她,从生下来,就不理睬她,因此,她父亲给她取名叫‘睬儿’,后来,因为适合女孩,才改为彩儿。”
“难怪她那样孤僻!”
“是的,她很孤僻。”陈星说,“那时,我们住在她隔壁,隔着竹篱经常看见她独自一人,坐在那日式房子后面的台阶上剪纸。从黎明到中午,从中午到黄昏。”
“哦!从那时候她就剪纸?”
陈星点点头,“唔,从那时候。她说,那是她消磨时间的惟一办法。”
“她没有上学?”
“她读到初中,但是,她不是个好学生,常常逃学,有时在班上捣乱。老师时常要请她妈妈到学校来谈话,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她反而变本加厉。后来,索性就退学了。那以后,我也搬了家。想不到,过了好几年,反而从你这里又遇到了她,她长大多了!”
“她很美,是不?”
陈星点点头说:“而且很聪明。现在我明白,她的一切怪诞的行为,都只是为了要弓!人注意。她逃学、捣乱,为的就是让老师去请她妈妈来。她说,只有那个时候,她妈妈在注意她,哪怕是打她骂她也好。”
“可是,她妈妈始终没有关心过她?”
“仿佛是的,因为她下面有了一个弟弟。”
“哦!大概就是药局那个少年了。”
“我想是的。她的爸妈,把全部精神去照料这个男孩,所以彩儿就更被冷落了。”
“她说她叫蓝葹。”
“那是她自己取的。”陈星说,“施是她外祖的姓,她在上面放一个草头;意思是把那施姓埋葬。”
“好可怕的想法!尽管那字在表面上看来是那么美!”
“她去找你,说她自己有病,而且编造种种离奇的故事,也无非是想吸引你的注意而已。”
我想了想,说:
“我觉得她是成功了。”
“我想也是的,你去了她的家。她一定很开心的,因为她妈从来就不相信她可以交到一个朋友,也不相信她有任何与众不同的才能。”
“而现在,她的天才被你证实了。”我善意地揶揄着陈星。
陈星那年轻的脸上掠过一抹难掩的喜悦。
“是的,”他说,“她在绘画上有非凡的天才,再加上后天孤独寂寞给她的磨练,她早就有了常人所不易到达的深度,那真是难得。”
我坐在那里,看着陈星那线条利落的脸。我把自从认识蓝葹以来的一切,都想了一遍,我觉得我了解她了。于是,我对陈星说:
“现在好了,让我祝福彩儿,也祝福你吧!”
陈星深思地看了我一会儿,说:
“也许我们更应当祝福的是颜料和彩笔。”
“是的,颜料和彩笔。”我笑着站起身来,说,“只有颜料和彩笔,才可以把苍白的人生涂染成绚丽的世界。才可以使死去的不致褪色,像彩儿画纸上的蝴蝶。”
八
多年不见彩儿,当然,她一定已经长大,而且很可能,她已成为一个出色的画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在我记忆中一直这样鲜活,这样清晰。或许因为她太像每年一到春天就开始翩跹的蝴蝶;也或许,她使我想到世界上还有更多像彩儿一般聪颖而寂寞的灵魂,她们寂寞地降生,而后无声地凋萎,只因她们生命中缺少爱的颜料和纯真的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