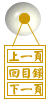时间:一个秋日黄昏。
地点:牙科医院的候诊室里。
椅子上坐着六七个人。有人在看报,有人在打盹,有人在以焦急不安的神情望着那扇垂着楼花帘饰的玻璃门。
只有靠近茶几那里,那个中年绅士安闲地坐着。
他刚吸完一枝烟。现在,他捻灭了烟头,把身子靠向那沙发的椅背,微微抬起他那两条长长的卧蚕眉,和炯炯有神的眼,去看他对面墙壁上挂的那张字画,看得很专心。
右边靠墙壁的这排沙发上,坐着一位女士,她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了。现在,她的眼光随着他的,也转向了那幅字画。
上面写的是一串甲骨文。仔细辨认,才看出来写的是:
“南天好,风外杏林香,
求智求仁名并立,
寿人寿世利同长,
齐祝万年昌。”
是董作宾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张画。
她把目光从字画移向了那绅士。他仍在专心地欣赏那上面的字,他那黑黑的眼瞳,专注在那个“风”字上。
甲骨文的“风”,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在风中傲然而立的绅士,那衣袂被风向后扫去,像西方人穿着燕尾服,在风中。
穿燕尾服的倒不只是西方人,东方人也穿,在婚礼的时候,在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她才20岁。
她不想再去看那甲骨文,她在看这绅士。
他的鬓发斑白,衬着方方正正的脸型。由侧面看去,那鼻子是他整个面貌的主题,而最能说明他的性格的还是他的嘴唇,方方的,下唇比上唇略微厚一些。不知他笑起来的时候,那牙齿是否还那么均匀?
来看牙,中年人的毛病了。
他的灰色西装,质料很考究,黑皮鞋也是上好的纹皮。
他略微侧过头来,眼光从甲骨文移向屋顶那新型的风扇,这一个动作,使她心里跟着动了一下:
“没有错。一定是他!”
他比以前胖了一些,胖得不少。因此,在他身上已找不到那灵活利落的神情,但是,这一个动作,却使她捕捉到了他性格中的那一点对外界事物热切的关注与好奇,他什么都要看看,都要研究研究,他是闲不住的。
只是胖了一点而已。当然,鬓上的星霜,眼角边的鱼纹也是以前所没有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的神韵。
“一定是他了!”她下着结论。
她动了动身子,去向隔座的一个女人商借她手中的报纸。她的动作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饱满的眼神向她移了过来,带着男人们对妇女注意时的那份含蓄与礼貌,他迅速地把眼光掠过她光滑整齐的发型,和那属于中年妇人的雅致的风韵。他把眼光收敛到那张甲骨文上,那个“杏”字,和那个“林”字,带着郊野自然的姿态,使他感觉到林木的芬芳和潇洒。
她等待他的反应,但是,他望着那“杏林”两个字,并未泄露出一丝他内心的感觉。
“那么,他是不认识我了!”她想。看着自己的手,和放在膝上的软软的手袋,那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镜子,假如不是为了礼貌,她会把小镜子打开来,看看自己,看看自己是否变得太多,多到唤不起他一丝一毫的记忆。
二十四年,足够使一个女人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她的手,按着那软软的手袋,感觉到里面那个小小的镜子,也感觉到那圆圆的镜面,怎样反映出她的面容。
眉毛经过修饰,比以前细了,而且长了。
眼睛却比以前松了,也没有以前那样大了。松弛的眼皮,盖住了那漆黑眼珠的一部分。皮肤有了皱纹,没有以前那一层夺人的光彩了。嘴唇不会老,但老的是它两旁的纹路,即使不笑,也无法抹去了。
上好的化妆品,和精细的化妆,曾使她以为可以拉回那逝去的青春,而在年轻粗率的少女面前沾沾自喜过;但是,现在,当她希望他能认出她来的时候,她才猛然醒悟到,化妆实在只能使她更不像她自己,把那仅余的一点青春的尾巴也抹去了。
年龄改变一个女人的程度,远比男人为多,难怪他认不出来了。
她的眼光从他鬓旁移向他的下额,那方方的下颏;他的领子一定不再是15英寸,而至少是17英寸了。那浆硬的白衬衫,衬着淡灰色起深红斑点的领带,上面有一枚细长的镶着宝石的领带夹。她注视着那枚领带夹,想到他比以前考究多了。
而他的眼光却由那“风外杏林香”移回来,移到了她那整齐雅致的发型,“如果没有那几根白发就好了!”他想。
由那发型,他的目光移向了她的面颊。抛开了那面颊的象牙色和口红的桃红色,他注意到那行将消失的酒涡的痕迹。
就在他的目光停留在她脸上的那一刻,她把目光由他胸前的别针收回来,发现了他的凝注。
眼睛与眼睛相接的一刻,他怔了怔,她开始向他微笑。
微笑里没有那漩转的酒涡,却有那聪敏柔媚的眼神。他的眼光在那眼神里搜寻,搜寻着她的善意。
“不认识我了吧?”她低低地说,尽量打算不引起其他候诊的人们注意。
还是有几个人抬头看他们。有人从诊疗室走出来,有人被叫进去,他和她就在这一瞬间被放过了。
“我一直在注意你,觉得好像……”
他走过来,坐在刚刚空下来的位子上。
“我以为你一直在看甲骨文。”
“是的,我在看甲骨文,我是想从那‘风外杏林香’的想像中,找到答案。”
她笑了。眼光在他鬓发间盘旋。
“风外杏林香?”她说。
“这里没有杏林,北方才有,我们每年春天都去看杏花。那时候……”
他顿了顿,眼光从她温和的微笑移到她黑色典雅的旗袍,停留在她衣襟上。他笑了笑,接下去说:
“年轻的时候,真是——”
“真是傻!”她替他说。
他摇了摇头,加一声叹息在微笑星,说:
“不是。我是说,年轻的时候真好!肯去做傻事,真好!”
她跟着他的微笑也在笑。笑容里透着倦怠和怅惘。
带着不知从何说起的困扰神情,她换一个比较轻易的话题。
“不知道你也在台湾。”她说。
“我也不知道你在台湾。”
“一直在台北?”
“不。原来在南部糖厂,最近才调来台北的。你呢?”
“我一直在台北。”
他想要问什么,顿了顿,没问出来。
还是她问:
“你——结婚了吧?”
“结婚了。”他的这三个字和叹气一同出来的,脸上却带着安闲的笑。
“是谁?”
“邢玉梅。”
“结果还是她!”她的惊奇隐藏在笑容里。
“想不到吗?”他很沉静。
“哦!想不到。”
“你以为我该再费些事去找一个好的?”
她摇头。笑容在她脸上闪烁。
“那你想不到的是什么?”
她仍在摇头。
“哦!你以为我会一辈子也不结婚?”
她停止了笑,对他注视了一刻,说:
“不会的。你不是那种一辈子也不结婚的人。”
“这就对了。所以我娶了邢玉梅。”
“那时候,你可并不喜欢她。”
“当然。那时候,我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男孩,以为自己该有权摘下一颗天上的星。”
他脸上的笑容停留在眉宇间,眼睛却去看那“南天好”的字画,一副对自己嘲讽而又宽恕的样子。
“我早就认出了是你。”沉了一会,她说。
“为什么不招呼我?”
她想了想,抬起眼睛看他。
“怕你不理我。”她说。
“怎么会?”
“怎么不会?”
“我又不是小孩子!”他嘴角在微笑,眼神很温和。
从他温和的眼神中,她搜索着。
“我以为你会恨我。”她口气很轻松,眼睑却垂下来,眼光就落在他那灰色西裤利落的褶痕上。
“当时是有一点。”他变换了一下坐的姿势。
那条利落的褶痕从她目光中移开去,她抬起头来,看了看他,他没有看她,却接着说:
“现在不了。”
“真的?”
“当然。”
“那时候,真是不讲道理!”她对自己摇头。
“女孩子,总是那样的,喜欢去伤害爱她的人。”
“邢玉梅就不是。”
“她是个平凡的女孩子。”
“看来,平凡比不平凡好得多了。”
“也许是的。”
她沉默,沉默了一会,又问:
“真的不恨我?”
“当然。”
“让我现在向你道个歉吧!”她说。
他看了看她,梳着雅致的发髻,精细的化妆,掩不住脸上细细的皱纹,一串岁月在他脑中掠过。
他摇头微笑,说:“为那么久以前的事情道歉,何必呢?”
“看来,你是真的不计较了。”
“当然。”
她静下来,诊疗室又走出来一个人,另一个人被叫了进去。
“苏莪林好吧?”他问。
尽管那声音很沉稳,但仍显得有点突如其来。
她抬头看了看他:“你还记得他?”
“怎么不记得?”
“他不在此地。”她说。
“哦?我以为你们结婚了!”
“我们是结婚了。”
“那么,现在?”
她扬了扬眉毛,说:“现在离婚了。”
“哦!那真遗憾!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风雅!”
“你不是就喜欢他的风雅?”
她摇摇头,微笑,沉落在回忆里。
“我还记得他送你的那首诗。”他说。
“哦?你还记得?”
“是你拿给我看的。”
“我好残忍!”她歉咎地说。
“那诗写得真好!我还记得两句。”
“哦?哪两句?”
“他说:‘你那杏形的眼瞳,围着如湖水般的淡蓝,’那句子多美!我永远也写不出来,难怪你喜欢他!”
她微笑,松弛的眼皮在微笑时更显得松弛,眼梢下垂。
“那杏形的眼瞳”已无处寻觅,现在,这眼睛是蝌蚪形,拖着长长的尾巴。
他把眼光由她的眼睛上收回来,无目的地在墙壁上巡回了一周,才问道:
“你们怎么会分手的?”
“他把那句诗又送给了别人。”
“哦!真想不到。”他说。
“你该说,你早就想到。”她说。
“也许我该那样说。那么,你现在呢?”他问。
“一个人,在做生意。”她说,很平静。
“做生意?”
“想不到吧?”
“哦!真想不到!做什么生意?”
“房地产,股票,另外,我还教教家馆。”
“教家馆?”
“是的。我教英文。”
“哦!我记得你英文很好。”
“没想到在这里派用场,是不是?”
“其实,你如果做生意,就不必再教家馆,何必这样忙呢?”
她低了低头,打开手袋,拿出一个小小的金色烟盒,弹开了盒盖,递给他一支香烟,她自己也拿了一支,说:
“就这样,我还是嫌我空下来的时间太多了。”
他掏出打火机来打火,帮她点着了香烟,再去点他自己的。喷出一口烟,然后把打火机慢慢地放回西裤的小口袋里。慢慢地说:
“刚才,我一直看那‘风外杏林香’,就在想,那时候,和你去看杏花。杏花好看吧?”他说了一半,突然向她发问。
“当然好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她歉咎地笑。
“你只顾欣赏杏花。”
“你只顾估计那杏林有多少亩,能出产多少杏,又能做多少杏仁。”她笑。
“对了!所以你说,我们谈不来。”
“真的是谈不来。”
“所以,尽管我连燕尾服都定好了,你还是从我身边逃开了,嫌我太不风雅。”
“实在用不着那样认真的。”她喷出一口烟,在烟雾里,她眯起了眼睛,轻轻地说:
“其实,我也并不真正计较你是不是风雅。”
“我知道,你只是不爱我而已。”
“其实,也并不是不爱你。”她说。
他坐直了身子,从烟雾里朝她注意地望着,说:
“当然是不爱我。你爱的是苏莪林!我知道。”
看见他的眼光,她笑了笑,说:
“年轻的时候,根本也闹不清自己究竟爱谁不爱谁。”
“那是因为什么呢?”
“女孩子爱的只是一些幻想。”
“你说的可能是实话。”
“当然是实话。”
“于是,你嫁给了苏获林。”
“于是,我的幻想终于不能持久。”
“我以为他比我会欣赏春花秋月,该适合你的。”
“他会欣赏春花秋月,适于任何人。”
“他使你伤心了?”
“不!应该说,他使我领悟了。”
“嗯?领悟什么?”
“领悟了婚姻是一件很现实的事,需要忠诚比需要幻想多。人生也是一件很现实的事,需要物质比需要精神多,所以,我做生意。”
“所以,我娶了邢玉梅。”
“她比我聪明些。”
“不!你应该说,她比你的机会少一些。她是个平凡的女人。”
“你们现在不是很好吗?”
“开始的时候,也争吵过。”
“为什么呢?”
“因为她不想从我身边逃开。”他笑。
她也笑。
“是真的。年轻人,对得来容易的东西,不免觉得平淡。”他说。
“现在呢?”
他坐直了身子,把烟灰弹到烟缸里。
“现在,她是个幸福的胖太太,我是个幸福的胖先生,孩子们是幸福的胖娃娃。”
“那真好!几个孩子?”
“四个。”
“够她忙了!”
“她喜欢忙家事。”
“不喜欢杏花?”
“这里没有杏花,她从来不关心外面的花,她只关心客厅瓶子里的花。”
“你的家一定很舒服。”
“还不错。什么时候请你来玩。”
“我要去的。”
“我给你一张卡片。”
“谢谢你。”她接过那张卡片。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地址?”
她想了想,说:
“我会去看你们的。”
诊疗室又走出来一个人,护士朝她招一招手。
“你先吧?”她朝他客气着。
“不。你先吧!我等一会。我只是检查一下牙齿,没有什么。”他说。
“那么,一会见。”
她站起来,朝诊疗室走去。
今天要镶上面整排的日齿,把那副临时的义齿拿下来,她把头仰向诊疗椅的靠垫。
时光从天花板的方格间移了回来,二十四年!
健朗的男人和迟暮的女人!
罗曼蒂克的女人和脚踏实地的男人!
失去的岁月!
放过的爱情!
一连串如麻醉针般刺痛的经历!
杏花……
写诗的男人!
平凡的女人!
幸福的胖太太!幸福的胖先生……
寂寞空旷的房间,
冰冷的床!
股票的行情,
厚重而拥塞的义齿……
张开嘴!咬紧!再咬紧!好!
医生的眼镜。
她把手握紧,捏皱了的名片掉在地上。
“我不会去看他的!”她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