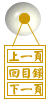有一年冬天。
北方,靠着海港,有几幢新建的考究的宿舍。
天气很冷,下着雪。
这雪已经下了一整天了,现在是黄昏时分,还在下着。无声的雪花,大片大片地飘下来,一层一层地落在已经有一尺多厚的雪地上,也落在屋顶上和树枝上。
他由港口工程处下了班,公家的吉普把他送到这排宿舍的一个门前。他推开车门,下了车子,北风由不远的海上,毫无阻挡地呼啸着吹来,抽打着他的脸和衣袂。
他伸手去按门铃。
工人老张瑟缩着开开大门,一见他,就说:
“有位女客找您。”
“女客?”他踩过院落里深深的积雪,一面往里走着,一面问,“是谁?”
“是您的朋友。”
他不悦地看了老张一眼,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他已来到客厅的门前。
推开那密闭的门,室内的暖热扑到了他的脸上,他迅速地把风雪关在门外。
女客在客厅一角的一只红色沙发上坐着,她还穿着在外面穿的皮大衣,头上系着一条方形粉紫色的羊毛头巾。
台灯的光很暗弱,他认不出来那是谁。带着被打扰的不悦,他说了一声:
“对不起!”
就径自走到衣架那边去,摘下他的帽子和围巾,又脱下他的大衣,把它们一一挂好。这才慢慢回过身来,按了一下墙壁上的开关。
中间那个吊灯亮了起来。
他望了望那个女客,说:
“你有什么事?”
女客看了看他,默默地把淡紫色的头巾解下来,甩了甩她浓密的黑发,他看清楚了她。
“哦!”他站定了脚步,“是你!”
“想不到?”
他无语地看看她,没有回答。
“还是不欢迎?”女客抬起她的眼睛问,一面站起身来,开始脱她的大衣。
他仍然没有说话,接过老张递来的热毛巾,擦着脸,一面对老张简短地吩咐道:
“给我一杯牛奶。”
老张答应着,望了那女客一眼。
女客把大衣翻过来折了一下,放在另一只沙发上。对他说:
“该招待我一杯吧?”
他脸上没有表情,对老张说:
“两杯。”
他把毛巾递还老张,走到书架旁边去拿报纸,找到了副刊,拿在手中,慢慢地踱了回来,坐在她斜对面那一角的沙发上。刚刚坐下,就又站起来去拿香烟。点着了一支,喷出一口烟雾,坐了下来,抬起头,看了看她。
“我好像打扰你了!”她说。
除掉了她的头巾和大衣,露出她灵俏的脸型,和纤秀的身段。当她对他说“我好像打扰你了!”的时候,那深黑眼睛的光暗了暗。
他对她的眼睛望了一眼,问: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不应该知道,是吗?”
“我想是的。”他说。
“那么,我倒真的是打扰你了。”
她说着,站起身来,走到他拿香烟的那张茶几旁,打开烟盒,拿出了一支,伸手向他要打火机,说:
“我可以抽你一支烟吧?”
他拿出他的打火机,放在茶几上,没有说话。
她把烟含在嘴里,又拿下来,淡淡地笑了笑,说:
“这样没有礼貌?”
他没有作声,回身去打开收音机。
音乐的声音刚一出来,她就去把它关掉了。
带着一点抑制不住的温怒,她说:
“我从这样远,在这样冷的天气来看你,不是来听音乐!”
“那么,你是来做什么?”
“我说了,来看你。”她为自己点着香烟。
“谢谢你,我不大习惯。”
“你这是什么话?”她回到她原来那只沙发,坐下来。
他看着她,看了一会,弹掉一截烟灰,才慢慢地说:
“我想,你该明白,我这是什么话。”
她忍了忍,才用平静地声音说:
“是的。我想,我是明白的,你一直是独身。”她抬头扫了这宽大的客厅一眼,“你一个人,住这样大一幢房子,未免奢侈。”
“我有条件让我这样奢侈。”
“是的,我很相信。”她说,“那个老张,是你特地从天津找来的厨子,你不搭公家的伙食。”
“老张跟你说了很多话吧?”
“我早就认识老张。”
“哦!”他怔了怔,“怪不得他敢留你。”
她也怔了怔:“哦,你现在竟然这样有权威!”
他冷冷地笑了笑,说:“不是权威,是规矩。我不在家,他不应该留客人在我客厅里。”
“但是,我似乎不是客人。”
“那是以前。”
“你倒真的像是改变了!”她的语气在失望中带着讥嘲。
“当然。时间会改变一切的。”他说。
她默默地看看他。
于是,他接下去说:“你该不会忘记这句话吧?你不是常常这样说吗?那时候。”
她默默地看看他,眼光在他坚定的脸上搜寻着,探索着。
“我想,我是一个很容易接受教训的人。”他说,“那时候,你既然那样诚恳地劝我相信‘时间会改变一切’,我当然也愿意尽量找机会去证实它。”
“那么,你说,你现在是证实了?”
“我想是的。”他说。把香烟头在烟缸里捻熄。又去拿第二支。
“你抽烟抽得太多。”
他笑了笑,喷出一口烟。没有说话。
“以前,你是不抽烟的。”
他看看她,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以前,你也不讲究吃穿的。”她回首四顾,看了看他屋里的陈设和衣架。
“以前,我也不这么冷静的。”他说。
她像被人迎面抽了一鞭,沉默下来。
他把后背靠在沙发上,昂起头,去看天花板。
看着,他说:
“你说你认识老张?”
“他以前在文利餐厅,你忘了?”
“哦?”他恍然地说,“怪不得……”
“嗯?”
他坐直了身子,把烟灰弹掉,说: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时常都是他把你爽约的字条交给我……对了,在文利,我约好了你,十四有九回你不到。末了总是老张交给我一张字条,‘我有事,不来了。’简单干脆。”
她沉默,吸着烟。
“而我当时明明白白地知道,你有什么事。”
“什么事?”她问,抬了抬头。
“跟别人去玩。”
她又沉默下来,沉默了一会,她说:
“我是偶然碰见老张的,前没多久。老张说,他在给你做事。说。你现在在新港工程处,很红。”
他看了看她,说:
“我做副处长,负责会计。”
“不画画了?”
他摇了摇头,“画画会饿死的。”
老张送来了牛奶,问:
“先生,什么时候开饭?”
“好了就开上来。”
“要不要添点菜?”老张望了望她。
他没有看她,对老张吩咐说:“不用。”
她喷出一口烟,在烟雾里,她望着他。
“你从什么地方来?”他问。
“天津。”
“坐火车来的?”
“嗯。在新河下车,这一截是走路。”
“这段路很长。”
“而且很荒凉。”
“是的。没有什么人走,这只是一条通往港口的路,只有我们在这里办公的人用。”
“雪很大。”她说。
“又是逆风。”
“是的。”
“在这样的天气,走这样的路,要有很大的决心。”他说。
“是的。
“我知道那一班火车的时间。你下了火车,走到我这里,时间就已经很晚了!”
“是的。天已经黑了。”
“因为这是冬天。”他说,“你来找我,有事情吗?”
她对他看了看,欲言又止。
“我替你说吧。”他说。
她愕然地望着他。
他伸了伸懒腰,站起来,看着她说:
“你想嫁给我了!”
她仍然那样望着他。
“十年前,你说过,‘等再过十年,我或许会嫁给你的。’还记得吗?”
他的眼睛扫过她的脸,“当然你记得,否则你就不会来了。”
“还记得那时候你说什么吗?”她问。
“我说,哦,我说你永远不会爱我的。”
“而我说,时间会改变一切的,不是吗?”
“当时,我是不相信的。”
“那么现在呢?”
“现在,我相信了。时间确实是会改变一切的。”
“那么,不用我说了。我是说,我来的意思是——”
“是的!不用你说了。”
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开始用手去抚摸她的头发,由她的头发慢慢地抚摸到她的脸颊。他说:
“你现在柔顺多了!”
她略微侧了侧头,没有说话。
“记得十年以前,那时候,你是一个多么桀傲不驯的女人!还记得吗?”
她摇了摇头,想说什么,咽住了。
“哦!时间真的是会改变一切的。”他说,“那时候,你滑得像一条鳝鱼。”
“鳝鱼?”她笑了。
“我曾是那样的想要抓住你,留住你,而你说,‘不要!不要!’你说,‘等十年之后……’。”
“那时候,我太年轻。”
“哦不!应该我说,那时候,我太穷。”
他的手抚摩到她的肩头。那村绒旗袍软绵绵的,他把眼光由那花色的旗袍收回来,望向火炉。火炉里正燃着熊熊的火,那火焰一跳一跳的,烧得炉壁通红。
“你大概不记得了,时间真的是会改变一切的。那时候,你说,我样样都好,只是缺少一点钱。”
他的手停留在她的肩头上。他说:
“所以,你要再去找一找看,看是否有另外一个人,具有我的好处,而又没有我的缺点。”
他把手臂收紧,她就倒向他的胸前。他低头吻了一下她的后颈,说:
“可是,你没有找到。”
他扳过她的脸,一只手臂拥过去,拥得她很紧。然后,他向着她的嘴唇吻过来,狂暴地吻过来。
她吃惊地挣脱了他,把头发掠向脑后,张大了眼睛向他望。她低低地说:
“你疯了!”
他冷静地笑了笑,站起身来,走向他的卧房。一面走,一面说:
“我有一件东西,送你。”
“送我?”
他答应着。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紫红丝绒的小盒。
他走出来,把小盒打开,里面是一只璀璨生光的钻石戒指。
她望向那只戒指,颤抖地说:
“哦!我以为你,以为你不再爱我,我没想到……”
“是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想不到的。这枚戒指,我买了很久,它光度好,粒又大,我一直想,什么时候送给你。你一向是喜欢这些东西的,我应该送给你。”
他伸手把钻戒连盒递给她,她接过钻戒,握住他的手,说:
“我真的,真的没有想到。”
老张端来一个托盘,里面是两碟炒菜,一碗汤,一副碗筷。
老张把它们摆在客厅另一端的餐桌上。
“该再摆一副碗筷吧?”她说。
“哦不!我很抱歉,今天我没有准备留客。”
她惊愕地望着他:“你是说——”
“我是说,假如我要请客,我会事先通知的。”他拉了拉他的西装衣领,“假如你不在意,我想,你该走了。外面风雪很大,天又太晚,你不能再不回去。”
“你是说……”她把钻戒放在桌上。
“我是说,这枚钻戒作为你对我激励的一点酬谢。世界上从不曾有一个人,令我这样肯竭尽心力来赚钱过。你使我知道,钱是最好的东西,钱也是最贱的东西。”
他把钻戒连盒递给她,“这只是一项馈赠,不代表什么意义。拿去吧!我亲爱的。”
她把钻戒轻轻地放在桌上,调转身来,穿起她的大衣,说:
“谢谢你,我走了!”
“不带着你的东西?”
她冷冷地对他看了一会儿,伸出她的左手,他看见她手腕上有一串钻链。
她用另一只手把钻链转了转,说:
“你说得不错。钱是最好的东西,也是最贱的东西。这些年,我发现,找钱容易,而要找一个懂得爱情的人很难;于是,我抱了一点希望来找你,找十年前那个清纯的你,以为你
她中止了她的话,抬头望他,发现他并没有在听她的话。
他也没有看她。
他在看她腕上那串钻石。
“光度真好!”他的脸因兴奋而发红,“每一粒都有一个克拉!”
“是的,每一粒都有一个克拉。你好有眼力!”她抽下手上的钻链,“假如你喜欢,这,就做为我今天来看你的一件礼物吧!”
“你是说——”
“我是说,你既然喜欢,你就拿去吧!”她伸手递过钻链。
“但是你——”他没有去接。
“我要走了,你说的,外面很冷,风雪又大,天也晚了,我戴这样贵重的东西,在夜晚,也不大好,你留着吧!”
她把钻链放在桌上,系上头巾,打开房门。
他向房门走了两步,迟疑着。
“不用送我,那些东西还没有藏好,你该有个保险柜!”她说,她把门碰上。
风雪关在门外。
爱情冻僵在风雪里。
他凝望着茶几上那串璀璨生光的钻石。
“时间真的是会改变一切的。”他想,伸手拿起钻链,到灯下去看着,“光度真好,真是一串好钻石。”
风在门外呼啸。
饭菜在餐桌上,在开始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