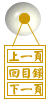这城市里布满着烟尘,好像是烟尘把夜空涂得越来越黑,于是只好亮起一串串浓妆艳抹的霓虹,掩饰一下它的肮脏。
但是,也正如同一切的浓妆艳抹一样,反映在人们心上的不是华丽,而是风尘气。
忙忙乱乱的,车子挤着车子,人挤着人。
多数人并没有目的。他们只是被卷入这不由自主的忙乱,或者他们只是想这样忙乱着,来掩饰自己的寂寞。
“河北恩××羊肉馆”,迎门挂着大大的横匾,黑底金字。下面两行傲然的告白“本馆清真,外菜莫人。”而那两排小小的涂着塑胶漆的廉价桌子,和它周围那四个圆圆的塑胶布面凳子,不知怎的,就好像是什么人干犯了小馆的禁例而“带’
进来的“外菜”。怎么看,怎么觉得那和傲然的金字牌匾不大调和。
这边坐着一对男女。男的40多岁,他从一进来,就殷勤地向女的推荐这里有名的羊杂汤。
女的很年轻,大大的一双眼,白皮肤,略嫌扁了一些的鼻子,宽宽的嘴,似乎她不爱说话,坐在男的对面,向那“羊杂汤”三个字,一遍又一遍地摇头。
跑堂站在那里,把搭在他肩上的毛巾拿下来,又搭上去。
“不要羊杂汤,羊肉汤要不要得?”河北恩××的跑堂,却是四川口音。
男的抬头看了看跑堂,说:
“你不是河北人?”
跑堂笑了笑,有点不得劲似地,说:
“掌柜的是,大师傅也是。”
男的重新把眼光在菜牌上扫了一扫,说:
“那么,就羊肉汤。”
女的皱了皱眉,还是摇头。
“那么,我要一碗羊杂汤。”男的说。
跑堂连忙答应说:
“好!一碗羊杂汤,一碗羊肉汤。”
女的一抬头,还没说话,男的抢过去说:
“她没说要羊肉汤。”
女的像是被逼得无可奈何,求援似地向饭馆四周望了望,忽然说:
“我要烧饼。”
“吃烧饼也好。那就来一碟卤牛肉。”男的说。
女的又摇头,说:“不要,我要一碟泡菜。”
男的带着一副无奈的表情,说:
“那好吧,给她烧饼和泡菜。我要一碗羊杂汤,另切一碟羊肉,再来两碟蒸饺。”
跑堂得令,大声吆喝着通知厨房。那嗓门,震得房顶上的日光灯一晃一晃的。
女的又皱了皱眉。
男的看了看她,说:
“早知你什么也不吃,我就不带你来了。”
“我一向不吃牛羊肉的,我全家都是。”
“我以为你可以尝尝。”
“下回吧。”女的说。
“下回到你喜欢吃的地方去。”
“那何必?我愿意陪你,这是你们家乡的风味。”
男的点了点头,脸上现出了凝重沉思的样子。
跑堂端上来羊杂汤,上面浮着白白的一层油,和青青的芫荽末。两碟蒸饺,热气腾腾。
男的咽了一下口水,开始用磁匙去搅动那羊杂汤。于是,那碗里面的羊肝、羊肚等等,就都跟着磁匙转了上来。
“不够肥,不够肥!”男的尝着,一面说,“总不是那个味道,不知怎么回事!”
跑堂又送来了烧饼和泡菜。女的拿过一个烧饼,掰一块,放一点在嘴里,眼睛注视着烧饼里面那一层赭色的芝麻酱。又皱了皱眉头。
男的没有朝她看,他在忙小碟里的饺子。饺子太肥,咬了一口,倒漏了两大滴油在饭桌上。
“饺子倒还不错,你尝尝。”他又忘了女的不吃羊肉。“我们从前在北方,一到冬天,总是吃羊肉饺子。那羊肉才叫肥!一口下去,满嘴是油!要趁热吃,凉了那油就凝在嘴唇上,一片一片的。”
男的自顾说着,没有看见女的把咬了一口的泡菜吐在小碟里。
“那时候,”男的拿一瓣蒜头,在手里轻轻地剥着。“那时候,我还在上学。
礼拜六,和同学一块儿去吃恩裕德的包子。”他看了看黑底金字的牌匾,“这儿是恩××。他们回教馆都用恩字的。那恩裕德有名,包子像饺子一般大小,一口一个,物美价廉。吃二十个,才5分钱。你说,那时候……”
女的刚吐掉一口泡菜,忘了,又用筷子去扒那碟白白的泡菜。
“泡菜好吃吗?”他问。
女的摇了摇头说:“像生白菜一样,不如重庆南路的那家餐厅。”
“那当然。”男的爽然地笑了,“那儿是四川馆,四川馆泡菜有名。这儿是北方馆,北方人不时兴吃泡菜。”
“那他们为什么还卖泡菜?”
“还不是因为客人有要泡菜的,比如说你——”
“我以为每个饭馆都有泡菜。”
“所以啊!别人也像你一样,找北方馆要泡菜,就等于找四川馆要坛子肉,文不对题。”
女的笑了笑,说:
“上回你说四川馆卖不辣的麻婆豆腐,和不辣的担担面,也是文不对题。”
“那还不是因为主顾要吃那个样子的?”男的说。
“真是!那么,你们北方人吃什么?不吃泡菜?”
男的想了半天,才说:“你看,我都快忘了。我们北方人吃啊,吃老腌咸菜,疙疽头。吃虾油小菜,里面有地瓜——哦!不是四川和这儿那种大大的地瓜。是那种小小的,脆脆的,像小葫芦似的。还有龙须菜,你没见过,像柏树叶子似的,只不过是黄色的。还有杏仁,也在里面。还有带刺的最小的小黄瓜——那虾油小菜啊,真够味!过瘾喏!”
女的咬了一口烧饼,慢慢地嚼着。笑了笑,说:
“你白怎么形容,我也是想像不出来,什么地瓜又像小葫芦,小葫芦又像什么嘛!”
男的也笑了。
羊杂汤不大够咸,不是不够咸,可能只是羊肉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不够味儿。也可能是想到了虾油小菜,太怀念那脆生生、齿颊生香的虾油小菜了。
饺子已经吃完,他饱了,就更想找点什么来爽爽口,夹了一口泡菜,放在嘴里,刚嚼了一下,他也把它吐了出来。
“真的是生白菜,连盐都没放,就端上来了,这叫什么泡菜!”他说。
女的朝他笑,说:
“不是你说的,吃泡菜要去四川馆?”
“真正要吃泡菜,这儿的四川馆也不行,得上四川!你知道吗?”男的一半玩笑,一半认真地说。
他吃饱了,女的还在那儿啃烧饼,啃得太慢。
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香烟的时候,摸到了新竹那女孩子来的信,这封信是今天上午才收到的。他和那个女孩来往了半年,费了不少力气,结果还是吹了。
他居然没有把信撕掉。在这一方面,他练得有涵养多了,虽然她信里的话说得那么不客气。
“我不懂你的意思,”她在信里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友谊以外的事。我还年轻,你也不想想自己,这么大年岁了,不做点正经事!以后别来信了!我不会再给你回信的。”
他把香烟点着,喷出一口烟。
他当然不会再给她写信。经验使他知道,一到了这个局面,那就是吹定了。
女人们总是喜欢假惺惺,什么叫“没有想到过友谊以外的事”?如果没有想到,她才更不会和你来往。
他看了看眼前这个女的,她还在啃烧饼,那烧饼像是很硬的样子,其实是油酥的。
“等”的感觉,使他觉得十分无聊。他40多了,把一切事都已看得很透。人生,在他感觉上是淡淡的,带着一点恍恍惚惚、茫茫然的厌倦。几乎每逢他从一件什么事上停止下来,那倦怠的感觉就袭上了他的心头。他无法抵御这倦怠的感觉,无法制止自己脑中那隐约浮现的问句:
“你这是做什么呀?!”
可不是,他想起了口袋里那封信上的话——这么大年岁了,不做点正经事!
他从鼻孔喷出一缕烟,那对自己嘲讽的冷冷的笑,就阻留在鼻子背后。
结婚成家真有点不像是件正经事!
吹就吹吧!好在她也并不是第一个。
这些年,自己追求的、朋友介绍的、报上征婚的、四川省的、江苏省的、山东的、安徽的、本省的、还有一个青海的,连眼前这个,数一数,少说也是一打了。
不知是谁说的,为了结婚去谈恋爱,真滑稽!他就这么滑稽!
这个吹了,再找一个,还是那一套,见见面,请看电影,吃馆子,到郊外走走,反正是花钱。假装在谈恋爱,其实是先友后婚。自己也闹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几分爱,也许,还没有来得及等到该发生爱情的那个火候,就又已经吹了。时间和金钱,和那也不知是谁发明的恋爱的种种公式,都白白浪费了
他厌倦了这一套公式,正如厌倦了坐在这里,对一个不见得有希望到手的女人的等待。
这算做什么呢?老大不小的了!还要学20多岁的人,谈什么恋爱!
难怪妞儿们看不顺眼,自己也觉得滑稽。
他看了看眼前这个女的,她还在啃烧饼,喝着那已经不烫了的茶。她不吃羊肉的,连牛肉汤也不喜欢。
他不知道他和对面的女人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再告吹,大概最后还是会吹的,吹了还得去再找。真烦!
旁边桌上,坐着个单身人。左边靠着电扇的地方,坐着两个女的,个子高大。
其中一个,穿着白运动衫,灰长裤,中年了,脸上黄黄的,没有化妆。
许是教体育的,不知结婚没有,不过,即使没结婚,他也不要那样的。他要年轻一点的才行,像面前这个。
朋友们面前背后总骂他不知自量。40多的人了,越老越要年轻的,难怪一辈子也结不成婚!
其实,朋友们哪里知道,一个人结婚成家,总得要一两个孩子。娶个叨多的,顶多是满足了自己。自己还不简单?为自己,又何必费那么大的事?
那边还有一个单身人,一面吃饺子,一面喝酒。
“都是北方来的。”他想。
人们到这里来,在吹电扇的天气,吃吃羊肉蒸饺,想想虾油小菜里的地瓜,想想那旧式的清真馆,牌匾上写着回文的,那儿的跑堂,不是说四川话的,他们不穿西式衬衫和西装裤,他们穿蓝布长衫,把一个衣襟的角塞在腰带上,上那木板楼梯的时候,布鞋踩得“咚咚咚咚”的。
那儿的北方饭馆不卖泡菜的。
他想着,有些惘然。
不知为什么,喜欢上这油腻腻的馆子。
他不是图省钱,他从来也不计较钱的。
存钱做什么?他又不想永远在这里落户。
但是,他喜欢来,来这里看看喜欢吃羊肉的不相识的人们,觉得他们那孤单落寞的脸都怪亲切的。
女的啃完了烧饼,打开钱包,拿出小粉盒子来擦粉。
他拿出30元来付账。
跑堂和掌柜在那里大声地喊着:“小账10块,谢!”
他的眼光在那块恩××的牌匾上停留了一会,然后,他站起身来,把香烟和打火机放进口袋里。
又该准备送她回家了,她每次出来都不能晚回去的。
送走了她,晚上的时间还长得很。
这是都市,都市的夜是睁着眼睛的。
他必须再单独一个人消磨剩下的时间,必须再投入那霓虹灯阻阻挡挡的拥挤的空间,去飘飘荡荡。他跟在女的后面往外走,挥不去那倦怠的感觉。
他没有喝酒,但是,他觉得自己脚下飘飘荡荡的。
他是个没有根的人。
那些吃羊肉饺子和羊杂汤的人也是。
没有根的人都是这么飘飘荡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