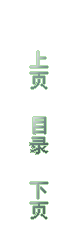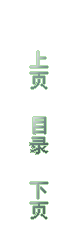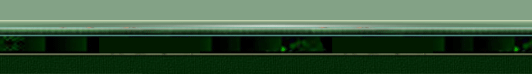|
不谋私利的朋友——怎样把“英尺”卖掉——我们不再打坑道——爱丝梅拉达之行——我的同伴——一个印第安预言家——洪水——那期间我们的住处
我们经常遇见在未开发的银矿中拥有一千到三万英尺的人,他们相信他们的每一英尺马上就会价值五十到一千美元——但通常他们连二十五美元也拿不出。你遇到的每个人都有值得吹牛的新矿,并且随时都准备着“样品”;一有机会他一定会把你拉到一个角落去,给你一些好处,并不是要占你的便宜,把“黄金时代”,“莎拉·简”或别的什么不知名的露头矿床分几英尺给你,代价只是凑够“大吃一顿”的钱,看情形说话。你绝不要露出他给你的好处会使你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因为完全是出于对你的友谊,他才肯作出这种牺牲。然后,他会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岩石,神秘地往四周看了看,好象害怕他这笔财产会给人抢去似的,他会舔一舔那块岩石,用眼镜盖在上面,激动地说:
“看这个!就在那块红色的泥土上头!看见了吗!看见这金斑点了吗?还有那条银线?这是从‘艾贝大叔’矿里采来的,那里有十万吨这种东西呢!眼都看得见。注意!当我们挖到矿脉,矿石集中的地方,它就是世界上最富的矿!看这张化验结果吧!我并不要你相信我说的,看看这化验报告吧!”
接着,他摸出一张油渍渍的纸,上面写明这块化验过的岩石确实含有金银,按比例折算每吨矿石价值几百美元或几千美元。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时的习惯作法是选一块“最富”的岩石拿去化验!一般说来,这块棒子果一样大小的矿石是一吨矿石中唯一含有点金属的那一块,而化验结果却弄得好象它代表那一吨废物的平均价值!
由干这种检验制度,洪堡地区变得疯疯癫癫。由于这种检验的权威性,这里的报纸记者们唾沫四溅,大吹大擂每吨值四到七千美兀!
读者是否还记得几页前摘引的那一段报道?照这样计算,采出矿石要用船运往英国提炼,矿主可以收回金银作为纯利润,矿石中的铜、锑和其它副产品就足以偿付一切费用。每个人满脑子都是这种“计算”,这倒不如说是在发痴。很少有人去实施这种计算,或者拿钱去支付费用,除非人家出钱,人家干活。
我们再也没有去碰一下我们那个坑道或竖井。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开发银矿的奥秘——那就是,不是靠自己额头上的汗水和双手上的气力去开发银矿,而是把矿脉卖给那些呆头呆脑的股东,让他们去开发!。
在离开卡森之前,州务秘书和我从几个爱丝梅拉达来的人手里买了“英尺”。我们原来希望不久就会得到金块银锭,万万没有想到反而给定期交纳的、没完没了的“应缴股款”弄得十分苦恼——要钱开发上述名矿。这些应缴的股款成了沉重的负担,似乎有必要亲自去过问一下。因此,我制定了个经卡森去爱丝梅拉达的计划,买了匹马就出发了,同行的还有巴娄先生,一个叫奥伦多夫的普鲁士绅士。这家伙不象别的外国人那样给自己的糟糕的外国语法弄得狼狈不堪,而是没完没了地重复人在谈话中从未发生过的、今后也不象有可能要发生的语法问题。我们冒着风雪走了两三天,来到了“蜜湖史密斯旅馆”,一家开设在卡森河畔的孤独的小客栈。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木房子,座落在一块大盆地或沙漠中央的小山丘上,丑陋的卡森河凄凄凉凉,弯弯曲曲地穿过这块沙漠。房子附近就是大陆驿站的土坯马房。在一二十英里的范围内再也看不到任何建筑。黄昏时分,来了大约二十辆干草车,围着房子扎下营来,车队的人一齐进来吃晚饭——一群非常粗野的人。有一两个驿车夫,六七个流浪汉和从其它队伍里掉队的人;结果,房子给挤得满满的。
晚饭后,我们出去走访了附近一个印第安人营地。这些印第安人正忙得不可开交,不知为了什么。他们在收拾行李,准备要尽快地离开这里。他们用那糟糕的英语告诉我们,“马上,许多水!”靠他们的手势我们才搞明白,他们的意思是洪水就要来了。天气好极了,又不是雨季,那条不起眼的河里只有一英尺深的水——大概两英尺吧,它并不比村子里的背巷子宽些,堤岸还不到一人高。那么,洪水从哪里来呢?我们就这个题目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得出结论,这是大惊小怪。印第安人要那么匆忙地离开这里,是因为某种特别的理由,而不是因为在这极干旱的时候害怕洪水。
晚上七点,我们上楼睡觉了——照常和衣而卧,三人同床,因为地板上所有可以利用的地盘连椅子上都占满了,就是这样还差点没有地方安置客人。一小时后,一阵骚动声把我们惊醒了,我们跳下床,从地板上那一排排正在打呼噜的人中间穿过,来到这间房子的前窗。一眼就看见了月光下的奇怪的景象。弯曲的卡森河水已经漫到岸边,波涛汹涌,白浪翻滚,在急弯处猛然一扫而过,水面上漂浮着一堆堆木头、灌木和各种废物。有一处洼地,原来曾是河床,现在已经灌满水,有一两处,河水已开始涌过主堤。人们跑来跑去,把牲口和马车一齐赶到房子旁边来,房子所在的这块高地前面只约有三十英尺宽,后面约有一百英尺。紧挨着老河床,有一座木马棚,我们的马就关在那里。在我们观看的时候,那地方河水涨得飞快,才几分钟,一股大水就在那小马棚旁边咆哮,水的前锋正对直向它扑去。我们猛然醒悟,这洪水不仅仅是一副壮观的景象,也意味着是一场灾难——不仅对那座小马棚,对河边的大陆驿站也同样是场灾难。这时波浪已翻过堤岸,正在堤坝上流淌着,向附近的大草捆进攻。我们跑下去,加入到那激动的人群和惊慌的牲口的行列。我们淌着没膝深的水进了马棚,解开马匹,水已齐腰,涨得真快。接着,人们一齐冲向草车,把大捆大捆的草卸下来,滚到房屋旁的高地上去。这时,有人发现一个叫欧文斯的马车夫不见了,一个男人冲进大马房,淌着齐膝的水进去,发现他还在床上睡觉,他把他唤醒后又淌水出来。可是欧文斯很疲倦,又睡着了,但只睡了两分钟,因为他在床上一翻身,手掉在床沿上就摸到了冰凉的水!这时水已淹到草垫了!他刚淌着快要齐胸的水走出来,那土墙就象糖一样融化在水里,那座大房子倒下来,一眨眼就被冲走了。
到七点钟,只有那小木马棚顶还露在水面上,我们的客栈立在一片汪洋大海中的小岛上。极目望去,月光下再也看不到沙漠,而是闪光的海洋。印第安人是真正的预言家,但他们是怎样得到信息的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群奇形怪状的人被水围困了八天八夜,每天的生活就是咒骂,喝酒,打牌,有时为了换个花样就殴斗一场。这是些社会渣滓和苍蝇——但让我们忘掉这些东西吧,他们精力充沛得令人难以置信——最好让他们永远这样吧。
有两个人——不过,这一章已经够长了。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