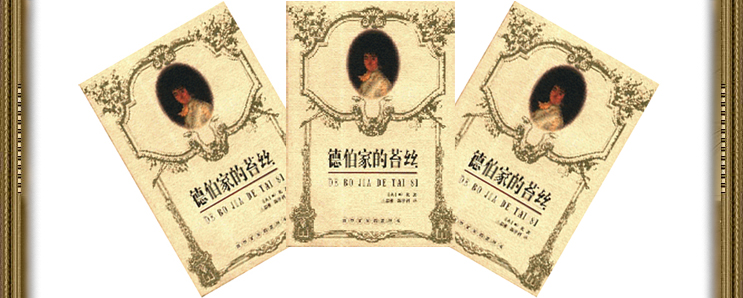 |
|

|
第41章
|

|
|
|
让我们从前面叙述的冬天的事情转而叙述现在十月的一天吧,这是安琪尔和苔丝分手八个多月以后。我们发现苔丝的情形完全改变了;她不再是把箱子和小盒子交给别人搬运的新娘子了,我们看见的是她自己孤零零地挽着篮子,自己搬运包裹,和她以前没有做新娘子时完全一样了。在此之前,她的丈夫为了让她过得舒服一点而给准备了宽裕的费用,但是现在她只剩下了一个瘪了的钱袋。
在她再次离开马洛特村她的家后,整个春天和夏天她都是在体力上没有太大的压力下度过的,主要是在离黑荒原谷以西靠近布莱底港的地方做些奶场上的工作,那个地方离她的故乡和泰波塞斯一样的远。她宁愿这样自食其力。在精神上,她仍然停留在一种完全停滞的状态中,她做的一些机械性的工作不仅没有消除这种状态,相反助长了这种状态。她的意识仍然在从前那个奶牛场里,在从前那个季节里,仍然在从前她在那儿遇见的温柔的情人面前——她的这个情人,她一伸手刚要抓住他,拥有他,他就像幻象中的人影不见了。
奶牛场里的杂工到奶量减少的时候就不需要了,因为她没有找到和在泰波塞斯奶牛场一样的第二份正式工作,所以她只能做一个编外的临时工。但是,由于收获的季节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她只要从牧场转到有庄稼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大量的工作,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收获结束。
在克莱尔原来给她的那笔五十镑钱里,她从中扣除一半给了她的父母,算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如今她只剩下二十五镑了,到如今她还只用了一点儿。但是现在到了倒霉的雨季,在这期间,她只好动用她剩下的那些金币了。
她真舍不得把那些金币用了。那些金币是安琪尔交到她手上的,又新又亮,是他为她从银行里取出来的。这些金币他抚摸过,因此它们就成了神圣的纪念品了——这些金币除了他们两个人接触过,似乎还没有其它的历史——用掉这些金币就如同把圣物扔掉。可是她不得不动用这些金币,只好让这些金币一个一个从她的手中消失了。
她不得不经常写信,把自己的地址告诉母亲,但是她把自己的境遇隐瞒了。当她的钱快要用完的时候,她母亲写来的一封信送到了她的手上。她的母亲告诉她,她们家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秋雨已经把屋顶淋透了,屋顶需要完全重盖;但是由于上一次盖屋顶的钱还没有付账,所以这次别人就不给盖了。还有,楼上的横梁和天花板也需要修理,这些花费加上上一次的账单,一共是二十五镑的数目。既然她的丈夫是一个有钱人,不用说现在已经回来了,她能不能给他们寄去这笔钱呢?
就在这时候,克莱尔的银行差不多刚好给苔丝寄了三十镑钱来,情形既是那样窘迫,所以她一收到那三十镑钱,就把她母亲需要的二十镑钱寄了去。在剩下的那十镑钱里,她又用了一些置办了几件冬衣,虽然严冬就在眼前,而她剩下的钱却是不多了。当她用完了最后一个金币的时候,她就只好考虑安琪尔给她说过的一句话了,当她需要钱的时候就去找她的父亲。
但是苔丝越是思考这个办法,她越是犹豫起来。因为克莱尔的缘故,她产生了一种情绪,敏感,自尊,不必要的羞耻,无论叫它们什么,这种情绪让她把她和丈夫分居的事向自己的父母隐瞒起来,也阻止她去找她丈夫的父亲,去告诉他说,她已经花光了她的丈夫给她留下的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大概他们已经瞧不起她了;现在像叫化子一样,不是更让他们瞧不起吗!这样考虑的结果,就是这位牧师的媳妇决不能让她公公知道了她目前的状况。
她对同她丈夫的父亲通信感到犹豫,心想这种犹豫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减弱;可是她对于自己的父母刚好相反。她结婚以后,回到父母家里住了几天,接着就离开了,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她最终找她丈夫去了;从那时到现在,她从来没有动摇自己等丈夫回来的信心,在无望中生出希望,她的丈夫到巴西去只是短暂的,此后她就会回来接她,或者写信让她去找他;总之,他们不久就会向他们的家庭和世界表现出和好如初的情形。她至今仍然抱有这个希望。她的父母用这次露脸的婚姻掩盖他们第一次的失败以后,再让她的父母知道她是一个弃妇,知道她接济了他们之后,现在全靠她自己的双手谋生,这的确太让人难堪了。
她又想起了那一副珠宝。克莱尔把它们存在哪儿,她并不知道,这无关紧要,即使在她的手里,她也只能使用它们,而不能变卖它们。即便它们完全属她所有,她用实质上根本就不属于她的名份去拥有它们,这也未免太卑鄙了。
与此同时,她丈夫的日子也决不是没有遭受磨难。就在此时,他在靠近巴西的克里提巴的粘土地里,淋了几场雷雨,加上受了许多其它的苦难,病倒了,发着高烧,同时和他一起受难的还有许多其他英国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也都是因为巴西政府的种种许诺被哄骗到这儿来的。他们依据了那种毫无根据的假设,既然在英国的高原上耕田种地,身体能够抵挡住所有的天气时令,自然也能同样抵挡巴西平原上的气候,却不知道英国的天气是他们生来就习惯了的天气,而巴西的气候却是他们突然遭遇的气候。
我们还是回来叙述苔丝的故事吧。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用完了最后的一个金币,也没有另外的金币来填补这些金币的空位,而且因为季节的关系,她也发现要找到一个工作极其地困难。她并不知道在生活的任何领域里,有智力、有体力、又健康、又肯干的人总是缺少的,因此她并没有想到去找一个室内的工作;她害怕城镇,害怕大户人家,害怕有钱的和世故的人,害怕除农村以外所有的人。黑色的忧患①是从上流社会来的。那个社会,也许比她根据自己一点儿经验所以为的那样要好一些。但是她没有这方面的证明,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她的本能就是避免接触这个社会。
①黑色的忧患(Black care),见罗马诗人贺拉斯《颂歌》第三章第一节第四十行。
布莱底港以西有一些小奶牛场,在春天和夏天,苔丝在那儿做过临时挤奶女工,而现在这些奶牛场已经不需要人手了。到泰波塞斯去,要是奶牛场老板仅仅出于同情,大概也不会不给她一个位置;从前在那儿的生活虽然舒服,但是她不能回去了。现在和过去倒了过来,这太不能令人忍受了;她要是回去,也许会引来对她所崇拜的丈夫的责备。她无法忍受他们的同情,更不愿看见他们在那儿相互低声耳语,议论她的奇怪处境;只要他们能够把知道的她的事情藏在心里,她差不多还是可以面对那儿熟悉她环境的每一个人。正是他们在背后对她的相互议论,使她这个敏感的人退缩了。苔丝无法解释这中间的差异,但是知道她感觉到了这一点。
现在,她正在向本都中部一个高地农场走去。她收到玛丽安写给她的一封信,那封信几经辗转才送到她的手上,推荐她到那个农场去。玛丽安不知道怎么知道了她已经同丈夫分居了——大概是从伊茨·休特那儿听说的——这个好心的喝上了酒的姑娘,以为苔丝陷入了困境,就急忙写信给她从前的这位老朋友,告诉她的老朋友,说她离开奶牛场后就到了这个高原农场上,如果她真的还是像从前一样出来工作的话,那儿还有几个工作位置,希望能在那个农场上同她见面。
冬日的白昼一天天变短了,她开始放弃了得到她丈夫宽恕的所有希望:她有了野生动物的性情,走路的时候全凭直觉,而从不加思考——她要一步步一点点地把自己同多事的过去割断,把自己的身分消除,从来也不想某些事件或偶然性可能让人很快发现她的踪迹,这种发现对她自己的幸福却是很重要的。
在她孤独的处境中,自然有许多困难,而其中她的容貌惹人注意却不能算是最小的。在克莱尔的影响下,她除了原先的天然魅力,现在又增添了优雅的举止。她最初穿着准备结婚穿的服装,那些对她偶然的注目倒还没有引起什么麻烦的事情,但是当她的衣服穿破以后不得不穿上农妇的服装时,就不只一次有人当面对她说出粗鲁的话来。不过,一直到十一月一个特别的下午,还没有引起人身侵犯的恐惧。
她宁愿到布莱底河的西部农村去,也不愿到她现在去的那个高地农场,因为别的不说,西部农村那儿离她丈夫的父亲的家也要近些。她在那个地方寻找工作,没有人认识她,她还想,她也许有一天打定了主意,会去拜访牧师住宅,想到这些她就感到高兴。不过一旦决定了到比较高和干燥的地方去找工作,她就转身向东,一直朝粉新屯的村子走去,并打算在那儿过夜。
漫长的篱路没有变化,由于冬日的白昼迅速缩短,不知不觉就到了黄昏。她走到一个山顶,往下看见那条下山的篱路,弯弯曲曲地伸展出去,时隐时现,这时候,她听见背后传来了脚步声,不一会儿,就有一个人走到了跟前。那个人走到苔丝的身边说——“晚上好,我漂亮的姑娘。”苔丝客气地回答了他的问话。
那时候地上的景物都差不多昏暗了,但是天空的余光还能照出她的脸。那个人转过身来,使劲地盯着她看。
“哎呀,没错,这不是特兰里奇的那个乡下野姑娘吗——做过德贝维尔少爷的朋友,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住在那儿,不过我现在不在那儿住了。”
苔丝认出他来了,他就是那个在酒店里对她说粗话被克莱尔打倒的有钱的村夫。她不禁痛苦得全身一阵痉挛,没有答理他的话。
“你老实地承认吧,那天我在镇里说的话是真的,尽管你那个情人听了发脾气——喂,我狡猾的野姑娘,是不是?我那天挨了打,你应该请我原谅才对,你想想吧。”
苔丝仍然没有答理他。她那被追逼的灵魂似乎只有逃跑一条路。她突然抬脚飞跑起来,连头也不回,沿着那条路一直跑到一个栅栏门前,那个门打开着,通向一块人造林地。她一头跑进这块林地,一直跑进了这块林地的深处,感到安全了,不会被发现了,她才停下来。
脚下的树叶已经干枯了,在这块落叶林中间,长着一些冬青灌木,它们稠密的树叶足可以挡风。她把一些枯叶扫到一起,堆成一大堆,在中间扒出一个窝来。苔丝爬进了这个窝里。
她这样睡觉自然是断断续续的;她总觉得听见了奇怪的声音,但是她又劝自己说,那些声音只不过是由风引起的。她想到了她的丈夫,当她在这儿受冻的时候,他大概正在地球另一边某个温暖的地方吧。苔丝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像她一样的可怜人?她还想到了自己虚度了的光阴,就说:“凡事都是虚空。”①她机械地反复地念叨着这句话,念到后来,才想到这句话对于现代社会已经不合适了。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所罗门已经想到了;而她自己虽然不是思想家,但是她想到的还要深刻些。如果一切只是虚空,那么谁还在乎呢?唉,一切比虚空还糟糕——冤屈,惩罚,苛求,死亡。想到这儿,安琪尔·克莱尔的妻子把手举到自己的额头上,摸着额头上的曲线,摸着眼眶的边缘,可以摸到柔嫩皮肤下的骨头,她边摸边想,总有一天这儿只剩下白骨的。“真希望现在就是一片白骨,”她说。
①凡事都是虚空(All is vanity),见《圣经·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正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她听见树叶中又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这也许是风声;可是现在几乎没有风呀。有时候是一种颤动的声音,有时候是一种拍打声音,有时候是一种喘气和咯咯的声音。很快,她确信这些声音是某种野外的动物发出来的,她还听出来,有些声音是从头顶上的树枝丛里发出来的,随着那些声音还有沉重的物体掉到地上的声音。如果她当时所处的境遇是比她现在更好的境遇,她一定要张惶失措的;但是,只要不是人类,现在她是不害怕了。
天色终于破晓了。天色大亮后不久,树林里也变亮了。
在世界上这个充满活力的时候,天上使人放心的平凡的光明已经变得强烈了,她立刻从那一堆树叶中爬了出来,大着胆子查看了一下四周。接着,她看见了一直闹得她紧张不安的东西了。这片她暂借栖身的树林子,从山上延伸到她现在所处的地点,形成了一个尖端,树林在这儿便足尽头,树篱外面便是耕地。在那些树下,有几只山鸡四下里躺着,它们华丽的羽毛上沾着斑斑血迹;有些山鸡已经死了,有些山鸡还在无力地拍打着翅膀,有些山鸡瞪着天空,有些山鸡还在扑打着,有些山鸡乱扭着,有些山鸡伸直了身子躺在地上——所有的山鸡都在痛苦地扭动着,不过那几只幸运的山鸡除外,它们在夜里流血过多,再也无力坚持了,已经结束了它们的痛苦。
苔丝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群山鸡都是在昨天被一群打猎的人赶到这个角落里未的;那些被枪弹打死掉在地上的,或者在天黑前断了气的,都被打猎的找着了,拿走了,许多受了重伤的山鸡逃走了,躲藏起来,或者飞进了稠密的树枝里,在夜晚勉强挣扎着,直到血流尽了,才一只一只地掉到地上;苔丝听见的就是它们掉下来的声音。
过去她曾偶尔看见过那些猪鸟的人,他们在树篱中间搜寻,在灌木丛里窥视,比划着他们的猎枪,穿着奇怪的服装,眼睛里带着嗜血的凶光。她曾经听人说过,他们那时候似乎粗鲁野蛮,但不是一年到头都是这样,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十分文明的人,只是在秋天或冬天的几个星期里,才像马来半岛上的居民那样杀气腾腾,一味地杀害生灵——他们猎杀的这些与人无害的羽毛生物,都是为了满足他们这种杀生嗜好而预先用人工培养出来的——那个时候,他们对大自然芸芸众生中比他们弱小的生灵,竟是那样地粗野,那样地残酷。
苔丝对这些和自己一样的受难者,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她首先想到的是结束那些还活着的山鸡的痛苦,所以她就把那些她能找到的山鸡都一个个扭断了脖子,免得它们继续受罪;她把它们都弄死了,扔在原地,等那些打猎的人再来找它们——他们大概还会来的——第二次来寻找那些山鸡。
“可怜的小东西一看见你们这样受苦,还能说我是天底下最痛苦的人吗?”她大声说,在她轻轻地把山鸡弄死的时候,眼泪流了下来。“我可是一点儿肉体的痛苦也没有受到啊!我没有缺胳膊少腿,没有流血,我还有两只手挣衣服穿,挣饭吃呀。”她于是为那天夜里自己的颓丧感到羞愧了。她的羞愧实在是没有根据的,只不过在毫无自然基础的人为的社会礼法面前,她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罢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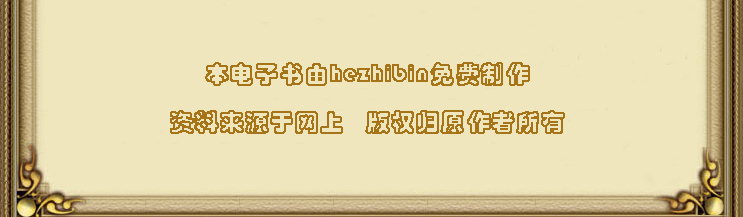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