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13章 胡尔达必的恐惧令人焦虑
|

|
|
|
他真的非常害怕,我也是惊悸得不知该说什么。我从没看过一向理性的他会如此恐惧不安。他脚步急促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偶尔待在镜子前,奇怪地看着自己,一只手放在头上,好像在问自己的影像:“是你,真的是你胡尔达必这样想吗?你真敢这样想吗?”与其说他“正在”想什么,不如说他“即将”要想。其实他看来是什么都不愿想。他用力甩着头,几近蹲在窗前,看着夜空,倾听远处海洋任何细微的声响。他也许在等托比的蹄声及拖车的转动声,好像一只伺机而动的野兽。
凶猛的浪潮已平静下来,整个大海渐无声息。突然在东方,有道金线映在黑色浪涛上,天亮了;几乎在同时,新堡从夜色中浮现,惨白暗淡,正如我们一夜无眠的脸色一样。
“胡尔达必,你和你母亲没有说很多话就分开了,是吗?”我问他,全身都发抖了,因为我发现我有点不可想议,居然那么大胆地问他。“朋友,朋友,我想知道她有没有告诉你,床头小桌上放的手枪走火了?”
“没有。”他很生硬地回答。
“她没有跟你说这件事吗?”
“没有!”
“那你有没有问她那枪声及尖叫声是怎么回事?她刚才的尖叫和在走廊之谜时的尖叫声一模一样!”
“桑克莱,你真的很好奇!你比我还好奇,我什么都没问!”
“因为她没向你解释枪声及尖叫声,你就发誓今夜发生任何事都不去听,也不去看吗?”
“没错,桑克莱,你必须相信我……我很尊重黑衣女子的秘密。我没有问她任何话。她只跟我说:‘我们此刻可以放心地暂别,因为再没有任何事能分开我们了!’之后我就走了。”
“啊,她跟你说‘再没有任何事能分开我们了’?”
“没错,朋友,而且她手上沾满了血……”
我们静下来。我站在窗户及胡尔达必身旁,他突然将手放在我手上,然后指给我看地下室门口的小灯—这道门通往老巴布的工作室。
“太阳出来了,而老巴布还在工作!他真的很有勇气。我们去看看他怎么工作吧,这会使我们的心情转变,我也不会再去想那个紧勒住我的脖子,使我窒息而失去力量的‘论证圈圈’。”然后他叹了口长气,自言自语说,“达尔扎克难道永远不回来了吗?”
一分钟之后,我们穿越庭院,走下鲁莽查理塔的小角室,里面空空的,工作桌上的小灯还在亮着,可是老巴布不在!
“喔!喔!”胡尔达必叫道。
他拿起灯,举得高高地检查周围事物。他看了所有装饰在地下室墙上的小玻璃窗。房里的东西都还在原位,还算整齐,并且很科学地都贴有标签。我们看着这些史前时代的骨骸、贝壳及角,标签上分别写着“贝壳坠子”、“长骨干锯成之坏”、“驯鹿层的刀子”、“马格德林时期的刮刀”、“大象层时期的伯隧石粉”等等。我们回到工作桌前,人类最早的头骨就在桌上,下额骨上还沾着红色的颜料。达尔扎克将它放在桌上,向着太阳把它晒干。我走到窗前检视,所有窗户前的栏杆都很完整,没有被破坏的可能性。
胡尔达必看着我说:
“你在做什么?在推测他会不会从窗口逃走之前,你不是应该先确定他是否从门口出去的吗?”
他将灯放在地板上,检查有无脚印。
“去敲方塔的门,问问贝合尼耶老爹老巴布是不是回去了;之后再去问守在暗门的马东尼及在铁门旁的杰克老爹。去啊,桑克莱,快去!”他说。
五分钟后,我问完所有人,回来找他。
“没有人看到他,胡尔达必。”
他有点担心,他说:
“地板上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我只发现瑞思及达尔扎克的足迹。昨晚暴风雨来之前,他们两人曾进来过;鞋底都沾着庭院的泥土,还有洪水区的铁质松土。可是到处都没有老巴布的脚印。他在暴风雨前来过,可能在那当中离开,但不管如何,之后他就没有回来过!”
胡尔达必站起来,再次拿起桌上的小灯照亮头颅,它血红色的下颚笑得阴森吓人。我们周围只有骨头,但老巴布不见了,这事比这些骨头更吓人。
胡尔达必看了一会儿腥红的头颅,然后拿在手中,眼睛凑近头颅的空洞眼眶看。然后他把头颅举高,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接下来再看侧面。后来他把头颅交给我,要我将它高高举在头上,同时,胡尔达必也将小灯高举过头顶。
突然我有了一个想法,我将头颅丢在桌上,跑到庭院的水井旁。那些压着井盖的铁棍都没被动过:如果已有人由井口逃出去或是进入井里的话,这些铁棍就一定被挪开过。我更焦虑了,跑回去找记者:
“胡尔达必!胡尔达必!老巴布逃出的惟一办法,就是那只袋子!”
我又重复说了一遍,可是记者好像一点也没听进去。我很惊讶地看着他忙着做另一件事,我想不出那有什么用。在如此混乱不安的时刻,大家都在等达尔扎克回来,想要知道“多出的尸体”结局如何;同时,黑衣女子应在老塔忙着擦拭她的手,就像马克白夫人,忙着将令人不敢置信的罪恶洗去;而在这种时候,胡尔达必居然在画图!他拿着一把角尺、鸭嘴笔及圆规在玩。没错!他坐在老人类学者的扶手椅中,将达尔扎克的绘图板拉到他面前。他也和达尔扎克先前一样,开始画一张平面图;他不说任何话,若无其事地像个学建筑的学生一般画着图。
他用圆规的一头在纸上刺上一点,用另一头画出一个圆圈;和达尔扎克的图一样,它代表鲁莽查理庭院的面积。
年轻人又画了几笔,然后把画笔放进半满的红色颜料瓶中沾一下——那是达尔扎克用剩的。他小心地将颜料涂满整个圆圈,全神贯注地让颜料涂得均匀一致。我们必须称赞这位学生真够聪明。他左右检视他的杰作,舌头微吐,像个小学生。后来他静止不动,我仍在跟他说话,可是他一直都不开口,两眼死盯着颜料变干,动也不动,突然他双唇紧缩,发出没人听得懂的可怕叫声;我再也认不得他那好像疯子样的表情!他猛然转向我,连椅子都翻倒在地上。
“桑克莱!桑克莱!快看这红色颜料,快看这红色颜料!”
我被他这野蛮惊惶的叫声吓到,弯身看画。可是没什么嘛!上面只有一圈带点紫色的红色颜料……
“红色颜料!红色颜料!”他痛苦地继续喊着,两眼睁得老大,好像看到可怕的景象。
我忍不住问他: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没有看到它已经干了吗?你没看出来这是血吗!”
没有,我一点都看不出来,因为我不确定这是血,我觉得这只是很普通的红色颜料啊!
可是我不想在这时候和胡尔达必辩论,所以装出对血大感兴趣的样子。
“谁的血呢?”我说,“你知道吗?是谁的血?拉桑的吗?”
“哦!哦!拉桑的血!谁认得出拉桑的血?谁见过他的血颜色?要认出拉桑的血,必须剖开我的血管看,桑克莱,这是惟一的方法!”
我难以用言语表示我的惊愕。
“我父亲决不会让别人这样取出他的血!”他又开始了,以一种绝望而骄傲的语气谈他父亲:“当我父亲戴假发时,别人绝看不出来!我父亲绝不会让别人这样取出他的血!”
“贝合尼耶老爹的手上沾满了血,黑衣女子也有,你曾看到不是吗?”
“是的!是的!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是这样说的!可是我父亲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杀的……”
他一直很激动,而且不停看着紫红色的颜料。说着,说着,他喉咙硬住,大声哭泣起来:
“我的天!我的天!上帝可怜我们吧!如果真是如此,实在太可怕了……我可怜的妈妈不该有这样的命运!我也不应该!没有人应该!”
一滴又圆又大的泪珠从他脸颊上滑下来,掉进颜料瓶。他说:
“哦!这会冲淡颜料的。”
他颤抖地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拿起颜料瓶,放进一只小橱里。
然后他握住我的手,拉着我;我看着他这一连串的举动,自问他是不是疯了?
“走吧,桑克莱!走吧!”他对我说,“桑克莱,时间已到了,我不能再退缩了,黑衣女子必须告诉我们一切,有关那只袋子的一切细节,啊!如果达尔扎克能马上回来的话就好,马上!这样会简单一点,没错!我不能再等了!”
等什么?等什么?他为什么那么害怕?他在想什么?为什么眼睛直直地看人?为什么他紧张得牙齿打颤?
我忍不住再次问他:
“什么使你那么害怕?拉桑没有死吗?”
他紧捏着我的手臂,重复说着:
“我跟你说过了,我跟你说过了,拉桑死了比活着更令我害怕!”
我们走到鲁莽查理塔前。他敲门,我问他想不想单独和他妈妈相处。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居然对我说,在“论证圈圈还没合起来之前”绝对不要离开他。
接着,他悲伤地又说:
“但愿这圈圈永远不要合上才好!”
塔门一直关着,他再度敲门,门开了。神情委顿的贝合尼耶老爹出现在门口,他好像很不高兴看到我们。
“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还要什么?”他说,“小声点,太太还在老巴布的起居室……老巴布一直没有回来过。”
“让我们进去,贝合尼耶老爹……”胡尔达必命令他。
他推开门。
“不要跟太太说……”
“不!不……”
我们走进城塔的玄关,室内几乎没有一丝光线。
“太太在老巴布的起居室做什么?”记者低声问他。_
“她在等……她等着达尔扎克先生回来,她再也不敢回到房间去……我也不敢……”
“好吧!回房去吧,贝合尼耶老爹。等我叫您时再出来。”胡尔达必命令他。
胡尔达必推开老巴布起居室的房门。立刻,我们着到了黑衣女子——不如说是她的影子,因为这房间仍很暗,仅有几道清晨的光芒泄进来。玛蒂修长的侧影挺立着,靠在朝向庭院的窗户边。我们进去时,她没有动。她开口说话时,声音变得那么厉害,使我简直听不出来是她。
“你们为什么来这里?我看到你们穿越庭院,你们并没有离开庭院。现在你们什么都知道了。你们来这里做什么?”然后她的嗓音变了,她难过地说,“你跟我发过誓,你什么都不看的。”
胡尔达必走向黑衣女子,握住她的手,无限尊敬地说:
“妈妈,来!来!来!”他的话像是温柔但带有强迫意味的祈求。
他拉着她,她没有拒绝,他一握住她的手,好像就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她。但是,当他领她走到发生意外的房间前时,她整个人直往后退。
“不要去那儿!”她呻吟着。
她靠在墙上才没跌倒。胡尔达必推推门,门是锁住的。他叫来贝合尼耶老爹。贝合尼耶老爹在他的命令下打开门,然后就消失了——或许该说是,逃走了。
推开门后,我们探头看。看到什么呢?整个房间乱成一团,这景象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血色般的晨曦穿过巨大的铁栏杆洒进来,使这团混乱更加恐怖。墙上、地板上及家具都布满了血!血色的太阳,以及被装进马铃薯袋中、被托比尔知拖往何方的男人的血!桌子、扶手椅及椅子全都翻倒在地。男人在临终前,一定曾绝望地拉扯过这条床单,它一半被拖在地上,还有一只血手印在上面。我们走进混乱的现场。胡尔达必一边扶着快支撑不住的黑衣女子,一边温柔地恳求她:“这是必须的!妈妈,必须如此!”我扶正一把扶手椅,他将她扶着坐进去,然后开始问她一些问题。她只能用一些单音节的字眼、点头、摇头或是手势来回答他。渐渐地,我看出来,随着她的何答,胡尔达必显得愈来愈迷惑、焦虑及害怕。他试着平静下来,这是他最需要的,可是他无法做到。他一直叫着:“妈妈!妈妈!”试着给她打气,可是一点也没用,她已失去一切勇气了。她向他伸出手,他投入她怀中。他们紧紧拥抱着,两人都快透不过气了。后来她开始哭泣,这好像能使她摆脱这可怕的负荷。我准备退出房间,可是两人都把我留住;我明白了,他们不愿两人留在这房间里。她低声说:
“我们解脱了……”
胡尔达必跪在她膝前乞求她:
“为了确定起见,妈妈……你必须将一切都告诉我,所有经过……所有你看到的……”
这时她终于能说话了,她看着关上的门,然后目光惊恐地盯住散乱一地的物件,盯着沾在家具及地板上的血迹。她低声叙述那场可怕的意外经过。我必须靠近她,弯下腰才能听清楚。她断断续续说着,她和达尔扎克回房没多久,达尔扎克就关上门,走到工作桌前。当事情发生时,他就站在房间中央。黑衣女子站在他左边,正准备回自己房间。房间只点着一根蜡烛,就在床头桌上,玛蒂伸手可及。以下是事情发生的经过:当时房间很静,但是家具突然传出喀哒声,他俩都抬起头,往同个方向看,两人都紧张得不得了,心跳加快。这声音是从衣橱里传出来的。接下来是一片静寂。达尔扎克走向放在右边尽头的衣橱。第二声喀哒声传来时,他定住不动。第二声比先前更响。这次玛蒂看到衣橱好像在动。黑衣女子自问这是不是她的幻觉,还是她真的看到衣橱在动。同样,达尔扎克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他立刻离开书桌,勇敢走向前。就在这时,门打开了,衣橱的门,在他们面前打开,是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开了衣橱的门。黑衣女子很想尖叫,可是她叫不出来,她吓坏了,害怕得把烛台弄倒在地上。就在这时,有个黑影从衣橱中窜出来,同时,达尔扎克也发出怒吼,扑向这影子……
“这个黑影是有面孔的!”胡尔达必打断她,“妈妈……为什么你没看到他的脸?你们杀了这影子,可是我怎能知道这影子就是拉桑?你们又没有看到他的脸!你们也许根本没有杀掉拉桑!”
“啊!有的!他死了!”她小声而简短地说了这句话后,就不再开口。
我看着胡尔达必,心里自问:他们杀的如果不是他,会是谁呢?如果玛蒂没看到他的脸,总会听到他的声音呀!玛蒂到现在还在打哆嗦,好像她还听得见他的声音。贝合尼耶老爹听到了,也听出了他的声音……巴勒枚耶的声音。他在那场恶斗中,宣判达尔扎克的死刑:“这一回我要你的命!”那时另一人只能喘着气说:“玛蒂!玛蒂……”啊!怎样的呼唤!深夜中,落败的达尔扎克在叫唤黑衣女子。而她,她无法帮助他,只能害怕地叫喊,她的影子和另两人的影子缠在一起,她只能喊救命,但帮不上任何忙。没有人能帮忙。然后,突然间,那声令她发出可怕尖叫的枪声响了,仿佛挨枪的是她一般。是谁死了?谁活着?谁开口说话?
开口的是荷勃!
胡尔达必再度拥抱黑衣女子,扶着她站起来。她几乎将整个身子靠在他身上,慢慢走回她房门口。他在那儿对她说:
“进去,妈妈,我要留在这里,我必须工作,我必须努力工作!为了你,为了达尔扎克,也为了我!”
她惊慌地喊着:
“别再离开我了!在达尔扎克回来前,不许你离开我!”
胡尔达必向她保证,恳求她试着歇会儿。他正在关上门时,有人在敲走廊上的门。胡尔达必问是谁。回答的是达尔扎克的声音,胡尔达必说了一声“终于”,然后打开门。
我们还以为进来的是个死人。没有活人的面孔会如此惨白,毫无血色,一点生气都没有。这张面孔受到了太多情绪的蹂躏,以至于什么表情都看不出来。
“啊!你们在这里,很好,一切都结束了吗?”他说。
他倒进刚才黑衣女子坐的椅子里,抬头望着她:
“你的愿望实现了,他已在你希望的地方了!”
胡尔达必立刻问他:
“您至少曾看到他的脸吧!”
“不,我没有看到……您以为我会打开袋子吗?”
我以为这点小意外会使胡尔达必很失望;相反,他立刻走到达尔扎克面前对他说:
“啊!您没有看到他的脸!太好了……这太好了!”
他感情丰富地握住达尔扎克的手,对他说:
“可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我们必须‘不要合上论证圈圈’,而你要帮助我们,达尔扎克先生。等一下!”
他好像心情很好,立刻趴到地上,在家具下面,在床下面转来转去,就像在黄色房间里一样。后来他露出面孔并说:
“啊!我总会找到什么东西;一个能救我们的东西!”
我看着达尔扎克,问他:
“我们不是已经获救了吗?”
“是要解救我们的理智……”胡尔达必说。
“这孩子有理,我们必须知道这男人是怎么进来的。”达尔扎克说。
胡尔达必突然站起来,手里拿着一把枪。这是他刚在衣橱下找到的。
“啊!您找到了他的手枪!还好他没来得及开枪。”达尔扎克说。
他一边说,一边从他外套口袋拿出自己的枪,将它交给年轻人。
“是一把好枪!”他说。
胡尔达必甩动手枪的旋转弹匣,把致命的子弹弹壳取出后,再将这把枪和他在衣橱下找到的那把从杀人犯手里掉出来的枪做了比较。那是一把短枪管的大手枪,上面还有伦敦制造的铭记,几乎是把全新的手枪,枪膛里满满的。胡尔达必肯定这把枪没有被使用过。他说:
“拉桑向来等到最后关头才会开枪,他痛恨弄出嘈杂的声响。他拿枪只是想吓唬你们,否则他绝对立刻就开枪了!”
胡尔达必将达尔扎克的枪还给他,将拉桑的手枪放进自己的口袋。
“啊,现在要手枪有什么用?我向你发誓不再需要了!”达尔扎克说。
“您这样想?”胡尔达必问他。
“我确定!”
胡尔达必站起来,在房间里踱了几步后说:
“与拉桑有关的事,我们都不能轻易肯定。尸体在哪儿?”
“去问我太太,我要忘了这一切。有关这场恐怖悲剧的事,我一概不知。每当我想起这男人死在我脚旁的景象时,我就会告诉自己,这是一场噩梦。我会驱散这梦魇!请您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只有达尔扎克夫人知道尸体在哪儿,如果她愿意,她会告诉你。”达尔扎克说。
“我也一样,我也忘了,必须忘了。”玛蒂说。
胡尔达必摇摇头,仍坚持说道:
“尽管如此,你们仍说过,这男人只是垂死。你们能确定他已经死了吗?”
“我确定。”达尔扎克简单地回答。
“结束了!哦,结束了,一切不是都结束了吗?”玛蒂好像求饶似的说着。她走到窗户旁。“看哪,太阳出来了!这恐怖的夜晚结束了,永远结束了,永远死了!”
可怜的黑衣女子!这些字眼表达了她所有的心情。她忘记了刚才那场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她眼前的惨事。再也没有拉桑了!他被埋藏了!拉桑被埋在马铃薯袋里了!
突然,我们都慌乱地站了起来,因为黑衣女子在笑;在一阵狂乱的笑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吓人的寂静。我们不敢看别人,也不敢看她。后来是她首先开口:
“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我不会再笑了!”
接着,胡尔达必低声说:
“要等到我们知道他是如何进来后,事情才算真正结束!”
“知道了又怎样呢?这是一个谜,而这谜已被他带走了,只有他才能告诉我们,而他已死了。”黑衣女子反驳他。
“在我们知道真相前,他不能算是死了!”胡尔达必说。
“没错,只要我们一天不知道,我们就会想要知道,而他就会在那儿,在我们心中。必须赶走他!赶走他!”
“那么就一同来赶走他!”胡尔达必说。
接着他站起来,轻柔地握住黑衣女子的手。他仍试着带她进去隔壁房间,让她休息一下。可是玛蒂说她绝不进去。她说:
“你们要赶走拉桑,我怎能不在!”
我们以为她又要笑了,于是我向胡尔达必做了个手势,要他不要坚持。
于是胡尔达必打开房间门,叫唤贝合尼耶老爹及他的太太。他们是受了强迫才肯进来的。
所有人都到齐了,一起归纳出这个事件的过程重点:
一、胡尔达必五点去过房间,搜过衣橱。没有人在房间里。
二、五点以后,贝合尼耶老爹只开过两次门。达尔扎克夫妇不在时,只有他能开门。第一次是五点过几分,他替达尔扎克开门;第二次是在十一点半左右,进去的是达尔扎克夫妇。
三、在六点一刻至六点半间,达尔扎克和我们一起出去时,贝合尼耶老爹曾关上房门。
四、达尔扎克每次进屋后,不管是下午那次,还是晚上那次,都曾立刻关上门,拉上门闩。
五、贝合尼耶老爹自五点到十一点间,都很警戒地守在房间门口。他只曾在六点时离开两分钟。
胡尔达必坐在达尔扎克的书桌前,将这些逐一记录下来后,站起来说: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很简单。我们只有一个希望:惟一有可能的时候,就是六点贝合尼耶老爹值班的时候。至少这时没有人站在门口。可是有人在门后,那就是您,达尔扎克先生。在尽力回忆之后,您可不可以再次重复,在您进入房间后,曾立刻关上房门、拉上门闩吗?”
达尔扎克毫不犹豫且表情严肃地说:
“我可以再重复!而且,我只有在您和您的朋友桑克莱来时,才拉开了门闩。我再重复一遍!”
这个男人说的话后来经过证实,都是真的。
我们谢过贝合尼耶夫妇后,他们便回到自己的房间。
后来,胡尔达必颤抖地说:
“很好,达尔扎克先生,您将论证圈圈合上了!方塔和黄色房间一样,关得死死的,就像个保险箱,也可说,当时在走廊之谜时一样。”
“我们立刻就看得出来这和拉桑有关,”我说,“都是同样的手法。”
“是的,桑克莱先生,这是他一贯的手法。”
玛蒂说着,将她先生的领带取下,露出他脖子的伤口。
“你们看,这是同样的手法,我很熟悉的!”她又说。
大家都难过得说不出话。
达尔扎克只想着这奇怪的谜题。这好像是葛龙迪椰城堡悲剧的翻版,不过这次更加凶狠。他重复了在黄色房间事件发生时已说过的话:
“这里的天花板、地板或是墙上一定有洞。”
“没有洞。”胡尔达必回答。
“那么,他一定是穿墙而过。”达尔扎克说。
“怎么说?黄色房间的墙难道有洞吗?”胡尔达必说。
“哦,这里不同。”我说,“方塔的房间比黄色房间更严密,因为事情发生之前及之后,都没有人能进去。”
“对,这不是同一件事。”胡尔达必做出结论。“这两件事刚好相反。在黄色房间时,是少了一个人;在方塔,却是多了一具尸体!”
他踉跄了一下,扶着我才没有跌倒,黑衣女子冲过去,他勉强用手示意她停住,说了一句话:
“哦!没什么,我只是有点累!”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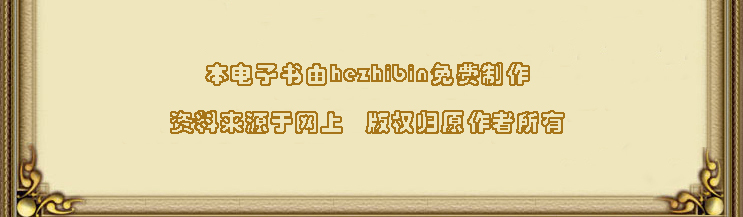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