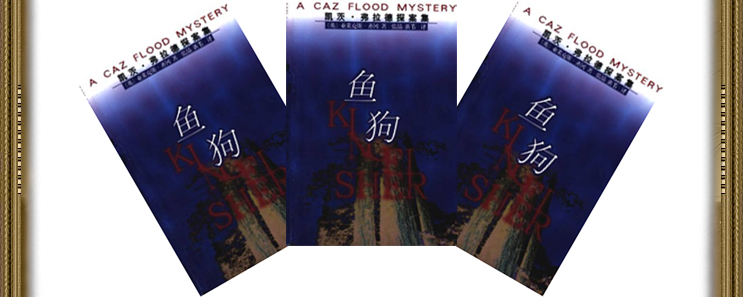 |
|

|
第19章
|

|
|
|
91
恶心的感觉消失了,凯茨又开始发抖。肾上腺素过早地在身体里跳动。她觉得皮肤上有刺痛感。他们回去找局长和穆尔。她先开口道:“对不起,长官,我没吃午饭。”
“我们得去拜访怀特和库克。”布莱克赛说,“谈谈我们的朋及冈兹先生。”
“我们有怀特的地址吗,长官?”
“我们有他的电话号,从交换台问到的地址。”
“那他住哪儿,长官?”
“蓝辛,离学院不远。”
“我能去吗?”
“可你不是不舒服吗?”
“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就好了,我现在没事了,长官。”
“鲍勃,你呢?”
“梅森警佐和弗拉德可以去蓝辛如果他们愿意。我可要睡觉了,丹尼尔·库克离得近多了。”
“那好吧!”布莱克赛打了个响指。“我们在这留6个警员,两辆车。每条船上总要有一个人,让他们每小时轮流值班,直到我下达新的命令。”
鲍勃·穆尔朝外面走去,凯茨跟上他:“有句话说,警佐。”
他站住了,她垂下眼帘。
“外面说吧。”他说。
凯茨往外走去,听见梅森和DCS说了句什么,布莱克赛的粗嗓门又答了一句。她走到甲板上,鲍勃正盯着淤泥看,她走到他身边:“警佐?鲍勃?”
穆尔转过身来,目光一片澄清,她笑了。
“我考虑过了。”她说,一边伸出手。
他握着她的手摇了摇,“多谢。”他说,微微点了一下头。
他放开她的手。“小心点。”她说。
她走开时觉得很轻松。
92
彼得·梅森把车从岛上开到公路上,径直朝布赖顿方向驶去。他们刚穿过铁索桥,凯茨就告诉他向左拐。他们顺着河边一条窄窄的路向上开去。绕过铁路,穿过老桥,来到A27号公路上。
“别迷路。”凯茨说,“走错了,这就像电线汇集处。”
他们打了个左转,滑上引桥。桥上那800英尺的支撑的钢索悬在阿道上空100英寸处。凯茨又问了一遍,彼得的手机是不是肯定开着呢?
“开着呢。”他说,“就像半分钟前你问的时候一样!”
“电池没问题吗?”
“弗拉德,它现在插在车上呢!”
“学院到了。”凯茨说,“看见灯光了吗?”
怀特家在一条路的尽头,是一座维护得很差的小屋。外圈的附属建筑随便地围着,屋顶是波浪形的,脏兮兮的。一条大狗拴在链子上,疯了一样地在周围30英尺内叫着,跑着,每次呛着了才停顿一会儿。
“天哪!”梅森说,“但愿那条链子结实点。”
没有灯,周围也没停着什么车。屋里看来冷清而空荡。他们仅仅是出于礼貌而敲了敲门,但直觉告诉他俩家里没人。
几分钟后他们离开了。顺着小巷走着,他们的手电照出一只红狐狸瘦瘦的轮廓。它站下了,一边晃着脖子,一边盯着他们看,然后躲过他们钻到路边树丛中去了。
“我们到桥上后能停一会吗?”凯茨说。
萨伯车停下了,梅森看着凯茨好像她要崩溃了一样。“相信我。”凯茨说。
狐狸消失在了夜色里。他们从小巷开到公路上,然后又回到通向山顶和布赖顿的一条石子柏油路上。他们身后蓝辛学院教堂前门的辉煌灯光笼罩着一切。这让凯茨想起了牛津的尖塔和瓦莱丽。接下来她就能听见阿莱德·威廉的声音和合唱队男孩们的声音。
夜渐渐深了,路上也越来越静。但不时还是会有车子同他们擦肩而过,大约30秒钟一辆。
“你要我在哪停车?”彼得说。
“桥的第一个跨度前面就有一个修车站。”
彼得把头灯打到最亮。几秒钟后,他说:“我看见了。”有一辆载货卡车停在那,只有三个轮子,一个千斤顶把车身弄倾斜了。
“撞车了。”
他们停在卡车后面,那是一辆J-reg型号的车,没有厂家的标志,他俩从车里出来时手里都拿着手电。两辆车夹着风飞驰而过。
那儿没人。“一定是没带备用轮胎。”彼得说。他绕到前面,“是的,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条:‘去找新轮胎,沃拉·普拉特’。”他又走回来,关上手电,把它斜靠在肩上,像扛着支枪,凯茨用手电指指河岸。
“我想去那边。”她说。
93
彼得知道现在她是崩溃了,尤其当她说“把电话拿来”时。
“你看。”他说,跟着她向河岸走去,“如果你想做爱,回车里有什么不好?”
“你正经点!”她说。
他们刚走到河堤下面天又开始下雨了。他们的手电装的都是卤素电池,但即便这样,黑暗还是很浓重。
“应该在这儿。”凯茨自信地说,一边穿过埠头上的树丛走向河边。
“到底找什么?”彼得说。
“空的桥墩。”凯茨就像在引用名人的话以自抬身价,“乔治·林塞尔说肯定有一个是空的。你带钥匙了吗?”
“我的钥匙对你有什么用?”
“乔治说所有的锁都一样。要不然管理委员会就得有上千把钥匙了。”
“那门在哪儿?”他说。
凯茨拨开几棵小树,“在这!钥匙呢?”
乔治说得没错。凯茨打开那把大锁,取下来,推开门,雨滴打在金属上啪啪地响,她淋湿了,但不要紧。她冲彼得晃了晃手电。
“我在你后面走。”
彼得摇摇头,“你他妈的开什么玩笑?”
“窝囊废!”凯茨说。
她走进去,里面大得令人吃惊。房间像个大厅,到最深处大概有60英尺深,40英尺宽,七八英尺高。墙和天花板上都是狭长的水泥带。
“他妈的!”彼得在后面说。
“歇会儿吧,你。”她说,“我们得干活啦!”
她转过身来,看见彼得把电筒放在下巴颏下面,像个食尸鬼。
“小心点门。”她说,“要是门锁上了,你就死定了!”
那儿有一堆堆的金属,旧栅栏,带着大大小小窟窿的防风设备,她模模糊糊地记起来,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把这一带叫做“鬼哭桥”,当地人都抱怨说有鬼魂和妖精。有好几个科学家和工程师正经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原因,就是那些防风设备。积累了几个月经验,他们才设法把这段桥封锁了起来,这就是旧址。
凯茨仔细环视着四周,但除了几个罐头盒,一堆金属器皿,几十袋水泥外,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干净的,甚至没有猫或鸽子到过的痕迹。据说乔治他们是第一批进来的人。
“至少这儿是干的。”她说。
彼得正要张嘴说话,电话响了。
是玛丽埃拉从一个地下室打来的。
“什么?不!你挂了吧!”凯茨说,“两分钟后再打给我!”
“信号不清楚,彼得。”她说,“我们得出去。”
“在车里信号更清楚。”彼得说。
“好吧!”
他们走出来,锁上门,然后一步一滑地爬上长满草的堤岸。雨下得很大,他们回到车里时已经湿透了。
“快插上!”凯茨叫道,“快!”
彼得启动车子,把雨擦和暖风都开到最大。过了一会儿,又不得不把暖风调低一挡。玛丽埃拉还没再打电话,凯茨紧张得要命。为了找点事干,她报告卡车的车号作一下交通工具检查。
控制台的女孩听出了她的声音,“还没睡吗,弗拉德?”
“我没法睡。”凯茨说,“男人太多,时间太少……”
女孩乐了,“是阿诺德·库克公司注册的。那是个新闻发布站,对吧?没有报告遗失。”
凯茨没听清,她正抬头看着桥冠,在公路中间,路两边的护栏中间,有胶皮扫过地面的声音,一件黄色夹克一闪而过。
“天啊?”彼得说,“在这时候,这种鬼天里干活!”
“你能再说一遍吗,杰克依……”
“是福特运输卡车,是阿诺德·库克公司的,那是家新闻发布……”
“谢谢。”她又看了看公路上,车窗上已经没有雨滴了,一辆过路车闪着红色的屋灯上了山。没有夹克衫,没有干活的人。
然后她注意到那也没有作警告用的三角标志。
她又向对讲机说:“杰克,你能帮我联系上穆尔警佐吗?”
94
凯茨从车里出来,雨下得正大,她走到卡车那试着拉拉门,又看了一遍那张条。她往驾驶室里看了一眼,手电筒的黄光照出几张纸,一卷绳子和一个铁皮容器。
她转到后面,雨水在她脸上淌着。这回借着手电的光她看见了一个大袋子,一条灰色的毯子和一堆其它什么东西。
“彼得!”
她转过去看看警佐彼得坐在挡风玻璃后面,嘴形好像是“什么?”然后指指胸口。萨伯车里的光把他照得亮亮的,她挥挥手,但他并没下车。她就走了过去,穿过车侧面的电子窗对他说:“我们得进那辆卡车里去看看。”
“我鞋里有个钉子。”他说。她走开了。
最后,当她拿着一根钢条从卡车里出来时,他也从干爽的轿车里钻出来,抬头看着雨,好像敢于再试一试似的。
“你干嘛呢?”他含含糊糊地说。
要看着他,凯茨就得盯着雨幕,她的眼睛很疼,就喊着:
“我想我们已经找到蒂姆了!”
彼得拿着撬,把它插入卡车货仓的门缝里并用力推。凯茨站在一码以外,拿着他的手电,锁头结实得要命,门一动也没动。
“试试底下。”凯茨说,口腔里聚集了许多唾液。
“他妈的没用!”
“我来帮忙,争取把一角撬弯。”
梅森在门底部一角处把铁条弄得出响。门没动,上面包的铁皮却卷了过来。凯茨把地上的手电滚向路边。她把手放到门下面,什么东西割了她一下。
“再来一次!”她喊道。
梅森又用力撬了一次,货仓门上出现了划痕。凯茨用力拉门的底边,梅森一边使劲一边嘟囔:“他妈的……”
锁头断开时哪的一声,是金属断裂的声音。
梅森大叫:“成了!”凯茨被反弹到地上。
一辆车鸣着笛慢吞吞地开了过去。凯茨站起来,已经湿透了。她捡起手电,问:
“你能看见吗,彼得?”
警佐看不见。他拿过手电,朝地板上晃了晃。凯茨从他旁边上了车,里面有种特殊的发霉的味道。一边前进,她一边晃动手电。突然她看见远处一端的内壁,立刻倒吸了一口气,喊道:“彼得!”他挪了过来,黑暗消失了,但光线在颤抖。
“看在上帝的份上。”彼得说,“你看一眼吧!”
“好吧!好吧!”凯茨喊。她一把把毯子拽下来,只抓住一个角,就像弹簧一样向后跳了回来。
她先看见的是衣服,看尸体前你总是先看见衣服,“噢,上帝!”她说。
但这一次没有尸体,没有血淋淋的场面。他们找到了蒂姆的书。
95
他们回到萨伯上,试着接通了控制台,她找穆尔。
“没劲。”杰克伊说,“我们已经派了一个警员守在他家周围,他一回来就能联系上。”
“好的。”凯茨说,她想了一会儿,“我们在布赖顿跨过阿道的桥上,你能通知局长吗?弄几辆车来?”
“布赖顿路,阿道桥,好了!”杰克伊说。
凯茨松了一口气。“好了!”她跟彼得说,“我们去跟那些夜班的工人聊聊。”
她下了车,走过头灯,来到驾驶舵一边钻了进去坐在司机后面。她拍拍彼得的肩膀:“从右边的车道开上桥去,慢慢地开。”
“干嘛?”
“我想看看那些工人都在哪。”
“那些夜勤的人会收拾我们的,我们可是停在快车道上。”
“冒次险吧!”
“这么着急干吗,凯茨?你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吗?”
“不能!”凯茨说。
“怎么他妈的不能?”
“帮你干什么,弗拉德?”
“找到皮克西·沃尔特斯。”凯茨说。
“谁?”
96
再等一会儿也没多大妨碍,凯茨告诉他。“比利·麦克林托克把偷来的东西都藏在桥里,对吧?”
“对。”
“他怎么会想出这个主意呢?你以前知道有的桥中间是空的吗?”
“从来没想到过。”
“比利为鱼狗队踢球,跟冈兹和怀特在一起,他们都是县里的工程师,管理道路和桥梁。可能是他们给比利出了这个主意,克莱尔·库克·布伦被囚禁时她认为那是条船,我们也这么想。金属,油漆,铆钉。她说关她的那个地方在动。非常轻微,所以我们认为那是条大船。小桥是固定的,彼得,但大桥是动的,像呼吸一样。”
“是我太迟钝还是怎么回事?”
“不是,彼得,你很正常。人们从来不抬头往上看,这就是为什么敌人会埋伏在树上。我们的街道都很陈旧了,对吗?建筑呢,二层,三层或更高,但我们见到的只是比较新的那一点点,第一层楼,不锈钢和玻璃。我们把桥看成通行用的工具,鸽子、老鼠和街上的孩子,他们把桥看成鸟窝,鼠洞和捉迷藏时的藏身之处。”
“那你是想说……”
“克莱尔·布伦就是被关在这儿,在这座桥里。”
他们以步行的速度向前开着。凯茨身体前倾,用电筒来回照着钢质路障中间的地带,每20码就有一个长方形的出入孔盖,四角都成弧形。这些出入孔中间到处是汽车上的废零件,螺钉,螺团,碎屑,甚至还有油漆罐和刷子。
她数到第十,十一,十二个盖时感觉有些晕车。这时他们来到一个出入孔前。
这个出入孔盖被漆成黄色,即便在手电的光下也显得很鲜艳,它被挪在一旁,是生铁的,很重。旁边是一个里层盖,是较轻的合金,这个盖也被放在一边。
“停车!”凯茨呼吸急促地说。
他们下了车,往回走了5码,刚才那个黄色夹克衫就是在这闪了一下,黑夜中的一抹银光和一双野兽般的眼睛。
他们翻过路障,两个人中间有一码的距离,就连这段距离上也布满了垃圾。她听见彼得踩上了一个螺栓,在那儿骂骂咧咧的。
他们走了过去。彼得勇敢地走过去,用手电往里照着。
“圣母啊!”他边说边向后摔去,脸色苍白。
凯茨走过去。
彼得仰面躺在地上,好像需要感觉一下桥身的存在。
“看在上帝的份上,凯茨小心点!那不是空的,这个出入孔直接通向底层,通向200英尺深的地方!”
她用手和膝盖向前爬行,将那些废零件都挪开。她爬到洞边,向里看去,她看见的是海水,河水和一条长长的通道。
“我给搞糊涂了……”她说,一脸迷惑,“如果那个工人就是从这下去的,那……”
正在这时候他们听到突突的引擎的声音,那声音似乎来自未知世界,恐怖而令人困惑。然后他们又听到火车头的咣咣声,钢轮走在钢轨上的声音。他们面面相觑,各种恐怖的鬼怪形像都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似乎任何时候他们都可能会面对什么怪物。
凯茨盯着彼得苍白的脸,“是从底下传来的!”他们感觉到它在滚动,那个东西,火车,站车,反正都在他们下面运动,然后凯茨透过洞口看见了一些金属框架,钢丝编成的地板,一架梯子,油漆罐,工具箱,之后她又看到一顶白色塑料帽子,那件夹克衫和操纵引擎的人。她感到身上一阵凉意。
彼得看着她,还是有些惊讶,凯茨把手放在唇上,又拍拍自己的屁股,警佐仍是一头雾水。但当她把手铐拿出来时,他点点头,把自己的也拿了出来。他俩从那个工人的视力范围内走开了。
97
一个脑袋冒了出来,洞口很窄,那个工人仔细挪着身体,上臂的肌肉在洞口四周蹭来蹭去,他的双手一定还扶在梯子上,因为他的肩膀出来后,他还在向下看,扭着身体把手臂和手也解脱出来。这时,两个侦探从他身后冲上来,一边一个把他制服并铐上手铐。凯茨用手电朝他脸上照去,是丹尼尔·库克。
一丝绝望的神情在他脸上一闪而过,他挣扎着,想退回洞里去。侦探们向后拉他的胳膊,他就像个被钉在地板上的臭虫似嚎起来。
“马上出来!”彼得说,“不然我们把你的胳膊拧下来。”
库克点点头。
“不,让他待在这儿!”凯茨小声说。
她移动了一下,让他能看清她。但她的手并没松劲,所以他还是很疼。
“下面是谁?”她直冲着他的脸喊。
“没人。”库克也叫着回答。
“皮克西·沃尔特斯在哪儿,你这杂种?”
“谁?”
“那个姑娘,她在哪儿?”
库克呲牙咧嘴地笑起来,她觉得恶心。他慢吞吞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真是他妈的贱种!”凯茨朝他吐了一口唾沫。她站起来拉着他的胳膊朝他身后跑去,跑到最远处时他叫唤起来。这时只听见一声断裂的声音,他带着哭腔嚷着:“上帝啊,上帝啊!”
“把他拽出来!”凯茨说着,一边把她的手铐打开。她的手腕很疼,她想她可能伤着了什么地方。
梅森把库克拖到地面上来。他的脑袋耷拉着,警佐检查了一下说:“我想你可能把他的肩膀弄脱臼了。”
“你不满吗?”凯茨说。
一辆过路车慢下来想看看怎么回事,上面有两个人,凯茨冲他们摆摆手。
“我得下去找找皮西克·沃尔特斯。”她说。
梅森把库克铐在路障上。他把凯茨的手铐取下来还给她。
“等等后援吧。我们说说话打发时间。”
“你听见库克说了?”凯茨说,“这下面没人。”
“所以我们等着就行了。”
“我不能。”凯茨想哭,“你不会明白的,下面的人可能会是我。”
警佐看看凯茨,很快说:“好吧,我来。”
“你永远也到不了那个平台上。”凯茨说。
“我闭着眼睛。”
“谢了!”她说,“不过不会有事的。”
她走到库克旁边,“下边是谁?”
“没人!”他说。她用手里筒猛击他的臂膀。
“上帝!我说过了!那儿没人,他们已经去了——”
他突然住了口,凯茨抓住他的肩膀。他看来好像要晕过去了。
“他们去哪儿了,丹尼?”
他疼得发抖。凯茨举起电筒。
“纽黑文。”他说。
98
凯茨把手电放在洞口边上,倒着进入洞口,滑到梯子上。她向后倾斜着身子,目光经过自己的胸和脚看着钢丝地板,透过这层地板她能看见水面,落差至少有100英尺。她紧紧抓着电筒。最后一刹那她向彼得要他的电筒作备用,她也不知道是否应该这样做。
她爬到洞穴的地板上,桥内壁从四周向她压迫过来,但在平台和墙之间有条2英尺宽的沟,直接通向下面的河水。如果让彼得来,他一定一惊一乍的。他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
她走到边上,向下看看水面,又抬头看看钢板,这确实像条船,金属,铆钉。在她面前甚至还有一扇4英尺高3英尺宽的门,用螺钉闩住了。
她想打开这扇门。但转念一想,如果库克用这个移动的笼子在桥下行动,无论他从哪来,这条路都不会通。
她又转到弓博旁边,发动机还热着,散发着气味。上面有一个按钮,原来像是红色的,后来被粗糙的手摸成金属的原色。她按了一下,它开始动起来,听着像个小型拖拉机。
她用手电来回打量这台机器,上面有一个横杆,标着“E-W”。她想可能是指“东-西”,就选定了“西”。她觉得震了一下,然后平台开始移动了,并发出咣咣的声音。她对自己很满意,拿手电往墙上照去。
平台向西移动时墙向东运动。大多数地方的油漆看起来都很干,很旧,但没人碰过。她知道外面正下着大雨,而她却在一个隐蔽的,干燥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她仔细观察着,这个笼子移动得很慢,像一种动物悬在树上向前蠕动。铆钉,铆钉,镶螺栓的门,门,铆钉……
她已经来到了河中间的平台上,现在她离刚才彼得和她看见的那个连接处已有大约50或60码了,她很快向后望了一眼,看见那座桥,像一条有生命的蛇一样跨过水面。
她转过去看了看没上锁的内壁,马上就明白了,伸出手把那个横杆拔到中间,运动停止了,只剩下轻微的晃动,但这是桥身在上升。她坐下来。她已经做到了简单的一步。
那里面不会是漆黑一片,她有手电,有两个呢。里面也不会太小,门是四乘三英尺的,管道至少是十乘十英尺的,她轻声自语道:“那儿不黑,不会被关在里面的。”
她俯过身去,咔嗒一声打开门闩,门闩打开时发出一种特别的冷冷的金属的声音。她把手塞进门底缝隙中,拉了一拉,门重得惊人,但还是荡了开来。
里面的黑暗似乎能发出回声,她赶快爬出来,试图不去想,但还是想起了佩图拉·沃尔特斯。
“坚持,皮克西,坚持住……”
她怎么也不可能预料到洞里面的形状。它比她想像的高得多,高得足够使电筒发出的光最后融入黑暗之中。8英尺高,大概10英尺宽,像一个高高的没有地板的房子,很干燥,电缆贴在离地面5英尺高的墙壁上。
她停下来听听动静,能听见的只有她自己的声音,听不见雨声,也听不见路面上车辆的过往声。她是在一个箱子里,虽然很大,但仍是个箱子,她照照前面,看见一个大大的椭圆形洞口;又照照后面,是另外一个大箱子,更长的桥。
她还没想好是否该喊几声,如果这儿有人,冈兹或怀特,那她的喊声就会使他们保持警惕。如果他们不在这儿,那就无所谓,她只会帮助皮克西·沃尔特斯。于是她喊道:“喂?”
第一声她几乎没叫出来。她突然记起一部电影。那是个人室抢劫者,但不能出击。一个警官大喊:“吐,你!吐呵!”她了试,咽了口唾液,深深吸了口气。
“喂?”这一次她听到了回声,回声跑过去又跑回,相互碰撞,有些吓人,似乎连她的身份也改变了。她不再喊了,开始走动。
在第三个大箱子里,她发现了床铺,一个录音机,一个一次用的电池,一瓶水,一个炉子和一些吃的。她还发现了一个医药箱,最顶层是一卷沙布。
在下一个箱子里,她找到了皮西克·沃尔特斯。她坐在一个大板条箱旁边。裸体外面裹着一条褐色的毯子。她手里拿着一个大杯子,里面还冒着热气。凯茨看到她的眼睛时,知道她挺过来了。她抬头看看她的救星,微笑了一下,然后又低头去喝她的热饮。
“别轻易下结论。”一个声音从她身后传来。
凯茨跳了起来,吓得几乎要晕过去,她的手电帮她认出了比利·麦克林托克,同时,他的手电也径直照在她脸上。他的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麦克林托克球棒。
“这和你想的不一样。”他说,把球棒放到地上。
凯茨仍然很紧张,吓得直想上厕所。她集中一下精力,恢复了沉着镇定的本性。然后她把手伸向第二支手电,一个用来照明,另一个防身。
“你是谁?”她说。
“比利·麦克林托克,队员中的一个。”
“我见过你的照片,你,冈兹还有库克和怀特。”
“我跟那些变态杂种们可没关系!”
“可你在这儿。”凯茨说。
“我知道。”麦克林托克叹了口气,“如果我想伤害你,我刚才就那么干了。”
他向那个女孩子走去。“看见了吧,没事了。很快就带你出去。”
皮克西抬起头,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又转向凯茨。
“我是流氓,对吧?我可能会跟警察打斗,但也得公平。一个女孩子,我是个男人,可不是禽兽。那帮家伙,圣母呵,他们都不正常。”
“你怎么来这的?”凯茨说。
“我藏在里面并找到了这个姑娘。那些人以为我要跟他们一起干呢,我只是等待时机好带她走。”
凯茨看看那个女孩,点点头。
“他很好,是正经人。”她小声说,“他照顾我,给我弄了些可可奶。”
凯茨稍微放松了一下,“你是不是卖过一台立体声电视机给库克?”
“是。”
“是他告诉你的关于这些桥的事?”
“是冈兹干的,那个美国人。”
“那丹尼尔在这干什么?”
“纠缠这个姑娘。他们最后都用她。库克就是想拥有她,你知道的。”他做个“强奸”的口形,“但冈兹说不行,他能让一个姑娘求他那么做。”
“其他人也这么干吗?”
“不,冈兹说如果他们碰她,就杀了他们。”
“他能吗?”
“噢,能的。我只在街头打过群架,但冈兹,他可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他好像在一支特种部队待过。”
凯茨蹲下身子,“那哈希特呢?还有别人吗?”
“我不认识叫哈希特的人,只知道有这个小姑娘。库克常和冈兹拿一个叫克莱尔的人开玩笑。”
“开玩笑!”
“是的,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到底能有多真,你知道的。”
“我们从这儿出去吧。”凯茨说。
麦克林托克用两只脚来回跺着地板。“我倒不太急着出去。”
“我们不会抓你的,比利,我保证。”
“那我兄弟们呢?”
“他们正被逮捕,比利,我无能为力。”
他伸出手,“你不错。”
“谢谢。”凯茨说。
99
他们穿过那些正方形的大箱子走出来,找到门,爬到外面运动着的平台上。麦克林托克隔着毯子抱着那个姑娘。凯茨问他为什么不径直离开,“还有我兄弟们呢。”他答,“再说这也挺有趣的。”
她重新发动引擎,选择“东”。平台抖动了一下,然后重新向河中间移去,她看了看那个苏格兰人和那个小女孩,《美女与野兽》。皮克西头一次突然决定开口:
“他们都是人渣。但我就是不肯,那个稍微文雅一点的说他能说服我,我说,只要我屁股上还有眼儿,他就休想。”
凯茨夸她勇敢,说要是换成她自己,她可能就挺不住。
“她是个聪明姑娘。”麦克林托克说。
凯茨让平台停下。他们头顶上就是出入孔,她来到梯子底下,向上喊:“彼得?警佐?”她想看清是什么东西砸了下来。
她坐起来,觉得很疼,脸上有血。她下巴疼得很。皮克西正呜呜地哭,甚至连尖叫都不会了。怀特正企图把她从比利手里抢过来,比利另一只手挥着那根球棍。
她摇摇头。这时冈兹走过来用什么东西碰了比利一下,他哼了一声就倒下了。然后那个美国人转过身来看着凯茨:“你是海盗吗?”
凯茨没理他,眼睛都白了,“那是什么?”
冈兹笑起来,“这个吗?”
她顺从地点点头。
“3万英镑。”冈兹说,“一次短暂出击的成果。别人就得不到这些钱,他们能吗?”
“他们杀人。”凯茨说。
“只是有时候杀。”冈兹说,“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把你打昏。那可有点副作用,就像抽羊角疯,但这不是我的问题。”
“你对我的警佐怎么了?”
“和比利那孩子一样,在这儿。”
“那丹·库克呢?”
“他脖子断了,摔下去了。”
她轻轻动了一下。她碰了碰下巴,下颏骨好像碎了。冈兹说:“关于这个可真对不起。我掉下去时,你正挡着我的路。”
“那现在怎么办?”她说,“你一定知道我们的车已经上了路,我下来之前通知他们的。”
“嘿,你就应该说‘你身后有人用枪指着你呢。’然后我就说‘噢,是的,我要栽了’。”
“那很有趣。”凯茨说。
“噢,是你很有趣。”冈兹说。他的眼睛突然变得像雪堆里的两个窟窿。有一小会儿,凯茨真正看清了他:“你要有麻烦了。”
他朝怀特和那个女孩子走去。怀特突然倒了下去,皮克西和他倒在一起。冈兹看着手电的武器:“哇,一下干倒两个,怎么样?”
皮克西呻吟着。凯茨说:“蒂姆·哈希特死了吗?”她在想这种袭击多长时间会来一次。
“快死了!”冈兹说。
“那他在哪儿?”
“他对诗的品味很糟,不喜欢美国诗,对惠特曼不太熟悉,认为弗罗斯特太腻,而狄金森太不成熟。”
“他在桥里吗?”
“被捆上了,没别的事做,只能想着他的女人。”
“天哪,你真是变态!”
他想了一会儿,歪着头:“嗯,是的。”
“他们会找到你的。”凯茨说。
“可能吧。”冈兹说,“但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待在一起,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身,电梯通道,通风系统,下水道。”
他走向她,“我们可以走了吗?”然后他大叫了一声,“噢!”
皮克西·沃尔特斯用球棍打了他一下,但只是女孩子的一棍,要吓他一下足够了,但不足以打倒他。他转过身,气得脸都黑了,“你这条小母狗!”
凯茨这时向他冲去,心里清楚自己撞上他时只有一条路可走。他被她撞倒时咕噜了一声,转过脸和她的脸凑在一起。他们撞到洞壁时他狞笑着,和她滚在一起,向水里摔去时他仍在狞笑。
“吻我!”她试图把他推开时他说。她看见他的眼睛,牙齿,然后他放开了她。落入水中前一瞬间她翻过身来,认为自己自由了。一切都停止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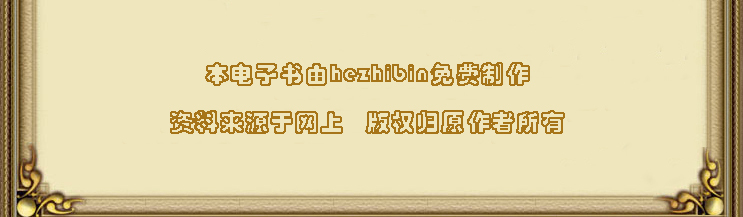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