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01章
|

|
|
|
三月清晨六点,天色还暗着。长长的列车侧身驶过机修场散出来的错落光线,轻轻地嘎啦一声开过火车铁轨的叉点,变换到另一个车道,进入铁路信号房发出的灯光里,然后出来,通过满是红灯点缀一盏寂寞绿灯的跨轨信号杆,朝那等在弧形下阴暗无人的空旷月台开去。
伦敦邮车即将抵达终点站。
足足五百英里的旅程被抛在身后,抛在通往伦敦尤斯顿车站和昨夜的无尽黑暗之中,五百英里月光洒落的田野和沉睡的村庄,五百英里漆黑的城镇和永不稍歇的火车炉火,五百英里的雨、雾、霜以及漫天飞舞的大雪,五百英里的隧道与陆桥。现在,三月萧瑟的清晨六点,山丘从周遭升起围拥着列车,列车状极轻松且平静,在它漫长而快速的旅程之后,即将停下来休息。整列拥挤的车厢之中,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人都因为火车到站而松了一口气。
那些松了一口气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人高兴得几乎要雀跃起来。其中一个是火车上的旅客,另一个则是铁路服务人员。这名旅客名叫亚伦·格兰特,而铁路服务员则为摩德·葛雷邱。
摩德·葛雷邱是火车卧铺车厢的乘务员,也是塞索至托基之间最令人讨厌的家伙。因为二十年来,摩德令旅客忍受他的恐吓,敢怒不敢言,并任由他敲诈——指的当然就是钱财上的勒索。毋庸置疑的,来往旅客的怨言也从未停歇过。比方说,头等车厢的客人里,他“酸奶酪”的骂名远近驰名。( 每当他那张拉长了的苦瓜脸在潮湿阴暗的尤斯顿车站出现时,大家就会说“天啊! 酸奶酪又来了。”) 而在三等车厢的客人之中,他的绰号更是五花八门,但不管大家叫他什么,都非常贴切且惟妙惟肖。至于他的同事叫他什么,反倒没什么重要了。这其中只有三个人能够治他:一个是来自德州的牛仔;一个是女王麾下喀麦隆高地军团的代理下士;另一个是三等车厢里那个扬言要用柠檬汁瓶子敲他秃头脑门的不知名的小个伦敦女人。摩德不买任何阶级或成就的账:他讨厌这个,怨恨那个,但他非常怕挨揍。
二十年来,摩德·葛雷邱在工作上没什么贡献。打从他做这工作不到一星期,他就觉得无聊了,但他发现这是个饶有油水的肥缺,他要留下来捞一把。假如你从摩德那里拿到早餐茶,你会发现茶很淡,饼干很软,糖很脏,托盘满满是水,而且汤匙不见了;但当摩德来收盘子时,那些原先演练许久的抗议却到嘴边就无疾而终了。偶尔像舰队司令这类人会大胆陈述“茶太糟了”,但一般人只会笑一笑,然后付钱了事。二十年来,或因不胜其烦,或被威吓、勒索,旅客付钱摩德收钱。他现在拥有顿努的一栋别墅,格拉斯哥的炸鱼连锁店,还有丰厚的银行存款。事实上,他早在几年前就可以退休了,但他无法忍受失去全额退休金,所以愿意再熬一下无聊,并以除非客人要求,否则不送早餐茶的方式来平衡他的心态;有时遇到他非常想睡,根本就将客人的吩咐抛诸脑后。每次火车一到站,他就欢呼得好像刚服完一段徒刑,离出狱的时间愈来愈近。
亚伦·格兰特透过蒙雾气的火车车窗看着月台的灯光,凝听车轮驶过铁路的叉点变换到另一车道的轻轻嘎啦声。他非常开心,因为结束这段旅程就等于结束了整夜痛苦。格兰特整夜强迫自己不去打开通往走廊的门,清醒地躺在昂贵的被褥上持续流汗。他流汗不是因为火车上的小房间太热( 事实上火车的空调很棒) ,而是因为( 噢,悲惨! 噢,惭愧! 噢,耻辱!)这火车上的小房间代表“一个狭小的封闭空间”。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个干净的小房间,有卧铺、洗脸盆、镜子和各式行李架;依喜好选择的开放式或隐藏式橱柜;还有一个漂亮的小抽屉可以用来放置旅客认为贵重的物品;加上一个可以挂手表的挂钩。但对个中之人,又可悲又像中了邪的个中之人而言,它是“一个狭小的密闭空间”。
“工作过度”,医生是这么说的。
温伯·史崔特医生优雅地翘起二郎腿,一边欣赏着自己不停摇晃的脚,一边说:“放轻松,看看杂志什么的。”
格兰特没法想像自己能怎么放轻松,同时他认为“看看”是一个讨厌的词,而且是令人不屑的消遣方法。看看,是堆一桌子东西,从而满足纯动物性欲望的愚蠢行为。看看,真是的! 这个词光听声音就是某种侮辱,某种轻蔑。
医生孤芳自赏的眼光由摇晃的脚移到鞋子,说:“你平常做些什么? ”
“没有。”格兰特简短地回答。
“你放假时做什么? ”
“钓鱼。”
“你钓鱼? ”心理医生说。显然格兰特的回答诱使他偏离原本的专注自恋。“你不认为那是一种嗜好? ”
“当然不。”
“那你说那是什么? ”
“某种介于运动与宗教之间的事物。”
温伯·史崔特对格兰特的回答报以体谅的一笑,向他保证,要治愈他只是时间问题,时间加上休养。
至少他昨晚真的没把门打开,但是这个胜利却得付出很大代价。他整个人枯竭了,掏空了,像一具半死不活的行尸走肉。“别勉强,”医生说,“如果你要出去,那就出去。”但是,如果昨晚真的开了这扇门,那无疑是宣判自己将无法复原,那将是对非理性势力的无条件投降。所以他躺在那儿淌汗,始终不开门。
但现在,在清晨杳无光线的漆黑里,冰冷而且无可言喻的漆黑里,宛如他所有的美意和价值都被彻底剥落一般。“这就是一个女人经历漫长的分娩过程后的感受。”顺着温伯·史崔特所提示并再三强调的最基本解释,格兰特心想,“但至少她们事后有个小孩当报酬,而我有什么? ”
这值得自傲,他想,很骄傲自己不曾打开一扇没什么理由需要打开的门,噢,老天啊! 现在,他打开这扇门了,勉强地,同时欣赏这个勉强的讽刺性意味。他讨厌去面对这个清晨,他真希望能把自己丢回到起皱的卧榻上继续睡觉。
他提起酸奶酪没帮他提的两只皮箱,卷起未读的期刊夹在腋下,走出卧铺进入走廊。走廊尽头的门被那些会慷慨给小费的旅客行李堵住了,而且几乎要堵到车顶,以至于几乎看不见车门。于是,格兰特往头等车厢所在的第二节客车走,但那个车厢的尽头,也同样堆满了及腰高的特权阶级的障碍物,所以他转而沿着走廊往后门走。此时,酸奶酪从远处尽头他的小隔间探出头来,以确定七B 卧铺的旅客是否知道火车即将到站。不论是七B 卧铺或其他任何床号的乘客,都知道他们有权在火车到站后,慢条斯理地从容下车。但酸奶酪可不想任由旅客沉睡,让自己等在车上耗费时间,于是他大声敲响七B 卧铺的门,然后走了进去。
格兰特走到门口时,酸奶酪正在拉扯穿戴整齐、躺在七B 卧铺上的旅客的袖子,而且粗暴地说:“快点,先生,快点! 我们就要到站了。”
格兰特的影子通过门扉时酸奶酪抬头望了一眼,厌恶地说:“睡死得跟只猫头鹰一样。”
格兰特注意到整个小房间弥漫着浓重的威士忌气味,浓稠得好像可以把手杖插住似的。他捡起酸奶酪摇晃那人时掉落在地上的报纸,再抚平那人的外套。
“你认不出死人啊? ”他说。透过隐隐的倦意他听到自己这么说:“你认不出死人啊? ”仿佛这不是一件什么紧要的事。“你认不出樱草花啊? ”“你认不出鲁本斯的作品啊? ”“你认不出亚柏纪念碑啊? ”
“死啦! ”酸奶酪几近怒吼地叫了起来。“不会吧! 我就要下班了。”
格兰特从旁观的立场注意到,这整件事对没人味、没心肝的葛雷邱先生而言,意义仅此而已。某人离开生命,从温暖、感受和知觉之中离开,进入虚无,而这一切对瞎眼的葛雷邱来说,居然是他下班来不及了。
“怎么办? ”酸奶酪说,“居然有人在我服务的车厢中灌酒灌死了。怎么办? ”
“当然是报警啊! ”格兰特说,同时这才再次感觉到生命本身可以有它的欢乐。格兰特感到一阵扭曲的、阴森森的快感,酸奶酪终于遇到大麻烦了:这个人不但不给他小费,还为他带来二十年铁路生涯中最大的不便。
格兰特再望一眼黑乱发下的年轻脸庞,继续往走廊尽头走去。死人不是他的责任。在他一生中,见过的死人多了,虽然对这件无法挽回的憾事,他也不免心头一紧,但死亡已经吓不了他了。
火车停止了嘎啦声,取而代之的是进站时低沉的轰隆作响。格兰特摇下车窗,望着月台上的灰色标志缓缓由眼前掠过。寒气袭来就像一记重拳猛打到他的脸上一样,他开始无力控制地颤抖起来。
他把两只皮箱放在月台上,心里愤愤不平自己的牙齿抖得像只该死的猴子,他真希望可以暂时死掉。在莫名的内心深处,他也知道比起身处绝境,冬日清晨六点在月台上因寒冷与紧张而颤抖已属幸事,至少代表人还活着。
但是如果真能暂时停止呼吸,然后在较快乐时再活过来,那可就太美妙了。‘“先生,去旅馆? ”火车站的脚夫说。“我用推车帮你推过去。”
他蹒跚走上台阶,然后过桥,脚下的木头发出鼓一样的空洞回声,四周也冒出一阵阵的水气,铿锵巨响与回音从黑暗的地底下传来。他想,关于地狱人们统统猜错了。
地狱不是拿来煎人的温暖好地方,而是一个既大又冷又有回音的洞穴,那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是一个黑暗、有回音的荒芜之地。地狱是一个一夜未眠的自我厌恶后,冬日清晨里百恶掺杂的浓缩物。
他走到空旷的中庭,突如其来的安静抚慰了他。这片漆黑虽然冷冽但很清新,一抹灰晕透露出清晨的气息,雪的气味则透露出位处高地的感觉。天亮之后,汤米会来旅馆接他,然后他们会开车到干净且广大的苏格兰高地乡间,进入广袤、单纯、不变的高地世界。在那里,人们终老在自己的床上,也不会有人会麻烦到想关门。
旅馆餐厅里灯火只亮了半边,幽暗无灯处,排了很多还没铺上桌巾的桌子。他想起过去从未见过这种未经桌巾装点的桌子,一堆脱去白色盔甲的破烂东西。
一个穿黑色制服裙子、绿色绣花紧身毛衣外套的小孩用头在纱门上抵来搓去地玩,看到格兰特似乎吓了一跳。他问早上有什么东西可吃。小女孩从餐具架上拿了调味瓶,一本正经地送到他面前。
“我去叫玛丽来。”她亲切地说,然后消失在纱门后面。
“服务”本身已经失去过去讲究的正式与光鲜,而变成家庭主妇口中的一切从简。但偶尔的一句“我去叫玛丽来”倒也弥补了她以绣花紧身毛衣来代替制服的不得体。
玛丽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胖女人,如果不是奶妈这行不再流行的话,她一定是个奶妈。在她的伺候下,格兰特觉得自己就像个慈祥长辈面前的小孩一样放松。这是一件美好的事,他苦涩地想。在他如此迫切地需要慰藉时,一个胖胖的饭店女服务生给予了他。
他吃了这女人送来的食物,觉得好些了。又过了一会儿,她回来把桌上切好的吐司面包移开,换上一盘小圆面包。
“这些小面包给你。”她说。“刚刚才送到的。现在这种小面包不比从前了,没有嚼头,但怎么说也比吐司强。”
她把果酱推到他手边,看他是否还需要更多牛奶,然后就又离开了。一点都不想再吃的格兰特,将小面包涂上奶油,伸手去拿昨晚没看的报纸。他拿到的是伦敦的晚报,但却一脸狐疑地认不出来。“我买了晚报? ”照例昨天下午四点他就已经读过晚报了,为何七点又买另一份? 难道买晚报已经变成一种反射动作,跟刷牙一样完全自动? 难道一见到灯火通明的书报摊就想买晚报? 难道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吗? 这份报纸是《信号报》——《号角日报》的下午版。格兰特再扫视一遍昨天下午看过的报纸标题,心想,天啊! 怎么老是同类型的新闻。它是昨天的报纸,但它也可以是去年的或下个月的,因为标题永远都和他现在看到的一样:争闹不休的内阁、梅达谷的金发死尸、关税实施、交通阻塞、美国明星莅临,以及街头意外等等。他把食物移开,但当他抽出下一摞报纸时,他注意到“最新消息”那一栏的空白处有铅笔涂鸦的痕迹。他将报纸翻了个面,好看清楚到底是谁在那儿涂来画去。从涂写的状况来看,并不像送报小童的匆忙笔迹,而是有人想写首诗。从他断续的写法来看,显然不是试图想回忆起某首名诗,而是一首原创作品。诗作中漏掉的两行诗句也已经勾好足量的音步了,这种技巧格兰特在学校名列最好的十四行诗写手时,就已经使用了。
但这首诗不是他的。
他突然意识到报纸是从哪里来的。他获得这份报纸,比平常买晚报更不加思索且自然而然得多。当报纸滑落在七B 卧铺的地板上时,他将它和其他杂志一起夹到腋下带走的。他头脑中意识,或者说经历过昨晚之后残余的意识,全都关注在酸奶酪对待那个无助的男子所引发的骚动上。他惟一刻意的行为是用抚平那人的外套来谴责酸奶酪,而为了要空出一只手来,才将报纸连同其他杂志夹在腋下的。
所以那个有着蓬乱黑发和轻率眉毛的年轻人是个诗人,是吗? 格兰特兴趣盎然地看着这些铅笔字,诗人似乎是想用八行诗来表现他的巧思,但他还没有想好第五行与第六行,所以草稿是这样子的:
说话的兽
静止的河
行走的石
歌唱的沙
看守着这道
通往天堂之路
呃,平心而论,这实在太怪了。这是精神谵妄症的前兆吗? 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个诗人酒精迷梦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平凡的。在这名有着率性眉毛的年轻小伙子眼中,自然界万物全变了面目,由如此恐怖的古怪形象所看守的天堂究竟是怎样一种天堂? 是一种遗忘? 而他又为何如此迫切地将遗忘当做天堂? 他为什么不惜经历已知的恐怖来趋近天堂? 格兰特一边吃着新鲜但没有嚼头的面包,一边思考这件事。成人的手写体会如此不成款式,并不是因为他的协调功能不好,而是因为他根本不曾真正长大,还是原来的小男孩。这个推论是从他的笔迹得来的,他的手写字都是习字帖的形式。奇怪的是这么一个有特性的人,居然没有意识地在字体上呈现自己的人格特性。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间就将学校时的习字帖型字体调整成自己喜欢的形式。
格兰特多年来的一个小小兴趣就是特别注重笔迹。
事实上,长期观察字体的结果,令他在工作上受益非浅。
当然,偶尔他的推断也会有错。但一般来说,笔迹为诠释一个人的性格提供了非常好的线索。一个杀人如麻、以强酸溶尸的凶手,刚好写了一手不平凡的好字,那只是特例。正常情况下,继续使用学校书写体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不够聪明,就是因为很少动笔,以至于无法将自己的个性融入字体当中。
此人能聪明地使用这些文字,来描绘天堂之门外梦魇似的危险,显然绝非因为缺乏个性才使得他的字体显得如此稚气。他的个性,他的活力与兴趣,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但跑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是某些更动态的、更外向的地方吧。像“托尼,六点四十五分坎伯兰酒吧见”这类便笺或者日志等等。
但他却又如此地思虑深沉,能够分析并写出通往天堂途中的奇幻国度。思虑深沉又能够跳出事物之外,观察并记录它。
格兰特嚼着小面包,陷入恍惚思考的快感之中。他注意到这些单词以ns和ms结尾的地方都紧紧地连在一起,是表示天性善谎,还是故作神秘? 这个有着率性眉毛的年轻诗人,呈现出不寻常的细腻心思。说也奇怪,容貌透露出来的讯息与眉毛息息相关,只要角度稍稍改动,整个效果就大不一样了。电影界的巨头们从包尔罕或马思威尔的山村里找来几个模样俊俏的女孩,剃掉她们的眉毛,改以不同的眉型,她们立刻就摇身一变,成为来自鄂木斯克及托木斯克的神秘尤物。有一回卡通画家崔柏告诉过他,就是因为眉毛的关系,厄尼·普莱思失去了当首相的机会。“他们不喜欢他的眉毛。”崔柏喝着啤酒,眼里闪露出严肃的神色。“别问我为什么,我只负责画。也许因为这种眉型看起来像脾气很坏的样子,他们不喜欢坏脾气的人,你不相信这种论调,但这确是厄尼·普莱思失去机会的原因。他们就是不喜欢他的眉毛。”有坏脾气的眉毛、高效的眉毛、焦虑的眉毛,正是眉毛为面部表情定下了基调。而就因为倾斜的黑色眉型,使得躺在枕头上的瘦白脸孔,即使死了,仍显得率性。
不过,至少这个人在写下这些诗句时是很清醒的。七B 卧铺的酩酊大醉——令人窒息的空气、皱巴巴的毛毯、地上滚来滚去的空酒瓶,还有架上翻倒的玻璃杯——也许正是他所寻找的天堂,但他在绘制这条通往天堂之路的蓝图时,人是清醒的。
歌唱的沙。
危险但充满某种魅力。
歌唱的沙。某处真的有歌唱的沙吗?(一种隐隐熟悉的声音) 。歌唱的沙。当你走过,它们在你的脚下哭泣,或当风吹起时……一名穿着格子图案的斜纹软呢上衣的男子来到格兰特面前,伸手从盘子里拿起一个小面包,“你看来很自得其乐嘛! ”汤米拉出椅子坐下说。
他把面包掰开涂上奶油,“现在这些东西一点儿嚼头也没有了,我小时候一口咬下去,让牙齿陷入面包里,再用力一拉,看这场牙齿与面包的争战谁胜谁负,如果牙齿顺利获胜,那你就能享受面粉与酵母在口中持续数分钟的美好滋味。可惜现在大不如前了,你就算把面包对折再放入口里也不会噎着。”
格兰特满怀情感地望着他,心想,再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了。这份亲密会令两个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朋友无法分开。他们一起上公立学校,但每次遇见汤米,他都会想起学龄前的那段时光。也许是因为这张清新、漾着粉棕色的圆脸,嵌着一双无邪的眼睛,和当年栗色上衣扣子扣得歪七扭八的那张脸没啥两样吧! 汤米总是不在乎运动衫上的扣子怎么扣才对。
一如往常,汤米绝不浪费时间和精力问候格兰特的旅程与健康,罗拉也一样。他们接受他的现状,就好像他已经在这儿有段时间了,或说他根本从未离开过,还留在上回的来访里。这种气氛自然且悠闲。
“罗拉好吗? ”
“棒极了,她说她胖了点,但我看不出来,我从来不喜欢瘦女人。”
他们都二十岁时,格兰特曾想过娶他的表妹罗拉,而且他确信,罗拉也曾想嫁给他,但在表白之前,爱情的魔力就消失了,而他们也退回到朋友般的关系里。这种魔力已然化作高地夏日漫长的幻梦,化作山坡清晨松针的气味,以及无数个带有甜蜜苜蓿香的薄暮。对格兰特而言,罗拉一直都是快乐的夏日假期的一部分,他们一起学会划桨,一起钓鱼,首次步行去拉瑞格他们在一起,首次登上布雷瑞克山顶他们也是在一起。但是直到那个夏天,那个他们青春期将近尾声的夏天,“快乐”才结晶为罗拉本身,整个夏日都聚焦在罗拉·格兰特一人身上。至今每当他想到那年夏天仍有些心绪难平。那件事就像泡沫绚烂的虹光,轻盈而完美,但因为两人都没有表白什么,所以泡沫至今没有戳破,还停留在轻盈、完美的状态不曾改变。那之后,他们两人分别朝向其他的事、其他的人。而罗拉就像玩跳格子一样,以孩子般的灵巧和漫不经心,不停地从一个人身边跳到下一个。后来,格兰特带她去铁哥儿们的舞会,她认识了汤米·兰金,然后事情就这样子了。
“车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些救护车都在那儿。”汤米问。
“有个人死在火车上,我想大概就因为这事吧。”
“噢! ”汤米话锋一转,带着庆幸的语气说,“还好死的不是你。”
“上天垂怜,不是我。”
“那样的话,你们苏格兰场里的那些人会怀念你。”
“我很怀疑。”.“玛丽,我要一壶浓茶。”汤米说,同时用食指轻蔑地一弹装小圆面包的碟子,“另外,我还要几个这种便宜货。”然后,他转动孩子般认真的眼神凝视着格兰特说:“他们一定会怀念你,他们会觉得少了一个人手,不是吗? ”
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几乎要爆出数月来首次的大笑。汤米为苏格兰场感到惋惜,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他的聪明才智,而是因为他们少了一个人手。他这种“家人”的态度倒与格兰特的上司公事公办的反应异曲同工。“病假! ”布赖斯睁大眼睛,扫过格兰特看起来很健康的身躯,然后一脸嫌恶地回到格兰特脸上来,“有没有搞错啊! 我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是拼命工作,直到救护车把你抬走为止。可是真正地鞠躬尽瘁啊。”要对布赖斯讲医生是怎么说的并不容易,就算说了,布赖斯也不会让他好过。布赖斯全身上下没一条神经,如果不是还有一丝聪明的话,根本就不像个人。当他得知格兰特的病情时,既不理解也不同情,相反,神情里带有一种微妙的暗示:格兰特怠忽职守。因为如此的重病,怎么可能外表看来还是这么好、这么健康? 那必定和格兰特想去高地河流一事有关;可能在他去找温伯·史崔特医生看病之前就已经安排好钓鱼的事了。
“他们会怎么填补你的空缺? ”汤米问。
“可能是提升威廉斯警官吧! 不管怎么说,他等升级也等很久了。”
要把这件事的忠实的威廉斯警官解释清楚,也不是那么容易。你的属下多年来一直把你当英雄崇拜,而你却在他面前为了一个不存在的恶魔成了毫无反击能力的疯子,那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还有,威廉斯也全身上下没有一条神经的,他对任何事都是逆来顺受。告诉威廉斯这件事,然后看着他的态度由崇敬转成关心,甚至怜悯?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把那瓶果酱递过来吧。”汤米说。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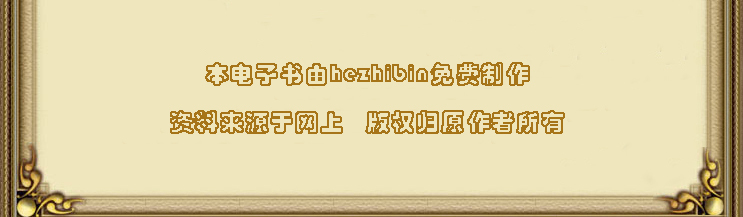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