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04章
|

|
|
|
如果格兰特认为上司会因为他可能提早康复,或因为他对顺手取回的报纸所持的谨慎态度而感到满意的话,那他就错了。布赖斯依旧与他作对,回信里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一派标准的布赖斯作风。格兰特边读信边想,只有布赖斯这种人才能成功地做到鱼与熊掌兼得。他在信中的第一段,就谴责格兰特不够专业,因为他居然会在一个突然发生而且原因不明的死亡事件现场拿走什么东西。然后,在第二段里,他谈到他很惊讶格兰特会拿窃占报纸这种小事来麻烦忙碌的警方。还说到正是因为格兰特现在离开工作岗位,才使得他缺乏判断力和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没有第三段了。
从这张熟悉的、薄薄的办公室信纸中所透露出来的强烈讯息是:格兰特已经被排除到外围了。其实这封信真正要说的是:“我实在无法想像为什么你,亚伦·格兰特,会想要麻烦我们,不论是报告你自己的健康状况,或是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事实上,我们对你的健康没有兴趣,你也不必关心我们的工作。”他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叛徒。
只有现在,在读了这封冷嘲热讽的信,并“享受”了让人在他面前“砰”的一声把门摔上后,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除了良心上觉得该向单位表白不小心拿了报纸,其实也是想一直掌握七B 的讯息。他的信以及那份歉意,就是一条通往信息的通道,因为七B 已经不是新闻了,所以想从报上得到消息已没希望。火车上每天都有人死亡。他们根本不会再感兴趣。对新闻界而言,七B 等于死了两次,一次是他实际的死亡;另一次则是就新闻价值而言。但就他而言,他一直想知道更多有关七B 的事,也许他自己没有察觉,但心里却希望他的同事就这件事坦白相告。
他一边把信纸撕碎丢人垃圾桶里,心里一边想着,虽然他跟布赖斯不太熟,但还有威廉斯警官啊! 谢天谢地,还有一个忠实的威廉斯。威廉斯可能会纳闷为何一个像他这种阶级,拥有丰富阅历的人,会对一个短短瞥过一眼的无名死尸感兴趣?当然,他也可能觉得这很无聊。不管怎么样,他一定得跟威廉斯谈谈。所以他写了一封信,问威廉斯是否知道一个礼拜前的星期二晚上,在开往高地火车上死亡的年轻人查尔斯·马汀的验尸结果,以及在验尸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任何有关这个年轻人的事。然后就是亲切地问候威廉斯太太以及安琪拉和伦纳德。
接下来两天,他处在一种急切等待威廉斯回信的快乐中。他检查不能钓鱼的突利河谷,一个池塘一个池塘的检查;修补那些停泊在德伍湖小船的缝隙。在牧羊人格雷厄姆,以及紧跟在后的赞格和汤格的陪同下,他走上山坡;他聆听汤米叙说在自家与山丘侧面之间弄一个九洞高尔夫球场的计划。第三天在邮件送达的时间,他急切地往回家的路上赶,这种急切是他以前将诗作投稿到杂志社后所特有的心情,十九岁之后再没有过了。
但当他得知没有他的任何信件时,无法置信的心情所带来的沉重并不亚于少年时收到退稿。
他提醒自己,自己实在太不理性了( 格兰特的心里总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事实上,验尸过程和警察局没任何关系,他甚至不知道哪个部门接手这项工作,威廉斯还得去查出来。而威廉斯也有他自己的工作,一个全天候二十四小时的工作。因此,要他放下手边的事,只为了去满足某个正在度假的同事不经意想起的不重要问题,那实在太不理性了。
他又等了两天,信来了。
威廉斯在信中说他希望格兰特别已经开始渴望回来工作了,他应该休息,同时每个同事也都希望他能得到充分的休息而且病情好转( 不是每个人! 格兰特心里想起布赖斯) ,他们都非常想念他。至于查尔斯·马汀,对于他个人或他的死亡,如果这是格兰特想知道的,其中并没有什么神秘之事可言。查尔斯·马汀只是后脑勺撞到瓷制洗手台边缘,虽然靠着自己的手和膝盖爬回床上,但很快就因为内出血死亡。而他之所以会后仰摔倒,是因为他喝了纯威士忌的关系。喝的量虽不至于使他烂醉,但却足以令他的头脑混沌不清。另外,火车转向所造成的车身倾斜,也是致使他跌倒的原因。关于死者本身,也没什么难以理解之处。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一般的法文报纸;亲友仍住在靠近马赛的家乡,只是很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了。他当年是因为一时嫉妒捅了女友一刀,惹上麻烦才离家的。现在他的亲人已经寄了丧葬费来,所以他不会葬在乞丐的墓园区里。
这封信不但没有为格兰特带来慰藉,反而更激起他想知道真相的渴望。
他推算好威廉斯正快乐地为自己准备好烟斗和报纸,威廉斯太太在旁边缝补,而安琪拉和里欧正在做着家庭作业的时间后,打通私人电话给他。当然,威廉斯有可能下班的时间还在外面办案,但也有可能现在正待在家里呢! 他在家。
适当地表达了对威廉斯回信的感谢之后,格兰特说:“你说他的家人寄钱来埋葬他,难道没有人过来认尸? ”
“没有,他们只认了照片。”
“活着时的照片? ”
“不,不,是尸体的照片。”
“没人亲自来伦敦认尸? ”
“好像没有。”
“这就怪了。”
“如果他是一个坏孩子,那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是家族中的坏孩子吗? ”
“不,这倒没有。”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
“技工。”
“他随身带着护照? ”
“没有。只有一般的报纸和一些信件。”
“噢,他有信件啊? ”
“就是平常人们会带着的两三封信。有一封是来自一个女孩的,她说她要等他。”
“那些信是用法文写的? ”
“是的。”.“那他有什么钱? ”
“等等,我找一下我的笔记。呃,纸币有二十二镑、十镑,然后硬币有十八便士和两便士。”
“都是英国钱? ”
“对啊! ”
“从他没有随身带着护照和用英国钱来看,他在英国应该已经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来认他? ”
“他们也许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毕竟这件事情并不算非常公开。”
“他在英国没住址? ”
“没有。这些信并没有用信封装,只是放在他的皮夹里。他的朋友可能都还没有出现呢! ”
“有没有谁知道他要去哪里? 或是为什么要去那里? ”
“没有,似乎没有。”
“他带了些什么行李? ”
“只是一个过夜的皮箱,里面有衬衫、袜子、睡衣和拖鞋,上面没有干洗店的标志。”
“什么? 为什么? 难道这些东西都是新的? ”
“不,不是,”威廉斯对格兰特明显的怀疑觉得非常有趣,“都已经穿得很旧了。”
“拖鞋上有制造商的名字? ”
“没有,是那种厚厚的手工制拖鞋,你会在北非的广场或是地中海海滨看到的那种。”
“还有什么? ”
“皮箱里是吗? 呃,还有一本法文版的新约圣经和一本黄封皮的平装本小说,两本都很旧了。”
接线生说:“你的三分钟通话时间到了。”
格兰特延长了三分钟,但是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七B 资料。除了他没前科——不管是在法国( 他捅女友一刀似乎只是纯粹的家务事) 还是英国,其他的事没人知道。
这的确是一个典型,有关他的种种惟一已知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对了,”威廉斯说,“我在回信时忘了回答你信中附注的事情。”
“什么附注的事? ”格兰特问,随即想起他曾写下他事后想到的事:如果你有空的话,也许可以问一下特工部门是否对一个叫阿奇·布朗的人有兴趣,他是苏格兰爱国主义者。
去问泰德·汉纳,就说是我问的。
“噢! 对,对,有关那个爱国主义者,你有空处理这件事吗? 它并不是那么重要。”
“对了,大前天我碰巧在白厅班车上遇见你提到的那个人,他说他个人对你的那只鸟没有意见,但却非常想知道大乌鸦是什么,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
“我想我知道,”格兰特愉快地说,“你告诉他我会尽力为他们查明,就当做是假期作业好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先不要操心工作,好好养病。只要尽可能在这个单位因为没有你而关门之前回来就好了。”
“他穿的鞋,鞋是哪里做的? ”
“谁穿的鞋? 噢,是卡拉奇做的。”
“哪里? ”
“卡拉奇。”
“噢! 对,你刚刚是这么说的。他似乎常常到处跑来跑去。圣经的扉页也没有名字? ”
“我想没有。我想我在记这些证物时并没有写到这一点,噢,有,有,我记下来了:没名字。”
“在失踪人口栏上也没有任何和他特征相似的人? ”
“没有,没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跟他特征接近的,他并不是失踪人口。”
“真费心了,麻烦你查这些小事,你也没不客气地要我回我的小溪钓鱼去。哪天我会报答你的。”
“你小溪里的鱼容易上钩吗? ”
“根本没有什么小溪,鱼都躲在池塘中最深处了,这正是为什么我会开始对这种忙碌的西南分局根本不会在意的小案子感兴趣的原因。”
但他知道这并不是事实。他并非因为无聊才对七B 的案子起了兴趣,这是——他几乎要这么称呼——某种一体相生的感觉。他对七B 有一种奇特的认同感,倒不是说他和七B 有何相同之处,而是因为格兰特对此人有一种兴趣上的认同。单就格兰特只见过他一次,且对他一无所知的事实看来,这显然非常不理性。或许他认为七B 和他一样在与恶魔搏斗? 是否他这种纯属个人的兴趣,而让这场竞赛开打? 他一直认为七B 所谓的天堂就是一种遗忘,他会这么认为是因为浓重的威士忌气味弥漫了整个卧铺,但这个年轻人并未醉得不省人事,事实上只是微醺而已。他摔倒,撞到坚硬厚实的圆洗手台,这种事是任何人都可能碰到的。他如此不寻常地护卫的天堂也许根本不是遗忘。
他把注意力转回威廉斯正说着的话头上。
“什么? ”
“我忘了告诉你,卧铺服务员认为马汀在尤斯顿上车时有人为他送行。”
“为什么你刚才没说? ”
“噢! 我只是想反正这也帮不上什么忙,只不过是卧铺服务员随口抱怨而已,据在场的警官告诉我,他视这整件事是对他个人的侮辱。”
酸奶酪似乎处理每件事都非常形式化。
“他是怎么说的? ”
“他说在尤斯顿,他走过走廊时曾看见马汀的卧铺车厢内有另一个人。他没看见这人的脸,因为当时门半开着,而马汀正面对着他,因此他惟一注意到的是马汀正跟另一个人讲话。他们似乎非常快乐而且友善,他们在谈论抢饭店的事。”
“什么? ”
“你知道? 那个验尸官的反应也是‘什么’? 铁路服务员说他们在谈‘抢凯利’的事,而既然没有人会去抢那支叫凯利的足球队,那这个凯利一定是家饭店了。似乎苏格兰的饭店不是叫瓦佛利,就是叫凯利多尼亚,大部分人简称为‘凯利’。但他说他们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这就是他所看到的送行? ”
“对啊! 就这样。”
“也许这根本不是来送行的人,只是在火车上偶遇的朋友而已,可能是看到卧铺外的名字,或经过他身边时认出来的。”
也许是这样。但如果真是如此,这个朋友隔天早晨应该会再度出现才是。“
“不尽然! 特别是如果他的车厢比较远,而搬动尸体又是如此地谨慎。我很怀疑有哪位乘客知道有人死了。同时就我所知,救护车是在整个车站的旅客全部离开后很久才来的,因为救护车到达时,我都快吃完早餐了。”
“是的。不过卧铺服务员说他之所以认为另外那个人是来送行的,是因为那个人衣帽整齐。他说,大部分人去火车上的咖啡座都是不戴帽的。乘客一到他们的卧铺,第一件事就是把帽子挂到挂钩上去。”
“提到卧铺上的名单,他这个卧铺是怎么订的? ”
“用电话订的,但他自己来拿票,至少来拿票的人是一个瘦削黑发的人,他是一个礼拜前预订的。”
“好,你继续说有关酸奶酪的事。”
“有关谁? ”
“有关那个卧铺服务员。”
“他说火车离开休斯顿约二十分钟之后,他走进车厢收票,当时马汀人在洗手问,但他卧铺的票根和通往史衮的去程车票预先放在镜子下的小柜子上了。他把票收了,并在旅客名单上划掉他的名字。在经过洗手间时,还敲敲门问:‘你是七B卧铺的客人是吗? ’马汀说是。服务员说:‘我已经收了你的车票了,谢谢! 你明早喝茶? ’马汀回答:‘不用了,谢谢! 晚安。”’“这么说他有回程票哕! ”
“有,他回程的那一半放在皮夹里。”
“那么这事似乎就非常明显了。没有人来询问关于他的事或认尸,可能因为他是出来旅行,没有谁预期他会很快回来。”
“可能就像你说的这样,加上消息的传播范围有限,我想就连他的家人也不会大费周折在英文报纸上发布他的讣闻,也许他们只在有人认识他的地方报纸上刊载一条消息意思意思而已。”
“那验尸官又怎么说? ”
“呃,还不是一样。死前吃了一点东西,胃里有大量的威士忌,血管里也有一些,够他身体受的了。”
“完全没有提到他是一个酒鬼? ”
“噢,没有,没有提到诸如此类的堕落情况。头和肩膀以前受过伤,除此之外还是个健康的人。但不算很强壮就是了。”
“能肯定他以前受过伤? ”
“是的,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是说跟他这次的死亡没有关系。他曾有过头骨破裂,锁骨也曾经断裂。
如果我问你,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案子会引起你这么大的兴趣,会不会不礼貌或太唐突? “
“那么,就帮助我吧! 警官。如果我知道为什么,我会告诉你的。我想我是越活越回去,越像小孩子了。”
“我倒觉得比较像是你觉得无聊了。”威廉斯同情地说,“像我,从小在乡下长大,从来不会想到去看草生长,乡下一直是个被高估了的地方。在乡下事事都很遥远不方便。我想一旦你的小溪开始流动了,你就会完全忘记马汀先生这档子事了。我们这里现在是倾盆大雨,所以你们那边大概不久就会有雨了。”
事实上,当天晚上突利谷并没有下雨,但却有其他事情发生。在持续的寒冷里吹起了轻微的风,既柔软又温暖;阵风与阵风间的空气显得潮湿且厚重;地面湿滑,雪水从山顶上流下来填满了河床;竞相奔驰的黄泥水带来的鱼儿跳过暗礁,在石头与石头间迎着倾注的水势向上溯源,在阳光下闪着一亮一亮的银色。派特从装虫子的盒子里拿出他珍贵的发明( 盒子里还有他自己的分格) ,非常正式而且仁慈地交给格兰特,就像校长颁发证书给学生一样。他说:“你会好好照顾它,是不是?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做好的。”这东西就像他妈妈说的,是某种很可怕的东西。格兰特心想,这东西看上去蛮像女人的帽子,但是他很清楚他是由众多人中被遴选出来,做为惟一配得上这项荣誉的接受者。因此,他怀着适度的感激接受,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怪鱼饵收进自己的盒子里,希望派特不会监督他使用。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次他要挑选新虫儿时,就会看见那个可怕的东西,心里随即涌起一股暖意,只因为他的小外甥对他的肯定。
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问在突利谷,面对着黄褐色的漩涡,心里既愉快又轻松。河水像啤酒一样清澈,上面还有白色的泡沫,水的流动听起来像音乐。他的日子过得惬意无比。潮湿柔软的空气形成露珠,滴在他斜纹软呢的衣服上;榛树树枝上的水则流入他的颈背里。
几乎一整个礼拜,他脑子想的、口中说的、嘴里吃的都是鱼。
然后,有一天傍晚,在吊桥下他最喜欢的池塘里,他的安心与满足被打破了。
他在水里看到一个人的脸。
在他的心脏还没有从嘴里跳出来之前,他就意识到这张脸并不存在于水的表面,而是在他的眼睛里。那是一张死白的脸,有着轻率的眉毛。
他嘟囔着骂了句脏话,然后对着池塘远处狠狠地抛出钓竿。他和七B 已经没瓜葛了。过去他在对七B 的情况全盘误解下生出对七B 的兴趣。他认为七B 和他一样深陷恶魔的罗网里,为自己勾勒出一张完全荒谬的七B 图像。结果七B 的卧铺隔间里,酒徒的天堂不过是倾倒的威士忌酒瓶。他不再对七B 感兴趣:他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年轻人,身体健壮却可怜地在一次夜车旅程中以一种相当没尊严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他摔倒后用手和膝盖挣扎攀爬,直到断气为止。
“但他写了这几句关于天堂的诗。”一个声音从他的心底升起。
“他没有,”他对着从心底升起的声音说。“没有一丁点证据证明是他写了这些诗句。”
“还有他的脸,一张不平凡的脸,这是一张一开始就征服了你的脸,早在你开始思索他的天堂之前。”
“我没有被征服,”他说,“因为职业的关系,我自然而然会对人感兴趣。”
“真的吗?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这间充满浓重威士忌气味的卧铺里倒下的是一个肥胖的商人,他脸上的胡子像没修好的篱笆,一张脸有如煮得太熟的布丁,你仍然会对他有兴趣? ”
“有可能啊! ”
“你这个不诚实的混蛋。从你看到他的脸,注意到酸奶酪对他的粗暴的态度的那一刻起,你就是七B 的拥护者。你从酸奶酪的魔掌中拯救他并帮他把外套抚平,就像个母亲整理他小孩的披肩一样。”
“闭嘴! ”
“你想知道关于他的事,并非你认为他的死有何疑点可言,而纯粹是因为你想知道关于他的事。他年纪轻轻但已死去,曾经轻率而且活生生过。你想知道他轻率而且活生生时是什么样子。”
“好吧! 我想知道。我还想知道谁将是林肯郡的新宠,我的股票在今天的开盘价多少,还有珍·凯斯的下一部电影,但我不会因为其中任何一件事而失眠。”
“不会,不过你也不会在你跟河水之间看到珍·凯斯的脸。”
“我并不想在我和河水之间看到谁的面孔,也不会有任何东西出现在我跟河水之间。我来这里是为了钓鱼,没有任何事能妨碍我这个目的。”
“七B 也是为某件事北上来的,我怀疑那是什么? ”
“我怎么知道? ”
“不管怎么样,绝对不会是钓鱼。”
“为什么不是? ”
“没有人会跑五六百英里来钓鱼,却不带任何钓具。
如果他还灵光,他至少会带着自己喜爱的鱼饵,即使他打算租钓竿。“
“是的。”
“也许他的天堂是提南欧,你知道的,就是盖尔人的那一个,那是很有可能的。”
“为什么很有可能? ”
“据说提南欧岛远在西边,远离着最外围的岛屿。它是个青春之岛,永恒的青春之岛,是盖尔人的天堂。但到底是什么护卫着这通往天堂之路? 似乎是有着歌唱的沙的岛屿,还有岛屿的石头站着就像人在走路一样。”
“还有会说话的野兽? 你发现它们也在外岛? ”
“我发现了。”
“你发现了? 它们是什么? ”
“海豹。”
“噢! 走开,别烦我,我现在忙着钓鱼。”
“你也许是在钓鱼,但是你什么鬼东西也没有钓到。
你的钓竿可以收起来了。现在你听我说。“
“我绝不会听你说。好吧! 就算这些岛屿中有歌唱的沙,有能行走的石头,也有饶舌的海豹,那都跟我没关系,而且我也不觉得跟七B 有什么关系。”
“没有? 那他来北方干什么? ”
“也许是来埋葬一位亲戚,来和一个女人幽会,或者来攀岩! 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为什么要在乎? ”
“他将会在某处的凯利多尼亚饭店停留过夜。”
“他没有。”
“你怎么知道他会在哪里过夜? ”
“我不知道,没人知道。”
“如果他打算在一家叫瓦佛利的旅馆过夜,怎么会有人荒谬到说他要去‘抢凯利’? ”
“如果他是要去格拉达,我打赌在格拉达绝对不会像内地有旅馆叫凯利多尼亚这种难听的名字。如果他去格拉达一定会经由格拉斯哥和欧本。”
“不尽然。经史衮去,路程又短又舒服。他也许讨厌格拉斯哥,很多人都不喜欢那个地方。要不然你今晚回到住处时就打个电话给史衮的凯利多尼亚饭店,查查看是否曾有一个叫查尔斯·马汀的人打算在那里过夜? ”
“我才不做这种事! ”
“如果像你这样拍打河水,会把河里的鱼都吓死的。”
晚餐时他心情郁闷地回家了,除了没抓到鱼,还失去了平静。
一天的工作全做完了,小孩也上床睡觉了,客厅里一片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他的眼光从手上的书游移至房间另一端的电话,电话摆在汤米桌上,静静地放在那里,吐露出一股潜伏的力量,不断地对格兰特招手。只要他拿起话筒,就可以跟美洲太平洋沿岸的人讲话,跟大西洋中每个人迹罕至的小岛上的人讲话,跟地表上空两英里的人讲话。
他也可以跟史衮的凯利多尼亚饭店的人讲话。
他压抑着这个念头,心里的愤怒渐渐升起,这样过了一小时。然后,罗拉去准备睡前酒;汤米把狗放出去;至于格兰特,则像个橄揽球球员一样冲到电话旁,而不是以文明人正常地走过房间的速度。
他拿起话筒才想到自己根本不知道电话号码;他放下话筒,觉得自己获救了。他起身想要回去看书,没拿起书却拿起电话簿。如果他不跟史衮的凯利多尼亚饭店的人讲话,今晚就得不到宁静了。虽然这个代价有点愚蠢,但要得到宁静可真是够便宜的了。
“请问是史衮1460……凯利多尼亚饭店?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两个礼拜前是不是有一个叫查尔斯·马汀的人跟你们订房间? 噢,好,谢谢,我等。没有? 没这个名字? 噢,非常谢谢,很抱歉打扰你了。”
那就这样了,他想。话筒“砰”的一声放下来。就他而言,七B 的事到此告一段落了。
他喝了令人舒适的睡前酒,然后上床,清醒地望着天花板。他关上灯开始使用自己对付失眠的独家秘方:假装自己今晚必须熬夜。他早在很久以前就发明出这套方法了,前提很简单:人类的天性就是想去做被禁止的事。直至目前为止这个方法始终很奏效。他只要假装不能睡觉,眼皮就会开始下垂,这种假装正好可以除去睡眠最大的障碍:越是害怕睡不着就越容易睡不着。
他的眼皮像往常一样垂下,但脑子里有个铃铛不断地响着,就好像笼子里的一只老鼠一样:
说话的兽
静止的河
行走的石
歌唱的沙
能够完全静止不动的河流是什么? 又跟那些岛屿上的什么东西有关? 不会是冰冻的河水吧,岛上并不多雪或霜,那会是什么? 是河水流进沙里,停止在那儿吗?不,发挥点想像力吧! 静止的河,静止的河? 也许图书馆馆员会知道,在史衮一定有大型的公共图书馆。
“我以为你对这些没兴趣了。”那个声音说。
“你去死吧! ”
他是一个技工,这是什么意思? 技工,这个字眼有各种可能性。
不管他是做什么的,他都成功到有能力坐头等卧铺。
过去这可算是百万富翁的享受呀! 而他花了这些钱,从他所携带的行李箱来判断,只是为了一趟短暂的拜访。
是拜访一个女人? 也许! 是那个承诺要等他的女孩? 但她是法国人。
一个女人? 没有一个英国男人会为一个女人跑五百英里,但法国男人就有可能,尤其是一个会因女友眼睛乱瞄而捅她一刀的人。
说话的兽
静止的河
噢,天啊! 不要再来了。你的想像力必须停止了,以免你兴起一股必须写下某些东西的冲动。如果你的想像力过于活跃,你会进入一种被某些想法盘踞而无法抽离的境地,你会因为自己所勾勒的庙堂的美妙台阶而狂喜不已,愿意拼命工作赚几年钱,空出假期,好真的到那里去。
再强烈一点的,可能会变成一种强迫性的热情,让你放下所有事情,去寻找那个令你心存挂念、挥之不去的东西:比如一座山、博物馆里的绿石头像、一条地图上没有标明的河,或是一点点帆布。
七B 勾勒出的图像到底诱惑他到何种地步? 足够让他展开一段寻找的旅程? 还是只够让他写下来? 只因为他写下了这些铅笔字。
当然这是他写的。
这些文句是属于七B 的,就好像他的眉毛和他那一手男学生的字体,都是属于他的。
“那些字体? ”那个声音挑衅地说。
“是的,那些字体。”
“但他是马赛人。”
“他有可能在英国受教育,不是吗? ”
“再过几分钟你就会告诉我他根本不是法国人。”
“是啊! 再过几分钟我就会这样做了。”
但是显然,这是进入了幻想的境地里。七B 根本毫无神秘可言,他身份明确,有家人,还有一个等着他的女孩。
他确确实实是个法国人,他用英文写下这段诗句,纯粹是偶发的。
“他也许在克拉伯罕上学。”他极度厌恶地对那个声音反驳说,然后立刻进入梦乡。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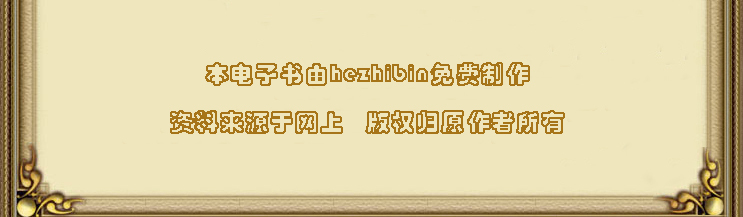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