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08章
|

|
|
|
罗勃决定利用这回在外留宿一晚的行程,尽可能地拜访对案情有帮助的人。
首先,他想去见见他的老朋友。眼下这种状况,没有人会比他求学时代的老友凯文·麦克德默更值得他去拜访了。对犯罪案件没有人比凯文·麦克德默知晓了解得更多;而且身为一个著名的辩护律师.他对人性的认知不仅广远,还是因汇集多方角度多年经验而独特精辟的。
至于麦克德默此刻是否会因高血压疾病而英年早逝,或是仍心康体健地足以在他七十岁时荣登大法官宝座,机会是均半的。罗勃当然希望机会是后者,他其实相当欣赏凯文。
当年在学校时,因为他们双方都有意修习法律而彼此认识,而最后他们能成为朋友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互补。对那爱尔兰人而言,罗勃沉着镇定,风趣并具有刺激性,而且——当他疲累时——非常静谧平和。对罗勃而言,凯文则具有凯尔特族人那种颇富绚烂异国风情的吸引力。罗勃对前景的期待不外乎回到他生长的乡间小镇执业,理所当然地过守成不变的生活;凯文的野心则是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惊天动地地做些改革。
截至目前为止,凯文是尽其所能地大展才华,可是推动改革显现成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过在他努力不懈、强硬中微带狠辣的过程中,也多多少少在法律界掀起一些波浪。有凯文·麦克德默出席的案子见报率会比平时多上百分之五十——造成的效果,远非金钱所能估计。
他已经结婚了——刚开始时乃为取其方便,但是桩快乐姻缘——在维桥附近有栋舒适的房子;有三个强壮的儿子,清瘦、黝黑、活泼,一如他们的父亲。为了进城工作方便,在圣保罗教堂庭院区有一间小公寓。从那公寓,套用他的话,“可以低头俯看安妮皇后。”只要罗勃在城里——次数并不多就是了——他们总一块儿吃饭,地点不是在那小公寓,就是在凯文可以找到好的红葡萄酒的附近餐馆。公务之暇,凯文喜欢品尝红葡萄酒,看生气勃勃的华纳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
凯文今晚要出席一场法律界晚宴,这是当罗勃从米尔佛德镇打电话跟他联络时他秘书告诉的;不过,他会很高兴有这么个正当理由躲开那些演讲,所以请罗勃晚餐后直接到圣保罗教堂庭院区的公寓等他。
这是好现象,如果凯文是从一顿晚宴回家的话,他必定是放松而且准备好享受夜晚的舒适——而不是像往常直接从法院回家时那样,满脑子仍是重重案件,不肯休息。
同时他要打电话给苏格兰场的格兰特探长,看他是否能在明天早上抽出时间见个面。他必须弄清楚苏格兰场对这起事件的态度;也许他们双方受着同样程度的苦恼,只是不在同一边而已。
在佛特肆坷区哲名街上坐落着一栋爱德华时代的老建筑,是自他少年时代起被允许独自到伦敦以来,每次留宿下榻的地方。这时,他们像欢迎子侄般接待他,给他“他上回来住的那问房”:一个光线微微昏暗但舒适的小房间,有一张高及肩膀的床及长毛绒小沙发;随后奉上置有超大号棕色普通茶壶的茶盘,上面另有乔治时代样式的奶油银瓶、盛在一个便宜玻璃碟子里大约一磅重的糖块、一个绘有花纹小城堡的杯子、一个红金双色小盘,以及一把有斑点的棕色把手餐刀。茶和茶盘同时替罗勃提起了精神,消除了旅途的疲劳。他带着几分自许,神采奕奕地踏入城里的街道,进行他的探险访查。
为了探询有关贝蒂- 肯恩的事实,下意识中,他来到一个原本有建筑物的空地;她父母就在这儿因空投炸弹掷中,而连同建筑一起爆裂粉碎。那是个已经过整理却仍一片光秃的空地,正等着进一步的建设。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出过去的痕迹。在周围,有着幸免袭击的房子独自沾沾自喜地矗立着,像未成熟的孩童不了解灾难的意义,只知道也只关心灾难曾怎样惊险地擦身掠过而庆幸着。
宽阔街道的另一侧是一排已站在那儿超过半世纪的小商店。罗勃穿过街道,走向那排商店中的一家烟草杂货店买香烟。一个兼卖烟草杂货报纸杂志的地方是探听茶余谈资的好处所。
“当那发生时你在场吗? ”罗勃问,头朝门的方向斜了斜。
“当什么发生? ”有着红润面庞的矮小男人问,他似乎已经习惯那片地变成空地而忘了以前的景观了。“噢,那场意外灾难? 没有,我因公外出了。我曾是典狱长。”
罗勃解释道他是问当时他是否就有这家店了。
嗯,是的,是的,这店面那时就有;而且在事件发生前很久就存在了。他在这区长大,然后自父亲手中接掌了这生意。
“那么,你熟悉这附近的人哕。你记不记得曾当过那栋大厦管理员的那对夫妇? ”
“肯恩夫妇? 我当然记得,为什么不呢。他们当时整日进出这家店。他早上来买报,不久之后她来买烟;然后他再来买晚报,而她第三次进来买烟;接着当我儿子放学回家帮忙看店后,我就和他到附近酒馆去喝一杯。你也认识他们吗,先生? ”
“不认识。但是我前些日子听到某个人提起过他们。
那整个地方是怎么被摧毁的? “
矮小的有粉红面颊的男人嘲弄似地啧喷出声。
“偷工减料。就是这样,那是一栋被偷工减料的建筑。
炸弹掉落在那区——肯恩夫妇就是那样送命的,他们躲在地下室以为安全了——整个建筑就像一叠纸卡般四散飞去。挺叫人震惊害怕的! “他抚平一旁的晚报。”她运气背啊,整个星期就那一晚她和丈夫待在家里,而炸弹就选那晚掉下来。“他似乎自得于这样的讥诮。
“那她通常在哪儿呢? ”罗勃问。“她在什么地方打夜工吗? ”
“工作! ”矮小男人非常轻蔑地说。“她! ”然后,恢复平静后说:“嗯! 对不起,真的。我几乎忘了他们也许是你的朋友——”
罗勃赶紧向他担保他对肯恩夫妇事情的探询纯粹是为研究用的。有人提起过他们是那栋大厦的管理员,如此而已。如果肯恩太太不是晚上出去做夜工,那她做什么去了? “当然是去享受游乐去哕。是啊,即使在战乱开始后,人们还是有办法找到乐子的——只要真想努力去找的话。
肯恩先生希望她能跟他们的小孩儿一同到乡下避难。可是她肯吗? 嘿,当然不肯! 她曾说,在乡下过不上三天就会要了她的命。她甚至没去看过被遣送到乡下去的他们的小女孩儿。那是政府当局的安排,很多小孩儿那时都这样被送往安全的地方。就我说,她是巴不得小孩儿被送走,那样她就可以没有顾忌地每个晚上出去跳舞了。“
“她跟谁去跳舞? ”
“军官呀,”矮小男人简单明了地说。“比看着草长大要有趣些吧。在这儿要提醒你一下,我并不是说那有什么坏处,”他匆忙地改正。“她已经过世了,我不想讲她现在无法为自己辩解的事。可是,她不是一个好母亲也不是个好妻子,却是最确实不过的事实了;没有人会对这点提出抗议的。”
“她漂亮吗? ”罗勃问,心中想着曾浪费在贝蒂母亲身上的怜悯。
“某一方面来说,是的。她是那种闷骚型的。你无法想像她活泼起来时的样子,顶泼辣刺激的。”
“她先生呢? ,”
“他啊,他算不错的,他叫柏特·肯恩。值得有比那女人好的运气。是那种好人的他。非常喜欢那小女孩儿。当然惯坏她啦。她想要什么他就想办法儿给弄到;不过她倒是个好孩子,老实讲,蛮谨慎端庄的。唉,是啊,柏特值得生命中有更好的际遇,而不是那只懂享受的妻子和一个虚情假意的小孩。好人一个啊,他——”他仿佛思绪回到了过去似的盯着路那边的空地。“他们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找他。”他说。
罗勃付了香烟钱,离开店铺,走到街上,心情既感到伤感又有些释然。伤感是为了柏特·肯恩,一个原应有较好际遇的好人;而释然是因为贝蒂·肯恩的母亲不是他原来想像中那样的人。到伦敦的这一路上,他一直为那死去的女人遗憾着:一个为了女儿的好处着想而宁愿受苦的女子;他几乎无法忍受去想像那受苦女子钟爱保护的女儿是像贝蒂·肯恩那样的孩子。而现在他完全释怀了。贝蒂‘肯恩的母亲正是那种如果他是上帝他就会编派给贝蒂·肯恩当妈妈的那种女人;而她呢,正就该是她母亲会有的女儿的样子。
“一个虚情假意的小孩。”这回,乌殷太太会怎么反应呢? “她哭过,因为不喜欢这里的食物,但我不记得她曾哭着要妈妈。”显然也不曾为那全然溺爱她的父亲哭过。
回到旅馆,他从简便的行李箱中拿出那份《艾克一艾玛》报纸,在佛特肆坷的旅馆饭厅独自晚餐时仔细阅读第二版的故事。开头是海报标语似的叙述:一个四月的晚上,一个女孩)LX 穿着内衣、鞋子,两手空空地回到她的家。她离开过家,一个明朗快乐的女学生——通篇文章极尽哗众取巧之能,堪称此类文体之一绝。
它完全达到想要的目的:用一个故事喂养不同需求层次的广大读者群。对寻找情色的,它提供了女孩儿单薄的衣着;对惜花怜月的,它提供她的年轻和甜蜜;对同类平侪,它提供了她无助的可怜境况;对悲观者,它提供被殴打的细节;对受阶级歧视待遇者,它提供巨墙深院里的高耸屋宇;对英国一般没脑筋的热心大众,它提供警察即使没有收受贿赂,也有怠惰拖延之嫌,正义因此被湮没掩盖。
是的,这是一篇相当聪明的文章。
当然,故事本身对报社而言是天赐良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立刻派人随雷斯利·乌殷回家做进一步采访。但罗勃觉得,在《艾克一艾玛》这样的精力下,即使破碎的片段也能被写出精彩完整的故事面貌。
它必定是个冷酷专断的事业,以独家形式来报导那些与人类弱点相互唱和的故事。他继续翻看这份报纸,尝试搜集他们是怎样以喧嚣闹腾为主旨来编排的规则。他注意到即使在“施捐一百万”这样的标题下,提到的内容是一个无耻的老人为了逃避所得税所玩的伎俩,而不是一名向上男子努力凭着一己之力所积聚财富的捐献。
这一切都让他恶心。他将报纸放进公事包,提着它走向圣保罗教堂庭院区。在那儿他看到那位“办公室门外桌畔”的女子,戴着帽子,麦克德默先生的秘书。她被交代开门让他在公寓等着;她让他进去,并告诉他在壁炉旁的茶几上有威士忌,柜子里另有一瓶;不过,倘若你问,她会告诉你最好不要让麦克德默先生知道,否则他会喝个不停忘了去睡觉,到第二天早上她可得烦恼该如何叫醒他了。
“不是因为威士忌,”布莱尔说,对她微笑,“是因为他身上流的爱尔兰血液。爱尔兰人讨厌起床。”
这让她在门旁顿了一顿,显然从没听过这种说法。
“我不会怀疑,”她说。“我老爸也一样,他正是爱尔兰人。不是因为威士忌,而是种原罪。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这是栋叫人喜爱的小公寓,温馨友善,在城市繁忙的交通巅峰时间过后,有着一份可人的宁静。他为自己倒了杯酒,到窗边俯瞰安妮皇后雕像;目光像往常一样停在那座大教堂上,再一次疑惑着整个建筑看来像是漂浮在基座上似的,却又那样平衡和谐,可以轻轻拾起垂摆在手掌,卜。然后他坐下来,紧绷的神经在此刻终于得到纾解,这才意识到自早上去看望那位重复删改遗嘱的疯癫老妇人以来,到现在方才觉得轻松。
他是在半睡眠状态中听到凯文开锁的声音,在他可以移动之前,主人就出现在房里了。
麦克德默走向茶几上的玻璃酒瓶,在经过他身后时,用力扭捏他的后颈。“一个开始,老朋友,”他说,“一个开始。”
“开始什么? ”罗勃问。
“你那漂亮的脖颈开始往粗厚变形。”
罗勃懒懒地抚弄被有些抓疼的后颈。“你提醒我了,我现在开始感觉到有冷风袭击我的颈脖了。”他说。
“老天,罗勃! 难道就没有事能困扰你吗? ”凯文说,眼睛在深黑色眉毛下显得有些苍白。“即使你面临失去你美好体格的迫切情况下,你也能不烦恼吗? ”
“事实上,现在正有事情困扰着我。只不过不是我的外观。”
“嗯,布哈坡律师事务所发生什么事了? 不会是破产;那么我猜,是为了个女人。”
“是为女人,但不是你想的那样。”
“想结婚了? 应该的,罗勃。”
“你以前就这样说过了。”
“你想有个儿子来继承布哈坡事务所的,不是吗? ”布哈坡事务所的持续稳定总是惹来凯文的戏弄,罗勃想着。
“事务所并不排除女子当家。而且,现在,至少纳维尔要结婚了。”
“纳维尔未来的妻子能产生出来的惟一东西是留声机。
我听说前些日子她又出现在一些什么正式场合中。如果她必须努力工作赚钱付她旅行的花费的话,她就不会那样热衷于四处亮相了。“他捧着酒坐了下来。”我不必问你这次来是否又是出公差。有时你真该放下一切事情,单纯地来逛逛这个城市。我猜你明天早上大概要赶赴十点钟和某某人的律师约会了。“
“不是,”罗勃说。“是和苏格兰场。”
凯文倾倒着酒入嘴的动作停顿在那儿。“罗勃,你滑过头了,什么时候苏格兰场进驻到你的象牙塔了? ”
“就是咿,”罗勃平静地说,故意忽略那句问话夹带的打击。“它就在眼前,而我不很确定该怎么做。我想听听对这类情况有累积智慧的人的意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麻烦你,你必定对这些问题烦腻得要死。可是你过去真的连代数问题都帮我解决。”
“而你总擅长于投资和股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股票上我简直是个呆子。对于你使我免于一桩失败的投资,我还欠你一回呢。事实上,仔细想来,你使我免于两次失败的投资。”他补充道。
“两次? ”
“塔曼拉以及托陂卡锡矿。”
“我记得是曾在托陂卡锡矿上提醒了你一下,可我没做什么让你和塔曼拉分开的啊。”
“嗯,你的确没有吗? 亲爱的罗勃,如果你看到当我介绍她给你时你脸上的表情。噢,不是,不是你现在这种表情,刚好相反,是你那种反射性的立即调整的‘友善’表情,那种可诅咒的英国绅士小心翼翼、好教养的面具——它说明了一切。我预见自己一生都会在介绍塔曼拉给人时,人们表现出的那种好教养的神色中度过。它提醒了我。我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感谢你。现在,拿出你公事包里的东西吧。”
没有什么可以逃过凯文善于观察的眼睛的,罗勃想着,拿出贝蒂·肯恩向警方陈述的笔录副本。
“这是一份非常简短的笔录。我希望你看过后能告诉我你的想法。”
他审视着凯文的表情,没有先把自己的看法意见提出来。
麦克德默接过它,快速扫过第一段说:“我猜这是个受《艾克一艾玛》保护的女人。”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读《艾克一艾玛》报。”罗勃惊讶地说。
“上帝爱你。我其实是靠《艾克一艾玛》维生的。没有犯罪,就没有供养名利的来源;没有供养名利的来源,就没有凯文·麦克德默,或者说只有今天一部分的他。”说完,他沉入完全的沉默,足足有四分钟。他是如此专注,让罗勃觉得这房间几乎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他的主人已经离开。“嗯! ‘' 他说,终于抬起头来。
“怎样? ”
“我猜你的客户是这案子里的那两个妇人,而不是女孩儿? ”
“当然。”
“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凯文说着,摆出一副倾听的架势。
罗勃将整个事件的始末向他娓娓道来。他刚开始时的迟疑;随后逐渐倾向同情那两个妇人,而不是贝蒂·肯恩;苏格兰场在没有有利证据之前按兵不动的决定;以及雷斯利·乌殷的莽撞闯进《艾克一艾玛》报办公室。
“所以今晚,”麦克德默说,“苏格兰场正全力上天入地地寻找有利证据来支持女孩的说词。”
“我想是,”罗勃带点沮丧地说。“但我要知道的是:你相不相信那女孩的故事? ”
“我从来就不相信任何人的说词,”凯文略带不满地指出。“你要知道的是:我认为女孩的说词有可信度吗? 对这点我当然抱肯定态度。”
“真的? ”
“当然,为什么不? ”
“可是它是这样的不合常理。”罗勃说,比他预计得更急切。
“它一点儿也称不上不合理。独居的女人本来就容易做疯狂的事——特别在当她们是贫穷的淑女时。就在前些日子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被发现把她妹妹用铁链锁在床上,放在一间相当于壁橱大的房间,只给她吃面包屑、马铃薯皮和其他她自己不吃的零碎食物。当事情暴露后,她说那是因为她们没什么钱,而那是她维持收支平衡的惟一方法。事实上,她倒是在银行存有不少钱,只因为不安全感作祟让她做出那么疯狂怪异的事来。那是不是比起那小女孩的故事——依你的不合理标准而言——更要超乎常理而不可信? ”
“是吗? 我觉得那像精神错乱的典型。”
“这只是因为你知道它确实发生过。我是说,有人的确亲眼目睹了。相反的,假设这仅仅是一个谣传,而那疯狂的姊姊风闻了谣传,在一切调查进行前释放了妹妹;调查人员只见到两个老女人住在一起,显然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只除了其中一个看来明显的孱弱些,你会怎么想? 你会相信那用铁链锁人的传言吗? 或者,你比较可能会想那只是一桩不可思议的荒唐故事? ”
罗勃陷入失望沮丧的情绪中。
“这个故事中有两个孤独的没有多大经济实力的女人负担着乡间一栋大房子,她们之中一个年纪太大无法做家务,另一个厌恶家务。什么是这种情况下稍带疯癫的女人会有的举动? 拘禁一个女孩儿强迫她做家仆,当然就顺理成章了。”
该死的凯文! 还有他雄辩又条理分明的心灵。罗勃以为他要的是凯文的意见,事实上他要的是凯文来支持他自己的结论。
“她们拘禁的女孩子恰好是一个离家很远而无辜的在校女生。那是她们运气背,碰到这样无可责难的女孩儿,她至今还没被发现说过谎,人们会愿意相信她的话的。如果我是警方人员,我会往这条路走的。对我而言,疯了的是她们。”
他饶有兴味地看了罗勃一眼,后者正把自己深深埋进坐椅里,皱着眉生气地看着伸长到壁炉旁的腿。他静默了一两分钟,揶揄似地端详着他朋友受挫折的样子。
“当然,”他再次开口,“他们会记得一个类似案件,一个女孩惹人怜惜的故事,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彻底相信。”
“类似案件! ”罗勃说,曲起双腿坐直身子。“什么时候? ”
“十八世纪左右。我忘记了确切时间。”
“嗯。”罗勃说,再一次失望了。
“我不懂那声‘嗯’是什么意思,”麦克德默温和地说。“编造托词的本质经过了两个世纪后并没有什么改变的。”
“托词? ”
“如果那件类似案件可以拿来作指引的话,那女孩的故事就是一桩假言托词。”
“那么你相信——我是说,你觉得那女孩的故事全是无稽之谈哕? ”
“从头到尾全是杜撰的。”
“凯文,你真叫人火大。你刚说你觉得那故事有可信度的。”
“我是这样说的,但我也同时觉得那故事是一连串谎言。我不特别偏重任何一方。即使在最短时间内,我都可以为任何一方辩护。就整体而言,我会比较愿意为那位来自埃尔斯伯瑞的小女孩儿辩护。她站在证人席上会有相当不错的效果,而从你告诉我的夏普母女,没有一个能在法庭里提供视觉上的便利,使辩护顺利进行。”
他站起来为自己倒了另一杯威士忌,同时伸出另一只手去取罗勃的杯子。然而罗勃失去了欢乐饮酒的情绪。他摇着头,甚至没有将投入火炉的眼光移开。他感到异常疲倦,而且开始对凯文失去了耐心。他来错了,当一个人做刑事辩护律师太久,就像凯文一样,他遇事只剩下争论和意见,而没有了探索真相的热忱。他会继续坐着等凯文喝掉那第二杯酒的一半,然后他就要告辞。也许此刻上床睡觉去,忘记他对别人的问题负有责任会比较好。至少,忘记他对解决那些问题有责任。
“我怀疑那一个月中那女孩儿都做了什么。”凯文与人对话似地说,同时吞了一大口威士忌。
罗勃张开嘴想说:“那么你真相信那女孩是个骗子! ”
但他及时阻止了自己。他拒绝继续玩凯文的游戏。
“如果在红酒之外你又喝这么多威士忌,那么下.一个月你惟一能做的就是接受治疗,老家伙。”他说。而让他惊讶的是凯文坐倒在椅子上,笑得打跌,像个小男生。
“嗯,罗勃,我真爱你,”他快乐地说。“你真是英格兰的精髓。你有着我们钦佩和嫉妒的所有特质。你坐在那儿,看来是那样温和有礼,任人欺负,让人们以为你只是个老病猫,可以尽情地戏耍愚弄你;而就在人们洋洋自得的那一刻,突然间轰的一响,一只脱了掩护手套的专业爪掌就闪电般亮到他们鼻端! ”他自罗勃手中拿走杯子,也没说请不要见怪等废话,就起身为罗勃倒酒。这回罗勃由他去了。事实上,他觉得平衡些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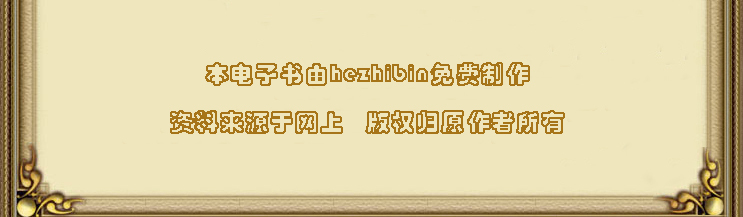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