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15章
|

|
|
|
河边的气温异常地低。柳树沙沙地响着,河水呈现白蜡一般的颜色,风的吹拂及骤雨的拍打使得河面水波荡漾。随着漫长的等待,罗杰斯惯有的焦虑表情也僵化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不速之客来与他们共享这守夜的滋味。磨坊屋已发誓会保守秘密,不过却发现没有什么秘密好守的。杜普太太已上床休息了,而汤米则和其他警察一样参与打捞的工作。宽广绵延的河岸与马路或道路有一段相当远的距离,而且附近也没有住家,所以不会有路过的行人停下来观望,然后再到处去散播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河边只独独留下这群苦候结果的工作人员。这一刻漫长得令人难熬。
格兰特与罗杰斯早在很久以前,就对任务检讨这种事感到疲累,这会儿更一点精神也没有。现在,他们只是寒冷的春天里伫立在沼泽边的两个男人。他们并肩坐在一棵倒下的柳树干上。格兰特凝视着打捞工作的缓慢进展,罗杰斯眺望着山谷宽广的平地。
“冬天的时候这里河水泛滥,”他说。“但只要你能忘掉它所造成的灾害,它的景色也算得上是相当迷人的。”
格兰特念道:“毁灭性的关啊它沉溺了求生的船桨。”
“这是什么? ”
“我在军中的一位朋友对洪水的描写。
一朝醒来望着纤细燃烧的绿草,毁灭性的美啊它沉溺了求生的船桨。“
“不错嘛。”罗杰斯说。
“悲伤的老调,”格兰特应道,“听起来像首诗。我想它是讲命运多舛。”
“它很长吗? ”
“只有两段以及一个含有寓意的结尾。”
“结尾的内容是什么? ”
“哦,终结的美. 浮现在这沉陷的大地上。
我们爱的不是你褪去的容颜,因为褪去的美已随大地沉陷。“
罗杰斯以为诗已吟完,开口说道:“很好。你的那位战友的确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是从来不读诗的——我是指诗集,不过,你晓得,有些杂志有时会刊印些诗啊、散文什么的,以补足杂志上的空间,所以也难免会读到。”
“我晓得。”
“我在杂志刊物上读过很多诗,每次总是会从字里行间推敲出些意思,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一首。严格说起来那不算是诗,我的意思是它缺乏诗的押韵,但它让我终生难忘。它是这样写的:我已把一切奉献给这块岛屿远离深不可测的海滨岛屿上有哭喊的海鸥还有我谁能听到那发自我婴儿期的海洋之声只有穿过绿野才能聆听潺潺河流的波动以及小鸟儿从林叶间发出的唧唧私语。
所以,你知道,我成长于海洋之畔,一个叫密尔港的地方,而我从来不曾真正适应过离开海洋的日子。这是一种不得解脱的窒息感。不过,一直读到这首诗,我才找到完全切合的表达之意。我完全能体会那个家伙的感受——‘小鸟儿的唧唧私语’! “
他那种轻蔑和带点愤怒的语气让格兰特觉得很有趣,但某件事情更令他觉得好笑,他开始笑了起来。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 ”罗杰斯有点防卫地问道。
“我只是在想像,如果一个很优秀的侦探小说家正好看见两个警察坐在柳树下交替着背诵诗句,那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个画面。”
“哦,他们! ”罗杰斯沉着声音说道,并且吐了一口口水,“不知道懂不懂得欣赏这些? ”
“当然,偶尔也会。”
“我的长官还对这些满有兴趣的,收集了不少。他的纪录是一本书中有九十二首,那本书好像叫做《上帝救命》。好像是一位女作家写的。”他停了一会,望了望远处然后又说,“有个女人正朝这儿走过来,推着一辆脚踏车。”
格兰特看了看说,“那不是一个女人,是女神,她来帮我们忙的。”
那正是打不倒的玛塔,她给大伙带来三明治和咖啡。
“我只能想到用脚踏车将它们带过来给你们,”她解释着.“但也满困难的,因为所有的大门都未打开。”
“那你是如何进来的? ”
“我先将东西拿下脚踏车,把脚踏车抬过去,然后再将东西放回脚踏车上。”
“就是你这种精神才造就了今天的大英帝国。”
“大概吧,但是回去时我需要汤米帮忙。”
“没问题,哈洛德小姐。”汤米满口嚼着三明治。
大伙上了岸后,格兰特一一地介绍给玛塔认识。
“我想消息大概有点走漏。”玛塔说,“托比打电话问我是否重新打捞过河一次。”
“你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吧? ”
“哦,没有,没有。”她说。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好像想起了那只鞋子。
到了下午两点,那儿来了一大群围观者。三点的时候,那儿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游园会场,需要当地警员努力地控制才能稍稍维持住秩序。
到了三点半,他们大约打捞到了莎卡镇,但却什么也没捞到,格兰特于是回到磨坊屋,并在那里遇到了华特·怀特摩尔。
“谢谢你告知我们这个消息,探长。”他说,“我本来应该去河边的,但我不行。”
“你一点儿也不需要来的。”
“玛塔说你在喝下午茶的时间会回来,所以我就在这里等你。有任何——结果吗? ”
“目前还没有。”
“今天早上你为什么想知道有关那只鞋子的事情? ”
“因为它被找到时还是系着鞋带的。我想知道西尔通常脱下鞋时是不是都会把鞋带松开来。很显然,他总是松开鞋带才脱鞋。”
‘’为什么那只鞋子在被发现的时候鞋带是系紧的呢? “
“如果它不是被水流吸走,那就是他为了便于游泳而将它踢开的。”
“我知道了。”华特沉寂地说。
他谢绝了下午茶,离去时的神情看似比往常更茫然。
“我希望我可以更为他感到难过一点,”玛塔说。“你要中国茶还是印度茶? ”
格兰特喝了三大杯滚烫的茶后( 玛塔说“那对身体不好”) ,感觉舒服多了,这时威廉斯正好来电话。虽然威廉斯很努力地搜集资料,但还是不够详尽。西尔小姐不是很喜欢她的堂哥莱斯里·西尔。她也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是在美国的另一边,直到长大后彼此才见过面。他们一见面就吵架。他来英国时偶尔会打电话给她,但这一次却没有。她不知道他来到了英国。
威廉斯问她是不是常常不在家,会不会西尔打电话来她没有接到。她说她到苏格兰高地去画画了,说不定西尔打了很多次电话来,但她没接到。当她不在时,整个房子就空着,不会有人接电话。
“你看到那些画了吗? ”格兰特问,“那些有关苏格兰的画。”
“哦,看到了。那个地方到处都有。”
“看起来像什么? ”
“很像苏格兰。”
“哦,很正统的。”
“我不知道,好像大部分都是索色兰及斯开岛。”
“有关他在乡间的朋友们呢? ”
“她说她很惊讶他会有任何的朋友。”
“她有没有跟你说西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
“没有,一点也没有。”
“她也没有说为什么他会突然失踪,或者他会消失到什么地方? ”
“没有,她没说什么。她只是跟我说他没有朋友,双亲也都死了,而他是个独子。她似乎对他的人际关系一点都不知道。他说他在英国仅有一个亲戚似乎是真的。”
“那么,谢谢你啦,威廉斯。我忘了问你,你早上是否看到班尼? ”
“班尼? 哦,有。那不是难事。”
“他大叫吗? ”
格兰特听到威廉斯在笑。
“没有,他这次耍了个伎俩,假装昏倒了。”
“他骗到了什么东西? ”
“他骗到了三杯白兰地和一大堆悦耳的交响曲。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们在酒吧里。两杯白兰地下肚后他开始抱怨他如何被迫害,所以他们给了他第三杯。我在那儿相当不受欢迎。”
格兰特认为这个说法只能算是轻描淡写。
“幸好那是西区的一个酒吧。”威廉斯说。这意思是说不会跟他的表现有任何冲突。
“他答应一起跟你去接受侦讯吗? ”
“他说他会,只要我先让他打一通电话。我对他说他可以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打电话给任何人,而且如果他是无辜的他就不应该介意我在旁边听。”
“他同意吗? ”
“他自己将我拉进电话亭里面。你猜那家伙打电话给谁? ”
“他的民意代表? ”
“不,我想民意代表们都已对他感到很厌烦了。他打给了一个在《看守人》写专栏的家伙,并且告诉了他整件事。他说他马上就会被苏格兰场的警察带回去侦讯,而且你想一个人和一大堆都不认识他的人在一起,又喝了点酒,他会说实话吗? 他似乎很高兴跟我一起走。”
“他对我们警场有任何帮助吗? ”
“没有,但他的女朋友有。”、“她说出秘密了? ”
“没有,她带着波比的耳环,波比·布朗特的耳环。”
“不会吧。”
“如果不是班尼,我想那个女的早就把他做掉了。她气疯了,他已好一阵子没有跟她在一起了。而她也有点想把他甩了,所以班尼‘买’了一对钻石耳环给她。班尼的智慧实在比一个五岁的小孩还低。”
“你拿回了波比其他的东西吗? ”
“没错,班尼全吐出来了。他还来不及把它们弄走。”
“做得好。那个写专栏的家伙呢? ”
“我本来想看那个家伙的笑话,但上面不让我这么做。
他们说这样才不会惹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只好打电话去告知那家伙。“
“你最少得到或学到某些事吧? ”
“是呀,我承认,整件事让我感到很有意思。我说:‘李特先生,我是威廉斯警官,几小时前班尼·史考尔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他说:‘你也在场? 但是他说了些对你不满的话! ’‘是呀! ’我说,‘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不认为对有些人来说言论这么自由,’他说,‘你不是就要强押他到苏格兰场去做侦讯吗? ’我回答说我是邀请他过去,他如果不想,他可以不去。
然后他又对我说了一大堆对待罪犯的话,什么你们没有权利再将他当作犯人一样问东问西的。‘你在他的朋友面前让他颜面尽失,’李特先生说,‘而且再一次将他推回绝望的谷底。班尼·史考尔今天下午在苏格兰场还好吧? ’‘值两千英镑。’我说。
‘什么? ’他说,‘你在说什么? ’‘那是他星期五晚上从波比·布朗特家偷来的珠宝的价值。’‘你怎么知道那一定是班尼偷的? ’他问。
我说是班尼自己交出来的——除了那两颗吊在他现任女友耳垂上的钻石耳环。然后我说:‘祝你晚安。’非常轻声细语地说,就像他们在儿童节目上那样。之后我就挂上电话。我想,他大概早已写好了一篇报导班尼是如何无辜的文章。他一定难堪极了。如果没有人要他写东西,作者一定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等到李特先生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格兰特说,“他一定会跑来对我们大声说不会放过那些罪犯们。”
“是呀,真是好笑,不是吗? 特别是这种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旧金山那边没有任何消息吗? ”
“还没有,但随时都可能有。不过现在看来似乎不太重要了。”
“不重要。就像我在威克翰讥问巴士司机一样,一整本笔记全都可以丢到垃圾桶里。”
“绝对不可以将你的笔记丢掉,威廉斯。”
“把它留下来以后还会有用吗? ”
“把它们留下就是,就算是你的自传也罢,留下它们。
可惜你目前工作不允许,否则我真想你回我这儿来,陪我在寒风中守候。“
“真希望在日落前会有新的进展。”
“我也希望如此。”
格兰特挂上电话后就马上回到了河边。围观的人群也随着天色的逐渐昏暗而渐渐散去,但是有些人就是饿着肚子、承受着寒风也一定要看到警方将尸体打捞上岸。格兰特看着这些痴人们的脸庞,他干警察这么多年了,但还是搞不清楚他们在看些什么玩意儿。不过有一件事他可以确定:如果哪天有了民怨,那么他进出办公室时就会变得比较麻烦了。
罗杰斯回威克翰去了,但接着却来了一大堆记者——当地及伦敦各报驻克隆的记者,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河流又重新被打捞了一次。长老也来了。长老的鼻子和下巴几乎连在一起,格兰特很难想像他如何刮胡子。他代表的老字号团体虽然地位不高,但因攸关“种族记忆”,不但受人尊敬,且分量十足。
“你们这样打捞是没有用的。”他对格兰特说,就像一位师傅对学徒讲话一般。
“没用? ”
“没有用,没有用的。她将所有的东西都吞了下去,吞到污泥里面了。”
很明显,“她”指的是那条河流。
“为什么呢? ”
“她走得很慢,好像很累似的。所有事物都向下沉。
然后等她走到威克翰的时候她又有精神了。啊,她就是这样,将她带来的东西全部都沉到污泥里面。然后她就会静悄悄地走到威克翰。“他突然对格兰特使了一个眼色。”狡猾,“他说,”她就是这样,狡猾! “
罗杰斯之前也说过,他也曾经接受了这个当地人的意见,但是他却不知道他们这样打捞为什么没用,而现在这位俨然“种族记忆”的代表人物正在跟他解释为什么。
“再怎么捞也没有用的。”他一边擦着鼻涕一边很轻蔑地说。
“为什么? 难道你不认为河底有一具尸体吗? ”
“啊! 是有尸体在河底。但是河底的那些污泥,它要等到它高兴的时候才会将你要的东西吐还给你。”
“那请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
“哦! 一千年内都有可能,黏性那么强的污泥、烂泥。
我祖父小的时候有一个球,有一次那个球掉了,而且一直滚,滚到了河里面。那儿本来很浅,他可以够到那个球,但他不敢下水去捡它。他跑回家去把他父亲找来帮他一起捡那个球,但污泥已经把它吞了下去。污泥把它吞下去后你也就没有任何办法。他们回去拿了耙子去捞它也没有用,污泥吃了它。会吃东西的污泥,我告诉你们,那是会吃东西的污泥。“
“但是你不是说它有时候会将它吞下去的东西又吐出来还你吗? ”
“啊! 是呀。偶尔。”
“什么时候? 淹大水时吗? ”
“不是的! 淹大水时她只会更加扩散她自己,并带来更多的泥沙。但有时她会吓一跳,并将她吞下的东西吐出来还你。”
“吓一跳? ”
“啊,就像她上个星期一样,大云层飘到欧特雷,倾盆大雨降到河里,就像有人在倒洗澡水一般。她还来不及扩散,大雨带来的大水在河道中流下,就像一把大刷子一样冲刷着她,偶尔就有些东西因此从污泥中被吐了出来。”
这对格兰特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这表示如果他想要找到西尔的尸体,他必须要等到下一次大雨的来临。渐暗的天色也使得他的心情低沉了下来;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必须要收工了。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也打捞完莎卡镇这段了,如果他们什么也没捞到,那他们还会有什么希望? 他整天都在想他们只是在大海里捞针。如果这第二次打捞工作又没有任何进展,那怎么办? 没有讯问,没有案子,什么也没有了。
就在太阳快要西沉,而他们的打捞工作再过大约五十码就要结束时,罗杰斯突然出现,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封信:“这是给你的。从美国来的报告。”
现在一点也不紧急了,但他还是拆开了信封将报告拿出来看。
旧金山警局里没有任何一点有关莱斯里·西尔的记录,对他的资料也一概不知。他总喜欢在冬季的时候来到西岸,其余的时间他会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摄影。他生活过得很舒适,很平静,没有任何奢华的花费或不检的行为。他没老婆,也不曾有过缠绵的恋情。旧金山警局里没有他任何记录,只得到大洋洲摄影公司的公关部门去查。根据他们的资料说,西尔诞生于康涅狄克州周柏林市,是达菲。
西尔和克莉丝婷娜·梅森惟一的小孩。经康涅狄克州周柏林市警局调查,发现他们早已在二十年前移居美国南部。
西尔是位药剂师,同时也对摄影很感兴趣,但这就是大家对他们仅有的印象。
这真是个乏味的报告,既无聊又没用。没有他想知道的西尔在美国相关亲友的任何线索,也没有描述西尔的资料。不过,其中有那么一丁点似乎让他感到疑惑。
他再次仔细地阅读,期待着突发一些灵感,但这次却没有任何反应。
满是困惑的他再慢慢地重读一遍。到底是什么让自己感到疑惑? 他竟然找不到。
他满腹疑云地把报告书折起来,暂放在自己口袋里。
“看样子我们完蛋了,我想你知道吧? ”罗杰斯说,“目前为止我们什么都没找到。莎卡镇的河里什么也没有。
此地有句俗语,当你要说‘放弃了吧’,或是‘永远都不要再想了’,他们就会说‘丢到莎卡镇的桥下去’。“
“人们为什么不偶尔挖挖河床,却让它淤塞成这个样子。”格兰特愤怒地说,“难怪隔年冬天河水都会淹没这里的房子。”
罗杰斯原本不悦的脸色瞬间充满了趣味,他和善地说,“如果你闻一闻罗许密尔泥巴的味道,就会好好考虑到底要不要把泥挖出来,让货车载着经过街道运走。要不要我现在命令他们停止? ”
“不。”格兰特顽固地说,“太阳下山之前叫他们继续打捞。天晓得,说不定我们会创下纪录,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从莎卡镇的河里挖出宝来的人。反正我不相信什么乡下的迷信说法。”
他们一直打捞到太阳下山,但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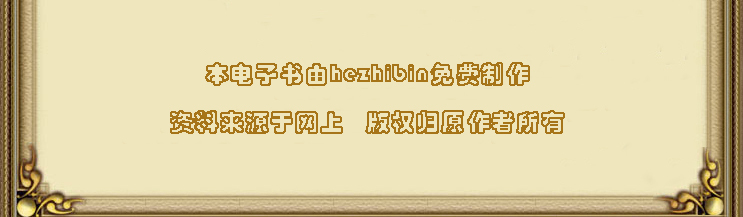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