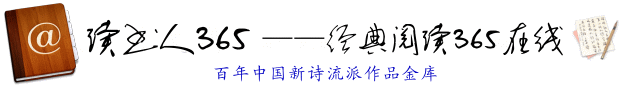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舒婷的诗
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
也像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你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77.3.27
神女峰
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离去,谁
还站在船尾
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
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为眺望远天的杳鹤
而错过无数次春江月明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1981年6月于长江
惠安女子
野火在远方,远方
在你琥珀色的眼睛里
以古老部落的银饰
约束柔软的腰肢
幸福虽不可预期,但少女的梦
蒲公英一般徐徐落在海面上
呵,浪花无边无际
天生不爱倾诉苦难
并非苦难已经永远绝迹
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
唤醒普遍的忧伤
你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
这样优美的站在海天之间
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
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
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
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
1981年4月
双桅船
雾打湿了我的双翼
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
岸呵,心爱的岸
昨天刚刚和你告别
今天你又在这里
明天我们将在
另一个纬度相遇
是一场风暴,一盏灯
把我们连系在一起
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
使我们再分东西
不怕天涯海角
岂在朝朝夕夕
你在我的航程上
我在你的视线里
1979年8月
最后的挽歌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
第一章
眺望
掏空了眼眶
剩下眺望的姿势
钙化在
最后的挽歌里
飞鱼
继续成群结队冲浪
把最低限度的重
用轻盈来表现
他们的鳍
家园
雪花无需签证轻易越过边界
循槐花的香味
拐进老胡同
扣错门环
作为一段前奏
你让他们
眺望到排山倒海的乐章
然后你再蔚蓝些
也不能
比泄洪的大江更汪洋
被异体字母日夜攻歼
你的免疫系统
挂一漏万
弓身护卫怀里
方形的蛹
或者你就是
蛹中使用地度的印色
一粒炭火那么暗红
白蚁伸出楚歌
点点滴滴
蛀食寄居的风景
岁月是一本过期的护照
往事长出霉斑
从译文的哈哈镜里
你捕捞蝌蚪
混声别人的喉管
他们不会眺望你太久
换一个方向
他们遮挡别人的目光
即使脚踩浮冰
也是独自的困境
以个人的定音鼓,他们
坚持亲临现场
如果内心
是倾斜下沉的破船
那些咬噬着肉体
要纷纷逃上岸去的老鼠
是尖叫的诗歌么
名词和形容词
已危及交通
他们自愿选择了
非英雄式流亡
你的帽子
遗忘在旗舰上
第二章
是谁举起城市这盏霓虹酒
试图与世纪末
红肿的落日碰杯
造成划时代的断电
从容凑近夕照
用过时的比喻点燃
旱烟管的农夫
蹲在田垄想心事
老被蛙声打断
谁比黑暗更深
探手地龙的心脏
被挤压得血脉贲张
据说他所栖身的二十层楼
建在浮鲸背上
油菜花不知打桩机危险
一味地天真浪漫
养蜂人伛着背
都市无情地顶出
最后一块蜜源
空调机均衡运转
体温和机器相依为命
感到燥热的
是怀念中那一柄葵扇
或者一片薄荷叶
贴在诗歌的脑门上
田野一边涝着
一边旱着
被化肥和农药押上刑场
不忘高呼丰收口号
多余的钱
就在山坳盖房子
乌瓦白墙意大利厕具
门前月季屋后种瓜
雇瘸三照料肥鹅
兼给皇冠车搭防盗棚
剩下的时间
做艺术
打手提电话
都市伸出输血管
网络乡间
留下篱笆、狗和老人
每当大风
掀起打工仔的藤帽
不由自主伸手
扶直
老家瓦顶的炊烟
画家的胡子
越来越长越来落寞
衣衫破烂
半截身子卡在画框
瘸三抽着主人的万宝路
撕一块画稿抹桌
再揉一团解手
炒鹅蛋下酒
都市和农村凭契约
交换情人
眺望是小心折叠的黄手帕
挥舞给谁看。
第三章
迎风守望太久
泪水枯竭
我摘下酸痛的双眼
在一张全盲的唱片上
踮起孤儿的脚尖
对北方最初的向往
缘于
一棵木绵
无论旋转多远
都不能使她的红唇
触到橡树的肩膀
这是梦想的
最后一根羽毛
你可以擎着它飞翔片刻
却不能结庐终身
然而大漠孤烟的精神
永远召唤着
南国矮小的竹针滚滚北上
他们漂流黄河
圆明园挂霜
二锅头浇得浑身冒烟
敞着衣襟
沿风沙的长安街骑车
学会很多卷舌音
他们把丝吐得到处都是
仍然回南方结茧
我的南方比福建还南
比屋后那一丘雨林
稍大些
不那么湿
每年季风打翻
几个热腾腾鸟巢
溅落千变万化的方言
对坚硬土质的渴求
改变不了南方人
用气根思想
北方乔木到了南方
就不再落叶
常绿着
他闪痛恨液汁过于饱满
怀念风雪弥漫
烈酒和耸肩大衣的腰身
土豆窖藏在感伤里
靠着被放逐的焦灼
他们在汤水淋漓的语境里
把自己烘干
吮吸长江黄河
北方胸膛乳汁丰沛
盛产玉米、壁画
头盖骨和皇朝的地方,也是
月最明霁风最酷烈
野狼与人共舞
胡笳十八拍的地方
北方一次次倾空她的
围腰
把我们四处发放
我们长城稗草进化到谷类
再蜕变为蝗虫
在一张海棠的叶脉上
失散
这就是为什么
当拳头一声嗥叫
北斗星总在
仰望的头顶上
第四章
放弃高度
巅峰不复存在
忘记祈祷
是否中止了
对上帝的敬畏
在一个早晨醒来
脚触不着地
光把我穿在箭镞上
射向语言之先
一匹风跛足
冉冉走远
日历横贯钟表的子午线
殉葬了一批鸡鸣
三更梆鼓
和一炷香的时晨
渡口自古多次延误
此岸附耳竹筒和锦帛
谛听彼岸脚步声
我终于走到正点居中
秒针长话短说
列车拉响汽笛从未停靠
接站和送站互相错过
持票人没有座位
座位空无一人
黑夜耄耄垂老
白昼刚刚长到齐肩高
往年的三色堇
撩起裙裾
步上今春的绿萼
一个吻可以天长地久
爱情瞬息名称
我要怀着
怎样的心情和速度
才能重返五月
像折回凌乱的卧室
对梦中那人说完再见
并记得请他
留下地址电话
阴影剥离岩层
文字圈定声音
在海水的狂飙里,珊瑚
小心稳定枝形烛光
朱笔和石头相依为命
却不能与风雨并存
每写下一个字
这个字立刻漂走
每启动一轮思想
就闻到破布的味道
我如此再三起死回生
取决于
是否对同一面镜子
练习口形
类似高空自由坠落
恪守知觉
所振动的腋下生风
着陆于零点深处
并返回自身
光的螺旋
再次或者永远
通过体内蛰伏蛇行
诗歌火花滋滋发麻
有如静电产生
你问我的位置
我在
上一本书和下一本书之间
第五章
那团墨汁后面
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现在是父亲将要离开
他的姿容
越来越稀薄
药物沿半透明的血管
争相竞走
我为他削一只好脾气的梨
小小梨心在我掌中哭泣
其他逝者从迷雾中显现
母亲比我年轻
且不认已届中年的我
父亲预先订好遗像
他常常用目光
同自己商量
茶微温而壶已漏
手迹
继续来往于旧体格律
天冷时略带痰音
影子期待与躯体重合
灵魂从里向外从外向里
窥探
眼看锈迹侵袭父亲
我无法不悲伤
虽然悲伤这一词
已经殉职
与之相关的温情
(如果有话
这一词也病入膏盲)
现代人羞于诉说
像流通数次已陈旧的纸币
很多词还没焐热
就公开作废
字词凋败
有如深秋菩提树大道
一夜之间落叶无悔
天空因他们集体撤出
而寥廓
而孤寒
而痛定思痛
只有擦边最娇嫩的淡青
被多事的梢芒的刮破
每天经历肉体和词汇的双重死亡
灵魂如何避过这些滚石
节节翘望
作为女儿的部分岁月
我将被分段剪辑
封闭在
父亲沉重的大门后
一个诗人的独立生存
必须忍受肢体持续背叛
自地下水
走向至高点
相对生活而言
死亡是更僻静的地方
父亲,我寄身的河面
与你不同流速罢
我们仅是生物界的
一种表达方式
是累累赘赘的根瘤
坠在族谱上
换一个方向生长
记忆摩挲灵魂的容器
多一片叶子
有什么东西漫了出来
我右手的绿荫
争分夺秒地枯萎
左手不在休眠
第六章
陆沉发生在
大河神秘消失之前
我仅是
最初的目击者
一个铸件经历另一个铸件
绕过别人的拖烟层
超低空飞行
瓦斯俘获管道风格
多快好省
划动蓝色节肢
活泼泼
将生米煮成熟饭
我抱紧柴禾
寻找一只不作声的炉子
逃离
每一即定事实
随时保持
举起前脚的姿势
有谁真正身体力行
当常识把我们
如此锁定
万花筒逆向转动
去冬馁毙的红襟雀
莞尔一笑
穿雪掠起而起
昨天义无反顾暴殄天物
今天面临临语言饥荒
眼睛耳朵分别拆解零件
装置错位
惟心跳正常
夹杂些金属之声
只要再翻过这座山
其实山那边什么也没有
如果最后一块石头
还未盖满手印
如果内心
有足够的安静
这个礼拜开始上路
我在慢慢接近
虽然能见度很低
此事与任何人无关
1997年2月1日至4月20日于柏林
作者简介:舒婷(1952—),本名龚佩瑜,福建泉州人。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