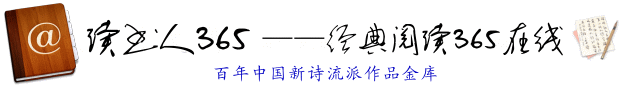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相关链接:1、时间:八十年代;
2、主要阵地:《绿风》;
3、成员方阵: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
昌耀的诗
鹿的角枝
在雄鹿的颅骨,生有两株
被精血所滋养的小树。雾光里
这些挺拔的枝状体明丽而珍重,
遁越于危崖沼泽,与猎人相周旋。
若干个世纪以后,在我的书架,
在我新得的收藏品之上,才听到
来自高原腹地的那一声火枪。--
那样的夕阳倾照着那样呼唤的荒野。
从高岩,飞动的鹿角,猝然倒仆......
......是悲壮的。
1982.3.2
筏子客
落日。辉煌的河岸。
一个辉煌的背影:皮筏和扛着皮筏的
筏子客。跋涉于归途,
忘却了鱼的飞翔、水的凌厉。
与激流拼命周旋原是为的崖畔的那扇窗口,
那里有一朵盛开的牡丹。
当圆月升起。
我看到一个托举着皮筏的男子
走向山巅辉煌的小屋。
1961年夏初稿
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
东方
堂·吉诃德军团的阅兵式
予人笑柄的族类,生生不息的种姓。
架子鼓、筚篥和军号齐奏。
瘦马、矮驴同骆驼排在一个队列齐头并进。
从不怀疑自己的猎枪头还能挺多久。
从不相信骑士的旗帜就此倒下。
拒绝醒醐灌顶。
但我听到那样的歌声剥啄剥啄,敲门敲门
(是这样唱着:啊,我们收割,我们打碾,我们锄禾。......
啊,我们飞呀飞呀,我们衔来香木,我们自焚,我们凤凰再生。......)
从远古的墓茔武术拔,满负荷前进。
一路狼狈尽是丢盔卸甲的纪录。
不朽的是精神价值的纯粹。
永远不是最坏的挫折,但永远是最严重的关头。
打点行装身披破衣驾着柴车去开启山林。
鸠形鹄面行吟泽边一行人马走向落日之爆炸。
被血光辉煌的倒影从他们足下铺陈而去,
曳过砾原,直与那一片丛生的锁阳--
野马与蛟龙嬉戏遗精入地而生的鳞茎植群相交。
悲壮啊,竟没有一个落荒者。
冥冥天地间有过无尽的与风车的搏斗。
有过无尽的向酒的挑战。
为夺回被劫持的处女的贞洁及贵妇人被践踏的
荣誉义无反顾。
吃尽皮肉之苦,遭到满堂哄笑。
少女杜尔西内亚公主永远长不大的情人,
永远的至死不悟--拒绝妖言。
永远的不成熟。永远的灵魂受难。
永远的背负历史的包袱。
饭局将撤,施主少陪,
堂·吉诃德好汉们无心尴尬。
但这是最最严重的关头,
匹夫之勇又如何战胜现代饕餮兽吐火的焰口?
无视形而下的诱惑,用长予撑起帐幄,
以心油燃起营火,盘膝打坐。
东方游侠,满怀乌托邦的幻觉,以献身者自命。
这是最后的斗争。但是万能的魔法又以万能的
名义卷土重来。
风萧萧兮易水寒。背后就是易水。
我们虔敬。我们追求。我们素餐。
我们知其不可而为之,累累若丧家之狗。
悲壮啊,竟没有一个落荒者。
悲壮啊,实不能有一个落荒者。
1993.8.5
划呀,划呀,父亲们!
——献给新时期的船夫
自从听懂波涛的律动以来,
我们的触角,就是如此确凿地
感受着大海的挑逗:
——划呀,划呀,
父亲们!
我们发祥于大海。
我们的胚胎史,
也只是我们的胚胎史--
展示了从鱼虫到真人的演化序列。
脱尽了鳍翅。
可是,我们仍在韧性地划呀。
可是,我们仍在拼力地划呀,
我们是一群男子。是一群女子。
是为一群女子依恋的
一群男子。
我们摇起棹橹,就这么划,就这么划。
在天幕的金色的晨昏,
众多仰合的背影
有庆功宴上骄军的醉态。
我不至于酩酊。
最动情的呐喊
莫不是我们沿椭圆的海平面
一声向前冲刺的
嗥叫?
我们都是哭着降临到这个多彩的寰宇。
后天的笑,才是一瞥投报给母亲的慰安。
--我们是哭着笑着
从大海划向内河,划向洲陆......
从洲陆划向大海,划向穹隆......
拜渴了长城的雉堞。
见识了泉州湾里沉溺的十二桅古帆船。
狎弄过春秋末代的编钟。
我们将钦定的史册连根儿翻个。
从所有的器物我听见逝去的流水。
我听见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
——划呀,父亲们,
划呀!
还来得及赶路。
太阳还不见老,正当中午。
我们会有自己的里程碑。
我们应有自己的里程碑。
可那旋涡,
那狰狞的弧圈,
向来不放松对我们的跟踪,
只轻轻一扫
就永远地卷去了我们父兄,
把幸存者的脊椎
扭曲。
大海,我应诅咒你的暴虐。
但去掉了暴虐的大海不是
大海。失去了大海的船夫
也不是
船夫。
于是,我们仍然开心地燃起爝火。
我们仍然要怀着情欲剪裁婴儿衣。
我们昂奋地划呀......哈哈......划呀
......哈哈......划呀......
是从冰川期划过了洪水期。
是从赤道风划过了火山灰。
划过了泥石流。划过了
原始公社的残骸,和
生物遗体的沉积层......
我们原是从荒蛮的纪元划来,
我们造就了一个大禹,
他已是水边的神。
而那个烈女
变作了填海的精卫鸟。
预言家已经不少。
总会有橄榄枝的土地。
总会冲必然的王国。
但我们生命个体都尚有阳寿短促,
难得两次见到哈雷彗星。
当又一个旷古后的未来
我们不再认识自己变形了的子孙。
可是,我们仍在韧性地划过呀。
在这日趋缩小的星球,
不会有另一条坦途,
不会有另一种选择。
除子五条巨大的舢舻,
我只看到渴求那一海岸的船夫。
只有啼呼海岸的呐喊
沿着椭圆的海平面
组合成一支
不懈的
嗥叫
大海,你决不会感动。
而我们的桨叶也决不会喑哑。
我们的婆母还是要腌制过冬的咸菜。
我们的姑娘还是要烫一个流行的发式。
我们的胎儿还是从血光里
临盆。
......今夕何夕?
会有那么多临盆的孩子?
我最不忍闻孩子的啼哭了。
但我们的桨叶绝对地忠实。
就这么划着。就这么划着。
就这么回答大海的挑逗:
--划呀,父亲们!
父亲们!
父亲们!
我们不至于酩酊。
我们负荷着孩子的哭声赶路。
在大海尽头
会有我们的
笑。
1981.10.6-29
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
1.春潮:她的梦一般的赞美诗
西羌雪域。除夕。
一个土伯特女人立在雪花雕琢的窗口,
和她的瘦丈夫、她的三个孩子
同声合唱着一首古诗;
--咕得尔咕,拉风匣,
锅里煮了羊肋巴......
是那么忘情的、梦一般的
赞美诗呵--
咕得尔咕,拉风匣,
锅里煮了个羊肋巴,
房上站着个尕没牙......
那一夕,九九八十一层地下室汹涌的
春潮和土伯特的古谣洗亮了这间
封冻的玻璃窗。我看到冰山从这红尘崩溃,
幻变五色的杉树由漫漶消融而至滴沥。
那一夕太阳刚刚落山,
雪堆下面的童子鸡就开始
司晨了。
2.我的掌模浸透了苔丝
她从娘家来,替我捎回了祖传的古玩:
一只铜马坠儿,和一只从老阿娅的妆奁
偷偷摘取的"乾隆通宝。"
说我们远在雪线那边放牧的棚户已经
坍塌,惟有筑在岸畔的猪舍还完好如初。
说泥墙上仍旧嵌满了我的手掌模印儿,
像一排排受难的贝壳。
浸透了苔丝。
说我的那些古贝使她如此
难过。
3.在雪原。在光轮与光轮的交错之上
牦牛:一头种公牛。
它有褐黑的腹长毛和洁白的眉毛。
它有金黄色鼻圈和金黄的犄角。
额上披发浅浅覆盖住了两只大眼睛。
当它从积雪的坡头率先直奔而下,
牛伙里它的后尾总是翘得比谁的都高挺,
像一株傲岸的蒲葵,
浮立在那一片黑色的波动。
浮立在那一片黑色的波动的最前沿。
黑色的波动呀
污染着白雪......
这是一头种公牛,一头牦牛。此刻它漫步在山阴。耸起的甲
驮负着牧人酬谢它的一皮袋稞麦。
它不喜欢这一象征。
回过头去,看到厩栏中那只俏丽的
花母牛还在朝它凝望,
那眼神是温柔的。
于是,我恍若又
听到了公牛的呼唤母牛的叫声。
恍若看到那只俏丽的花牛向这边靠拢。
看到一圈光轮从这只母牛的头顶升起。
看到成百、成千圈光轮从母牛群全体
成员的头顶升起。
从白雪、从黑色的波动,
在光轮与光轮的交错之上
是种公牛所独具的一轮
雄性的
犄角。
4.两个女孩的历史
小小的胖女孩。光腚的
一个胖女孩儿,歇在篱墙边。
这小女孩儿兴冲冲地朝前爬行。
又停住了。歇在篱墙边。屁股蛋儿
在嫩草地上蹭出一溜拖曳的擦痕。
小女孩儿兴冲冲地笑着,认真地
把每个过路的男子唤作"爸爸"。
报以无声的笑,他们走了过去。
草滩里有一只驯化的山雉
随着家禽啄食。
篱墙背后
女孩儿的土伯特母亲也悄悄地笑着。
忆起自己原是草滩里另一个女孩儿,
一个佩戴松石耳环的小女孩儿,
一个富有三只印度皮箱的小女孩儿,
一个身著绿布长袍的土伯特小女孩儿,
正弹跳于春草。十七个少年猎手围拢来
将贡礼轮番向她的怀中投去。
投去的那些蛤士蟆在天空飞着。
她提起两只袍角轻盈地跳着。
那些蛤土蟆,那些牺牲品,
那些蛤土蟆的大坟冢有他们带笑的
泪水。
时间呵,
你主宰一切!
5.阳光:火的颜色:温暖
残雪覆盖的麦垛下面
散发出阳光的香气。
这里:阳光就是香气。
就是麦草秆儿。
落叶林里
闪过雪鸡的白领羽毛和鲜红的鸡冠子。
我想起了白雪和雪地上的野火。
想起了西天沉落的火烧云。
想起了火的温暖。
这里:火的颜色就是温暖。
但是,垫在牛栏的草木灰同样温暖。
老牛哞哞的叫声同样温暖。
腐熟了的粪草同样温暖。
在温暖的日子,
猎人弯腰奔过亮晶晶的田野。
他在吊在腰带上的钢精饭盒哗啦啦响。
搁在钢精饭盒的小铜匙子哗啦啦响。
从田野弯腰奔过的亮晶晶的猎人
嗅到了麦垛下面的阳光的香气。
看到了落叶林里雪鸡的红冠子。
听到了河岸上老牛哞哞的叫声。
猎人弯腰奔过田野。亮晶晶的。
他的双筒猎枪从未装压过霰弹。
他并不需要射击。
我并不需要射击。有写生画家与我一同
从野外归来。欢迎我们的
是我的土伯特妻子和三个孩子。
1982.11.2-18初稿
作者简介:昌耀(1936—2001),本王昌耀,湖南桃源人,著有《昌耀抒情诗集》、《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