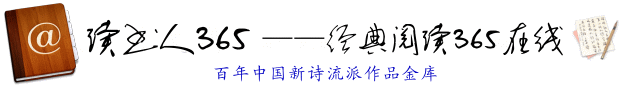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相关链接:1、时间:1993年开始,松散型流派。
2、主要阵地:陈东东主编《倾向》、《南方诗志》、周瓒主编《翼》、
森子主编《阵地》。程光炜编选《岁月的遗照》,孙文波,臧
棣、萧开愚编《中国诗歌评论--语言:形式的命名》,王家
新编《九十年代诗歌备忘录》,诗生活网站等。
3、成员方阵: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臧棣、翟永明、张曙光、
孙文波、黄灿然、张枣、陈东东、萧开愚、西渡、席亚兵、王艾、
冷霜、胡续冬、蒋浩、穆青、曹疏影、姜涛、森子、郭志杰、
桑克、周瓒、宋琳、林木、清平等。
欧阳江河的诗
拒 绝
并无必要囤积,并无必要
丰收,那些被风吹落的果子,
那些阳光燃红的鱼群,撞在额头上的
众鸟,足够我们一生。
并无必要成长,并无必要
永生。一些来自我们肉体的日子
在另一些归于泥土的日子里
吹拂。它们累累吹拂着泪水
和面颊,吹拂着波浪中下沉的屋顶。
而来自我们内心的警告像拳头一样
紧握着,在头上挥舞。并无必要
考虑,并无必要服从。
当刀刃卷起我们无辜的舌头,
当真理像胃痛一样难以忍受
和咽下,并无必要申诉。
并无必要穿梭于呼啸而来的喇叭。
并无必要许诺,并无必要
赞颂。一只措辞学的喇叭是对世界的
一个威胁。它威胁了物质的耳朵。
并在耳朵里密谋,抽去耳朵里面
物质的维系,使之发抖
使之在一片精神的怒斥声中
变得软弱无力。并无必要坚强。
并无必要在另一个名字里被传颂
或被诅咒,并无必要牢记
一颗心将在所有人的心中停止跳动。
将在权力集中起来的骨头里
塑造自己的血。并无必要
用只剩下几根骨头的信仰去惩罚肉体。
并无必要饶恕,并无必要
怜悯。飘泊者永远飘泊,
种值者颗粒无收,并无必要
奉献,并无必要获得。
种植者视碱性的妻子为玉米人。
当鞭子一样的饥饿骤然落下,
并无必要拷打良心上的玉米,
或为玉米寻找一滴眼泪,
一粒玫瑰的种子。并无必要
用我们的饥饿去换玉米中的儿子,
并眼看着他背叛自己的血统。
1990.4.5.于成都
空中小站
下午,我在途中。
远方的小火车站像狼眼睛一样闪耀。
火车站并不太远,天黑前能够到达,
我要去的是一座没有黑夜的城市--
警察局长的办公室桌放在空无一人的
广场中央,大街上的行人是雕塑,
密探的面孔像雨水在速写的墨水中
变成深色。汽笛响过之的
无人乘坐的火车
开出车站后,我错过了开车的时间。
有一座高层建筑,顶端是花园。
有一个空中小站,悬于花园之上。
有一段楼梯,高出我的视野。
有一次旅行,通向我对面的座位。
而从未去过的城市中,狂欢的
露天晚宴持续到天明,吹了一夜的风
突然停止,邮件和人事档案漫天飘落。
下午,我在途中。
远方有一个
高于广场和楼顶花园的空中小站。
1992.2.15
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
时尚最终将垂青于那些
蔑视时尚的人。不是一个而是
一群儿女如云的官员,缓缓步下
大理石台阶,手电的光柱
朝上直立:两腿之间虚妄的攀登。
女秘书顺手拔下充电器的金属插头,没有
再次插入。
阴阳相间、空心的塑料软管,
裹紧100根扭住的
散布在开端的清晰头发丝。电镀银
消褪之后,女秘书对官员
的众多下属说:给每秒钟
3000立方米的水流量
安装100个减压开关。
硬的软了下来,老的
更老。顺着黑夜里
一道微弱的光柱往上爬--
硬币、纸币,家庭的流水帐目,
一生积蓄像火焰在水底。
一个官员要穿过100间卧室,
才能进入妻子的、像蓄水池上升到唇边
那么平静的睡眠。录音电话里
传来女秘书带插孔的声音。
一根管子里的水,
从100根官子流了出来。爱情
是公积金的平均分配,是街心公园
耸立的喷泉,是封建时代一座荒废后宫
的秘密开关:保险丝断了。
1992.4.6于成都
手 枪
手枪可以拆开
拆作两件不相关的东西
一件是手,一件是枪
枪变长可以成为一个党
手涂黑可以成为另一个党
而东西本身可以再拆
直到成为相反的向度
世界在无穷的拆字法中分离
人用一只眼睛寻找爱情
另一只眼睛压进枪膛
子弹眉来眼去
鼻子对准敌人的客厅
政治向左倾斜
一个人朝东方开枪
另一个人在西方倒下
黑手党戴上白手套
长枪党改用短枪
永远的维纳斯站在石头里
她的手拒绝了人类
从她的胸脯拉出两只抽屉
里面有两粒子弹,一枝枪
要扣响时成为玩具
谋杀,一次哑火
1985.11.于成都
傍晚穿过广场
我不知道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
从何而始,从何而终。
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
有的人用一生--
早晨是孩子,傍晚已是垂暮之人。
我不知道还要在夕光中走出多远才能
停住脚步?
还要在夕光中跳望多久
才能闭上眼睛?当高速行驶的汽车
打开刺目的车灯。
那些曾在一个明媚的早晨穿过广场的人
我从汽车的后视镜里看见过他们一闪即逝
的面孔。
傍晚他们乘车离去。
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
离去的重新归来,倒下的却永远倒下了。
一种叫做石头的东西
迅速地堆积,屹立,
不像骨头的生长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也不像骨头那么软弱
每个广场都有一个用石头垒起来的脑袋,
使两手空空的人们感到生存的
分量。以巨大的石头脑袋去思考和仰望,
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石头的重量
减轻了人们肩上的责任、爱情和牺牲。
或许人们会在一个明媚有早晨穿过广场,
张开手臂在四面来风中柔情地拥抱
但当黑夜降临,双手就变得沉重。
惟一的发光体是脑袋里的石头,
惟一刺向脑袋的利剑悄然坠地。
黑暗和寒冷在上升,
广场周围的高层建筑穿上了瓷和玻璃的时装
一切变得矮小了。石头的世界
在玻璃反射出来的世界中轻轻浮起,
像是涂在孩子们作业本上的
一个随时会被撕下来揉成一团的阴沉念头。
汽车疾驶而过,把流水的速度
倾泻到有着钢铁筋骨的庞大的混凝土制度中、
赋予寂静以喇叭的形状。
过去年代的广场从汽车的后视镜消失了
永远消失了--
一个青春期、初恋的、布满粉刺的广场。
一个从未在帐单和死亡通知书上出现的广场
一个露出胸膛、挽起衣袖、扎紧腰带
一个双手使劲搓的带补丁的广场。
一个通过年轻的血液流到身体之外
用舌头去舔、用前额去下磕、用旗帜去覆盖的广场。
空想的、消失的、不复存在的广场,
像下了一夜的大雪在早晨停住。
一种纯洁而神秘的融化
在良心和眼里交替闪耀,
一部分成为叫做泪水的东西,
一部分在叫做石头的东西里变得坚硬起来
石头的世界崩溃了,
一个软组织的世界爬到高处。
整个过程就像泉水从吸管离开矿物,
进入蒸馏过的、密封的、有着精美的包装的空间。
我乘坐高速电梯在雨天的伞柄里上升。
回到地面时,我抬头看见雨伞一样撑开的
一座圆形餐厅在城市上空。
这是一顶从魔法变出来的帽子,
它的尺寸产不适合
用石头垒起来的巨人的脑袋。
那些曾经托起广场的手臂放了下来。
如今巨人靠着一柄短剑来支撑。
它会不会刺破什么呢?比如,曾经有过的
一场在纸上掀起的,在墙上张贴的脆弱的革命?
从来没有一种力量
能把两个不同世界长久地粘在一起。
一个反复张贴的脑袋最终将被撕去。
反复粉刷的墙壁,
被露出大腿的混血女郎占据了一半。
另一半是安装假肢、头发再生之类的诱人广告。
一辆婴儿车静静地停在傍晚的广场上,
静静地,和这个快要发疯的世界没有关系。
我猜婴儿车与落日之间的距离
有一百年之遥。
这是近乎无限的尺度,足以测量
穿过广场所经历的一个幽闭时代有多么漫长。
对幽闭的普遍恐惧,
使人们各种的栖居云集广场,
把一生中的孤独时刻变成热烈的节日。
但在栖居深处,在爱与死的默默的注目礼中,
一个空无人迹的影子广场被珍藏着,
像紧闭的忏悔室只属于内心的秘密。
是否穿过广场之前必须穿过内心的黑暗?
现在黑暗中最黑的两个世界合成一体,
坚硬的石头脑袋被劈开,
利剑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如果我能用劈成两半的神秘黑夜
去解释一个双脚踏在大地上的明媚早晨--
如果我能沿着洒满晨曦的台阶
登上虚无之巅的巨人的肩膀,不是为了升起,而是为了陨落--
如果黄金镌刻的铭文不是为了被传颂,
而是为了被抹去,被遗忘、被践踏--
正如一个被践踏的广场必将落到践踏者头上
那些曾在明媚的早晨穿过广场的人
他们的黑色皮鞋迟早会落到利剑之上,
像必将落下的棺盖落到棺材上的那么沉重。
躺在里面的不是我,也不是
行走在剑刃上的人。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的人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晨
穿过广场,避开孤独和永生。
他们是幽闭时代的幸存者。
我没想到他们会在傍晚离去或倒下。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不是广场
一个无人站立的地方也不是。
我曾经是站着的吗?还要站立多久?
毕竟我和那些倒下去的人一样,
从来不是一个永生者。
1990.9.18于成都
作者简介:欧阳江河(1956—),原名江河,四川泸州人。著有诗集《透过词语的玻璃》、《谁去谁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