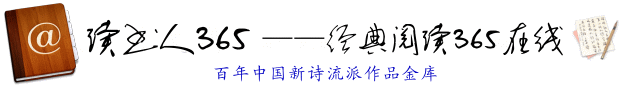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王家新的诗
瓦雷金诺叙事曲
--给帕斯捷尔纳克
蜡烛在燃烧
冬天里的诗人在写作,
整个俄罗斯疲倦了
又一场暴风雪
止息于他的笔尖下
静静的夜
谁在此时醒着
谁都会惊讶于这苦难的世界的美丽
和它片刻的安宁,
也许,你是幸福的--
命运夺去一切,却把一张
松木桌子留了下来,
这就够了。
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已别无他求。
何况还有一份沉重的生活
熟睡的妻子
这个宁静冬夜的忧伤。
写吧,诗人,就像不朽的普希金
让金子一样的诗句出现
把苦难转变为音乐......
蜡烛在燃烧,
蜡烛在松木桌子上燃烧,
突然,就在笔尖的沙沙声中
出现了死一样的寂静
--有什么正从雪地上传来,
那样凄厉
不祥......
诗人不安起来。欢快的语言
收缩着它的节奏。
但是,他怎忍心在这首诗中
混入狼群的粗重鼻息?
他怎能让死亡
冒犯这晶莹发蓝的一切?
笔在抵抗
而诗人是对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严酷的年代
享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为什么不能变得安然一点
以我们的写作,把这逼近的死
再一次地推迟下去?
闪闪运转的星空
一个相信艺术高于一切的诗人。
请让他抹去悲剧的乐音!
当他睡去的时候
松木桌子上,应有一首诗落成
精美如一件素洁绣品......
蜡烛在燃烧
诗人的笔重又在纸上疾驰,
诗句跳跃
忽略着命运的提醒
然而,狼群在长啸,
狼群在逼近,
诗人!为什么这凄厉的声音
就不能加入你诗歌的乐章?
为什么要把人与兽的殊死搏斗
留在一个睡不稳的梦中?
纯洁的诗人!你在诗中省略的
会在生存中
更为狰狞地显露。
那是一排闪光的狼牙,它将切断
一个人的生活,
它已经为你在近处张开。
不祥的恶兆!
一首孱弱的诗,又怎能减缓
巨大的恐惧?
诗人放下了笔。
从雪夜的深处,从一个词
到另一个词的间歇中
狼的嗥叫传来,无可阻止地
传来......
蜡烛在燃烧
我们怎能写作?
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
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
那一声凄厉的哀鸣
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
来自我们的内心......
帕斯捷尔纳克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
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
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为了获得,而放弃
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宁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的牧畜眼中的泪光
在风中燃烧的枫叶
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
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
正如你,要忍受更剧烈的风雪扑打
才能守住你的俄罗斯,你的
拉丽萨,那美丽的、再也不能伤害的
你的,不敢相信的奇迹
带着一身雪的寒气,就在眼前!
还有烛光照亮的列维坦的秋天
普希金诗韵中的死亡、赞美、罪孽
春天到来,广阔大地裸现的黑色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这是幸福,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
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
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
发掘我们:它在要求一个对称
或一支比回声更激荡的安魂曲
而我们,又怎配走到你的墓前
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12月的冬天
这是你目光的忧伤、探询和质问
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
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
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
转 变
季节在一夜间
彻底转变
你还没有来得及准备
风已扑面而来
风已冷得使人迈不出院子
你回转身来,天空
在风的鼓荡下
出奇地发蓝
你一下子就老了
衰竭,面目全非
在落叶的打旋中步履艰难
仅仅一个狂风之夜
身体里的木桶已是那样的空
一走动
就晃荡出声音
而风仍不息地从这个季节穿过
风鼓荡着白云
风使天空更高、更远
风一刻不停地运送着什么
风在瓦缝里,在听不见的任何地方
吹着,是那样急迫
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落叶纷飞
风中树的声音
从远方溅起的人声、车辆声
都朝着一个方向
如此逼人
风已彻底吹进你的骨头缝里
仅仅一个晚上
一切全变了
这不禁使你暗自惊心
把自己稳住,是到了在风中坚持
或彻底放弃的时候了
醒 来
大地蒙蒙细雨的早晨
九月的港湾
雾中拉响的汽笛
一座老吊桥朦胧的倒影
渐渐连成一片
无法倾听的雨声......
不是梦,是在醒来的一刻
我惊讶于这一切
我已是另一个人
大地上的漫游者,忍受
盲目命运的驱使
并最终看清了命运,
仿佛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梦
并在此地醒来,茫然颤栗,
蒙恩于秋天的第一场雨
依然滞留于一个临时的港口
有什么迷失在忧伤的梦中
我已无法追忆
但我必须起来,向雨
向这再次下来的天色
向所有把我唤醒的事物,致礼
虽然我还无法看清
而我正走向这--
被雨雾充满的港湾,
在雾中移动的船只(请过一会儿
再拉响你们的汽笛!)
以及这再次倾下的雨声......
我曾倦一切
也倦我自己,但此刻
我走向它,比走向伟大的神殿
还要静默,无声
这就是生活,在雾中出现
在我心中再次诞生
船舶驶进港湾,吊桥放下
红、白和比雨雾更蓝的车流
闪闪驶过
--而我向它致敬
并把自己献给更远外的天空
1992.9比利时根特
纪 念
1
又是独自上路:带上你自己
对自己的祝福,为了一次乌云中的出走。
英格兰美丽的乡野闪闪掠过,
哥特式小教堂的尖顶,犹如错过的船桅
曾出现在另一位流亡诗人的诗中。
接受天空,墓碑与树林的注视,
视野里仍是一架流动钢琴
与乐队的徒劳对话,而你自己
曾在那里?再一次丘陵起伏
如同心灵难以熨平
2
虚幻的旅行。下午二点钟,
惟有检票员怀疑的眼神,表示了
某种肯定。"梦里不知身是客",你试着
在另一种语言中把它复述出来
而在对面,在另一梦中,幸福的人
正悲伤地读着一本罗曼司......
直到从车厢过道的地毯上,开始飘散
被吸收乌云的气息--它好似
做爱后留下的。"看在上帝份上"。
买下一份《泰晤士》吧,不是为了读
是为了把脸藏在它的后面
而铁轨,如同一个被反复引用的句子
承受挤压,不再发出呻吟。
3
这就是众神的土地?"我来到这里
为了一首十四行诗"。从凯撒大帝的
踟蹰不前(他的力量已为
另一片大陆所耗尽),到弥尔顿、叶芝
相继在他们自己的词句中受阻,
历史一次次扬起骑者的滚尘
在历中里一个帝国的意志形成,却失陷在
对它自己的叙述里......
列车再一次摇晃着周末度假的人们
朝向永不可及的地平线
而何时,那让人暗自神伤不已的"蓝花花"
已化为一个满脸雀斑
在中途上车的女大学生。
4
于是另一个旅程浮现(如果你学会
以宇宙的无穷来测量自己):从北京
以一个个缓慢无尽的外省......
如同履行一种仪式,在节前
回老家看望父母的人们,期待渐渐
让位于恐惧("良知"是它的学名)
尘埃中一声河南梆子响起:到站了
而你茫茫然不知走向哪里。
(你将再次回到那里,作为陌生人
或者永不?)春节,"穷人的宗教"
父亲的咳嗽。一片无神的干燥土地
到处是尘埃的金色手艺与祝福,
泥土的酒与伪造的三五牌烟,一起
呛入你的灵魂......
5
"不是异邦学会了讥讽,是人到了
讥讽的年龄"。回忆如一支冗长的挽歌
在寻求与讽刺的平衡。
雀斑女孩又在轻晃着她的双腿
眼中发出了物理的蓝色(而不再是梦的)
随着耳机那无以领略的节奏。
你想到了家乡,父亲的咳嗽传来,
你想起"祖国",奥德修斯却在风暴中闪现
(而荷马是否应该修改那个虚假的
史诗的结尾?)你放下《泰晤士》
于是母语出现在泪眼中......
--远远地,从风云陡起的天空下
升起一个审判的年代
强烈有如音乐,迎面又错过去了......
6
偶尔的出游,伦敦远了(乌云
仍在反复地修辞着那个乌云中的城市)
这是时间中的逆行:火车向北、再向北
为的是让你忍受无名。
在叶芝的日记中我遇上面具:他总在
他不在的地方",而火车照行不误,
火车不再抽着那种十九世纪烟卷
哈代的沼泽却在你的头脑中燃烧,
火车绕开了呼啸山庄,为的是空出另一条路
让你自己通向那里。
而当它再一次停稳时,你终于
想起了可怜的拉金,"像从看不见的地方
射出密集的箭,落下来变成了雨"。
7
那么我是谁?一个僭越母语边界的人
音乐对话中骤起的激情?永不到达的
测量员?被一乌鸦所引证的
隐喻?那么又是谁,为了哈姆雷特
永不从自己的葬礼中回来
最后却发现这并不是一出悲剧?
当北中国一扇蒙霜的窗户映出黎明
浊雾扑向伦敦那些维多利亚式街灯"
--而你曾在哪里?不,那已是
另一个人。永远有风暴
在记忆中进行:永远有一只未被杀死的
信天翁,在你的船后追逐......
而我宁愿做个幸福的人。"看在上帝份上,"
让它摇着我,摇着,直到我能听出
一种从未听到的话语。
8
短暂的旅行,长于百年。
人在一首诗的展开就历尽了沧桑。
车过约克郡:它更空了
而树木退向天边,犹如正在消逝的和声,
更空了,空得就像为你一人而准备的
旅行,空得使你几乎就要听到
从空中发出的声音......
"需要抑制怎样的恐惧,才能独自
去成为?"我已不再去问。
其实我已不在这列车上:为你祝福吧--
终点即是斯卡堡海岬,而它通向无地
那里,一座座承受狂风的童话式小旅馆
如同诸神丢弃在夏天的玩具
作者简介:王家新(1957—),湖北丹江口人。著有诗集《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