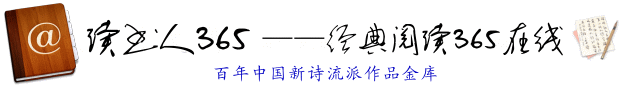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路也的诗
尼姑庵
生活也像这庵堂一样
每天跟任何一天没有什么不同
一辈子还没有过就要结束
门前的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
屋后的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连一株小草也摇曳着她的时装
可是我呢,永远是青砖灰瓦的颜色
骨髓里的香气因长期囚禁而变质发霉
我被禁锢在一个小小的壁龛里
欲望和道德非法共眠,互相合食着内脏
暮鼓晨钟把每个白天和黑夜处决
那些断气的美好假日像在春天就连根拔起的玫瑰
永远不会相信复活
经书有一副棺材铺的外表,以及口琴般处处是
孔的心计
其厚度刚好能够把轻快的步履绊倒在地
我活着,却已和生命分手
性情比那面锈着的山崖还要荒僻
身体比枯死的树还要严肃
表情还不如一块青石板,连苔藓都不生
甚至,在我映衬着田野的空空臂弯里
根本感觉不到空气存在
可是,一只时空时满的水罐,不知是为什么
里面映出的总是一张许多年前的脸
用火焰镶嵌的笑容如一个从尘世匿迹的密语
在水中闪闪烁烁
那哑默的木鱼在悲伤
想打一个被敲响的时刻还原,从水中游走
你看,梦的酵母从来不需太多
只要有了那一丁点儿,就可以使心鼓胀起来
某种念头像白炽灯泡,像成群吱吱扭扭的尖叫
的耗子
从寂静奔向寂静,在南墙上反弹回不祥的回音
我多么羡慕窗前那束杏花,朝生夕死
魂魄像一块白绢那么温柔
我不知爱情是什么,不曾写过甜言蜜语
但我将留下遗书
我的遗嘱会像私生子那样隐蔽,石破天惊
镜 子
一面从未照过的镜子最透明
其内部的时间是凝固着的
它盲目、寒冷、空旷、像处女
只有风在流连顾盼
在里面照映着某种空想
其实,这时候的镜子还不是镜子
使镜子真正成为镜子的
该是一个充满期冀与忧伤的女人
她在岁月的躯体里种植豌豆或蔷薇
以白日梦替代什么也不是的生活
她有这么一面挂在墙上的心扉
美丽的隐私使平面玻璃充实起来
表情像汉语一样闪烁歧义和双关
镜子是可拷贝的软盘
往它的最深层遥望
一长串多年贮存的映像呈透视效果
排成一条幽长幽长的隧道
初春的嫩绿一定会变成深秋的枯黄
无论多么衰老,这女人都可以穿透镜子
沿隧道返回青春年少的时光
在那里,她依然眼眸如星
黑发永远拖在脑后,像泛滥的柔情
镜子是她的信仰,她的乌托邦
今生与她最相爱的,不是别人
而是囚禁在镜中的那一个
两个女人如此对称地
栖居在不同的深渊里
连光阴也被复制出蒙蒙的影子
无数瞬间在镜子重重叠叠
成为同一瞬间
镜面蒙尘,那叫遗忘
如果镜子出现裂痕
那是命运遇上了劫数
心撕裂过才知道什么叫沧桑
如果镜子彻底摔碎
那就是一个宇宙遭到了毁灭
那样的碎片真的不亚于一场嚎啕
女生宿舍
其实女生宿舍就相当于
古代小姐的闺房
如果念的是中文系
那就算是潇湘馆或蘅芜苑了
窗外晾晒的衣裙正值妙龄
被阳光哄骗又滋养
楼下槐树影里总有男生伫立
失魂落魄,个个像贾宝玉或张君瑞
挂风铃的窗口在虔城的目光里
被仰望成革命圣地的宝塔
这是通往爱情的最后一站,如同前哨阵地
像债务似的,书桌上堆积着待补的笔记
给好日子笼罩上阴影
课桌里塞着伙食费换来的口红
这是给美丽上交的那么一点点税
印染床单铺着大面积的鲜花
花丛里隐匿着蜜蜂般的机缘
床架上的长筒袜很慵懒
一件颜色愁苦的连衣裙月经不调
布娃娃比她的主人还出众
脸上的小雀斑古色古香
日记本暗暗地在枕头底下怀春
一枝红杏已伸出了硬壳的封皮
还有刚刚封口的信函,
郑重其事得犹如精心装修过的房间
像不爱江山爱美人一样
她们有时不爱身材爱巧克力
看书总要吃着五香瓜子,喀嘣喀嘣
其速度与准确度超过阅读
并随时准备像嗑瓜子一样
把她们自己的身体也嗑开来
方便面吃多了怎么有股肥皂味呢
它的保质期跟爱情一样,超不过半年
而最疯狂的恋爱,也无非等于
害一场偏头痛。副产品是一大批
诗与散文,属哼哼唧唧派
时光跟口香糖般耐嚼,不见消耗
总得发生点儿什么吧,总得
从青春这朵玫瑰中提炼出点什么来
在最关键的时刻
最好是病上一场,病成西施的模样
爱情跟革命的性质相仿
往往在身心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
在这里,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
生活影片中的女主角
并把某男生的殷勤看成上帝发给自己的奥斯卡奖
作者简介:路也(1969—),山东济南人。著有诗集《风生来说没有家》、《心是一架风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