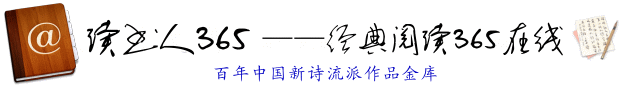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诗之防御战
□成仿吾
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文艺的玩赏是感情与感情的融洽,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冲;文学的目的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情感的传达,而不是关于他的理智的报告--这些浅近的原理,我想就是现在一般很幼稚的作家,也无待我来反复申明的必要。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他的始终。至少对于诗歌我们可以这样说,不仅诗的全体要以他所传达的情绪之深浅决定他的优劣,而且一句一字亦必以情感的贫富为选择的标准。假使F为一个对象所给我们的印象的焦点focus或外包envelope,
F为这印象的焦点或外包所唤起的情绪,那么,这对象的选择,可以把F所唤起的f之大小来决定。那浅显的算式来表出时,便是我们选择材料时,要满足
一个条件。如果这微分系数小于零时,那便是所谓蛇足。这算式所表出的意思,如用浅近的语言说出,便是诗中如增加一句一字,必是这一句一字增加全体的情绪多少。
这些都是很显而易见的道理。由鲜美的内容与纯洁的情绪调和了的诗歌,是我们所最期待的。我们即不主张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的文学,而情感在诗歌上的重要与他的效果,我们是不能赞赏的,尤其当我们想起过量的理智怎样把诗歌的效果打坏了的时候。理智是我们的不忠的奴仆,至少对于诗歌是这般。他是不可过于信任的,如果我们过于信任他,我们所筑成的效果,就难免不为他所打坏。而最可恶的叛徒,便是浅薄的理论reasoning。诗的职务只在使我们兴感tofeel而不在使我们理解tounderstand。使我们理解,有更明了更自由的散文。诗的作用只在由不可捕捉的创出可捕捉的东西,于抽象的东西加以具体化,而他的方法只在动用我们的想象,表现我们的情感。一切因果的理论与分析的说明是打坏诗之效果的。固然,真的智慧是直观的,是诗的,而且是我们所希求的;然而凡智的欢喜只是一时的,变迁的,只有真情的愉悦是永远的,不变的,像吃了智慧之果,人类便堕落了一般,中了理智的毒,诗歌便也要堕落了。我们要发挥感情的效果,要严防理智的叛逆!
现在试把我们目下的诗的王宫一瞥,看他的近情如何了。
一座腐败了的宫殿,是我们把他推倒了,几年来正在从新建造。然而现在呀,王宫内外遍地都生了野草了,可悲的王宫啊!可痛的王宫!
空言不足信,我现在把这些野草,随便指出几个来说说。
一、胡适的《尝试集》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
倘有人爱他,更如何待他?
--《他》
这简直文字的游戏,好像三家村里唱的猜谜歌,这也可以说是诗么?《尝试集》里本来没有一首是诗,这种恶作剧正自举不胜举。又譬如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里惨凄。"
车夫告客,"............"
--《人力车夫》
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自古说:秀才人情是纸半张,这样浅薄的人道主义更是不值半文钱了。坐在黄包车上谈贫富问题劳动问题,犹如抱着个妓女在怀中做了一场改造世界的大梦。
雪色满空中,抬头忽见你!
我不知何故,心里很欢喜;
踏雪摘下来,夹在小书里;
还想做首诗,写我喜欢的道理。
不料此理很难写,抽出笔来还搁起。
--《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
胡君做诗原来只想写道理呀!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我的儿子》
这还不能说是浅薄,只能说是无聊。
"这棵大树很可恶,
他碍着我的路!
来!
快把他砍倒了,
把树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
--《乐观》
哈哈!好了!不要再抄胡适之的名句了。
二、康白情的《草儿》
我们想,所贵乎做同学的应该怎样?不是说要互劝道德,互砥学问,互助事业么?......我呢--更该万死!我受同学的厚爱以当全国学友的重托,而我诚还未足以感人,学还未足以济用,致酿成今日的危局而前功几于尽弃。......"
--《别北京大学同学》
这实是一篇演说词,康君把他分"成行了"便算是诗了!无怪乎草儿那么多,那么厚。
德熙去了;
少荆来了。
舜生来了。
舜生去了;
葆青绛霄终归在这里。
--《西湖杂诗》
这确如梁实秋君所说是一个点名簿。我把他抄下来,几乎把肠都笑断了。还有那篇《卅日踏青会》,我从头看去,总以为是一篇序文,后来才又发现了那七十一人的点名录。
入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
劳动是日间第一件大事;
少用心是晚上第一件大事;
打拳,看星子,是临睡前第一件大事。
--《律己九铭》
这些确是每天应做的大事,亏他想得周到,写得出来。
三、俞平伯的《冬夜》(及《雪潮》第三集)
飞--飞他的;
滚--滚他的;
推--推他们的。
有从来,有处去,
来去有人所以。
尽飞,尽滚,尽推;
自有飞不去,滚不到,推不动的时候。
--《仅有的伴侣》
这是什么东西?滚,滚,滚你的!
留你也忽忽去,
送你也忽忽去;
然则--送你罢!
--《山居杂诗》
这真未免过于忽忽了;然则--不成其为诗罢!
"朋友!说你是愚人,可是吗?"
恭恭敬敬的回答,
"先生正是呢!"
--《愚的海》
朋友!说你的不是诗,可是吗?恭恭敬敬的回答,先生,正是呢!
四、周作人(《雪潮》第二集)
三座门的底下,
两个人并排着慢慢地走来。
一样的憔悴的颜色,
一样的戴着帽子,
一样的穿着袍子,
只是两边的袖子底下,
拖了一根青麻的索子。
我知道一个人是拴在腕上,
一个人是拿在手里;
但我看不出谁是谁来。
--《所见》
这不说是诗,只能说是所见,倒亏他知道了
五、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
"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一回加入呢......那一回,苍前山一所茶楼的上边,街上正在迎神,......不是我一个人赢了!王三五十元,张桂二百元,我赢了一共七百五十元。
......你们怎能忘记呢......
这些赌棍们--就是王三张桂等--向来没有和他表过同情:他们总是忙碌着,轻蔑嘲骂他一顿:"贼东西,不做梦吧!"
--《失败的赌棍底门》
这样的文字在小说里面都要说是拙劣极了。徐君何不把其余的人所输的钱也一齐写出呢?
我现在手写痛了,头也痛了!读者诸君看了这许多名诗,也许已经觉得眼花头痛,我要在这里变更计划,不再把野草一个个拿来洗剥了。我只把近来在《觉悟栏》上发见的一首小诗写在下面,聊与读者诸君解颐:
雄鸡整理他的美丽的冠羽,
在引吭高歌后,
飞到粼园里去强奸了!
我们的诗坛自从摆脱了词调,再进而洒脱了白话以来,像取了两种新的方向:
1所谓小诗或短诗
2所谓哲理诗
这两种因为他们的外样比前面的那些野草来得漂亮一点,他们的蔓延颇有一日千里之势。我现在要进而一窥他们的真相。
讲起小诗二字,我们便联想到周作人介绍的所谓日本的小诗。最初我听了这个名字时,很有点不明白周君所指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就是日本的和歌与俳句。本来俳句是从和歌蝉蜕出来的。而和歌日本人通称为歌(uta),原是歌的民谣,以音乐为他的生命的。后来虽渐变为可读的抒情的词,而严格地说起来,可称为抒情诗的究是极少数,--至少俳句是这般。日本语是多音节的。往往一个名字占四五个音,如杜鹃一个名字,在日语占五个音,莺一个名字,占四个音之类。和歌一首为五七五七七的三十一音,俳句更只五七五的十七音。以这样少数的语音,要写出抒情的诗句,在和歌或犹易为,在俳句却实很困难的。我觉得俳句要成为抒情诗,至少有下面的几层困难:
1、音数既经限定,字数自然甚少,结果难免不陷于极端的点画派punktierkunst。
2、同时又难免不陷于极端的刹那主义Momentalismus。
3、容积既小,往往情绪的负载过重。
4、刹那主义与点画的结果,最易陷于轻浮。
和歌的首数几比俳句多到一半,他的困难自然也小,可是音数间的限制,即五七五七七总得严守,比俳句实在笨重,倒不如俳句轻快而新鲜。然而俳句的轻快与新鲜,同时又是他的致命的病毒。他每每不是些轻浮的感情,便是些浅薄的"洒落Share",芭蕉这人是一个例外,他确留下了几首好点的俳句。然而别的人便少有好的了。土居光知在他们那本《文学序说》上说:
"俳谐由最初的滑稽洒脱之趣味和语言的游戏渐进为芭蕉那样的从心底发出来的静调而近于抒情诗,然犹不外是自然情趣之客观的表现,不是以恋爱为主题而出之以滑稽,便是使与自然同等而加之以客观化。"
和歌虽则音数较多,而他的笨重与呆板,实令所得不偿所失,而且一个固定而呆板的铸型,久后必归无用。和歌与俳句,在日本早已成了过去的骨董,正犹如我们的律诗与绝句。周君把他们介绍了过来,好像是日本的新诗的样子,致使我们多少羽翼未丰的青年,把他们当做了诗的王道,终于把我们的王宫任他蹂躏了。这是我不解周君所以介绍什么日本的小诗的第一点。
其次,俳句既多是轻浮浅薄的诙谐,在文艺上便没有多大的价值,至少没有普遍的价值。譬如周君所译出的:
风冷,破纸障的神无月。
给他吮着养育起来罢,养花的雨。
在作者是利用纸与神,饴与雨的同音,显他的小巧,可是译出来的东西,却连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又如《芭蕉》的名句
古池,--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
照周君这样译出来,简直把他的生命都丢掉了。古池之下原有一个感叹的呀字,是原文的命脉,周君却把他丢了。而且这古池呀在日文是Furuike-ya的五音,并且是二二一的关系,周君译作古池两个字,把原有的音乐的效果也全失了;不过这倒是两国文字不同的地方,怎么也没有办法的。青蛙的"青"字是周君添的蛇足。俳句以粗略Simpleorrough见长,添上一个青字,亦不能于全体的情绪有所增加,倒把粗略的好处都埋没了。水里的声音的"里"字,也是周君添的蛇足,把原文的暗味的美点全失了。我以为俳句既以音节的关系来暗示一种文字以外的情调,则译他时当然也应保留原有的音节才好。所以我想《芭蕉》这首可以译作
苍寂古池呀,小蛙儿蓦然跳入,池水的声音。
以保存二二一,三二二二一二的音节的关系。然而这里面不免也加了些无益的蛇足。
一个这样短短的句子,周君那样译出来,既是呆板,我这样译出来,也是干燥无味。这样好一点的,尚且如此,其余差一点的,怕难免都果如前面所引的那两句,弄的不成话了。从这地方我们可以提到一个判断,就是,俳句是日本文特长的表现法,至少不能应用于我们的言语。外国也有许多好文人,仿做了一种俳句。然而一是因为外国文本有做短诗的可能,如法国的P.Verlaino便有把一句短话分行为诗的,二是因为外国人在他们本国文字的运用上,已经用尽了他们的技巧,所以他们模仿俳谐,为的是要满足他们的异乡情调oxoticisme。在我们的文坛,却没有这样的可能与必要。中国人老是易于误解外国人的言行。梁任公听见外国人研究东方思想,便喜得眉飞色舞。这种浅薄的观察,我们只可把来当做笑柄。所以西洋人模仿俳谐,实在不能成为我们也可以模仿的理由。而且俳谐之不足模仿还有两个理由:
1、抒情诗的真谛在利用音律的反复引我们深入一个梦幻之境,俳句仅一单句,没有反复的音律,他实在没有抒情的可能。
2、如土居光知所说"歌人的理想是闲雅,俳人的理想是洒脱、幽玄、静寂。......闲雅是一生安于游乐的贵人的境地,静寂是离脱人生之苦恼的隐士的境地。"所以我们如果甘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则已,否则我们是不能不把他当做古董看待。
俳谐之不可模仿,也有两个理由:
1、我们的新文学正在建设时代,我们要秉我们的天禀,
自由不羁地创造些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不可为一切固定的形式所拘束了。善于模仿的小孩,长大了也是无用的,我们不可任我们的小孩模仿。
2、我们的新文学要有真挚的热情做根底,俳谐那种游戏的态度,我们决不可容许。
关于俳谐所说的话,大抵都可以应用于和歌,总之这两件臭皮囊,即日本人-与俳偕一样浅薄无聊的日本人,已经早为他们奏了薤露之歌,不知周君为甚拾得他们的残骸,偏要为他们大吹大奏。这是我不解周君所以介绍什么日本的小诗的又一点。
现在流行的小诗,不必尽是受了周作人的影响,然而我关于俳句所说的话,是可以应用于别的短诗的,我已经侵犯了他人的篇幅,我暂不多说了。
与小诗凑成一对的所谓哲理诗,我们现在要把他拿来审定一下了。国内哲理诗的作者,大概以宗白华与冰心女士为代表。他们自称是受了太戈尔的影响。
哲理诗!这是多么冠冕堂皇的名字。然而在我们现在的诗坛--哲学大家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时代的诗坛,我们只一听这个名字,而这名字里面所含蓄的滑稽,就足以令我们破颜而大笑了。
我在这里论及哲理诗,要请读者诸君恕我不抄录宗白华与冰心女士的大作了,因为我只报章上看过几回,随时随地把他们与电闻通信一齐丢了。他们对于别人,似乎具有不可当的引力,然而我只觉得宗君不过把概念与概念联络起来,而冰心亦不过善于把一些高尚的抽象的文字集拢来罢了。本来哲理如果硬要加入诗中,我们先要求他不是哲理。如果带上了诗形而又自称哲理,我们只好取消他的诗的资格。太戈尔的《迷途之鸟》,终于不过是些迷途之鸟罢了。
我在前面已经预先把理智的叛逆说过了,把抽象的东西须加以具体化也说过了。所以理论或概念的,与过于抽象的文字,纵列为诗形,而终不能说是诗,大约可以不消多说了。而且如果目的在阐明哲理,我们可以取更严肃的论理,可以用更自由的散文;如果想利用诗的形式希图增加哲理的效果,那必自陷于冗长的叙事诗的失败。我们赏玩诗歌,是为诗歌自己,他自有他内存的目的。如果哲理可以诗传,则科学的论文也可以诗来代替,教科书也可以用诗的形式写出了。这样的梦是很愉快的,然而毕竟是一个梦啊!伽莱尔T.Carlyle教人说理不要用诗形,称那些铿锵的假诗是一些打木板的嘈音woodonnoise。
固然,古人的诗中往往含有不少的哲理,然而那不外是偶成的现象,决没有人预先怀着说理的心去做诗的。我们现在的所谓哲理诗人,往往有专为发泄他的所谓哲理而做出许多诗来,(譬如冰心女士在她《繁星》的附白中便说明了她是借迷途之鸟的形式来记载的零碎的感想)然而结果却不外一些畸形的概念与抽象的文字,使我们看了,如像在读格言,如像看了一些与我们不常会面的科学书籍,引不起兴致来。诗也要人去思索,根本上便错了。我们读诗,与我们对画听音乐,原则上是一样的。我们只是要由诗的内容,与诗人共赏内容所具有的情调,内容间的理论reasoning,我们是不必去多事的。现在要我们劳心的理论一天天多起来了,诗也要我们去劳心,至少已经失去了他的存在的根据之一部。
太戈尔做出了一部《迷途之鸟》,大家便一齐争着传诵,争着翻译,争着模仿,犹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得着了一部古典的稿本。这固然是饥不择食,却也可以证明我们现在的青年易于盲从了。周作人介绍了他的所谓日本的小诗,居然就有数不清的人去模仿,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们不由得要想起《浮士德》中的:
Soschwaetztundlehrtmanungestoert;
WerwillsichmitdenNarr'nbefassen?
GewoehnlichglaubtderMensch,WennernurWortehoert,
Esmuessesichdabeidochauchwasdenkenlassen.
(大意)人总是胡言乱语神气泰然:
谁去和那些傻子们纠缠?
听了一句话便做天启一般,
这本是一般庸人们的习惯。
我把我对于现在的小诗与哲理诗的反对的意见约略说了:我把小诗的缺点指出,证明了他是犯不着去制造的,一种风格甚低的诗形,我说了诗是不当拿去讲哲理的。可是我并不说小诗与哲理诗决不能成诗。有些天才的句子,天然的是一个字也不能增减的小诗;有些天才的诗人,于优美的诗中,写出了不少的哲理。而且诗是天才的创造,天才是能征服一切的困难,不为所限的,所以如果真是出自天才,则小诗变为优美的抒情诗,哲理与真情调和,亦并非不可能之事。不过这是进一步的说法,就一般而言,我在上面所说的话,是可以成立的。没有内心的要求勉强去做诗,已经是不对的;而以小诗为标的去做,便更不对了。把哲理夹入诗中,已经是不对的;而以哲理诗为目的去做,便更不对了。目下的这两种倾向,很使我们感着不安,多少朋友们的活力已经消耗在这两种倾向之下了!我们如不急起而从事防御,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怕不要在这两种倾向之间沉淀起来了?而且文学只有美丑之分,原无新旧之别,如果现在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可以称诗,则那些文妖的游戏诙谐,也可以有称诗的权利。现在的那些小诗实在令人作呕,我真不知作者怎样能泰然发表出来,我真不知提倡者看了这层光景,心中应当怎样。
至于前面的那些野草们,我们应当对于他们更为及时的防御战。他们大抵是一些浅薄无聊的文字;作者既没有丝毫的想象力,又不能利用音乐的效果,所以他们总不外是一些理论或观察的报告,怎么也免不了是一些鄙陋的嘈音。诗的本质是想象,诗的现形是音乐,除了想象与音乐,我不知诗歌还留有什么。这样的文字也可以称诗,我不知我们的诗坛终将堕落到什么样子。我们要起而守护诗的王宫,我愿与我们的青年诗人共起而为这诗之防御战!
这篇一路写来,不知不觉写得太长了,有些地方写得过多,有些地方容有未尽。我只暂把这篇做一总纲,有暇当更分别讨论。
五月四日仿吾附织